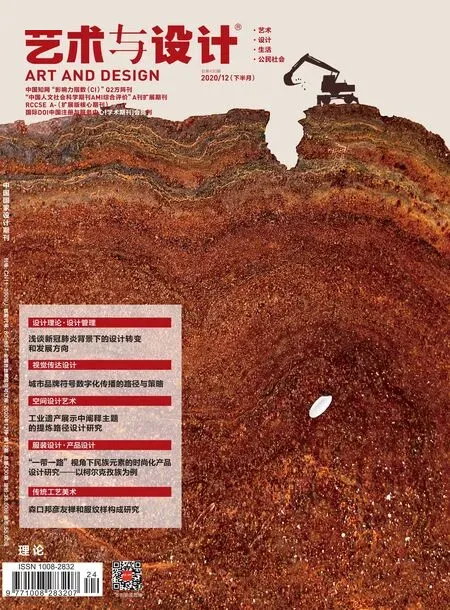巖山寺壁畫中的山水元素研究
王元芳
(忻州師范學院,山西 忻州 034000)
巖山寺壁畫作為五臺山佛教藝術寶藏中璀璨奪目的一顆明珠,構圖壯觀,布局獨特,技法嫻熟,設色雅致,神態逼真,具有典型的北宋院體畫風格。巖山寺壁畫中的山水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代山水畫承襲北宋院體畫的面貌,構成了中國山水畫發展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階段,也是這一時期山水畫融合傳統并創新的典型案例。山水畫作為佛教壁畫中必不可少的表現內容,體現了特定的佛學思想和藝術形式,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中發現,大部分學者更多關注巖山寺壁畫的建筑、人物等市井風俗和佛教故事,而對于壁畫中山水畫部分的研究相當少。縱觀巖山寺壁畫,山水畫部分主要分布在東西兩壁的上部,有青綠和水墨兩種表現形式,更為重要的是整鋪壁畫蘊藏了卷軸山水畫的各種元素,如全景式構圖、三遠法、色彩及意境的傳達。本文試就東西兩壁山水畫藝術形式及各要素進行探討論證,以探求山水畫的理法對佛教壁畫的作用及影響,為壁畫的繼承與發展提供更好的借鑒。
一、巖山寺壁畫山水元素
巖山寺位于繁峙縣天巖村,古稱靈巖院、靈巖寺,其建寺年代久遠,可以上溯到金正隆三年(1158年)。又一說宋代,今從寺內尊勝陀羅尼經幢上刻文所見“維大宋國代州界繁畤縣咸寧鄉天巖村”,落款處為大宋元豐二年(1079年),以此可推斷巖山寺在北宋時期已存在。有關寺內碑文所記“金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建正殿(即水陸殿)五楹,并繪制水陸壁畫;隨之又建文殊殿(南殿),并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繪完南殿壁畫,寺額靈巖。”可知正隆三年巖山寺進行了大規模的營造,其后在元、明、清時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修葺。宋金時期的巖山寺并非現今如此偏僻,有著重要的地理位置,其坐落于五臺山北麓,是周邊佛徒朝拜五臺山的必經之地。由于地理位置顯赫,被佛家所看重,成為宣揚佛法的重地。同時,在北宋末金代初期,宋金戰役接連不斷,巖山寺所處地帶更是戰爭連年,統治階級為了安撫當地百姓,超度亡靈,以此建寺作畫,減輕人們對戰事的痛苦。
現寺內僅存文殊殿為金代所建,水陸殿因清末寺僧拆卸已不復存在。東西配殿為清末建制。文殊殿內文殊菩薩及各塑像均已損毀嚴重,東西兩壁壁畫相對完整,南北壁已漫漶不清。殿內壁畫氣勢恢宏,精美壯觀,代表了金代壁畫的較高水平,成為中國寺觀壁畫發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階段,于1982年被列為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其規格可與晉南永樂宮相媲美,被專家稱為山西寺觀壁畫的“雙壁”。
文殊殿內東壁壁畫繪佛本生、經變故事,西壁壁畫以佛傳故事為藍本。壁中山水畫不是獨立畫種,而是作為畫面的背景出現的。東西兩壁皆以宮殿建筑為主線,周圍穿插佛法故事,再點以山石、樹木等物象豐富畫面,這種全景式的構圖方式明顯借鑒了傳統山水畫的布局;宮廷建筑的繪制精致細微,有卷軸界畫之風,又具備皇家院體的工整寫實;西壁局部對市井生活的細致刻畫,又似一幅壁上的“清明上河圖”;畫面遠處山巒疊翠,煙云環繞,把佛教故事置于真實生活場景之中,既體現了宋金社會世俗化的傾向,也體現了山水畫中“三遠法”在壁畫中的運用。兩壁山石表現兼用青綠與水墨兩種方法,再現了宋代卷軸山水畫的風貌。壁畫的整體風格在唐風的基礎上,融合五代、北宋水墨,呈現出有別于同時代壁畫的高雅之風,進一步體現了壁畫創作的時代性。
二、巖山寺壁畫山水元素的應用
(一)承襲傳統山水筆墨語言
山水畫的發展歷史悠久,從《洛神賦圖》可看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山水畫雛形,山水只作為配景出現,直到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面世,才改變了山水畫的地位,山水畫自此由配景上升到一門獨立畫科,在傳統繪畫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游春圖》畫面中山石雙勾填色,青綠暈染,奠定了青綠山水畫的初始面貌。發展到盛唐時期,大小李將軍的青綠山水繪制技法已趨成熟,影響并引領了這一時期的山水畫發展方向,同時出現了王維的水墨山水畫風格,豐富了山水畫的表現形式。五代、北宋初期,水墨畫興起,畫家創造各種皴法,像范寬的雨點皴,李成的斧劈皴等,文人畫家運用水墨皴擦代替了青綠敷色,改變了當時社會的審美風尚,到了宋代中后期水墨形式不能滿足社會進一步世俗化的審美需求,出現了“復古思潮”,開始重新審視色彩在畫面中的作用,并把青綠山水與當下水墨創作性地融合,形成了既有古韻又迎合社會的新面貌。
金代,統治者實行漢制,且大多數畫家來自前朝,山水畫的面貌承襲唐宋之風。巖山寺壁畫中的山水畫就是這一典型,且因作者為御前承應畫師王逵,技術嫻熟,格調雅致,與同一時期民間畫工所畫的寺廟壁畫有明顯的差異。殿內東壁整體風格沿襲院體畫風,精工嚴謹,山石雙勾填色,水墨打底,山體雄偉挺拔、高聳入云,與李昭道《明皇幸蜀圖》中的山石挺勁之質頗為相似。但通過對比作品仔細分析,筆者認為兩者在筆墨上具有明顯區別,小李將軍采用空勾無皴,再以色彩兼墨色深淺敷之,勾線用筆較為規范,而巖山寺壁畫中青綠山石顯然書寫筆意較濃,近處坡石兼具少量皴法,從這點可以看出此階段壁畫青綠山水已不是傳統的青綠技法,而是融合當下水墨筆法的新創造,是“筆墨當隨時代”的典范。這種筆法與王詵的《煙江疊障圖》頗為相似,都是以青綠與水墨相融,顯高雅之氣。而山頂墨苔點染與李成的《茂林遠岫圖》極為相似,尤其與西壁壁畫左上部分的水墨山水如出一轍,技法直取李成風骨,山石用筆中鋒勾勒輪廓,斧劈皴皴染結構,盡顯書寫之意,山石形態也沒有東壁陡峭直立,更顯幽深淡遠之境。
青綠等石色隨著時間的洗禮更加沉穩、豐富。巖山寺壁畫山水以赭色打底,石綠大面積渲染,石青稍作點綴增加層次,山腳保留赭色。石青、石綠厚薄不同,其下依稀可見赭底色,而赭色與石青、石綠的疊加因厚薄不同呈現出豐富的青綠色階,既豐富了畫面色彩關系,又代替了用皴法表現質感,為當下青綠山水畫對石色的創造性運用提供寶貴經驗。如果忽略或隱去巖山寺壁畫中的故事內容,無疑是一幅壯麗的全景山水畫。
西壁壁畫上部左右兩部分山石明顯不同,左上部分采用李成山石的筆法,表現遠山的深遠效果,中部最上端借鑒了郭熙的山石之質。而畫面右上部分則用青綠技法表現山林。筆者認為之所以表現技法不同,則是與畫面主題思想和畫面經營的藝術需要息息相關。畫面右上部分根據題榜和內容可分析出是一組太子離宮后在深山野林苦行修煉的場面,為了襯托太子修煉的環境,則選用高聳入云的山體,同時也與東壁青綠技法相呼應。左上部分由于前景內容層次豐富使上部空間受限,只能安排遠山作為補充,這種補充并不是隨意“填空”,而正是暗示了佛國世界的無限之大。同時用水墨淡彩迎合了遠山的虛淡,也與西壁整體淡雅的色調相一致。
花草、樹木用筆技法多樣,有雙勾填色的勾填法和水墨韻致的點葉法,近處宮殿周圍樹木用雙勾填色,其后用點葉法襯托,更顯層次豐富,遠處山腳松樹多用點葉法,尤其是山頂樹木排列錯落有致,體現了山體的厚重之質。其他配景如云水的刻畫直取古法,云的畫法自古有兩種,為勾勒法和留白法,均在壁畫中有所體現。這里除了大自然的真實云氣之外還有表現佛教壁畫題材中特定的云,東壁上部因云的存在使得山川時隱時現,這與《明皇幸蜀圖》中的云法近乎相同,而山腳虛空的處理卻有著李成、郭熙的風骨。為了襯托佛界人物的往來,都會在這些人物周圍環繞黃白云彩,這種云彩一般都以線條勾勒,這也是傳統壁畫表現云彩的慣用方式,在各個寺廟壁畫中都可看到。有關水的描繪并不多,但卻極富裝飾性,重復排列的細勁線條成組交錯描畫出橋下湍流不息的河水。并行排列的弧線與建筑的并列直線形成呼應,藝術手法上也體現出寫實與裝飾的融合,與北宋水紋的寫實刻畫明顯不同。
東西壁畫風格不同,東壁嚴謹,近院體畫風;西壁抒寫,有文人畫之趣,尤其是山石表現上,兩壁山石青綠與水墨并存,印證了宋金山水畫的發展現狀。
(二)沿襲卷軸山水的觀察方法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三遠法”,即高遠、深遠、平遠三種特殊的觀察方法,這種觀察方法打破了時空的局限性,以仰視、俯視、平視等不同的視點來描繪景物。巖山寺壁畫在空間布局上借鑒了山水畫中的三遠法,改變了傳統佛教題材壁畫平鋪直敘、連環畫等構圖形式,把各種故事情節穿插于四維空間內,人與事物置身于廣闊的現實世界,既體現了宋金社會世俗化的傾向,同時更能深刻地體現佛教的文化內涵。
東壁畫面中,遠山巍峨宏偉,山腳一行人趕著毛驢行于山間曲徑,身后是氣勢逼人的山川,此景使人聯想到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中騾馬的行進與山勢的雄壯,兩個場景都運用三遠中的高遠,即自山下仰視山巔,取勢巍峨高聳,壯氣奪人。雄壯的山川象征著至高無上的佛法,感受山川高大的同時能把佛教文化植根于心。深遠,謂之“自山前而窺山后”。東壁凈瓶觀音所處位置即是取自s形的崇山峻嶺,這種深遠場面宏大,能表現出大自然山川的層巒疊嶂,一山望盡又一山,視野更加廣闊、深邃,類似情景在東壁上部盡可顯現。平遠,反映的是一種平視的境界,即自近山而望遠山,元代畫家常用平遠之景抒發心中之境,像趙孟頫《水村圖卷》、倪瓚《江岸望山圖》等。東西兩壁中除了建筑和山川外山野的描繪大多以平遠的方法表現寬廣的大千世界,市井街道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幽深的小巷中,西壁宮殿外不遠處由近及遠依次排列的故事情節有“太子離宮尋見馬跡之處,五君輪尋覓太子不見之處,牧女鮮乳太子食處,太子中年苦行修持之處”。這種由近及遠、步步營造的形式運用了山水畫中的平遠法,二維平面中建立立體深遠的意境,描繪出清曠平遠的景象。
巖山寺壁畫借鑒了山水畫中的“三遠法”營造畫面,采用多點透視,突破傳統壁畫平面裝飾的空間處理,把跨時空的物象組合在一起,使畫面中宏大的場面舒展流暢、條理分明,充分體現了中國透視法則的靈活性和獨特性。同時運用宋代院體工謹寫實的方法,所繪建筑皆可依圖所建,山石、花鳥、人物無一不精,正如郭思所言,其父每落筆必曰:“畫山水有法,豈得草草。”
(三)變通傳統壁畫的布局形式
在敦煌壁畫中山水元素最初以符號的形式出現,其作用是為了填補畫面中的空白,到了北朝后期,山石形狀較為多樣,但也僅限于連續的多次重復,鹿本生故事中的山石以多次重復的三角形裝飾交代地理環境,同時把山石作為間隔符號以連環畫的布局形式將故事情節連接起來。隋代出現了大篇幅的山水背景,構圖依舊平面處理,山石、樹木平鋪排列,極具裝飾性和形式感。初唐壁畫中的山水占據了畫面很大空間,在布局上不再是點綴畫面,而是以具象造型描繪自然山川,畫面中有了一定的空間感和層次。自此,壁畫中的山水技法逐漸完善。五代、宋時期,卷軸山水畫發展日益成熟,其全景式構圖便影響了這一時期壁畫的布局形式。莫高窟61窟西壁為五代末繪制的《五臺山圖》,山勢連綿不斷、氣勢恢宏,采用了橫幅長卷的卷軸畫形式。雖與《五臺山圖》內容、風格不同,但在布局上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巖山寺壁畫同北宋的高平開化寺壁畫的連環畫構圖方式不同,它突破了傳統壁畫的連環畫形式,將眾人物與事件合理安排在真實的大千世界中,近景建筑、中景山林、遠景山脈,由近及遠,山石、樹木、人物、景觀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把佛家所言的“一花一世界”描繪得淋漓盡致。將佛傳故事以全景式布局呈現給世人,這種融合創新的構圖在壁畫中少有,是作者王逵藝術修養的唯一見證。
歷代壁畫中的佛傳故事大多是對稱構圖,將眾神以對稱形式安排于畫面中,而巖山寺壁畫則把佛國世界與大自然緊密聯系起來。在佛教故事中,釋迦牟尼生于無憂樹下,涅槃于娑羅樹下,佛家提出山林修凈戒,追求淡泊簡樸,認為自然山川可以助其達到身心寧靜,達到智慧的顯現和開展,而現實生活中的自然風光即是佛國無數個大千世界中的一個。隨著山水畫技法的不斷成熟,畫師們具備了寫實的觀察力和精湛的技法,開始注重對故事環境的理解和思考,把山水元素參與到故事情節的表達中,成功借鑒了全景山水對景物的安排與描繪。
(四)恰到好處的意境營造
意境是山水畫的靈魂,是景與情的結合,寫景就是為了抒發感情,毛主席的詩句,每一句都是說景,每一句又都是充分表達了人的思想感情,山水畫亦是如此。每一座山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色,要通過山水畫家的筆墨語言和自身思想情感的夸張渲染,才會有不同的意境產生。北宋郭熙提出山水畫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四可”之境,而“可游”“可居”為最高境界,巖山寺壁畫正是利用作者巧妙的構思、經營位置及筆墨、色彩等來表達這“四可”之境的。釋迦牟尼從出生到涅槃這一漫長歷史都與山石、樹木不可分割,為了表達釋迦牟尼在人間的內心感受和過往經歷,畫家就要用環境描寫襯托出他內心的思想感情和每一個故事情節,即通過對客觀事物的藝術再現,來表達釋迦牟尼歷經磨難、犧牲自我、弘法渡眾、解救苦難的主觀精神。這種精神境界也需要作者審美修養的積淀和人生感悟進行苦心經營,才能移情于物,托物抒情。畫面中通過對遠山的虛實處理,營造了一種虛遠之境,讓人體驗佛國世界的無限之大,畫家把百里之勢濃縮于咫尺之間,讓觀眾從這有限的咫尺感受無限的大千世界。色彩渲染也增強了對主題氣氛的營造,巖山寺壁畫承襲了宋代的綠壁畫,整鋪壁畫以青綠為主調,赭石、朱砂、石黃、胡粉各盡其妙,其中樹葉以雙勾填色和點葉法刻畫,填色也是以白色為主,或者雙勾不填色,保留了畫面底色,避免畫面色調過于艷麗。色彩意境渲染上與南宋青綠山水畫家趙伯骕《萬松金闕圖》有相似之處,沉穩高雅,整體色調彰顯宋人樸素淡雅的風度。色彩運用上區別于李思訓《江帆樓閣圖》中明顯的補色對比,純度也不高,但因瀝粉貼金的精工制作,兼備富麗堂皇之氣派。同時設色的典雅之風明顯高于民間畫工所畫的壁畫,這種高雅之境來自于宋代院體格調。這種氛圍符合了宋代世俗化的審美和佛教壁畫的思想內涵,體現了佛教壁畫的時代性。
綜上所述,巖山寺文殊殿壁畫是金代壁畫的瑰寶,承載著宋元壁畫的銜接使命,壁畫中的山水元素從側面反映了這一時期卷軸山水畫的發展程度,為研究山水畫的發展脈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巖山寺壁畫中的山水畫承襲了青綠山水和水墨山水的語言,將壁畫中傳承的青綠山水融入水墨元素,使畫面沿襲了院體的精工細膩,又體現了當下水墨表達的筆情墨趣,最終形成雅俗共賞的意境;在空間營造上采用“三遠法”和全景式構圖,運用山水畫中的透視法則營造畫面,使畫面在表現上趨于寫實,迎合了宋代世俗化的傾向,突出了佛國世界的廣闊,體現了深遠的意境;在氣氛的營造上傾向宋代的簡淡樸素,更有力地襯托出佛教故事的深沉之境。它呈現出的獨特壁畫語言和風格影響了其后的寺觀壁畫創作,為壁畫藝術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些創新的舉措為寺觀壁畫開辟了新的領域,用這一創新理念啟發當今壁畫及青綠山水畫的創作思維,借鑒、汲取更多有益經驗,創作出別具一格的藝術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