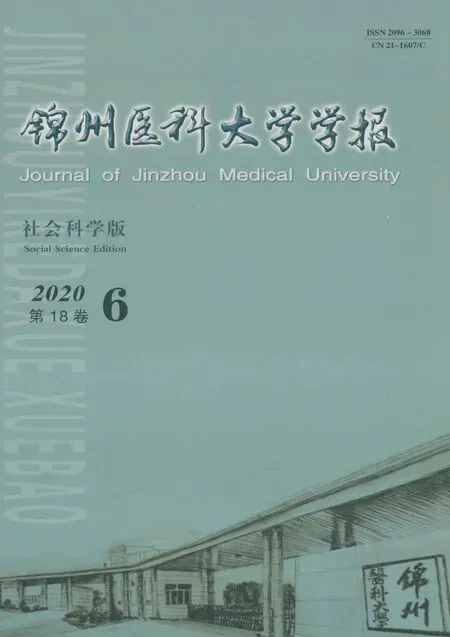漢字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碼
葛昭纓
(遼寧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中華民族在共同生活和發展的過程中創造出屬于本民族的漢語言文字。漢字作為唯一存留的表意方塊字,記錄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象形漢字是對現實的一種簡約,一種省略,是一種人的視覺選擇表現。”[1]漢字是中華人民通過對世界進行圖像性把握而將世界可視化的一種文字符號,是通過直觀世界并懸置,過濾無關物后對世界的濃縮的表達。這種視覺選擇從深層次來講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漢字對世界的重組與整合的方式也暗含了中華民族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因此,漢字中蘊含著中華民族精神密碼。然而這種民族精神的產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古就開始孕育、形成。精神往往需要通過物質載體來體現,中華民族精神,這種刻在中華民族骨子中的基因在自殷商時期前便出現的漢字中得以體現。因此,筆者在孟華創立的漢字符號學基礎上,結合現象學的方法分析漢字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將在漢字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稱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碼,并將其歸結為中華民族的務實精神、創造精神以及和諧精神。
一、務實精神
務實精神,即致力于實在的、具體的事物,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孕育出來的。中華民族的務實精神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所體現,而在漢字上,體現在與西方文字相比,漢字具有“直面事情本身”的特點。
1.西方文字的特點——“不直面事情本身”。漢字與西方文字分屬兩種不同的體系。傳統的西方哲學具有邏輯化的特點,而西方文字正是這種邏輯化思維下的產物,“不直面事物本身”。一方面,西方文字體系“預設了一個一成不變的本源”[2],它在記錄世界的時候,并非直面事物本身,而是用高度邏輯化,抽象化的拉丁字母代替事物。西方文字遵循的是任意性的原則,其能指和其所指沒有直接的理據性聯系,而只是形狀各異的記音符號。并且,西方文字的意義產生于系統的分配,在于每個字母之間形態的差別而非自身形態的特征。一個民族的文字是該民族看待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是該民族眼中的世界的縮影。因此,西方人用文字再現世界的時候不是以“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而是將世界化身為一種能指與所指毫無理據性、高度抽象化的符號。另一方面,西方文字在文字形體與意義表達中間有語音作為中介物,這與西方傳統哲學偏向于尋找一個“中間物”內在相通,也符合“言本位”的西方傳統觀念。在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影響下,西方人認為,語言是第一性的,而文字是第二性的,西方的拼音文字是一種代替性的文字,是言本位的文字。文字只不過是語言的附屬物,是對語音鏈條的摹寫,而無自身存在的意義。“字母是音位的替代形式,是對語音的書寫,讓文字最大限度地體現聽覺語言符號的線性特征”[1]。在“文字—語音—含義”這一鏈條上,文字不直接面向所指,而需要通過語音這一中介才能表達意義。因此,西方人用文字表達意義的時候不是以“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而是將語音作為中介物,并且這種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語言觀與傳統西方哲學中將思想對象看得比感官對象更重要的觀念具有內在契合性。在西方傳統哲學中,畢達哥拉斯強調的數是本原為形式普遍和本質真實論建立了原初范式,從這以后,在西方的傳統中便有了本質重于現象的觀念。
2.漢字的特點——“直面事情本身”。而漢字帶有“直面事物本身”的特點。中國人具有很強的“象思維”,而漢字正是這種“象思維”下的產物。一方面,漢字以直觀的、形象化的方式記錄世界。漢字是通過“六書”構造的,即通過象形、會意、指示、轉注、假借、形聲的方式將世界壓縮為一個個文字符號,而象形是其他構字方式的基礎,單體的象形字是所有字的字元,會意字、指示字、轉注字、假借字、形聲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礎上產生、發展的。“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是通過對物體的大體輪廓的刻畫來表現其物,見“日”之形可知其是太陽,見“月”之形可知其是月亮,這是一種通過直觀,并記錄直觀的方式創造文字符號,與胡塞爾的“面向事情本身”有內在的相通之處。因此,中華民族用文字再現世界的時候采取的是“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將世界化身為一種形象化,具有肉身理據性的符號。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小學早期僅為文字之學,而將音韻排除在外,可見,中國以字為本位的文化傾向由來已久。而在字本位的中華文化中,漢字形體與意義表達之間不需要中介物,它自身就攜帶了意義。漢字與漢語不具有同構性,它不是漢語的附屬物,不是對漢語語音的摹寫,并且在漢字與漢語的關系中,漢字是第一性的,它以自身形體的出場推遲語音的出場,即漢字遵循理據性的原則,能指通過與所指搭建的肉身理據性聯系使所指直接出場,對于漢字而言,觀其形可明其義,每個字的形態和含義有著不可切斷的聯系,所以,漢字與含義的關系不需語音這個中介。盡管隨著漢字的演變和簡化,我們難以在當今使用的簡化字中直接看出這種聯系,但肉身理據性仍然潛藏在漢字的形體中。因此,中華民族人民用文字表達意義的時候是以“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這種字本位的文化與中國將視覺感官看得比聽覺感官更重要的觀念內在契合,體現出中華民族致力于實在的或具體事情的務實精神。
綜上所述,漢字這種“直面事情本身”的特點是在與西方文字的對比中彰顯的,并且這種“直面事情本身”特點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務實精神,漢字的形象化,再現世界的直觀性以及其直接表意的特點就是一種致力于實在的或具體事情的務實精神的體現。這種在漢字中得以體現的務實精神是中華民族血脈中的基因,它促使中國人更多地思考人倫和“在世間”的哲學,也促使中國人在實用技術發明上自古領先。
二、創造精神
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孕育出創造精神,而此處的創造并非指西方思辨式、邏輯式,或是科學范疇下的創造,并非是基于一個觀念或原理下的創造,而指的是一種意境的創造,是從源頭生發出的生生不息的涌動[3]。在漢字這種能夠體現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的符號中,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可見一斑。
1.刪繁就簡創設意境的漢字。從漢字的造字角度看,早期漢字是通過立象的方式構成的,這種立象意味著通過刪繁就簡而創設意境。立象不是指對物象的精準描摹,而是指對物象的簡約化和創造性表達,在省略部分內容的同時有所創造,而達到一種非臨摹性的象征性,這是一種“對現實的創造性把握”[1]。也就是說,中國的漢字是人們站在人的立場對物象的再現,在這個再現的過程中,漢字并不還原物象的全貌,而是呈現其大致輪廓或者部分一角。“衣”字這個字甲骨文寫為:,納西文寫為,相比之下,納西文是具有臨摹性的符號,而甲骨文具有簡約性的特征,這種簡約性可稱為意象性,而正是這種意象性,才顯現出漢字構造過程中人的主體地位以及人在其中對物象加以創造的過程,這就像把寫實畫與寫意畫進行對比,從意境和創造性上來說,寫意畫更勝一籌。
2.運用毛筆書寫韻味的漢字。從漢字的構字角度看,漢字的能指中的形式與實體構成了一種張力關系,尤其是毛筆這種特殊的書寫工具使其書寫出的漢字意蘊無窮,體現出于有限中生無限的創造精神。
符號的能指面構成表達面,所指面構成內容面,葉爾姆斯夫將每一個面都分為兩個層次,即形式與內質。[4]孟華在《文字論》中稱其為形式與實體。漢字能指的形式指漢字的形體結構,是漢字的軟件系統,包括形體單位、形體結構規則和書體,漢字能指的實體由漢字的書寫工具、書寫表面決定,是漢字的硬件系統。[1]漢字能指的形式和實體之間具有一種張力關系,用不同的書寫工具能夠書寫出不同的書體,產生不同的書寫效果。而使用毛筆可以“讓其形體具有‘中性’或類文字性質:它既是筆畫又是線條,作為筆畫,它構成字形,作為線條,意味線條構成漢字書法,摹狀線條構成美術字或文字畫。而筆畫的自由化就是線條,線條的習語化、程式化、規范化就是筆畫。”[5]用毛筆書寫出的漢字是筆畫與線條的統一體,兼具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特征。因此,用毛筆書寫的漢字能夠在漢字書寫的規范內充分展現線條的自由,或舒展,或緊收,或上揚,或下抑,即便同一筆畫內也有粗細變化而非均質化。人們能在實體與形式的張力中,在筆畫與線條的融合中,在筆畫與筆畫間的舒展變化中品味到一幅字的韻味,能在漢字營造的氛圍中流連忘返,漢字的創造性與獨特魅力由此而生。
3.具有當場構成性的漢字審美形式。從漢字的審美體現——書法中看,書法具有當場構成性,書法不預設一個不變的本原,而是書寫者在不同人生階段以及不同情景下對主體內在的表達,它的本原不是一種固定不動的對象,而是一種變動不居的,從生活源頭生發的,如同溪水一般源源流動的“源泉”。筆者認為,書法的書寫是一種胡塞爾意義上的“還原”,很多“過去的東西”被懸置起來,當下的書寫即是當下所感,比如顏真卿在早年和晚年的書體中呈現出不同的風格,早年的書法較為秀氣柔和,但是晚年的書法卻變得渾圓。創作《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時,顏真卿是在一種從容不破的狀態下書寫,因而筆畫醇厚舒緩。而《祭侄文稿》,顏真卿是在家國破滅,痛失親人的狀態下書寫,因而全文多次涂抹,枯筆較多,墨色濃重枯澀。正是因為書法的創作具有當場構成的特點,不同派別、不同筆體、不同作品才會異彩紛呈,源源不斷的書法作品才能涌現,這是一種原生的創造,是一種于生活源頭處的創造。
綜上所述,漢字在造字、構字以及審美中都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勞動人民用立象的方式創設意境,用毛筆這種漢字能指的代表性實體書寫韻味,用當下流露的書法墨跡創造新作,這種創造不預設任何東西,只在生活本源中不斷生發意義。因此,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以某一邏輯為基點向外衍生的創造,而是一種更本源處的創造,也是一種中華民族獨特的價值取向和審美精神。
三、尚和精神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有“以和為貴”的傳統觀念,即便在存有矛盾體的陰陽模式中,中華民族也強調的是陰與陽的相伴相生,強調二者的融合統一而非斗爭對立。在漢字中,這種和諧精神體現在以下方面。
1.整體構義的漢字。從漢字的造字角度看,漢字體現了一種注重從宏觀上把握整體的和諧精神。上文提及:象形字是漢字的字元。我們通常把漢字稱為象形文字,漢字這種象形文字“本于圖畫”[6],并且演變至今,仍然帶有圖畫的意味,與其他文字相比,具有較強的圖像感,比如觀察“暮”的古字“莫”,仿佛能看到太陽落到草叢的場景;觀察“森”,仿佛能看到樹木林立的狀態,而這種圖像感是從漢字的宏觀整體上把握的,單看“莫”或者“森”中的某一個部件,無法領會字的含義,從整體上把握漢字,直觀從整體構成的“圖像”才能領會其義。漢字的前身是圖畫,每一幅圖、每一個畫面都是一個整體,演變為漢字之后仍保留了這種整體性,盡管后人將漢字拆解為偏旁部首,但這些偏旁部首在一個漢字中具有互文性,它們在彼此參照,互相牽連中才能使漢字顯現其義。漢字這種從宏觀上把握整體的特征強調部件之間的相生相諧,而非原子式個人間的分散,這是一種從宏觀上把握整體的和諧精神。
2.穿插避讓的漢字。從漢字的構字角度看,漢字強調穿插避讓,這種包含了謙讓意蘊的穿插避讓是一種尚和的體現。上文提到:漢字能指的形式指漢字的形體結構,是漢字的軟件系統,包括形體單位、形體結構規則和書體。其中形體結構規則包括筆畫與筆順,部件與部件組合,整字與行款,[1]在漢字的形體結構規則中筆畫及部件間的組合方面,穿插避讓是一個重要的構字原則。穿插避讓是指通過對筆畫,部首間的縮短、伸長,穿插、位移等技巧的妥善處理,使漢字各部分之間形成一個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它包括避讓和穿插兩個部分,避讓是指筆畫的適當縮短,使筆畫之間互不相犯,比如,左右結構的漢字,左邊部件要適當縮短,為右邊部件留出位置。然而,這種避讓是有底線的避讓,否則,筆畫或部件各部分之間相隔過遠而無法構成完整統一的漢字,而穿插就是這種有底線的避讓的體現。穿插是指一部分筆畫插入另一部分筆畫的縫隙之中,使漢字的結構連接緊密。比如“教”字右面部件的上撇的收尾處穿插在左面部件“子”的橫折與短提中間;“諸”字右面部件的長撇穿插在左面部件的空隙處。穿插避讓使漢字的筆畫與部件在相互避讓的基礎上達到統一,既互不相爭,又相互依存,使筆畫與筆畫之間,部件與部件之間獲得一種依存感和整體性,是一種達到整體和諧的體現,是中華民族尚和精神的體現。
3.和而不同的漢字。從漢字的審美體現——書法中看,書法中包含著和而不同的審美意蘊,體現了中華民族包容、尚和的價值取向。從書法角度看,和而不同是指在書法作品中,如果一個字中有相同的筆畫或部件,那么這些筆畫或部件的寫法不盡相同,須在起筆、走勢以及長短等方面體現出各自的不同;同樣,如果一幅作品中出現兩個相同的漢字,那么它們也須書寫出不同的形態。比如,“品”字中有三“口”,若這三“口”的寫法,大小、形狀完全一致,就會有僵硬、呆板之感,而書法中的“品”,三“口”各不相同,左邊的“口”面積最小,其次是上面的“口”,而右邊的“口”面積最大。并且這三個“口”雖然都是由“豎—橫折—橫”構成,但是它們的寫法都有所不同,或長,或短,或粗鈍,或纖細,或化橫為點,使漢字生動而活潑。這是書法中筆畫,部件書寫追求多樣性,和而不同的體現,是中華民族包容多樣,海納百川的尚和價值追求在書法藝術審美中的表達。
綜上所述,漢字在造字、構字以及審美上都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尚和精神。漢字的整體表意,穿插迎讓以及書法中和而不同的審美體現都是中華民族追求整體和諧的尚和精神在漢字中的表達。筆者認為漢字與中華民族之間是“符號與主體間性”的關系。一方面,中華民族在共同生活中創造了漢字符號,漢字符號不僅僅是語言的凝固,更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中華民族在創造其的過程中,將本民族的價值追求和精神意蘊也融入在其中。另一方面,漢字中蘊含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碼,這種蘊含了中華民族精神密碼的漢字具有一種“模塑功能”[7],即具有形象化、意境化和整體性特征的漢字不斷誘導,固定著使用這套文字系統的中華民族感知世界的獨特方式,并強化中華民族的形象化、象征性和整體性思維模式,進而不斷強化中華民族血脈基因中的務實精神、創造精神以及尚和精神。蘊含在漢字中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碼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追求,在與“生于斯,死于斯”[8]的穩固社會相去甚遠的不斷變動的現代社會中,漢字符號以及蘊含在其中的價值追求不斷強化我們對于民族和國家的身份認同,并為中華民族找到精神穩固的核心。因此,漢字需要被傳承,被書寫,要在漢字的傳承與書寫中挖掘并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碼,帶著中華文明的底色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