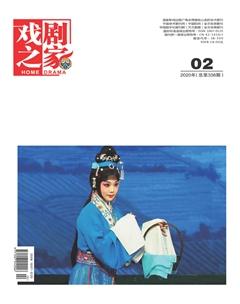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文化的發展現狀
程龍 熊奎 安滔 商丹
【摘 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鄉村文化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呈現出別具一格的表現形態。通過對貴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儺戲儺文化的考察后發現,道真儺戲儺文化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經歷了由原生態到現代化的嬗變,成了以鄉村文化推動鄉村振興的典型范式。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文化;儺戲儺文化;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
中圖分類號:J825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02-0012-03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社會的走向提供了行動指南。2018年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了《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指出了鄉村文化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地位。自此,鄉村文化與鄉村振興成了鄉村社會、政府部門、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論題,尤以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文化的發展現狀最為突出。而以儺舞、儺戲、儺藝、儺俗為內容的儺文化,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生命力最頑強、歷史積淀最深厚的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1],是鄉村文化的代表。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地處貴州省東北部,是全國僅有的兩個仡佬族苗族自治縣之一,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儺戲儺文化更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自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來,道真儺戲儺文化的保護、傳承與發展狀況都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挑戰與機遇共存,成就與困境同在。
文章將以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的儺戲儺文化為例,通過對縣域內文家壩村、新生村的走訪和調研,就現階段鄉村振興背景下道真儺戲儺文化的現實情況做出初步考察,為今后進一步研究道真儺戲儺文化打下基礎,并以此窺探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文化的發展現狀。
一、儺文化的原生土壤:儺戲在鄉村
儺文化產生于民間,厚植于鄉村,是老百姓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種精神文化信仰。儺文化包含著儺戲、儺舞、儺祭、儺技等多種成分,內涵復雜,形式多樣。儺文化的主要承載方式和表現形式是儺戲,它具有祭祀、表演、娛神和娛人等功能,原生態的儺戲只能在鄉村看到,因為儺戲中的某些祭祀成分、唱詞中的俚俗成分難以登上“大雅之堂”,不能在城市舞臺上完整呈現。在道真縣三橋鎮新生村紅光小組,筆者實地觀看和錄制了一出陽戲,為詳細了解儺戲在鄉村社會的表現情況,現簡要介紹相關事項,以便做出進一步分析。
(一)名稱:酬還陽戲神愿一宗。
(二)時間、地點:2019年1月28日,農歷臘月二十三。貴州省遵義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三橋鎮新生村紅光小組×號。
(三)緣由及目的:事主李某的父親嘴皮腫脹破裂,醫治無效后死亡,在臨死前向兩兄弟說自己還有心愿未曾了結,加之李某的兩個兒子都已接近40歲,至今未婚。臘月二十三正好是李某六十歲大壽,便借此機會還了其父親的陽戲神愿,祈福納吉。
(四)掌壇師:周仲倫,男,1968年生,道真縣接龍村人,法名周覺河,師承其父周興全(法名周本海),18歲請職,會唱陽戲、梓潼戲、做道場、煞鏵、算八字、安香火等。
(五)壇場選擇和布置:陽戲在事主家堂屋外院壩進行。壇場由主香案、三師香案和南門香案組成,懸掛或擺放著各個香案需要的神案、法器、衣物、文書、祭品等。
(六)程序:打鬧臺、申文發褋、申文搭橋、提戲、開壇、提上香童子、引馬土地、二郎領牲、上領牲錢、靈官鎮臺、上靈官錢、破腹斷怨、造船、上回熟錢、打唐二、勾愿、送神、招呼香火、掃火堂。
以上就是這出陽戲的大概事項,通過這樣一個模式,我們可以看到儺戲在鄉村的演出是繁冗復雜的,無論是時間與空間的選擇,還是唱戲的具體過程,都很有講究。經仔細觀察后發現,這出陽戲的儀式性最為突出,所占比重顯而易見。就以壇場的選擇為例,壇場是法事活動的主要空間,而“空間是儀式舉行的地方, 是世俗世界中圣地的象征, 是神靈居住活動的場所, 同時它又是一個人向神祭獻的空間, 因而, 它是一個人神溝通、人神聚會的地方。”[2]陽戲的首選空間是在“堂屋”,當地人稱為“桃屋”,以前這間屋子是沒有封頂的,意為在此地開展祭祀活動可以通達天地神靈。掌壇師周先生說,“屋子里太小了,人又這么多,為了大家一起熱鬧一下,所以就在這個院壩進行,這里是正對‘桃屋的,也沒有違背什么規矩,心誠就好了”。可見,“堂屋”在鄉村是獨具神圣氣息的地方,它是儺事活動進行的主要空間,儺戲因此而增添了幾分儀式感與祭祀性。
就其戲劇性而言,乃是以法師扮演神靈的方式進行表演,他們借用面具、畫臉、胭脂水粉等喬裝打扮,穿上特制的服裝,從而完成由儀式向戲劇的過渡,其間依然透露出一份崇敬神仙的味道,但戲劇已然占據主導位置。在唱戲的過程中,開壇仙姐、楊二郎、大小先鋒、土地等角色相繼出場,各種插科打諢,引得鄉民陣陣歡笑。比如《引馬土地》一節就是法師頭裹紅布,戴土地面具,穿黃色褶子,右手拄拐杖出場,與壇班其余法師相互問答,模式多是扮演土地的法師故意出錯,其余法師來糾正,然后再唱。這些儺戲藝人還會與圍坐著的鄉民進行親密互動,吸引觀眾的眼球,其舞臺性和神秘性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于無形,表演者與鄉民的聯系因而得以強化,這是儺戲作為“戲”的重要體現。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儺戲在鄉村社會兼具儀式性和戲劇性,且儀式性更為突出”的結論。正如學者所言,祭祀觀念與戲劇觀念交融以數千年來的農業性社會為前提,故而民間祭禮中的戲劇元素往往表現為祭祀與戲劇交叉的相對混沌現象。[3]這充分體現了儺戲融合祭祀的、戲劇的、民族的等多種成分,具有娛神、娛人、祈福納吉的功能。儺文化的本體是一種巫文化,可一經少數民族吸收轉換,其民族性特征就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道真儺戲儺文化正是這種吸收再轉換模式下的產物,它代表著仡佬族人的生活態度、行為習慣和精神信仰,飽含了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與情感思維。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道真儺戲儺文化雖然失去了其本身具有的一些內涵性特征,但卻不會從根本上喪失鄉村本色,因為儺文化的原生土壤是在鄉村。無論是人還是物,只要脫離了“原生”二字,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生存危機。為此,道真仡佬族儺戲儺文化在鄉村的發展不僅要保持現狀,使之不再衰退,還要讓它更加活躍于鄉村,形成永葆儺文化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
二、儺文化的現代化轉向:儺戲的舞臺化
近年來,隨著鄉村空巢化問題日益嚴峻,鄉村城鎮化進程逐漸加快,儺文化在鄉村的呈現次數和傳承規模已經大不如從前,生存與發展的活力日趨衰退,處于堅守與變遷的重要節點。隨之而來的是,儺文化等鄉村民族文化也得到了國家和社會各界的重視,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呈現出新的時代面孔。也就是說,作為一種鄉土社會信仰文化和社會禮俗,儺文化被當地的鄉民社會頑強堅守,但當其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被開發利用的時候,它又具有一系列的發展,也極具現代性特征。[4]所謂現代性特征,就是儺文化在現代化轉向的過程中內涵與外延的變化,儺戲的舞臺化就是這一現象的典型體現。
具體而言,道真仡佬族儺戲的“舞臺”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在鄉村地區搭臺表演的儺戲,這種“臺”也是舞臺,且呈現面貌較為完整,但觀眾大多局限于附近的村民。二是政府舉辦的活動或者是學者開展調研時,邀請民間藝人進行的表演,這種舞臺具有特定的觀眾,且劇目多經刪減。三是由旅游公司聘請儺戲藝人在旅游景點展開的表演。這里所說的儺戲舞臺化,主要就是針對后兩種情況而言的,在這樣的“舞臺”之上,既有原生態的傳承,但更多的是帶有時代特色的轉變。在大謙鎮文家壩村的中國儺城,每天上午九點半開城儀式后,都會有儺戲藝人表演“山王祈福”儀式,筆者在詳細觀察后與儺戲藝人,也是儺戲壇班的掌壇法師左朝元先生進行了交流。據他所說,真正的“山王祈福”儀式其實有九個環節:安師、開壇、搭橋、立樓、出土地、迎五猖、迎山王、靈官鎮臺、造船,所需人數8人左右,時長至少兩個小時,其目的在于祈求山王降臨,賜福給信眾。由此可見,在儺城所表演的“山王祈福”儀式是極其簡化的,其人物、服裝、過程、舞步、音樂等都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形態,這是僅就外在的變化而言的。若從內在的角度進行分析,舞臺化的“山王祈福”儀式與在鄉村進行的祈福儀式則有著一些共同的因素,這就是儺戲本身含有戲劇的成分以及祈求人們平安幸福的功能價值,這是儺戲之所以能夠搬上商業化的舞臺而發生巨大轉變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應看到,舞臺化的“山王祈福”儀式已經脫離了原有的生存語境,“戲”的部分更加濃烈,“儺”的部分大幅縮減,鄉土社會所含有的文化心理結構是片段式的、零碎式的、分裂式的呈現,但消災納吉的功能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關于儺文化的現代化轉向這一話題,不同的參與主體有著不同的看法。對于儺戲藝人來說,他們其實并不愿意自己從事了這么多年的儺戲被“舞臺化”而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可受困于經濟因素,他們只能盡力在這種舞臺化的過程中去保留一些原始成分,以體現出對自己職業的認同和對神靈先祖的崇敬。對于觀眾來說,他們看到的是一種現代化的表演,是自己所能接受的人物和角色,同時也能從中看到一些民族文化成分。值得注意的是,當今社會有許多人都把舞臺化的儺戲視作了解儺文化的窗口,將其完全等同于儺戲儺文化,從而陷入了認識上的誤區。我們應當認識到,舞臺上的民俗表演只能說是對生活部分還原或近似呈現,很難真正還原所表演的真實生活,更無法還原表演背后所指向的那種地方性知識和傳統。[5]可無論站在何種角度去看待儺戲的舞臺化,都不能否認它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對儺文化的傳承保護和時代化的藝術創造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三、儺文化作為旅游資源:鄉村振興的典型范式
習近平總書記說,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文化是鄉村振興的根和魂,是達成鄉風文明、生活富裕的重要抓手,以鄉村文化引領鄉村振興自然是題中應有之意。道真儺戲儺文化作為獨具特色的鄉村文化代表,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得到了新的發展,同時作為旅游資源,為進一步實現鄉村振興添磚加瓦,成為鄉村振興的典型范式。
經過不斷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實現鄉村振興的途徑多種多樣,而最適合少數民族地區的則是“文化+旅游”的扶貧開發模式。地處道真北部的大謙鎮文家壩村不僅毗鄰重慶,交通便利,仡佬族人口更是占該地區總人口的90%以上,具有豐富的民俗文化資源。文家壩村共2300余人,在開發儺文化之前,外出人口在65%以上,留守人口依靠種烤煙、蔬菜為生,年收入在1萬元左右。自2016年“中國儺城”開業至今,98%以上的村民都已選擇返鄉就業,主要從事園林綠化、服務業、建筑業、餐飲業,村民的年收入增加了兩倍,走上了家門口前的脫貧致富路。當然,儺文化的開發,不僅為當地村民提供了就業機會,避免了因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而導致的一系列問題,還推動了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從而增強了鄉村貧困地區的發展活力,為全面實現脫貧致富、建設美麗鄉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鄉村文化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并非是單向的,而是雙向式的互動,鄉村文化在作為旅游資源推動鄉村(經濟)振興的同時,也使得其更加活躍于民俗文化、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視域中。在“中國儺城”建成前,政府或學者的目的大多在于挖掘可用的民族文化,為實現脫貧致富貢獻力量,儺文化本身并沒有進入大眾傳播的領域,就連當地的人們也很少知道道真儺文化的存在。可近兩年,隨著儺城影響力的提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儺文化逐漸得到了民眾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對儺文化充滿了好奇,儺文化與儺城成了當地群眾熱議的話題。而對于儺文化的研究來說,本地的學者或其他高校的學者紛紛來到道真調研,開啟了道真儺戲儺文化研究的新篇章,為非遺文化的傳承與弘揚貢獻了智慧與力量。這就是說,道真在將儺文化作為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同時,儺文化的影響力在逐漸擴大,鄉村文化也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道真儺戲儺文化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就其內涵而言,儀式性在鄉村社會仍然存在且較為突出,而經過舞臺化的儺戲則失去了儀式性的特征;就其外延而言,適應了現代化轉向的儺戲儺文化,具有了新的表現形態,成了推進鄉村振興的有力助手。所以,鄉村文化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雖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但同時也存在著諸多不利于鄉村文化發展的因素,這值得社會各界予以關注并展開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曲六乙,錢茀.東方儺文化概論[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1.
[2]楊蘭,張業強.岑鞏的喜儺神儀式及儀式象征[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01):50-56.
[3]周華斌.祭祀、儀禮、戲劇的學理思考[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8,32(02):15-19+105.
[4]羅芳艷. 堅守與變遷:沿河土家族儺文化研究[D].貴州民族大學,2019.
[5]曾瀾.從鄉村戲臺到城鎮舞臺:江西儺藝人身份的藝術人類學考察[J].戲曲藝術,2016,37(02):48-54.
基金項目: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道真仡佬族儺文化研究”{貴大國創字2018(039)}。
作者簡介:程 龍(1997-),男,貴州遵義人,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民俗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