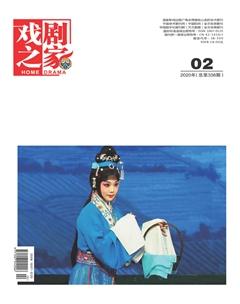從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分析《月亮與六便士》中德克·斯特羅夫怪異行為的背后原因
葉慶豐
【摘 要】《月亮與六便士》是毛姆的三大長篇小說之一,憑借著小說本身的魅力,以及深刻的語言,在文壇轟動一時。本文將聚焦小說中一個平凡又特別的配角人物,通過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對他“特別”的心理展開分析,從而對其“怪異”行為做出心理學闡釋,以期讀者能從一個新的角度對這個人物有更深刻的理解。
【關鍵詞】德克·斯特羅夫;《月亮與六便士》;超我;自我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02-0201-02
《月亮與六便士》講述的是一個普通的證券交易人斯特里克蘭德突然像著了魔一樣愛上藝術,拋妻棄子以及優越生活,在遠赴南太平洋小島時遇到的種種故事。小說從第十八章開始, 內容就與德克夫婦有關。德克·斯特羅夫的妻子布蘭琪深深愛上了斯特里克蘭德,德克·斯特羅夫痛苦的內心和扭曲的行為讓人費解。本文通過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分析德克·斯特羅夫的“怪異”行為背后的理由。
一、人物形象與理論分析
(一)德克·斯特羅夫的極善形象
德克·斯特羅夫是一位三流畫家,他有美麗的妻子、愉快的生活,以及足夠的經濟來源。后來,他與小說的男主角斯特里克蘭德相識,生活開始出現巨大改變。德克·斯特羅夫對藝術充滿崇敬之情,恰巧斯特里克蘭德擁有天才般的藝術天賦,德克給予他極大的包容,從而導致悲劇的發生。德克的妻子布蘭琪耐心照顧著斯特里克蘭德并喜歡上了他,要求與德克離婚。德克無奈選擇暫時離開,隨時等候布蘭琪回心轉意,誰知布蘭琪選擇了自殺。布蘭琪死后,德克在畫室看到斯特里克蘭德為布蘭琪畫的裸體畫,內心極其憤怒,卻依舊詢問斯特里克蘭德是否愿意跟自己一起。這一次,他并沒有不惜一切代價救助斯特里克蘭德,而是選擇離開巴黎回到老家,此時他已經一無所有,孑然一身。
(二)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簡述
弗洛伊德的《自我與本我》一書中對人格結構理論進行了歸納總結,他將人格結構理論分為三塊,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指的是人類最初的原始欲望和沖動,沒有任何的道德概念,可以理解成原始獸性。“自我”作為“本我”的發展,“超我”的源頭,起到橋梁作用,其在社會中發展,產生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超我”,在弗洛伊德的《自我與本我》中又被稱為“自我典范”,指的是“自我”中的一個最高等級,它是道德化的完美“自我”,沒有任何缺陷的極端善良,是一種極端情況下的道德。[1]
二、“超我”狀態:“可憐女人”的保護神
(一)旁人眼中德克的愛情
德克對妻子深沉的愛常溢于言表。在文中“我”的面前德克直言不諱對妻子的愛,甚至讓妻子感到不好意思。“斯特羅夫矢志不渝地愛著她,哪怕她到了垂老的歲月,身材不再苗條,臉龐不再迷人,她在斯特羅夫心目中的形象依然不會改變。對斯特羅夫來說,她將永遠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2]這是斯特羅夫留給文中的“我”的印象。他不介意妻子的出身,向來大大咧咧、不拘小節的他連自己的糗事都愿意說給大家聽,哪怕被人當作笑料,但是,對外人只字不提妻子的出身。這些看起來都十分正常。其實,他做這些的目的,都是對一個“可憐女人”的包容和溺愛,他希望能夠讓這個他認為的“可憐女人”在以后的生活中都充滿快樂。小說中,德克的妻子本是某個貴族家庭里的家庭教師,那戶人家的少爺勾引她,最后卻慘遭拋棄,當時懷著孩子,德克發現她的同時,娶了她。“以前我也經常奇怪這對極其不般配的夫妻為什么會結婚,但我從來沒想到情況會是這樣。”小說中的“我”也這么說。從表面上看德克找到如花美眷對他來說是一件難得的喜事,到后來才發現其實是德克出手相助,救了布蘭琪。
(二)“更愛”的真正原因
在布蘭琪愛上斯特里克蘭德之后,大多數人都覺得由于對妻子深沉的愛,德克會選擇原諒,并努力挽回妻子。小說中,德克似乎在乞求,乞求斯特里克蘭德回自己畫室休養,乞求妻子留下,乞求斯特里克蘭德和自己一起回老家。他看上去是一個極其軟弱、沒有骨氣的年輕人。“但你肯定知道他不會給你幸福的啊。為了你自己著想,請你別走。你不知道你將來會遇到什么事情。”[2]甚至在被背叛后,德克依舊乞求妻子,全身心地為妻子以后的生活考慮。這應該是從最常規的角度來解釋了。
其實不然。從心理學角度看,尤其是從弗洛伊德人格結構理論看,這是他的“超我”過于強大,即對弱者的同情,企圖幫助弱者的道德境界過于強大,以至于忽略了“本我”的欲望,也忽視了現實狀況。這間接解釋了德克知道自己妻子與斯特里克蘭德離開之后,為什么和“我”說道:“唉,比以前更愛啊。斯特里克蘭德不是那種能給女人幸福的男人。他們的關系維持不了多久。我希望她知道我永遠不會讓她失望。”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似乎“超我”的狀態反而能夠更好地解釋德克的想法。他希望做一個“可憐女人”的保護者,他深知斯特里克蘭德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自己的妻子跟了他之后生活一定再次陷入之前的痛苦——被拋棄。
“不要走啊,親愛的。我不能沒有你,我會殺了我自己的。如果我做了冒犯你的事,我求你原諒我。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更加努力讓你幸福。”[2]他企圖把一切原因都歸咎于自己,并極其卑微地乞求原諒,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妻子回心轉意。他甚至能夠預料到以后妻子的生活會多么痛苦。其實,這是他的“超我”在遵循至善原則,“現實原則講究理性思考,而至善原則有點類似于本我的非理性特點,只考慮應當性,不追求合理性。”[3]看似并不合理的行為背后,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的觀照下,可以找出合理的解釋,即德克·斯特羅夫對“自我”典范的強烈要求,他只是希望曾經被拋棄的妻子不再被拋棄。因而,甚至說出:“比以前更愛啊!”
三、“三我”狀態:“藝術天賦”的救世主
(一)“自我”和“本我”的強烈沖突
在《月亮與六便士》第三十九章中,德克去畫室看到了斯特里克蘭德為布蘭琪畫的裸體畫。“悲哀,妒忌和狂怒紛紛涌上心頭,他發出了嘶啞的喊叫聲,他說不出話,他握緊拳頭,激動地揮舞著,似乎面前有一個隱形的敵人。”從這時起,他內心最原始的野性徹底覺醒,就像是從深處迸裂而出的一股邪惡力量,“他想要把那幅畫砍得粉碎,一分鐘都不能讓它存在。”[2]德克這時的狀態其實是“本我”和“自我”的相互交織,“本我”主導他的心理。
(二)“超我”狀態下的極善
緊接上述場景,故事發展得讓人難以理解,“我不知道當時自己怎么回事,我正準備在那幅畫上戳一個大洞,我的手已經準備出擊,可是突然之間,我看到它了。”“那幅畫,它是藝術品,我不能碰它,我很害怕。”[2]從弗洛伊德人格結構理論來看,這是他的“超我”占據了整個內心。“超我”會反對能量不正常宣泄,在心理狀態中對原始的暴力沖動有抵制作用,抵抗“本我”做出任何魯莽或者沖動的行為。就在德克感到恐懼的那一瞬間,“超我”產生了徹底擊垮“本我”的強大能量,將發狂的德克不僅恢復到之前的心態,更讓他有了“自我”的升華,即“自我典范”。而他所感受到的害怕和雙手的顫抖,是因為焦慮。弗洛伊德把焦慮分為三種,其中一種是道德性焦慮,即“自我”對“超我”的恐懼。起初“自我”被“本我”牽制,“本我”占據主體全部,從而導致德克準備立即撕毀畫,但是被其內心的極端道德化的“超我”狀態所恐嚇和擊潰,從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匕首。“當自我意識到自己的動機或者是行為違反了超我的自我理想和良心時,就會產生一種羞恥和悔罪感的情感體驗,這就是道德性焦慮。”“自我典范表現特別嚴厲,經常以殘酷的方式激烈反對自我。”[1]甚至在最后,在情緒冷靜之后,德克經歷了足夠的思想掙扎,最終“超我”占據了他的整個情感。“我邀請他跟我去荷蘭。畢竟我們都愛布蘭琪。我母親的房子里會有多余的房間給他住。我想和純樸的窮人相處會給他的靈魂帶來很大的好處。我覺得他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某些對他非常有用的東西。”[2]
他始終堅守著對斯特里克蘭德的責任感,認為自己對他的藝術天賦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即便在被侮辱到沒有任何尊嚴的情況下,他始終在為斯特里克蘭德今后的生活考慮。“超我”遵循至善原則,“至善原則的基本工作機制就是觀測和監督自我,繼而懲惡揚善,舍丑逐美,超我通過自我來控制本我的本能能量的流瀉。”[3]“超我”是人格結構中最為理性、最為文明的一個層面,它能夠進行自我批評和道德約束,包容萬物,理解萬物,是極端道德下理想“自我”的充分體現。
四、結語
弗洛伊德總結,在人格結構內部,當“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統一時,人的心理處于一種平衡狀態,當三者失去平衡,處于紊亂狀態,人的心理就不能進行調節控制,造成精神失常,這就是為什么德克在離開畫室之后徹夜難眠的原因。人格結構內部的“自我”“本我”“超我”三者并沒有明確的界限,三者相互依存、相互扶持,才能構成一個統一的健康整體。從弗洛伊德的理論分析整個故事情節,以及德克的行為和心理,德克的“自我”“本我”“超我”分別占據內心的主導地位。總體來說,德克·斯特羅夫是一個經常處于“超我”階段的人,對自己的約束力強硬,深知自己存在的價值是“藝術天賦”(斯特里克蘭德)的救世主,也是“可憐女人”妻子的保護神。雖然在最后,他既沒有保護好妻子不受傷害,也沒有拯救斯特里克蘭德的藝術天賦。“從人生觀的角度來說,在倫理學家看來,現實通常就是痛苦的代名詞,所以他們要求超越現實,追求極善。”[3]在小說中,德克的種種做法都表現出在“超我”階段受到的折磨讓其身心俱疲。
參考文獻:
[1]弗洛伊德. 自我與本我[M]. 林塵, 等, 譯. 上海: 譯文 出版社, 2011.
[2]月亮與六便士.(英)毛姆[M];李繼宏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9.1
[3]孫貴林. 弗洛伊德人格理論中的倫理思想研究[D].湘潭大學,2008.
[4]高俊利.《月亮和六便士》中的多維人性[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5,28(13):186-18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