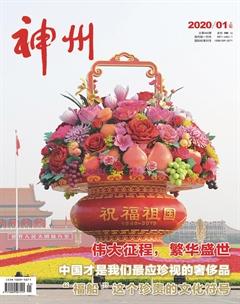試析非時間處所名詞作補語
劉曉明
摘要:在現代漢語中,存在著大量的謂詞性結構帶補語的情況,補語大多由形容詞充當,名詞中只有時間處所名詞可以充當補語。但在最近一段時期,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的情況卻屢屢見諸新聞標題或報道中。本文試從漢語動詞題元結構理論、漢語雙賓語句、介詞結構和“把”字句等角度就名詞充當動詞性結構補語的現象及其成因進行分析和解釋。
關鍵詞:名詞;動詞性結構補語;題元理論;雙賓語句;介詞結構;“把”字句
依據形態分類法,世界上的語言可分為孤立語、屈折語、粘著語和復綜語四種。印歐語用豐富的內部屈折和一套精致的形態標志表示語法意義,屬于屈折語。漢語屬于沒有明顯的形態標志和形態變化的孤立語。也就是說,根據詞形,我們無法判斷出哪個是名詞,哪個是動詞,哪個是形容詞;另外,漢語的詞語進入句子后也沒有相應的形態變化。基于以上漢語的兩個特點,因此漢語的詞類與句法功能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這就造成了漢語中的某一詞類可以同時充當幾種句法功能。例如名詞不僅可以作主語、賓語、定語,它還可以在名詞謂語句里充當謂語,如:他,上海人。名詞可以充當狀語,多見于書面語中,如:你們不能機械地處理這些問題。甚至有時名詞(不包括時間處所詞)還可以充當補語。
由此可見,漢語中六大成分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和補語,名詞均可充當,所以當我們需要判斷名詞在具體的句子中究竟充當什么句法成分,起什么語法作用的時候,就不能僅僅依據名詞所處的語法位置,也不能依靠語序,例如存現句中名詞主語處于句尾,更不能依據形態(漢語沒有明顯的形態變化),只能依據名詞在具體句子中與其他詞語的語義結構關系和語法結構關系綜合判斷,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語義。而印歐語則不同,由于印歐語有一套精致的形態標志以及表達語法意義的語法手段,如:時態、語態、格、語氣助詞等,不同的詞類在句中有各自相對固定的語法位置,例如形容詞、動詞跑到名詞的語法位置上要在形態上加以變化(即名詞化),不同詞類之間的組合也不像漢語那樣靈活,某些詞語組合時常常要在形式上加以變化,甚至要改變語序。漢語屬于意合式語言,由于沒有形態的束縛,詞語之間的組合如果意思完整,邏輯通順,也就是語義特征具有一致性,并且語義自足,就可以相互組合,這也就出現了某一詞類可以具有多種句法功能的現象。
在現代漢語中,存在著大量的謂詞性結構帶補語的情況,如:動詞性結構帶補語,“踢足球踢累了”,形容詞性結構帶補語,“腰弓得厲害極了”,補語大多由形容詞充當,名詞中只有時間處所名詞可以充當補語。但在最近一段時期,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的情況卻屢屢見諸新聞標題或報道中。如:“掛職副區長”、“掛職黨支部”、“落戶上海”、、“登陸中國”、“留學英國”、“接班李嘉誠”等。本文試就名詞充當這些動詞性結構補語的現象及其成因進行分析和解釋。
我們通常所說的補語,指的是動詞性結構或形容詞性結構的補語,它對謂詞性結構起補充說明的作用,位于謂詞性結構后面,有時中間加“得”。謂詞性結構帶補語有以下幾種情況:1、結果補語,表示動作、行為產生的結果,與中心語有因果關系,補充說明動詞性成分,由形容詞充當。如:燙<傷>,照<亮>。2、程度補語。用“極、很”和虛義的“透、慌、死、壞”等,表示達到極點或很高程度,也可以用量詞短語“一些、一點”表示很輕的程度。如:好<極了>,謙虛<一點兒>,補充說明形容詞性成分。3、狀態補語。表示由于動作、性狀而呈現出來的狀態。中心語和補語中間都有助詞“得”,補充說明動詞性或形容詞性結構,由形容詞性成分充當。如:跑得<很快>,綠得<可愛>。4、趨向補語。表示動作的方向或事物隨動作而活動的方向,補充說明動詞性成分,由趨向動詞充當。如:跳<下去>,扔<過來>。5、數量補語。包括兩種:一種是動量補語,由表動量的量詞短語充當,用來表示動作發生的次數,如:跑了〈兩趟〉、轉了〈五圈〉;另一種是時量補語,由表時量的量詞短語充當,用來表示動作持續的時間,也就是時量、時段,如:掛了〈兩年〉、看了〈三天〉。6、時間、處所補語。多由介詞短語表示動作發生的時間和處所,包括表示動作終止地點。如:生〈于1959年〉、站〈在門口〉。7、可能補語。可能補語是表示可能或不可能的補語,它只表示可能性,多數是尚未實現的事情。可能補語有兩種。一種是用“得”或“不得”充當,表示有無可能進行,或表示動作結果能否實現。如:這雜志翻〈得〉翻〈不得〉?另一種是在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和中心語之間插進“得、不”(輕聲),表示動作的結果、趨向可能不可能實現。如:提高——提得高、提不高放大——放得大、放不大。以上七種補語類型,除了時間、處所名詞可以充當時間、處所補語之外,均沒有名詞充當補語的情況。
名詞(不包括時間處所詞)不能作補語已經成了一條語法規則存在于漢語使用者的腦海中,然而當翻閱報刊雜志或打開電視或廣播收聽新聞時,卻不乏“掛職黨支部”、“落戶開發區”、“登陸熒屏”等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的說法,且有普遍使用和流行開來的趨勢。我們使用了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現代漢語語料庫和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通過對“掛職”、“落戶”、“登陸”等動詞的檢索,得出“掛職副區長”、“落戶上海”、“登陸中國”等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具有以下特點:
1、能帶名詞作補語的動詞性結構大多不及物。如:“掛職”、“落戶”、“登陸”為不及物動詞。
2、能帶名詞作補語的動詞或動詞性短語本身是動賓結構。如:“掛職”一詞中的詞素“掛”與“職”是動賓結構關系。
3、這種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的情況大多出現在新聞標題等,由于字數、版面限制或考慮到音節緊湊等方面因素而使用。
4、能帶名詞作補語的動詞大多是雙音節詞語,由單音節動詞與單音節名詞組成一個音步。其后所帶的名詞補語則不限于雙音節,但至少是雙音節詞語。
5、作補語的名詞前均可添加介詞,如“掛職副區長”意思等同于“掛職為副區長”,“落戶上海”意思等同于“落戶在上海”,“登陸熒屏”意思等同于“登陸于熒屏”。
6、“掛職”、“落戶”、“登陸”等動詞之所以是不及物多是由于這些詞語本身由動詞加名詞組成,如果再帶名詞則顯得冗余。但由于這些詞語較強的動作性,所以在新聞標題中偶有使用,人們對這種現象并不排斥,因此相互模仿而普遍使用開來。
7、作補語的名詞,如“副區長”、“上海”、“英國”、“李嘉誠”等多是人名、地名、職務等專有名詞。
8、帶名詞作補語的動詞性結構在句中往往只能處于句尾的位置,也就是說,這種結構之后不能再帶其他成分。
9、這種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的情況主要用于書面語,口語中絕少出現。
既然這種新的結構屢次出現在新聞標題和新聞報道中,我們不禁要問其背后的成因和機制是什么。以下試從漢語題元結構理論、雙賓語句成句的特點、介詞結構和“把”字句等方面解釋動詞性結構帶名詞只能作補語。
漢語動詞題元結構理論認為,所有可能出現在結構中的名詞性成分都是預選NP,名詞的語義角色由謂語動詞決定。所有預選NP可以在謂語動詞前無標記出現,即主語。所有預選NP可以在謂語動詞后有位置出現,即賓語。漢語里,只要在動詞后的名詞,不管其題元角色是什么,都看作賓語比較合適,謂語動詞后的賓語至多出現兩個。既然出現在謂語動詞后的名詞都看作賓語,那么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謂詞性結構后面極少出現名詞作補語。
如果假設“掛職副區長”、“落戶上海”、“登陸中國”這種動賓結構帶名詞為雙賓語結構,可以通過現代漢語中雙賓語中的遠賓語(即直接賓語)必須帶數量短語這一現象來否定。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句子是雙賓語結構,那么遠賓語必須是數量結構才能成句。如:小張送給小李一本書。如果省略數量短語“一本”,直接說“小張送小李書”則不成句。再如虛指賓語:小張喜歡喝酒就喝它一個痛快。如果省略數量短語“一個”,直接說“小張喜歡喝酒就喝它痛快”則不成句。既然雙賓語結構中的遠賓語如果要成句必須帶數量短語,那么我們就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掛職副區長”、“落戶上海”、“登陸中國”中的名詞“副區長”、“上海”、“中國”不應看作賓語,而應看作補語。
“掛職副區長”等這種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也可以通過在名詞前加介詞來判斷。如“掛職副區長”意思等同于“掛職為副區長”,“落戶上海”意思等同于“落戶在上海”,“登陸熒屏”意思等同于“登陸于熒屏”,“留學英國”意思等同于“留學去英國”,“接班李嘉誠”意思等同于“接班自李嘉誠”。如果我們對“掛職為副區長”、“落戶在上海”、“登陸于熒屏”、“留學去英國”和“接班自李嘉誠”等結構進行句法分析,不難看出,這些結構中的介詞帶名詞組成的介詞短語充當了補語。名詞在這個結構中起到的語法作用等同于介詞短語(即介詞+名詞),只是人們在實際的語言運用中,出于語言使用的經濟、省力原則而省略了名詞前的介詞,使之成為了一個形式上為不及物的動賓結構直接帶名詞。
介詞結構作補語還有一個特點是它可以提前至動語或動詞性結構之前作狀語。如:“落戶上海”意思等同于“落戶在上海”,也可以說成“在上海落戶”,“留學英國”意思等同于“留學去英國”,也可以說成“去英國留學”。既然介詞結構作補語這種結構可以提至謂詞性結構之前作狀語,這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出“上海”、“英國”等名詞在這里只能作補語。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有一類動詞+補語+賓語結構,如“吃壞肚子”、“哭啞嗓子”,這里的“肚子”不作動詞“吃”的賓語,而作動詞+補語結構“吃壞”的賓語。這可以通過“把”字句的轉換看出。如:“吃壞肚子”可以轉換成“把肚子吃壞了”。“把”字句要求介詞“把”帶賓語,動語或動詞及其復雜形式放在賓語之后,由此得出,“吃壞肚子”中,“吃壞”作為一個整體帶賓語。同理,我們討論的“動+賓+補語”也可以通過轉換成“把”字句看出一些現象。如:“落戶上海”可以轉換成“把戶落在上海”,因為“把”字句的結構要求介詞“把”帶賓語,所以“戶”在這里作賓語,而“上海”并沒有跟在介詞“把”之后,所以不能看作賓語,只能看作補語。
基于以上討論,我們認為“掛職副區長”、“落戶上海”等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應該看作是名詞前省去了相應介詞的介詞結構作補語的情況。這些介詞之所以可以省略,原因在于“掛職”等動賓結構與“副區長”等名詞結構在組合時語義上可以自足,連用時不會造成歧義或語義不通。相應的介詞在這些結構中可有可無,并不是非出現不可,也就是說,出于語用的經濟、省力原則,省去這些介詞不僅不影響語義表達,反而起到了簡潔、讓讀者和聽眾感到新奇的表達效果。
認知語言學認為,隱喻是不同概念域之間的映射,一般是由具體域激活抽象域,也就是人們常常用具體、常用、容易理解的概念來隱喻比較抽象、難以理解的概念。“登陸”一詞其原意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渡過海洋或江河登上陸地……”關鍵在于有“登上”之意。所以,“登陸”一詞可以通過隱喻表達具有從下到上,從外到里進入之意。“登陸中國”即可以用來表示某種事物從中國之外的領域進入中國的范圍。如果與“登陸”搭配的事物不限于具體事件,也就是進一步抽象化,與抽象的事物連用,就可以說成“登陸熒屏”。從構造方式看,“登陸”本是不及物動詞,它只出現在“XX登陸”結構中,如:“諾曼底登陸”,“登陸中國”則屬于概念糅合,將“登陸”與“中國”糅合成一個結構。取“登陸中國”中的“登陸”和“熒屏”,概念截搭成“登陸熒屏”。同樣,“落戶”指在某地報入戶口,長期定居。所以,“落戶”一詞可以通過隱喻表達某物從原來的地方長期轉移至某地。如果與“落戶”搭配的事物不限于具體某個街道或社區,也就是抽象度增加,與抽象的地點連用,就可以說成“落戶上海”。
認知語言學認為,漢語遵循相似原則中的時間相似原則,語言成分之間的排列順序同其所表達的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一致,即先發生的事件在句法結構中位于后發生的事件的前面。如“留學英國”,“留學”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早于留學的目的地“英國”,如果我們說成“去英國留學”,雖然在句法上也成立,但由于聽話人先聽到“去英國”,往往會有疑問:“去英國干什么?”“去英國怎么了?”,只有當聽話人聽到“留學”時,“去英國”在意思上才表達完整。“去英國留學”這種語序不符合人們基本的認知規律。而如果先說“留學”,由于句子中謂語動詞是表達的核心,聽話人聽到“留學”,就可以預測說話人即將說出目的地,這樣就不違背人們的思維順序。意象圖式理論認為漢語語序中,背景先于目標,如“湖中心有個亭子”,“湖”是背景,“亭子”是目標。也就是說,漢語句中的焦點往往位于句尾的位置。但有些時候需要強調目標時,目標在句中則可以位于背景之前,如“這間屋子比那間屋子寬敞”,“這間屋子”是目標。“那間屋子”是背景。“在上海落戶”、“去英國留學”等結構中,介詞結構是背景,動賓結構是目標。而在“落戶上海”、“留學英國”等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里,動賓結構是目標,介詞結構是背景。
當一種新的語言形式產生時,它一定是偏離的。既可能是正偏離的,也可能是負偏離的;如果是前者,它就很大的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而即使是后者,也有可能“習非成是”。當新的偏離形式被人們普遍接收后,它就有可能成為新的規范形式,而新的規范一旦確立,它就開始了歸于零度的運動,并且開始醞釀著新的偏離。語言的發展過程,從宏觀角度看,也就是從零度到偏離的轉化(零度偏離化)和從偏離到零度的轉化(偏離零度化)的交錯進行。分解開來看,前者是語言變異的表現,后者是語言發展的表現,一切語言單位都處在一個運動的中介環節或過渡狀態。
以上所分析的名詞作補語只存在于某些特殊的動賓結構之后,在漢語中并不是如同名詞作主賓語那樣是一種普遍現象。這種動詞性結構帶名詞作補語的結構式可以概括為:V+N,V=動詞詞素+名詞詞素,即(動詞詞素+名詞詞素)+N。從結構的表面形式看,似乎可以看作是動賓結構帶賓語,但基于我們以上討論的雙賓語句成句條件及介詞結構等因素,這種結構只能分析為動賓結構帶名詞作補語。(動詞詞素+名詞詞素)+N組成了一個結構模式,能進入之一模式的動詞(即動詞詞素+名詞詞素)必須為不及物雙音節動詞,且N多是人名、地名、職務等專有名詞,且音節數至少是雙音節。雖然仿照這一結構模式,漢語中出現了一些(動詞詞素+名詞詞素)+N的短語,但這一結構模式是否具有能產性,還要看其在人們實際語言運用中的使用頻率。
參考文獻:
[1]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陸儉明.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陸儉明,沈陽.漢語和漢語研究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4]陳本源.略談古漢語中名詞用作補語的問題[J].語文知識,1995(1):19-21.
[5]宋成吉,張桂梅.淺析名詞性詞語作狀態補語[J].語文教學與研究,2007(35):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