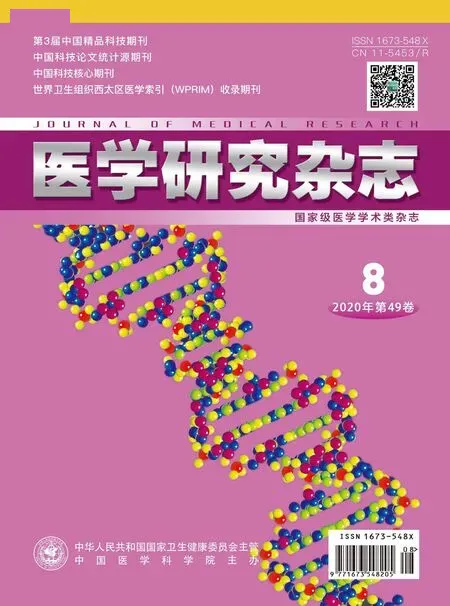血管化復合同種異體移植物的免疫細胞亞群變化及基因譜表達
王晨羽 丁文蘊 龍 笑 王曉軍
在過去的20年中,逐漸開始嘗試使用由異體的皮膚、肌肉、肌腱、脂肪、血管、神經以及骨骼等多種組織組成的血管復合同種異體移植物(vascular composite allotransplant, VCA)對截肢、嚴重燒傷、顱面缺損、褥瘡等原因導致的手部、面部和臀部等部位的大面積組織缺損進行移植修復重建[1]。相較于傳統的修復重建手術,VCA可以有效改善局部和整體形態功能,患者術后的滿意度和生活質量明顯提高。然而,VCA移植術后存在著嚴重的免疫排斥問題,其復合組織的耐受性,特別是皮膚成分,極具挑戰性,需要患者終身使用免疫抑制劑,但仍常出現急性或慢性排斥反應(上肢移植急性排斥率為88%,面部移植急性排斥率為73%,實體器官移植急性排斥率為10%~30%),導致移植物死亡[2,3]。有關VCA移植的免疫學機制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其中免疫細胞亞群的變化及相關基因譜表達的研究,對于理解VCA排斥反應發生的免疫機制和研究相關非侵襲性檢查具有重要意義。
一、VCA免疫排斥機制
在VCA移植早期,主要引起的是細胞介導的急性排斥反應,亦是最常見、最主要的排斥反應,其依賴于通過抗原的直接和間接途徑來啟動T細胞識別。最常見的形式為不匹配的MHC分子反應,以CD8+細胞釋放誘導移植細胞凋亡的細胞毒素攻擊移植物細胞[4]。隨著淋巴組織中抗原的初始暴露,抗體介導的免疫反應被激活。通過補體固定以及通過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性的發生,以及自然殺傷細胞和巨噬細胞受體結合的抗體Fc區以誘導移植物細胞死亡[5]。當移植物進入慢性反應期間,炎癥持續誘導內皮損傷,繼而產生慢性平滑肌細胞重塑機化,形成外膜增厚、血管周圍炎癥和膠原蛋白過量沉積等病理改變[6]。
二、免疫細胞亞群變化
目前來看,對免疫細胞亞群進行定量分析可以借以評估移植后的機體免疫狀態并有利于預防機會感染和惡性腫瘤。在腎臟和心臟移植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外周循環中的記憶T細胞數量與急性排斥反應的發生風險密切相關[7, 8]。外周血中活化的T細胞裂解的細胞產物的濃度水平可以預測移植后患者出現嚴重移植排斥反應的概率[9]。因此利用VCA的免疫細胞亞群的定量分析被認為是無創性臨床檢查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10]。
1.外周血中的免疫細胞亞群:由于VCA急性排斥反應主要依賴于具有細胞毒性的T細胞,因此其亞群變化是首要的研究方向。有研究對6例接受全臉移植患者外周血中的淋巴細胞進行了表征,發現效應記憶T細胞是VCA移植后淋巴細胞的主要亞群。CD4效應記憶T細胞(CD45RA-CCR7-)是CD4+T細胞中的主要表型,而CD8+T細胞中則由效應記憶T細胞(CD45RA-CCR7-)和RA效應記憶T細胞主導。在大多數患者中,外周循環中主要的T輔助細胞(T helper,Th)類型是Th2細胞,其次是Th17和Th1細胞。發生排斥反應前后外周血液中的CD4+和CD8+T細胞數量沒有顯著變化,效應記憶T細胞亦無明顯減少(CD45RA-CCR7-),但CD4+和CD8+效應記憶RA T細胞(CD45RA+CCR7-)均增加。排斥反應期間,調節性T細胞(CD4+Foxp3+)在移植物中大量積累,導致外周循環中的調節性T細胞的數量減少[11]。
抗體介導的排斥反應與T細胞介導的排斥反應的免疫學特征有所不同,在T細胞介導的排斥反應中,CD8+群體中的T效應細胞數量增加,但是調節性T細胞數量沒有變化。而在抗體介導的排斥反應中,外周循環中的Tfh細胞(CD4+PD1+CXCR5+)和記憶B細胞(CD19+CD27+)數量均增加[12]。
此外關于VCA和實體器官移植之間淋巴細胞亞群的差異也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向。有研究比較了穩定的手部移植受者和穩定的腎臟移植受者外周血中的淋巴細胞亞群[13]。穩定的腎臟移植受者的外周血中B細胞數量較健康人減少了4倍,而穩定的手移植受者的B細胞數量與健康人比較則變化不大。手移植受者外周血中的調節性T細胞(CD4+CD25+CD127-)數量也與健康對照相似,但腎移植受者的調節性T細胞數量則顯著減少。此外,手移植受者外周血中CD8+與CD28-T細胞數量亦顯著增加。
2.移植物中的免疫細胞亞群:移植物中與外周血中的的免疫細胞亞群非常不同。與周圍循環比較,VCA移植物的皮膚中存在著更多的T細胞,特別是有更多的效應記憶T細胞,以及分布有多種T細胞受體,并具有特征性的Th1表型。VCA移植物的皮膚中還有大量CD8+記憶T細胞[14]。排斥移植物的供體T細胞中,超過90%是組織定居記憶性T細胞(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s, TRM)表型(CD69+、CD103+、CLA+)[15]。起初,當發生輕度排斥反應時,主要由CD3+T細胞浸潤,并且CD8+細胞比CD4+細胞更為突出。真皮層內的CD3+T細胞的百分比和CD4/CD8的比率會隨時間而增加,而CD20+B細胞則較為稀少[16]。轉變為急性排斥反應時,大多數淋巴細胞是供體來源的CD8+記憶T細胞,并進一步表現為移植物中CD4+、CD8+和CD14+細胞的大量積聚[11,15]。
移植物內與受者體內其他部位的免疫細胞亞群亦有所不同。以手部移植為例,與患者自身皮膚比較,移植物的皮膚具有更多的CD8+淋巴細胞和CD68+巨噬細胞,但沒有CD4+細胞。不論是否發生排斥反應,均在VCA移植物的皮膚中發現了CD20+B細胞,卻未在自身皮膚中發現這一現象[17]。此外,VCA移植物的真皮和表皮中的樹突狀細胞均增加。班夫分級(Banff grade)1級反應的患者移植物真皮中的CD1a細胞數量亦增加。在面部移植中,移植物的表皮中僅有樹突狀CD8+T細胞作為供體細胞,而在皮脂腺和血管周圍則存在著CD8+和CD4+T細胞作為混合供體和受體。
三、基因譜表達
通過鑒定細胞或組織中信使RNA的全部或部分基因的表達情況,可以估計大量基因之間的關聯性,并探尋調控基因。基因譜表達在診斷疾病或探索機體對治療的反應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基于基因譜表達的臨床及臨床前研究可以進一步加深對VCA分子免疫學機制的認識[18]。
1.排斥相關基因:在出現排斥反應的面部移植患者體內,γ-干擾素(interferon-γ,IFN-γ)信號通路(包括IRF1和STAT1)被激活,然后通過CXCR3/CCR5通路(包括CXCL9和CCL5)產生趨化因子配體,繼而上調負責募集細胞毒性細胞的基因的表達,激活由CD8+細胞毒性T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的基因表達(包括GZMB),實現免疫效應功能[12]。在人和動物模型中,IFN-γ已經被證明是同種異體移植排斥反應過程中促進炎癥的關鍵因子,可以與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協同發揮作用,誘導CXCR3配體(CXCL9、CXCL10、CXCL11)和CCR5配體(CCL3、CCL4、CCL5)的表達。后兩種配體是同種異體移植急性排斥反應中最常見的上調趨化因子。這些由樹突狀細胞、活化的巨噬細胞、內皮細胞和NK細胞分泌的趨化因子,又可促進IFN-γ的產生增加,從而進一步促進炎性刺激的放大和趨化因子分子的釋放[19]。
抗體介導的排斥(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和T細胞介導的排斥反應(T cell-mediated rejection,TCMR)的相關基因有所不同。AMR與血管內皮基因如細胞間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ICAM-1)、VCAM1和SELE的過度表達有關,而TCMR的特征是與細胞毒性相關基因GZMB的表達上調有關[12, 20]。
基因譜表達顯示,炎性皮膚疾病模型(接觸性超敏反應)與急性皮膚排斥反應的發病機制有各自特征。皮膚中CCL7、IL-1β、IL-18和TNF的基因表達譜,在排斥反應模型與炎性皮膚疾病模型間存在明顯差異。IL-12B、IL-17A和IL-1β基因表達水平在兩種疾病模型之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并且表達水平與皮膚類型無關[21]。
VCA與實體器官移植的排斥反應基因譜也有所差異。與健康人比較,在手移植組中,排斥相關基因(CD8、IL-10、NOTCH1、PDCD1和TNF)明顯上調。而腎臟移植組中,此類基因表達與健康人沒有差異。此外,與腎臟移植組患者比較,手移植組中與排斥相關的基因(CD8、NOTCH、TNF)的表達水平也更高[13]。
2.耐受相關基因:叉頭轉錄因子3(factor forkhead box 3, FOXP3)的表達可影響調節性T細胞的功能,例如CD25+FOXP3+T調節細胞在人自身免疫疾病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在VCA相關研究中,發現FOXP3與吲哚胺2,3-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的表達水平與VCA排斥反應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22]。IDO的表達在移植后3個月~1年最強,隨后出現FOXP3+表達增多的趨勢,表明FOXP3 mRNA水平與移植后的時間直接相關[16,23]。Jindal等[24]對接受hIL-2/Fc(一種持久的人白介素-2融合蛋白)處理的大鼠出現急性排斥反應時進行了皮膚活檢,并比較了調節基因FOXP3和效應基因GZMB、IFN-γ和Prf1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這些基因的表達情況與VCA的長期耐受情況完全相關,即在長期存活的可逆性排斥情況下具有更高的調節/效應基因比。但是,目前仍不清楚FOXP3是否可以通過未知的獨立途徑來調節免疫反應,對此尚需進一步研究。
糖皮質激素誘導的腫瘤壞死因子受體(glucocorticoid-induced tumou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GITR)是一種參與抑制調節T細胞的活性并延長T效應細胞的存活的表面分子[25]。與穩定的腎臟移植接受者以及健康人比較,穩定的手移植接受者體內GITR明顯上調[13]。與正常大鼠皮膚或同系移植物比較,大鼠同種異體移植物中白介素-18、TNF-α、CCL7、CCL17、CX3CL1、CXCL9、CXCL10和CXCL11的表達均顯著上調,表明它們參與了適應性免疫反應[26]。
3.內皮黏附分子:目前研究顯示,許多可以內皮黏附分子可以作為VCA免疫反應中的炎癥相關基因。ICAM-1可以在白介素-1和TNF誘導下由血管內皮、巨噬細胞和淋巴細胞表達,繼而激活涉及多種激酶的級聯信號轉導來產生炎癥趨化作用。E-選擇素、P-選擇素和L-選擇素可以起凝集素的作用,識別白細胞或內皮細胞表面的結構[27]。Hautz等[16]發現,在出現輕度排斥反應的手移植患者體內,黏附分子如淋巴球功能性抗原1(lymphocyte function-associated antigen 1,LFA-1)、ICAM-1、E-選擇素、P-選擇素和VE-鈣黏著蛋白的表達上調,而對于P-選擇素,其表達隨移植時間的延長而增加。此外,Win等[12]也發現,出現抗體介導的急性面部移植排斥反應的患者移植物內表達增幅最大的是內皮黏附分子ICAM-1。
四、展 望
實體器官移植的大量研究提示了外周循環中的記憶T細胞數量與急性排斥反應的發生風險密切相關。而VCA移植后,外周循環中效應記憶T細胞是淋巴細胞的主要亞群,Th2細胞是主要的T輔助細胞類型。VCA由于其自身免疫特性,與周圍循環比較,VCA移植物的皮膚中存在著數量更多的T細胞,具有更多樣的效應記憶T細胞表型和T細胞受體,以及分布有特征性的Th1表型。基因譜表達方面,排斥相關基因主要包括IFN-γ通路、CXCR3(CXCL9、CXCL10、CXCL11)與 CCR5(CCL3、CCL4、CCL5)通路的相關基因,耐受相關基因主要為FOXP3和GITR。內皮黏附分子在炎癥趨化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代表是ICAM-1、E-選擇素、P-選擇素和L-選擇素。
VCA的免疫細胞亞群的變化及相關基因譜表達的臨床研究對于理解VCA排斥反應發生的免疫機制和研究相關無創性檢查具有重要意義。外周血中細胞產物的濃度水平、免疫細胞數量與表型的改變,相關排斥、耐受調節基因譜的表達變化,可以探索機體免疫反應的狀態、預測移植后患者出現嚴重移植排斥反應的概率,研究個體對免疫治療的反應機制,選擇個性化免疫抑制方案。特別是在今后可據此開發非侵襲性的臨床檢測方式,實現在組織病理學檢查前就可提示即將發生或已經發生排斥反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