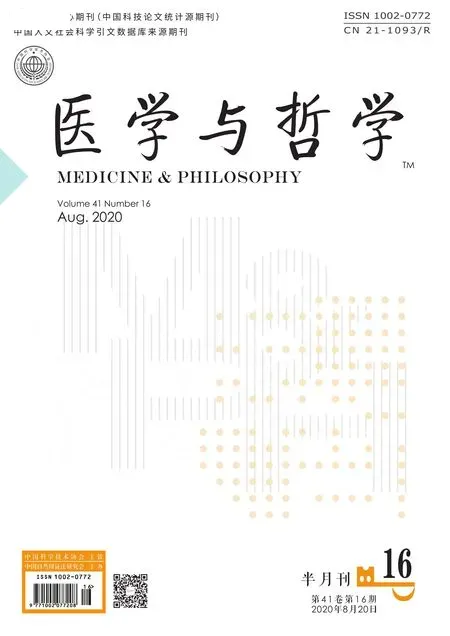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是醫學的一枝兩花*
何小菁
醫學技術至上主義,醫學萬能論,醫源性、藥源性疾病增加,醫患關系的疏離、不信任和日趨緊張,質疑醫學之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其根本原因在哪?醫學包含哪些內容?人們到底在質疑醫學什么?回答這些問題,能夠使人們更好地得到醫學的護佑,享受生命帶來的快樂。
1 醫學模式變革是醫學內在發展的顯化
醫學的發展是與其他學科不斷滲透、交叉、融合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醫學的研究內容、對象和方法不斷分化。社會進步對于醫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而又深刻的影響。由于不同社會階段人們的關注角度存在差異,或者是重視程度、認識深度的差異,人為造成了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的割裂。每一門科學都是在研究一個特定的運動形式,或是一系列相互聯系、轉化、相屬的運動形式。醫學則是隨著人類身體痛苦最初表達和減輕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誕生。筆者將人文社會醫學定義為:從人文社會學層面,研究人類身體痛苦的表達和減輕痛苦愿望的醫學;將生物技術醫學定義為:從自然科學層面,通過特定醫學技術對癥預防、診斷、治療疾患,減輕人類身體痛苦,促進康復和健康,延長生命的醫學。在這樣一種共識前提下不難發現,20世紀以來,以生物工程、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現代醫學技術,給生物技術醫學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技術至上主義”和“醫學萬能論”一度讓人們誤以為生物技術醫學可以與一切疾患抗衡,各類疾病痊愈皆有可能,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使輝煌的現代醫學遭遇了屢次三番的難題和尷尬。生物技術醫學過度重視醫療科學技術的應用,卻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客觀存在,造成了醫患關系的物化。尤其在國內,隨著醫療改革的步伐,醫療被推向了市場,醫院自負盈虧商業化的傾向,使生物技術醫學在失人格化道路上漸行漸遠。對于生物技術醫學而言,重視科學技術的應用本身無可厚非,然而技術上的一葉障目,形成了“只見疾病不見病人”的一孔之見,演變為近現代生物技術醫學的根本特征和危害之源。現代醫學發展面臨著諸多現實挑戰,醫療高新技術與社會倫理沖突,疾病譜與社會環境的共同演變,醫學與科學的交融,醫患關系的物化,醫學非人格化的傾向等[1],與健康戰略下人的高品質生活、高質量發展需求的矛盾,以及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此種種,生物技術醫學越來越無法適應現實需要。
生物醫學范式下醫學人文精神的暫時衰落成為人文社會醫學復興的歷史動因。人文社會醫學伴隨生物技術醫學的發展,20世紀中期以來,社會和醫學界認識到,由于對患者權益的重視,特別是許多新醫學技術的出現,如新診療技術、新藥物和新材料的開發與應用,現代醫學迫切需要人文社會醫學的許多知識和理念。醫學經歷了原始醫學、經驗醫學,發展到如今的現代醫學,人文社會醫學體系不斷完善,內涵不斷豐富。1975年人文社會醫學主題論文的出現[2],便表明人文社會醫學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下已經開始形成獨立體系,并開始以獨立的醫學角色走上歷史舞臺。醫學模式已經變革,但是對于醫學的認識并沒有發生深刻變革,仍停留在原來的以生物技術醫學為主導的醫學認識之中。人文社會醫學的復興并不是空穴來風,其動力來自于醫學自身發展的需求,醫療技術內部技術主義思潮和技術外部的市場經濟環境所造成的種種負面影響,需要我們重新審定醫學的內涵[3]。
2 關于醫學的分類方法
醫學分類反映的是醫學知識體系的內部結構及學科間的源流關系,學科分類一般按“母子一家”原則進行。分類應該依據所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進行。明確醫學中的具體研究內容、對象和方法是劃分醫學的根本。借鑒邏輯學屬種關系,根據學科的研究對象、知識的源流關系和實證性特點等標準,可將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組成的醫學理解為學科屬,即生物技術醫學學科種群與人文社會醫學學科種群都是由若干學科組成的學科種群。根據醫學研究內容、對象和方法的差異性,將醫學屬二分為生物技術醫學種與人文社會醫學種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1 醫學在學科分類方法中的地位
“科學分類思想不僅能從科學的整體上反映知識的本質屬性及其相互關系,同時也可清楚地顯現知識的體系結構和內在規律性。”[4]19世紀中期,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建立了以自然界基本運動形式為區分依據的知識分類方法。分類,即分類別、分門別類。分類也是以事物的本質屬性為根據,把一個屬概念劃分為若干個種概念的過程。《尚書·洪范》的“九疇”、春秋的“五行”皆是知識的分類法;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按照研究對象不同,將學科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杜威十進制分類法將學科分為10個大類,《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國家標準(GB/T 13745-2009)》將學科分為五大類;還有一些學者也根據自己獨特的視角對學科進行分類,如馮澤永將所有學科劃分為哲學、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在不同的分類體系中,醫學的歸屬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如杜威十進制分類法中,將醫學歸于醫學門類,具體包括:人體解剖學、細胞學、組織學;人體生理學;健康的推動;疾病的發生及預防;藥理學及治療學;疾病;外科學及相關醫學專科;婦科學及相關醫學專科;實驗醫學九個類別。在筆者近來收到的一份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實證研究課題組的網絡調查問卷中,其將學科分類劃分為人文類(文、史、哲、新傳、外語和藝術等)、社科類(政、法、社、信管和經管等)、理學類(物、化、生、地理和天文等)、工學類(材料、建筑、環境、社科和電子類等)、醫學類(臨床和口腔等)。
2.2 醫學發展史上的醫學分類
為了全面認識醫學、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的概念,有必要借助于分類的方法。通過醫學技術史上的標志性事件,醫學則被分為古代醫學與現代醫學。不同學者與醫學技術的結合也是可作為劃分醫學的依據。哈維(William Harvey,1578年~1657年)推翻了心臟運動和血液運動論,提出血液循環運行論,建立血液循環學說;莫干尼(Morgagni,1682年~1771年)提出疾病與器官的關系,認為每一種疾病都有和它相應的一定器官的損害;克勞德·伯爾納(Claude Bernard, 1813年~1878年)確立了生理學在醫學科學中的地位,也奠定了現代生理學和生物化學的基礎;魏爾嘯(Rudolf Virchow,1821年~1902年)將細胞學說應用于醫學,認為每一種疾病都是局部的、細胞的損害[5]。從哈維到魏爾嘯,將生物的烙印深深地鐫刻在醫學上。生理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免疫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和基因學等輝煌成就,將生物技術醫學拓展到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病原體、人類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新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眾多領域,為人類認識疾病、治療疾病、預防疾病提供了源源活泉。
醫學發展史上,對醫學的劃分還有很多種標準,如內科學(內科系統)、外科學(外科系統)是根據治療手段劃分的;診斷醫學、治療醫學和預防醫學是根據工作范圍劃分的;古代醫學、近代醫學、現代醫學等是根據時代劃分的;中國醫學(中醫學)、印度醫學、阿拉伯醫學等是根據地域、國家和民族劃分的。在此基礎之上,國內學者進一步對醫學分類進行研究。阮芳賦的三分法,將醫學分為基礎醫學、實踐醫學和理論醫學三個門類。艾剛陽的四分法,則從學科群的角度將醫學分為基礎醫學、技術醫學、應用醫學和人文醫學四個門類;賀達仁延用艾氏四分法,進一步明確基礎醫學、技術醫學、應用醫學和人文醫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并重點分析存在爭議較多的技術醫學和人文醫學的內涵。賀達仁[6]認為,艾氏醫學分類中的技術醫學實質是醫藥技術工程,但可簡稱技術醫學;并進一步指出對現有的和潛在的人文醫學學科進行分類,可以以研究對象作為劃分人文醫學與非人文醫學的標準,可以以知識源流關系為劃分人文醫學內部子學科的標準。馮澤永[7]將醫學歸入認識自然之“事實”,尋求自然規律的自然科學,他認為,醫學兼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特點,但是主要屬于自然科學。劉虹[8]利用歐拉圖將醫學主要分為生物醫學與人文醫學(注:人文社會醫學的簡稱)。以上每個醫學的分類方法,都有一定根據、有一定價值。筆者認為,依據醫學與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滲透、交叉、融合,二分為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符合分類學學理和醫學客觀事實。
3 醫學本就是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的統一體
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實質是同根相伴而生,是醫學的一枝兩花,是并蒂蓮。神靈主義醫學模式、自然哲學醫學模式、生物醫學模式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生物技術醫學范式下的生物醫學模式的產生和發展,都是一種醫學技術巨大的進步在醫學上的應用。醫學技術的進步為生物醫學模式下的醫療活動奠定了診治基礎,但是缺失了人文社會醫學的生物醫學模式,注定被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替代。如,R.H.惠特克提出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植物界、真菌界和動物界5界系統。陳世驤從真核生物進化的3條主要路線,提出非細胞總界(病毒界)、原核總界(細菌界、藍菌界)、真核總界(植物界、真菌界和動物界)6界系統。生物技術醫學模式是一種以維持動態平衡的醫學觀所形成的醫學模式,注重生物醫學方面的診治技術,在其結構內缺乏給心理的、社會的行為方面留下診治、思維空間。生物醫學模式,在人類與疾病的抗爭史上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生物技術醫學脫離“人”的整體,也給醫學思維活動造成一定消極影響。
有學者認為,人文社會醫學指的是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下,以身體哲學為基礎,著重視察人的具身感受與外在環境對人體的健康和疾病的影響,并用哲學思辨和道德、法律等社會價值觀指導醫學研究和醫學應用。劉虹與姜柏生編著的《人文醫學新論》一書中指出,人文(社會)醫學是以醫學人文精神和醫學人文關懷為研究對象,涉及醫學價值世界和身體感受性的醫學分支學科,是當代醫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還進一步指出,人文(社會)醫學包含學科與學科群兩層含義;當將人文(社會)醫學作為獨立學科理解時,其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進路是相對獨立的,主要研究人文社會醫學的一般性問題,具有總論性質;當將人文(社會)醫學作為學科群理解時,它可以由醫學倫理學、醫學哲學、醫學法學、醫學史等若干種學科組成,是從各個種學科的專業視角研究醫學場域中專業性問題的一個學科種。人文社會醫學的學科種中,人文精神是第一屬性,貫穿始終。“以身體哲學”為基礎的人文(社會)醫學,通過弘揚人文精神,解決醫學目的異化問題,使生物醫學能夠回歸,進而還原醫學本來面目[9]。發展人文社會醫學,可以補全生物技術醫學短板,賦予醫學應有之義,完善醫學認識。生物醫學模式轉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是醫學內生動力驅動的,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相輔相成、水乳交融,方能使醫學在護佑生命健康的歷程中相映生輝。
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看待疾病的角度大相徑庭。魏爾嘯斷言一切疾病都只是局部的、細胞的。于光遠[10]認為疾病的起因與心理、情緒、環境和社會因素緊密相關,“醫學本質上是社會科學”歷歷在目,西格里斯(H.E.Sigerist,1892年~1957年)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是使人成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醫學本質上是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系。”[11]醫學不只是生物技術醫學的舞臺,生物技術醫學健康發展離不開人文社會醫學的滋潤,兩者雙向交叉融合。雖然有學者認為人文社會醫學是一門年輕的醫學學科。醫學是研究身體的學科,人文社會醫學說到底是研究醫學與身體關系的學科。生物技術醫學追求醫學技術的進步,將疾病打敗、扼殺;人文社會醫學則追求安撫病患的情緒,讓病患得以寧靜,最終獲得人性解放。醫學需要將人文社會醫學的內容滲透至生物技術醫學之中,兩者合二為一,使人能夠“認識自己”。
醫學從來都不排斥、不忽視生物技術醫學的作用,強調生物技術醫學要關注人文社會醫學。例如,從心理學研究心理因素與腫瘤、心血管疾病的相關性;從社會學研究發現,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對健康與疾病影響總是要以人體生物的結構和(或)機能為中介、為表現形式的。把生物技術性研究和人文社會性研究對立起來,不是生物技術醫學的真諦。因此,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之間普遍聯系、相互交錯、永恒發展,在醫學內部兩者對立統一,是醫學的一體兩翼,人文社會醫學并不與生物技術醫學的重大顯性作用相抵觸。
4 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的辯證關系
4.1 兩者的元哲學都是身體哲學
身體,是人類生命、生存、生活之本;“近取己身,遠取諸物”,身體是一切認識之源;關于身體的學說,是一切理論的本源。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克里克這樣描述:DNA制造RNA,RNA又制造蛋白質,這就是作為一個物質系統的身體的由來。醫學乃身體之學,身體學說,是醫學的基礎理論。生物技術醫學研究的身體,是“自在的身體”,即自然演進的、不受主觀因素左右的、生物性的組織、結構、功能、心理、思維的多維統一體。生物技術醫學研究的內容是身體的自然屬性和生物屬性。身體是一切存在的基本條件,生物技術醫學身體學說因此成為身體理論大廈的奠基石。人文社會醫學理論基于生物技術醫學理論,又高于生物技術醫學理論。生物技術醫學身體學說理論也是人文社會醫學的基礎。作為醫學的分支,生物技術醫學關于身體的研究成果,毫無疑問是人文社會醫學的理論基礎之一。身體不僅是軀體的存在,更是心理和精神的存在。建立在人文社會學基礎之上的人文社會醫學,能夠更為透徹地開展關于身體感受和行為的研究,更為準確地研究醫學人文精神的實質和醫學人文關懷的實施。關注身體的感受,傾聽身體的呼聲是人文社會醫學的本真和使命,在這個意義上而言,關注身體和身體感受的身體哲學對人文社會醫學最具有親和力,也適合作為人文社會醫學之元哲學。
4.2 兩者的核心精神各有側重
人生關懷包括物質關懷、精神關懷和終極關懷。醫學服務于生命,生物技術醫學的物質關懷與人文社會醫學的精神關懷,共奏保羅·蒂里希倡導的“生命終極關懷”華章。生物技術醫學通過遵循客觀規律,懷疑、批判,嚴謹探索,追求真理,創新醫學技術手段,防病治病,維護人類健康。科學精神是生物技術醫學的核心精神。生物技術醫學從經驗醫學,到實驗醫學,再到技術醫學,創造了相對成熟的知識體系,同時也不斷探索出一條務實、創新、批判與奉獻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是人們探索生命奧秘并造福人類的原動力,已經成為人類價值取向所崇尚的楷模[12]。基于物質關懷的人文精神關懷,是人文社會醫學基于人的社會本質出發的一力量。人文精神是人文社會醫學的核心精神。深入研究醫學人文精神,是人文社會醫學理論研究之綱,也是人文社會醫學的歷史使命。生物技術醫學以求真求精,人文社會醫學以求善求美,前者以科學精神為導向,后者以人文精神為導向;前者以軀體為研究對象,后者以身體為研究對象。沒有人文精神的身體只是軀體,沒有人文精神的醫生只是醫匠,沒有人文精神的醫學純粹是生物技術醫學。缺乏形而上的精神關懷,醫學關懷終將無法走向終極。醫學的人文精神是身體靈動之流,涌動于身體中,生物技術醫學的物質關懷與人文社會醫學的人文關懷交織,是醫學關懷從基點走向終極運行的軌跡[13]。
4.3 兩者相互交融體現醫學歸屬
精益求精是生物技術醫學的追求,而醫學人文關懷則是人文社會醫學的終極歸屬。重硬件輕軟件的技術決定論、崇洋媚外的技術崇拜論,導致的技術和學術商品化、技術庸俗化、醫德醫風滑坡等去人格化現象,這些都不應是生物技術醫學的屬性。求真、求精、嚴謹、務實、創新、奉獻、批判,追求醫學科學的真善美的統一,才是生物技術醫學科學精神的真實體現。“醫乃仁術”,“醫學是藝術”。醫學的價值,最終要在生物技術醫學之中體現醫學人文關懷,實現醫學人性化的終極關懷。醫學人文關懷是醫學人文本質可見端、可感態、可觸面;人文精神通過醫學人文關懷得以落實之時,就是醫學人文精神的花朵絢爛于醫學園地之日。醫學人文關懷涉及到醫學診療、醫學技術和醫學服務等生物技術醫學的各個活動環節、各個方面。人文社會醫學與身體結緣,就無法與人文精神無涉,生離死別、死守放棄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都需要人文社會醫學的精神關懷。
4.4 兩者的學科差異
學科的問題是學科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全部基礎、核心與實質所在。生物技術醫學研究對象既包括認識人體及生命現象、相關因素的本質與規律的學科種群,還包括研究解決各種醫學問題的物化技術的學科種群,還包括維護和促進人類健康、預防和治療疾病,使機體康復的學科種群。人文社會醫學研究對象是以追問醫學世界的價值為使命,從總體研究醫學之善、醫學之美、醫學之圣、醫學之愛、醫學平等、醫學和諧等醫學價值形態,澄清醫學的大是大非問題,從局部研究人的健康需求、情緒表達、身體感受、醫學人文關懷、醫學人文信仰。賀達仁以知識源流關系作為人文社會醫學內部子學科的劃界標準,人文社會醫學學科種群包括:醫學文化類、醫學史類、醫學哲學類、醫學管理與醫學經濟類、醫學倫理與醫學法學類和醫學社會類六個門類。劉虹從學科研究對象、內容、方法等方面,尤其是研究視角和學術位置方面,認為人文醫學學科種群主要包括醫學倫理學、衛生法學、醫患溝通學、醫學哲學、醫學史五個學科。筆者認為,如果將生物技術醫學理解為物化世界,那么人文社會醫學則可理解為文化世界,且具有深刻哲學思想性質和屬性。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宛如太極陰陽魚圖中的兩條魚,一陽一陰。醫學負陰抱陽,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相互交融、共生發展,因此,兩者在學科屬種方面,既有涇渭分明的學科種群差異,也存在相互交叉的學科種群融合。如基礎醫學中研究具體醫務人員的心理學則應屬于人文社會醫學范疇,因為這些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醫學的主體。又如醫學倫理學應屬于人文社會醫學學科種群,而生命倫理學則應屬于生物技術醫學種群。生物技術醫學學科種的研究方法重測量、在精準,人文社會醫學學科種的研究方法重思想、在質性。
5 結語
醫學現象本質是一種人文社會實踐。在醫學發展史中,曾經由于科學技術進步的易顯性,使人們過度倚重技術,反而偏離了人文社會屬性,一度使人們認為生物技術醫學就是醫學全部,向技術索要一切健康要素。雖然人們對醫學的認識產生了偏差,但是醫學中人文的特性一直存在,并且生物技術醫學終究是要和人文社會醫學齊頭并進的,方顯醫學本色。
人文社會醫學作為醫學屬一門獨立的學科種,是伴隨生物技術醫學的實踐產生,并且不斷強大起來的,其作用也越來越明顯,是形而上的醫學,是生物技術醫學學科種的并行醫學種類。脫離生物技術醫學的人文社會醫學是不具有銳度的,沒有人文社會醫學伴行的生物技術醫學也是缺乏溫度的。人文社會醫學與生物技術醫學是醫學的陰陽兩體,沖氣以為和,兩者相互促進,方能體現醫學真正內涵與要義。生物技術醫學與人文社會醫學本質上并沒有沖突,也不應該產生沖突,無論是生物技術醫學的工作者,還是人文社會醫學的實踐者,只有共同努力,在醫學中將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并行,實施人文關懷,真正做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融貫,才能彰顯醫學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