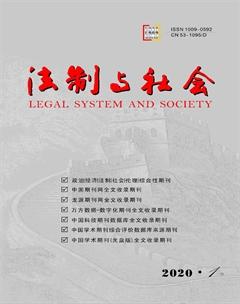淺析死刑不引渡原則與國家主權
關鍵詞 死刑不引渡原則 國家主權 司法管轄權
作者簡介:湯浩圩,澳門科技大學。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1.219
一、死刑不引渡原則概述
引渡是主權國家在追訴外逃犯過程中,解決因法域不同而產生的國內訴訟法律管轄障礙的國際司法合作形式,是有效行使司法管轄權的法律制度保障,目標是遏制跨國犯罪。持續探索建構死刑與引渡的“制度橋梁”能夠使死刑不引渡發揮在公民權利保障中的“安全閥門”功能 。隨著我國針對貪污賄賂罪在內的經濟犯罪的防治進入新階段,大量涉案金額巨大并且涉嫌其他特別嚴重犯罪的嫌疑人紛紛潛逃至境外,利用所在地奉行的死刑不引渡原則挑戰我國司法權威,從程序法上阻礙我國法院的外逃人員引渡工作。
死刑不引渡是被請求國有理由相信在接受引渡之后,被引渡人可能被請求國法院判處死刑時拒絕接受引渡請求的原則。 除非請求國向被請求國作出對被引渡人不適用死刑的保證,否則被請求國將不予引渡,該原則所涉及的對象包括宣告刑為死刑的罪犯。國家主權原則是引渡制度的基石,引渡由當事國協商決定,是國家間的約定而非法定義務。在國家間尚未訂立引渡條約的情況下,為避免本國司法管轄權受到損害,多數國家拒絕承認他國法律的域外效力。基于屬人管轄原則,請求國對不在本國領域內的公民主張管轄是主權國家應當享有的權利。但被請求國根據屬地管轄,在收到引渡請求后不會立即作出交付決定。根據“生命尊嚴”的法理精神,西方法學界產生了死刑存廢議題的爭論。伴隨“生命權保障運動”的興起,死刑不引渡適用的伸縮彈性正在降低,由特殊規則上升為普遍原則,甚至“堅硬到了不容妥協和商量的程度” 。隨著公民權利保障在引渡條款內容中的具體化,促使公民權利保護成為死刑與引渡制度連接的樞紐。
二、死刑不引渡對國家主權的影響
“只要國際法是主權國家間的法律,就不會有合適的刑法體系” 。各國法律體系的沖突使死刑不引渡成為外逃犯逃避刑事責任追究和刑罰懲處的“擋箭牌”。瑞士《聯邦國際刑事協助法》明確規定:“如果請求國不承諾將不在請求國境內對被追究人處以死刑,或被追究人將會受到有損其人格尊嚴的待遇,應當拒絕引渡”。聯合國《引渡示范公約》第4條“拒絕引渡之任擇性事由”亦規定了該原則的適用。但“只有在廢除死刑后方可引入死刑不引渡”的主張阻礙了我國拓展引渡合作的空間。本文支持“即便是不贊成立即廢除死刑的國家,也可以為引渡合作附加條件,或承認合作伙伴所提出的類似條件” 的見解。
“沒有哪個國家會接受他國對本國司法事務的管轄” ,量刑承諾對司法管轄權構成了挑戰。請求國若將嫌疑人成功引渡歸案,需要被動接受被請求國拒絕死刑判決的量刑承諾。而外國法院對我國法院判決的審查,弱化了法院運用刑罰權懲治犯罪的職能,在形式上是對我國審判權的干涉。但請求國法院在刑法允許的解釋范圍內合理讓渡一定程度的利益,接受對方提出附加條件,使嫌疑人接受我國法律管轄以實現成功引渡的目的。對被請求國而言,量刑承諾同樣意味著放棄司法管轄權。在請求國作出量刑承諾的情況下,被請求國仍有權拒絕引渡。
國際法秩序的出發點在于國家主權原則 。有學者為避免因法律沖突而產生罪責刑不相適應,主張不應當接受任何形式的量刑承諾。本文認為,在我國拒絕附條件引渡,而被請求國堅持將死刑作為拒絕引渡的強制性理由時,我國司法機關將犯罪分子緝拿歸案、追繳贓款的目標將落空,罪刑法定精神更無從談起。因犯罪分子無法依我國法律接受起訴和審判,是對我國司法權威的現實挑戰。如“余振東案”正是基于其本人與美方進行“辯訴交易承諾”以及我國司法機關與美方達成的量刑協議,才成功將余振東引渡回國,并依我國刑法對其定罪處罰。
三、死刑不引渡的立法適用研析
《引渡法》對死刑不引渡的適用暫采回避立場,第8條規定了絕對不引渡情形,即被請求引渡人在請求國曾經遭受或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應當拒絕引渡。有學者則認為“酷刑”應包含生命刑,而死刑與“酷刑”的界限卻十分明確。我國簽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規定了“酷刑”的概念,排除了“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的疼痛、痛苦以及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隨的疼痛、痛苦”。“酷刑”即法外用法,體現為司法工作人員為恐嚇威脅涉案人員而實施的徇私枉法行為,《引渡法》并未明確該原則。另據《引渡法》第50條規定:“被請求國就準予引渡附加條件的,對于不損害中國主權、國家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代表中國政府向被請求國作出承諾;對于限制追溯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于量刑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因而《引渡法》還是十分有限的接受了死刑不引渡原則 ,將其作為間接適用死刑不引渡原則的法律依據。
四、立法和司法制度完善建議
(一)提供國內法依據
“我國立法不應繼續回避死刑不引渡問題,而應使該原則在《引渡法》中占有一席之地” 。俄羅斯作為暫時保留死刑制度的國家,在國內法中明確了該原則之后,其司法適用與國內法律制度并未產生實質沖突。在沒有明確法律依據的條件下,在實踐中易使條約所產生的法律效力高于國內法。因此,引渡條約與國內法之間的沖突,促使我國將條約的適用規則轉化為國內法律規定,在《引渡法》中對量刑承諾制度作出明細規定。通過變通適用死刑不引渡條款,為該原則的適用提供國內法依據。德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將“有條件的部分立法模式”保留在了引渡合作中。鑒于此,我國《引渡法》亦可增加一款,將“可能判處死刑”的犯罪規定為“有條件拒絕引渡”的情形,正式確立死刑不引渡原則。使《引渡法》第8條與第50條的內容更加明確化。
(二)推動死刑改革
絕對死刑條款對懲治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是必要的,但頻繁的量刑承諾易弱化請求國司法主權的安定性。因而我國應堅持刑法謙抑性和罪刑均衡原則,穩妥推進非暴力犯罪死刑改革,嘗試終身監禁措施作為嚴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替代措施,限制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執行。“終身監禁是控制和預防犯罪的強有力措施,潛在犯罪人想到犯罪后果可能使自己進入漫長煎熬的與世隔絕環境中,這比起撲朔迷離的死亡更具威懾力” 。基于刑事古典學派提出的“同害相侵”報應理論,應持續降低經濟犯罪的死刑配置數目。依據《刑修案(九)》,終身監禁措施完善了死緩制度,使終身監禁開始成為替代相當數量生命刑的死緩變通行刑方式。應設置終身監禁制度的矯正途徑,改革非暴力犯罪刑罰結構,升格死緩判決標準,延展自由刑期限。完善附加刑種類,發揮資格刑與財產刑協調并配效能。
(三)健全缺席審判制度
通過缺席審判制度,能夠明確外逃人員刑事責任,敦促其盡速歸案,提升訴訟效率,構建追逃追贓的嚴密法網。使奉行“條約前置主義”的國家通過裁判文書積極配合引渡。堅持最低訴訟保障標準,使在逃被告人知曉訴訟情況確定為啟動缺席審判程序的前提條件。全面評估向在逃被告人送達傳喚的客觀困難,針對查無下落的外逃犯檢察機關則無必要提起公訴。立法應完善量刑承諾與重新審理程序的規定,前移辯護律師指派程序,便于通過辯護人向被告人傳達訴訟通知。對明確接受“勸返”,自愿回國伏法的已受到缺席審判判決的罪犯,在法院重新審理過程中依然可以適用《刑法》關于立功和自首的規定 。
(四)堅持附條件引渡模式
將被引渡人緝拿歸案接受我國法院審判是保障司法主權的前提。在附條件引渡合作中,絕對拒絕是被引渡人已經被請求國判處死刑,而被請求國拒絕引渡的情況。部分拒絕是絕對不引渡的變通適用,即附條件引渡。變通的量刑承諾具有較強的靈活適用性,對符合量刑承諾減輕刑罰條件的,我國法院應在法定最高刑期以下處罰 。《刑法》第63條規定了罪犯雖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但依案件特殊情況,經最高法核準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因而量刑承諾可以適用于特殊案件情況。采取附條件引渡方式,能夠避免直接引入死刑不引渡原則,將死刑與引渡制度有機結合,在條約協商中提升引渡合作的靈活性,使被請求國更容易接受。可行模式例如:一是使用相對籠統模糊的措辭,避免直接表述;二是在正式條文中作籠統規定,在會談紀要中附加說明,而不在條約中對死刑不引渡原則作直接表述 。最后,應積極面向加拿大等外逃犯主要潛逃目的地國家拓展引渡合作。針對美國與荷蘭等奉行“條約前置主義”且未與我國簽訂雙邊引渡條約的國家,可以建議其允許將多邊公約或者個案協議作為引渡合作的依據。
(五)健全外逃犯移交制度
引渡不再被認為僅僅是體現“國際禮讓”的法律程序,而更多被視為合作條約成員國相互承認司法判決的法律程序。使成員國更加尊重由合作伙伴發出的具有法律強制力的司法文件,即針對涉嫌嚴重犯罪逃犯的逮捕令 ,逮捕令制度能夠強化引渡審查的司法性。在歐洲逮捕令制度中,執行國若認為在本國執行刑罰更有助于被請求人在被判處刑罰后重返社會,且被請求人同意在執行國執行由簽發國作出的判決,可以不予移交。我國應考慮建構相互承認判決的司法制度,建構中國特色區際逮捕令制度。被請求國則可直接依據我國簽發的逮捕令拘捕被請求引渡人,經過簡捷的司法審查之后即可將其移交予我國。被請求國不再重新簽發逮捕令,僅以簽注形式對我國簽發的逮捕令予以承認,以提高引渡合作的效率。
五、結語
死刑不引渡原則逐漸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遵循的剛性司法合作規則。因外逃犯無法被依法遣送歸案,挑戰了我國刑法的規制功能和秩序維持功能。推動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制度改革,完善引渡法律制度。廣泛拓展引渡條約關系,更深入的參與國際引渡合作,探尋引渡合作規則的完善路徑,切實捍衛我國司法主權。
注釋:
張旭.國際刑法論要[M] .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241.
王水明.死刑不引渡原則與國家主權[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1(8).
黃風.引渡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24
[希臘]尼古拉斯·波利蒂斯著.國際法的新趨勢[M].原江,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7.
黃風.中國引渡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14.
趙永琛.國際刑法與司法協助[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189.
周鯁生.國際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77.
劉亞軍.引渡新論——以國際法為視角[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245.
趙秉志.死刑不引渡原則探討——以中國的有關立法與實務為主要視角[J].政治與法律,2005(1).
[意]貝卡利亞著.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6-68.
黃鳳.對外逃人員缺席審判需注意的法律問題[J].法治研究,2018(4).
陳雷,薜振環.論我國引渡制度的量刑承諾[J].法學雜志,2010(1).
張旭.死刑與引渡-源自人權保護的思考[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2).
黃鳳.國際引渡合作規則的新發展[J].比較法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