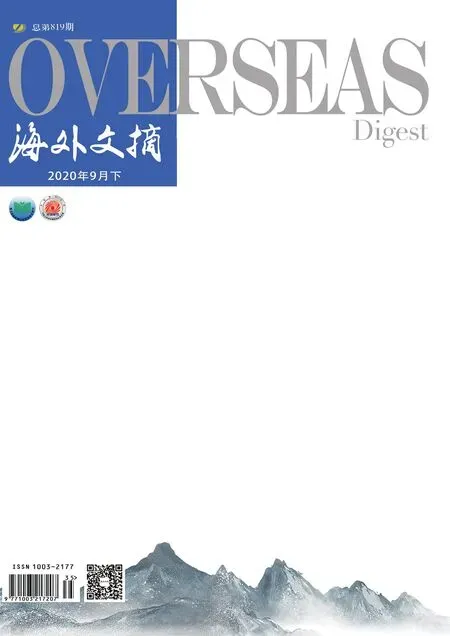過程名物化的西漢翻譯
——以小說《蜘蛛女之吻》為例
楊芊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 100089)
1 研究背景
1.1 名物化——語法隱喻的一種
“名物化”或“名詞化”是“語法隱喻”的一種。韓禮德(1895)在《功能語法導論》中提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由音系層、詞匯語法層和話語意義層組成[1]。詞匯語法層是話語意義層的體現,主要通過“一致式”和“隱喻式”兩種方式傳達。一致式指“詞匯語法層表達的表層意義和話語意義層所表達的深層意義彼此相同”[2],如例句(1a);而(1b)使用名詞表示事件,屬于隱喻式中的“過程名物化”。
(1a)They constructed the bank.
(1b)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nk.
韓禮德對名物化的研究主要基于英語,但其它語言中同樣存在該現象:
(2)La aparición de lasmáquinas.
與一致式相比,名物化語句呈現高度書面化、概括化的特點[3],詞匯豐富程度更高,并具有模糊動作發出者和發出時間等功能。在下一章節中,筆者將結合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析以上特點的具體運用。
1.2 名物化現象的漢語翻譯
學界對名物化漢譯的討論主要基于英漢翻譯,涉及文體主要為新聞、科技和法律領域。例如,法律文本中的名物化可濃縮邏輯關系,在翻譯時應使用漢語分句進行分解。此外,名物化有主位述位銜接、詞匯銜接的雙重性,并對這一性質下的科技類文本翻譯進行了分析。由于名物化可省略事件施動者,將動作過程轉變為概念,因此被認為具有操縱意識形態的作用。
在文學領域,對名物化的討論集中在歸化和異化兩種思想,對名物化在作品中起到的藝術效果、思想表達涉及較少。而在本文即將討論的小說《蜘蛛女之吻》,名物化手法對其審美、敘述構架起到關鍵作用。因此,筆者希望從作品的語言風格、敘事技法等方面分析名物化的作用,探尋名物化的翻譯策略。
2《蜘蛛女之吻》作品介紹
2.1 內容簡介
《蜘蛛女之吻》(El beso de la mujer ara?a)是阿根廷作家普伊格(Manuel Puig)的代表作,屬于典型的拉美“后文學爆炸時期”作品。小說以兩位主人公在獄中的對話和自白為線索,講述了其牢獄生活和情感變化。從結構上看,小說各元素被簡化到極致,即一個空間場所、兩個人物[4];然而,作者以談話和獨白為載體,融匯了多元文化和社會群像,這正是該時期作品的特色。例如,在談話過程中,一位主人公講述了曾看過的電影;作者將其內心活動穿插在講述中,并用斜體將標注出來:
-Patrulla policial, escondite, gases lacrimógenos, la puerta se abre, puntas de metralletas, sangre negra de asfixia sube a las bocas.Seguí, ?por qué parás?
這些內心活動表現了人物在敘述時的聯想,以意識流的方式刻畫出其潛意識。實際上,整篇小說正是通過人物內心來表現外界壓迫下人類的心理變異和情感訴求[5]。在例句中我們看到,對內心活動和人物對話的描寫有很大的風格差異:后者是隨意的日常口語,前者則普遍省略動詞、關聯詞,主要是名詞性成分的羅列,大量運用名物化表達。這一特點在小說第五章尤為明顯。此處集中描寫了主角對一部電影的回憶,以跳躍、破碎的主觀回想展開。
(3a)Despedida del ciego, entrada de la chica, fea, a la casita. Carta de recomendación para la solterona, trato para quedarse allí de sirvienta, explicación de la solterona, anuncio de la inminente llegada de los inquilinos. 和盲人道別后,丑女孩便走進房子里。她拿出推薦信給老處女看,說了不少客氣話,想留下來當女仆。老處女對她作了一番說明后宣稱,不久就要來房客了。
(3b) ……supervisión de la limpieza a cargo de la solterona, gesto de mujer muy mala, el arrepentimiento después de cada reto debido a la técnica imperfecta de limpieza de la sirvientita.老處女對清潔衛生工作進行監督。她一臉兇相,由于年輕女仆在打掃衛生時弄得不干凈,她大發怒火。嗣后又后悔了。
(3c)Estallido de la guerraen 1914, muerte del novioen el frente.一九一四年爆發了戰爭,未婚夫在前線戰死。
2.2 名物化在作品中的效果
筆者認為,小說作者連續、大量使用名物化手段,有其特殊意圖。要選擇正確的翻譯策略,須先分析它為小說帶來的藝術效果。
2.2.1 模糊動作時態
由例句可知,作者普遍在動名詞后用短語“de+s.”補充了動作發出者,如(3a);即使個別地方未標明,也可通過上下文識別。因此,作者并非使用名物化隱藏事件施動者。
例句描述的一系列動作發生在過去并已完結,在西語中對應的時態為簡單過去時。連續使用該時態可模擬事件接連發生的情形,營造強烈的時間行進感;筆者認為,小說作者正是通過名物化手段,隱去動詞的時態、體貌,以此模糊動作發生時間。湯普森指出,過程名物化不受時空關系限制。句中動名詞僅限于指出事件內容,沒有時間概念或行進感。這一點與作品的敘事意圖相吻合:作者并非要還原電影情節的時空構架,而是通過人物對電影的回憶展現他的內心世界。
2.2.2 模仿電影表現手法;豐富小說敘事維度
《蜘蛛女之吻》運用了影視藝術中的“蒙太奇”手法,將發生在不同時空的事件相互拼接。筆者認為,作者利用名物化形式簡單、信息密度大、動態程度低的特點,以動名詞的堆疊模仿影視中多個場景的切換。此外,使用動名詞、把動作過程當作固定概念來描述,文章可能暗示此處的敘述已被說話人加工重組,含有其主觀理解和視角。對電影的講述,實際上是對人物性格、心理的展現。這種僅由名詞構成的、破碎的敘述語言,又與小說人物間的對話口語體形成明顯差別,兩者分別構造出人物內心和外在世界這兩種維度,拓寬了小說的敘述格局。
總結來說,《蜘蛛女之吻》中的名物化對小說的藝術表現形式、內容主旨建構起到重要作用;如何翻譯這些名物化表達直接關乎小說內涵能否被正確傳達。
3 屠譯本對名物化現象的處理
由例句翻譯可知,屠孟超的譯本幾乎沒有保留名物化,而是通過動詞化將名詞性結構還原為一致式表達,用主謂、述賓結構來描述事件的過程。
3.1 符合中文表達習慣
從譯語風格的角度講,屠譯符合中文表達習慣。由于原文中的動名詞后幾乎都帶有介詞結構“de+s.”,如果保留名物化,那么譯文將大量出現由助詞“的”連接的偏正短語,如(3c)會被譯為“戰爭的爆發”“未婚夫在前線的戰死”。賀陽[6]認為這種“N 的V”結構屬于漢語的歐化表達,而對過程名物化的直譯正是該表達產生的重要原因。劉丹青[7]指出,漢語是動詞型語言,其中謂語動詞的“強制性范疇(如變位、變格、時態變化)”較少,因此漢語傾向于使用動詞性成分。
盡管如此,名物化現象在漢語中屢見不鮮,如要保留也未必不可取。然而,原文中的某些名物化表達很難直譯到漢語:一些動名詞前有多重定語,有的定語中甚至又包含了名物化。例如,(3b)轉化為偏正短語會被譯為:“每次女仆用不精湛的技術打掃清潔后她的后悔”“房客的即將到來的通知”,嚴重影響譯語的流暢和清晰程度。
在原文中,作者幾乎全篇使用名詞性成分,風格整齊、統一。筆者認為譯文也應當保留這一語言特點,并贊同屠譯中將原文全部動詞化的策略。如果名物化表達部分直譯、部分動詞化,會導致譯文句式不一;保留下的名物化還可能被誤認為是句子成分殘缺。
3.2 未傳達原作藝術效果
在藝術效果方面,筆者認為屠譯稍有欠缺。在對原文進行動詞化處理時,譯者添加了一系列詞匯,主要包括助詞“了”、方位詞“后”、量詞“不少”“一番”等和副詞“便”。添加這些詞匯對譯文可能造成兩方面影響:
3.2.1 時間、細節被強化
與原文相比,譯文的時間概念增強。以(3a)的譯文為例,方位詞“后”明確指出“道別”和“走進房子”這兩個事件的先后順序,而副詞“便”體現出前后兩者接連發生,銜接緊密。正如前文所說,此處敘述采用意識流寫法,主要用于體現人物對電影的回味,并非重現電影的情節;若強調時間先后,反而弱化了此文段的敘事意圖和藝術特色。
此外,譯者添加的量詞在原文中并無根據,如(3a)中的“不少”。該類詞從數量上對文中的事件進行了細節描寫,這與原文高度概括、點到為止的描寫不符,且可能給讀者造成誤導。
3.2.2 語言風格隨意、松散
在添加上述詞匯后,譯文語言失去了凝練緊湊的特點。例如(3a)中,譯者加入助詞“了”、量詞“一番”、方位詞“后”和副詞“就要”等修飾語,使語句變得口語、隨意。語法隱喻具有形式簡單、語義復雜的書面化語言特點;屠譯的處理方式使譯文與原文風格不符。此外,譯語隨意化導致上述例句與小說中人物對話的語言風格趨近。如前文所說,文中兩位人物的日常對話和內心活動是這部作品敘事構建的兩個維度;兩者語言的趨近磨滅了這不同維度的界限,且無法表現作者對“蒙太奇”手法的運用。
4 針對屠譯的翻譯策略建議
結合上一節中的論述,筆者認為將動名詞全部動詞化的處理是必要的,但應避免添加原文中未包含的修飾語,根據這一原則,筆者為(3a)作出試譯:
(3a)道別盲人,丑女孩進屋。給老處女看推薦信,商量留下來當女仆。老處女向她解釋,告知房客馬上到來。
筆者認為,此策略能夠保留原作中跳躍、無銜接的敘述,一定程度上模仿了意識流手法。去掉修飾語后,各小句趨近于短語,與原文中名詞羅列的特點相近,從而與人物對話的口語體區別開。最后,這種不帶助詞及語氣詞的敘述方式常用于劇本旁白,可讓讀者聯想到影視中的鏡頭切換,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蒙太奇”手法。
5 結語
小說《蜘蛛女之吻》大量使用名物化,通過動名詞的堆疊展現主人公的所思所想。名物化的使用模糊了小說敘事的時間概念,以跳躍朦朧的語言展現了人物心理,是意識流和“蒙太奇”手法的重要實現途徑。此外,作者在敘述人物心理時密集使用名物化,在記敘人物對話時采用口語體。二者相互輝映,為小說構建了豐富的敘事維度。

筆者認為,譯者屠孟超普遍去名物化策略,保證了譯文的通順和自然,未能傳遞出原文藝術效果。其中原因可能為:譯者在去名物化后添加了大量助詞、量詞、方位詞和副詞,強化了事件的時間和細節。另一方面,這些詞匯導致譯文書面化程度降低;譯作中人物心理和對話描寫在語言風格上差別減弱,作者的藝術手法和敘事特色別削弱。針對這一問題,筆者提出了翻譯策略:進行動詞化處理,但避免添加無法在原文中體現的修飾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