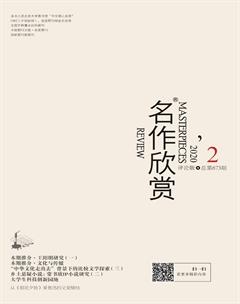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策略
摘 要: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電影作為“影以載道”的文化輸出的主要陣地,以傳播主流價值觀,傳播中華文化,彰顯當代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姿態為祖國獻禮。主旋律電影更多地承擔了國家的歷史影像記錄和表達的功能,在其發展過程中越來越注重類型化的探索,同時也開始考慮電影市場對其的影響。2019年的國慶檔期影片《我和我的祖國》 以平民視角的選擇、個性化的敘事風格策略,為主旋律電影的探索之路指出了新的方向。
關鍵詞:主旋律 平民視角 敘事
鄧小平同志將主旋律電影概括為“一切宣傳真善美的電影都是主旋律電影”,在電影市場多元發展的今天,主旋律電影更進一步表現為體現官方意識形態導向的電影。早期的主旋律電影多為表現“革命斗爭”主題,塑造英雄形象為主,如《智取威虎山》 《紅色娘子軍》 等,有極大的斗爭色彩,結合歷史戰爭承先啟后地喚醒人民的記憶,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1978年之后,主旋律電影呈現多元化的創作樣態,題材多樣,百花齊放。主旋律電影的時代性凸顯,類型多樣化,從以戰爭片、歷史片為主,加入了喜劇、愛情片等類型。但主旋律電影多元化發展的背后,觀眾對于大多數主旋律影片出現了觀影距離,這種距離既存在歷史時間線的距離,同時也不乏高、大、全形象的不可觸及之感,觀眾在觀影時的震撼感轉瞬即逝,得不到感同身受的情感認同。時間線跨度越大這種感知力就越弱,這也是不同年齡的觀眾對于主旋律電影的評論呈兩級化的重要原因。近年來,主旋律電影的探索之路雖艱辛,但也的確驚喜不斷。《建國大業》 《建黨偉業》 《建軍大業》 三部曲,以歷史史實為內容,精良考究的制作,眾多明星參與出演的方式,獲得了口碑和票房雙豐收。2016年根據真實事件湄公河慘案改編的電影《湄公河行動》 從跨國拍攝、激戰爆破的場面、集體形象塑造等方面打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一貫單一刻板的敘事形態,為主旋律電影注入了新鮮血液。此后,吳京導演的《戰狼2》 以破釜沉舟之勢登頂主旋律電影商業大片的榜首。之后的《紅海行動》等影片更是將主旋律電影推上了電影市場的浪尖。主旋律電影在收獲一定的成功之時,也應當注意到依然存在的問題:宏大的敘事難以深度走入觀眾內心,高大的英雄形象塑造使得在人物主體上難以尋找到突破口,雖然在情感表達、喜劇元素、群像塑造等方面轉變思路,但仍存在忽略真實性、刻意夸大化呈現等問題。2019年中國電影人以主旋律電影為祖國獻禮,《我和我的祖國》則以平民視角喚醒集體記憶的敘事方式讓主旋律電影真正走入觀眾內心。
一、平民視角的敘事選擇
《我和我的祖國》 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制片人,由陳凱歌、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 文牧野等七位導演共同講述新中國七十年的風雨征程,以“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 為拍攝方針,以關鍵歷史時刻的時間線索敘述,講述了七個“你我他”記憶中的片段節點,以七個獨立的篇章故事喚醒人們的民族記憶。《我和我的祖國》突破了主旋律電影以往的創作方式,以普通人與祖國大事件息息相關的經歷作為大時代下的真摯寫照,融入新中國重大歷史事件于人性最普通卻又最閃耀的時刻,這種平民敘事視角的選擇本身就自帶一種寫實的功能,更能觀照人心,喚醒真實的記憶。宏觀視角轉向微觀表達的方式,在不同導演的個性化表達和細節刻畫下顯得更具貼近性,更富感染力。打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的宏觀敘事,將鏡頭投射到普通人的生活環境中,七個故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通過普通人個性化和細節化的情感認知,實現了全國人民的情感認同。
二、平民視角下的私人記憶
看似私人化的記憶呈現,多了一種私影像的意味,但卻毫不刻意地表達了每一個中國人命運共同聯系的情感。私人化情感的顯現、普通人物的放大化渲染、每一段歷史進程里潛藏著的偶然性和曲折性,電影在書寫歷史的同時讓觀眾感受到裹挾其中的強大感染力。張一白導演的《相遇》,講述的是1964年10月16日中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故事。張一白之前參與的電影多為純粹的愛情故事,這種風格在主旋律電影當中并不多見,張一白以其擅長把握的情感力量為創作重心,從細微處體察一對戀人在“研制原子彈時期”的久別重逢,時代背景下,愛情在高遠身上被縮小,在方敏身上被放大,二人的愛情又在人群的熱情中,歷史的見證下,達到一種理解和成全。這樣既表現了二人的私人情感記憶,又有了較好的集體情感呼應,這種精神情感是那個年代能夠理解的愛情,也是那個時代下科研工作者共同的精神信仰表達。
三、平民視角下的個性化表達
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七個故事,每十年選取一個重要的歷史瞬間,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年齡都會找到一個感同身受的故事,體驗感和帶入感達到一種全面覆蓋,這就是《我和我的祖國》 中呈現的全民記憶。
七個故事的不同風格能夠同時滿足不同觀眾對于影片的期待,管虎導演的《前夜》 作為首個故事以開國大典前夜,林志遠擔負極大榮譽感和緊迫感的升旗任務時,小人物性格當中的猶豫、彷徨的情緒表現從側面表達了他對于這件事情的重視程度,也把觀眾的心情帶入緊張的氣氛中。在時間緊迫、困難百出的情況下,將全國人民一條心的真實情景再現,這種心情也正是開國大典前夜每一個中國人的心情。最后,林志遠克服心理障礙爬上天安門的旗桿親手解決掉最后的技術問題,反映了小人物在面臨重大時刻顯現出的英雄品質,平凡的英雄就像影片當中所有人都呼應張嘉譯在《相遇》 當中說的那句“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第二個故事《相遇》 則將影片節奏放慢,情感更為柔和,使觀眾從緊張振奮的狀態下關注到細膩傷感的情感本身。張一白以不流于表象的情感把控重塑主旋律命題,緊緊抓住時代號角,細膩深刻的鏡頭把控使觀眾融入影像背后的人文情懷當中。第三個故事《奪冠》,徐崢導演則將喜劇元素和小孩的純真表現聯系在一起,在女排奪冠的激動時刻,在祖國的歷史高光瞬間開始有了輕松卻不失激奮的時刻。冬冬最終選擇了集體榮譽,當他最后一次爬上屋頂舉著天線接收信號,不小心掛上的床單暗喻著他變作“捍衛國家榮譽”的小英雄,創造出詼諧而深邃的藝術意境。徐崢的喜劇風格的個性化表達在本片當中十分突出,導演將其“囧系列”的風格關聯到一個小孩的視角當中,主題的表達反而更加深刻,集體榮譽與個人情感成為冬冬的取舍問題。這種個性的敘事策略也使得主旋律電影多了一份輕松愉悅的色彩。《回歸》從薛曉路導演的女性視角出發,從細節的把控中表現人民迫切相聚的心情,以“表”為主要線索表達了主權問題分秒必爭的原則。當《東方之珠》 的歌聲響起,香港上空煙花璀璨,演員任達華在樓頂飽含熱淚地輕撫著自己的心臟,這種寫實性細節呈現,訴說著普通人對于香港回歸難以言說的心情,同時也表現了一顆期待多年的赤子歸心。《北京,你好》 則極大地凸顯了寧浩影片的戲謔風格,草根市民小人物在重大時刻那股說不上由頭的興奮勁兒,通過葛優含蓄幽默的表演,將一個極具偶然的故事呈現得十分自然。田壯壯在接受采訪時說:“《白晝流星》 是一個真實生活里的寓言。”陳凱歌在表現歷史的高光時刻的同時呈現了當下時代“扶貧”的艱巨任務,老李不僅要在物質上扶貧,更要在精神上扶貧。當沃德樂和哈扎布明白了“白晝流星”,也就成為扶貧攻堅路上的“白晝流星”。《護航》這個故事則和七十周年的閱兵達成了互文,以女飛行員呂瀟然的視角展開,導演文牧野將視角從閱兵正式飛行員轉移到備份飛行員身上,在護航“殲-10”梯隊之外更有一層引申意義,即所有參加閱兵的軍人都是在為祖國與人民護航。透過電影展現出的護航精神,則更為內斂和純凈,即祖國在保護我們,而我們要努力地去為祖國護航。
七個故事,七種風格,不同的個性化表達同一個愛國主題,同樣的平民視角下影片節奏的控制既能夠帶著觀眾體會祖國這七十年來的發展進程,又以個性化的表達滿足了觀眾觀影的需求。無論是從影片創作本身還是市場把控上面,《我和我的祖國》 都為主旋律電影樹立了標桿。
四、總結
《我和我的祖國》 不僅打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的刻板印象,同時也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平民視角敘事,個性化的風格處理,以私人記憶更好地打動觀眾。比起以往的宏觀敘事,在情感上更加真誠,也更貼近觀眾的內心。主旋律電影從來不缺乏振奮人心的故事內核和激烈的鏡頭呈現,只有寫實的情感和感同身受的生活化表現才能夠帶來持續發酵的內心認同。《我和我的祖國》這部影片在2019年的中國電影市場中既贏得了票房也獲得了口碑,這也是主旋律電影探索之路上的一次高光時刻。
參考文獻:
[1] 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1981.
[2]劉璐 .“主旋律”的提出及時代意義[J].學理論,2015 (10).
[3] 陳犀禾.改革開放40 年主旋律電影中的國家形象研究[J] .藝術百家,2019.35 (1).
[4] 陸顯祿.中國電影主旋律流變及其特征——基于新中國電影70年的考察[J].電影評介 2019 (19).
[5] 尹鴻,黃建新,蘇洋.歷史瞬間的全民記憶與情感碰撞——與黃建新談《我和我的祖國》和《決勝時刻》[J].電影藝術,2019 (6).
[6]戴錦華.電影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作 者: 康慧,藝術碩士,山西工商學院教師,研究方向:廣播電視。
編 輯: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