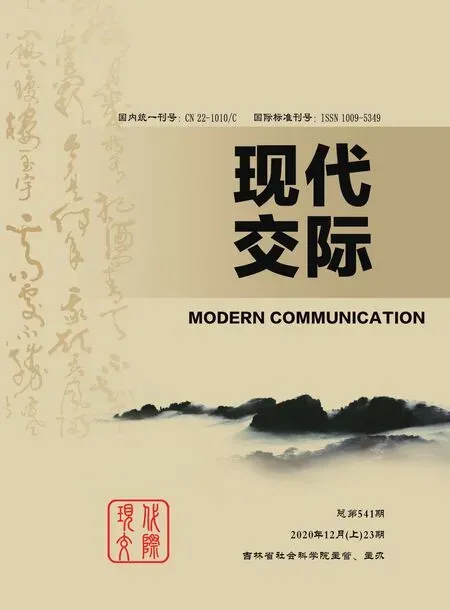淺談日語中的漢語詞匯
(西藏民族大學外語學院 陜西 咸陽 712082)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延綿2000多年,在這漫長的歷史中,中日兩國人民相互學習、互相借鑒,促進了各自國家的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的發展,中日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多領域的合作也更加拓展與深化,亟須一批掌握日語語言基本功,具有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復合應用型外語人才。本文主要分析和研究了日語中的漢語詞匯,旨在對中國日語學習者提供一定的幫助。
一、日語中漢語詞匯的定義
關于現代日語詞匯的分類情況,大體有三種分法。根據意思可分為名詞、動詞、形容詞、其他詞;根據語法性質可分為自立語和附屬語;按照其詞種(來源)可分為和語、漢語、外來語和混種語。
和語指日本民族固有的詞匯,讀音一般為“訓讀”(即漢字相應的日語讀法),漢語指采用音讀(即保留漢字的中國式讀音)的漢字詞匯。本文中的“漢語”一詞表達以上所指的特定概念,并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用語言。為敘述方便起見,本文中的漢語一詞均不加引號。外來語指借自西洋諸語的音譯詞匯,一般用片假名書寫;混種語是指詞源為不同語種的詞素組成的合成語。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于1994年有關雜志詞匯用語調查報告顯示:在所有詞條中,和語占25.7%、漢語占33.8%、外來語占33.8%、混種語占1.9%。在現代日語中,口語中和語詞匯較多,新語辭典中外來語較多,其余資料中漢語詞匯數量占有不少的比重。
二、日語中漢語詞匯的分類
日語中的漢語詞匯,從起源來說大體可以分為在中國創造的和在日本創造的,如果再詳細劃分的話,可參照朱京偉在《日語詞匯學教程》一書中的分類,如圖1[1]:

圖1 日語中漢語詞匯的分類
中日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已近兩千年。為了鞏固政權,求得生存與發展,日本的有識之士大舉輸入中國的先進技術、文學藝術、宗教和風俗習慣等,從漢唐的律令制度、詩文典籍到宋明以后的朱子理學、白話小說,漢文化對日本倫理道德、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化等方面都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據史料記載,公元604年,圣德太子時期頒布的《憲法十七條》中就有漢字“以和為貴,無忤為宗”。到了明末清初,來自歐美國家的傳教士活躍在中國各地,為了傳教,也為了介紹西方的科學,以利瑪竇、馬禮遜、裨治文等為代表的傳教士們獨自或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合作漢譯相關書籍,在翻譯過程中也創造了部分漢語新詞,如“幾何、病院、地球、銀行、保險、細胞、鉛筆”等。
漢字傳入日本之后,日本人結合日語中的固有詞匯,利用漢字創造出形似漢語的和制漢語詞匯。比如有“看板、見物、心配、贅沢、堪能、厄介”等詞。在和制漢語中,有部分詞匯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中創造出的新詞,包括從江戶中期到江戶幕府末期以學習荷蘭語書籍為主的“蘭學”翻譯和明治以后所創造的新詞。在翻譯西方書籍過程中,日本人為了學習和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新概念,使用漢字(包括仿照漢字創造的造字詞),并利用漢字的表意功能,創造出大量的新詞和譯詞,采用音讀方式是這類詞的最大特征。例如神経、盲腸、元素、概念、哲學、主観、客観、価格、常識、派生、進化、情操、神経、悲劇、義務等數量龐大的漢字詞匯。
甲午戰敗之后,中國開始大規模地吸收西方知識。大量留學生赴日學習先進技術和制度,并大量翻譯日本圖書或從日語轉譯西方書籍,來彌補中國在政治制度、醫學、現代科學詞匯及概念等方面的缺乏,這也導致大量的日制譯詞、新語流入漢語,形成漢語中的“日語借用詞”。不過關于部分 “日語借用詞”究竟源自中國還是日本,目前學術界尚有爭議。沈國威將其定義為“中日互動詞”,其概念為那些在詞語形成及普及定型的過程中,中日雙方均以某種方式參與其間的詞,詞語的流動方向可以表示為“中·日·中”。例如中國典籍、小說、傳世名作中的詞語,被日本借用來做譯詞,用來翻譯西方語言所表達的新意義,后來又回流中國成為現代漢語詞匯中的一員,如:“革命、共和、經濟、衛生”等。另外一種情況是,漢譯西書中的譯詞在中國未能得到普及,但傳入日本后與外語的對譯關系得以確定,最后回流到中國成為漢語近代新詞[2]。
三、二字漢字詞匯的中日比較
在日語中的漢語詞匯中,二字漢語詞匯數量最多,用途最廣,本節將從中日語言中的二字同形詞的關系來進行中日兩國語言的對比,這也是母語為漢語的日語學習者特別要注意認真學習,避免誤用的部分。
近年來,學界對漢語和日語的同形詞做了大量的比較研究。曹珺紅認為“根本標準應該是‘視覺上的統一性’。因漢語漢字在簡化過程中造成的字形的差異的漢字、與漢語在字形上大同小異的漢字、日語的表記漢字屬于漢語中沒有,但又能引起聯想的漢字,漢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完全可以把它們視為同形”[3]。潘鈞總結出判定中日同形詞的三個條件:“1.表記為相同的漢字(繁簡字體差別及送假名、形容動詞詞尾等非漢字因素均忽略不計);2.具有共同的出處和歷史上的關聯;3.現在中日兩國語言中都在使用的詞。”[4]在以上研究基礎之上,施建軍、許雪華更加詳細地界定了同形詞的概念和范圍。作者認為:“判斷中日同形詞的首要標準應該是形態要素,中日同形詞應該是中日兩國語言中具有相同形態的詞匯。但是考慮到中日兩國語言中漢字字形的差異以及同形詞形成的歷史復雜性,還有必要對這條標準進行補充,增加以下3條補充原則:1.中日同形詞的構成要素歷史上曾經使用相同的漢字;2.中日同形詞中由日語進入漢語的訓讀詞匯;3.因語言接觸而吸納到對方語言中,雖詞形發生變化,但中日之間仍存在嚴格對應關系的詞匯。以上原則滿足其中一條即可納入中日同形詞的比較范圍。根據以上原則我們將中日同形詞劃分成以下兩類:標準同形詞,符合上述首要標準或者補充原則1或者2的中日漢字詞匯;廣義同形詞,符合補充原則3)的中日漢字詞匯。”[5]根據以上原則,除去漢日完全同形的詞匯“新鮮、感情、學校”等詞之外,日語中的“付屬、熱中、予定、知力”與中文中的“附屬、熱衷、預定、智力”等詞是同形對應的關系。
從意義來說,中日同形詞可分為同形同義、同形近義、同形異義三類。中日兩國語言中的同形同義詞,如學生(中)—學生(日)、山脈(中)—山脈(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本著方便簡潔、便于應用的原則,于1956年1月發布《漢字簡化方案》,1964年5月審定通過《簡化字總表》,1986年重新發表經少量修訂后的《簡化字總表》,一直在中國大陸使用至今。由于中國古代漢字是用繁體字書寫的,因此傳入日本的漢字均為繁體字。再者,在傳播過程中也會有增減筆畫、書寫錯誤等誤傳現象,導致日語中某些漢字字形與中文漢字不能完全吻合,但如果所表達詞義完全相同,均視為同形同義詞。比如:會議(中)—會議(日)、圖書館(中)—図書館(日)、散步(中)—散歩(日)等詞匯。
在中日兩國,有不少是同形異義詞,對于這類詞匯,要勤查字典,記清詞義,切莫妄生穿鑿,貽笑大方。比如中文的“交代”有移交、接替;囑咐、吩咐;說明、解釋之意,而日語的“交代”是交替,輪流,替換之意,意思完全不同,漢語中的“便宜”一般指價格低廉,劃算之意,而日語中的“便宜”指方便,便利之意。
中國學生在學習日語時,特別要注意區分中日同形近義詞的詞義和用法。比如中文的“風俗”指“社會上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其組成的詞組一般有風俗習慣,節日風俗等,而日語的“風俗”除有此意之外,還有其他詞義也是中文中所沒有的。比如「風俗営業」指服務行業的總稱,「風俗犯罪」是指與賣淫、賭博等相關的犯罪,「風俗店」指風月場所(歌廳,舞廳,夜總會等),中日同形異義詞比較的范圍可以從詞義范圍的差異、詞義的虛實、感情色彩、文化含義、用法等多個方面進行比較研究,這也是筆者要繼續深入研究的課題。
四、日語中漢語詞匯的特征及作用
首先,漢語詞匯優美、典雅,極大豐富了日語的表現能力。漢語詞匯被稱為“書面語”,同詞義相對應的和語詞匯相比,漢語詞匯更加鄭重和禮貌。其次,漢語構詞能力非常發達,通過詞素的自由組合組成數量龐大的詞語。漢語的造詞成分分為“詞基”和“詞綴”兩部分。具有實質意義并能夠單獨存在的詞被稱為“詞基”,在二字漢語詞匯中,多數情況下前后兩個漢字均為單一詞基,比如“出発”里“発”字被認為是詞基,可以引申出“延発、始発、続発、多発、突発、連発”等詞匯。“病院”中“院”被認為是詞基,可引申出“入院、退院、通院,産院”等新單詞。另外,漢語詞匯的造詞能力還體現在“詞綴”,也就是“接續性漢語詞基”上,這些詞能夠組合成數量龐大的三字或四字漢語詞匯。比如表否定的前綴“非”,可組成“非常識、非行、非民主的、非人道的”等詞,表費用的后綴“料”可組成“入場料、給料、授業料、送料、手數料”等詞。據2002年出版的《新選國語辭典》第8版統計,在73181個收錄詞中,和語24708個,占比33.8%,漢語35928個,占比49.1%,外來語6415個,占比8.8%,混種語為6130個,占比8.4%,充分說明漢語詞匯造詞能力的強大和其在日語中的廣泛使用。第三,漢語詞匯具有高度概括力,能用精煉的詞語表達復雜、深奧的抽象概念。比如在日語中,與和語相對應的漢語詞匯,他們與其他漢字詞匯組成復合名詞,用來表達抽象概念。比如,與“行い”表意相同的漢語詞匯有“行為、行動、活動、動作”等詞,他們可以組成復合名詞“不法行為、暴力行為、軍事行動、消費行動、経済活動、就職活動、異常動作、言語動作”等。與和語“出來事·有り様”表意相同的漢語詞匯有“現象、事態、狀況、狀態”等詞,他們可以和其他名詞組成復合名詞“自然現象、流行現象、緊急事態、最悪事態、実施狀況、整備狀況、普及狀況、健康狀態、精神狀態”等來表達抽象概念。由此也可以看出,和語詞匯詞義廣泛,表意不太明確,而相比較而言,漢語詞匯能夠簡潔、明確限定詞義。與此同時,漢語詞匯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日語中的漢語詞匯中存在大量的同音詞,在聽力中很難分辨。比如讀作“こうしょう”的詞匯有“交渉、公証、高尚、公稱、工商、高尚”等。讀作“きこう”的詞匯有“機構、紀行、寄稿、帰校、貴校、気候、奇効”等,漢字在日語中也起到在書面上區分同音漢語詞匯的作用。另外,漢語詞匯的音讀有好幾種讀法,增加了學習者的學習難度。漢字在日本的音讀主要有吳音、漢音和唐宋音。吳音是公元5、6世紀后傳入日本的漢字音,以當時和日本交往較多的中國江南地方(古代吳國)的發音為主體,漢音是隋王朝成立后,在日本的奈良時代(8世紀)到平安時代初期(9世紀),由遣隋史、遣唐使、留學僧等帶回日本的,以長安為中心的基于北方音韻體系的讀音,同一漢字在不同詞源中可能有吳音和漢音兩種不同的讀音。比如在日語中“萬”字組成的詞語“萬一”讀吳音“まんいち”,而“萬歳”中讀漢音“ばんざい”,“無”字組成的詞語“無理”讀吳音“むり”,而“無事”中讀漢音“ぶじ”。唐宋音是從中國宋代到清代中期,也就是日本平安時代中期到江戶時代末期,由禪宗僧侶、商人等傳到日本的漢字音讀,主要是禪宗用語及部分生活用語。比如“和尚”讀音為“おしょう”,扇子讀音“せんす”,漢字的不同讀音也是在學習中需要特別注意的。
五、結語
由于日語中的漢語詞匯對中國的日語教學以及日語學習有極其重要的應用價值和學術價值,所以有許多中日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系統簡要地總結了日語中的漢字詞匯的定義、特征、分類以及其中的二字漢字詞匯的中日比較,今后將會進一步做有關日語中漢語詞匯的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