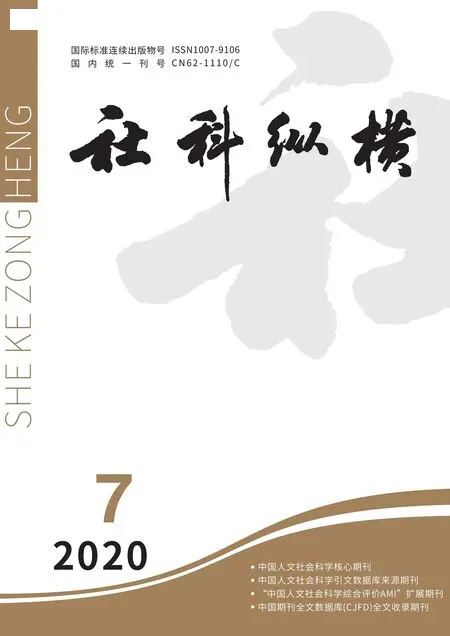主體間性視域下傳統(tǒng)文化教育新路徑探究
朱 帥 張 宏
(曲阜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 山東 曲阜273100)
《關(guān)于實(shí)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jiàn)》中明確指出,“按照一體化、分學(xué)段、有序推進(jìn)的原則,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全方位融入各教育領(lǐng)域”。長(zhǎng)久以來(lái),傳統(tǒng)文化教育未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教育方式未得到及時(shí)的轉(zhuǎn)換,教師被視為教育過(guò)程的中心與權(quán)威,學(xué)生則成為被動(dòng)的知識(shí)接收者,學(xué)生處于客體地位的教育模式使得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效果堪憂。主體間性是重要的哲學(xué)概念,其蘊(yùn)含的多維主體的共生性、共通性、共融性特征決定了師生間的平等交往與對(duì)話,將主體間性理論引入傳統(tǒng)文化教育,是對(duì)傳統(tǒng)主體性教育模式的優(yōu)化與超越,能夠顯著增強(qiáng)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時(shí)效性。
一、主體間性視域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機(jī)遇和挑戰(zhàn)
主體間性理論所蘊(yùn)含的認(rèn)識(shí)方式的雙向互動(dòng)性、交往儀式的和諧發(fā)展性、動(dòng)態(tài)教學(xué)的思維融合性為傳統(tǒng)文化教育帶來(lái)了新的機(jī)遇。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是傳統(tǒng)文化教育理念的革新,教育方法的轉(zhuǎn)型和教育內(nèi)容的轉(zhuǎn)變,為傳統(tǒng)文化教育帶來(lái)新的挑戰(zhàn)。
(一)主體間性視域下傳統(tǒng)文化教育面臨的機(jī)遇
1.交互主體性營(yíng)造傳統(tǒng)文化教育民主性雙向互動(dòng)儀式
在傳統(tǒng)文化教育過(guò)程中,主體間性肯定了主體的重要地位,并把人的主體性向主體間做了延伸,教師應(yīng)該樹(shù)立以主體間性代替教師主體或?qū)W生主體的教育觀念,把知識(shí)的傳授看做主體之間雙向互動(dòng)的交流活動(dòng),避免落入單向灌輸式和教師主導(dǎo)式授課模式的俗套。民主式雙向互動(dòng)儀式是教育者指導(dǎo)下的民主授課形式,是學(xué)習(xí)知識(shí)、形成能力的儀式,它遵循相互理解、互相尊重的人文主義原則,要求教育者尊重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意識(shí)到賦予受教育者一定能動(dòng)權(quán)力的重要性,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不僅與受教育者進(jìn)行知識(shí)與技能之間的互動(dòng),而且通過(guò)儀式化教學(xué)模式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取向、態(tài)度情感、精神風(fēng)貌之間的互動(dòng)與融通,從而促進(jìn)民主性師生關(guān)系的構(gòu)建[1]。與傳統(tǒng)“教師教,學(xué)生學(xué)”的授課模式不同的是,民主式儀式化教育營(yíng)造的是一種民主性和諧氛圍,教育者的引導(dǎo)和鼓勵(lì)既是對(duì)受教育者能力的肯定,又是對(duì)受教育者水平蒸蒸日上的期許,因而能夠有效激發(fā)受教育者的積極主動(dòng)性,從而實(shí)現(xiàn)自身價(jià)值并服務(wù)奉獻(xiàn)于社會(huì)。
2.交互主體性打造傳統(tǒng)文化教育理解式和諧發(fā)展儀式
交互主體性尋求“主體—主體”間的共生共在,傳統(tǒng)文化因其內(nèi)容和性質(zhì)的特殊性,如果僅憑借課堂上“講解—記憶”式的授課方式,受教育者將難以理解和領(lǐng)悟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很大程度上,傳統(tǒng)文化的育人途徑是通過(guò)心靈陶冶和置身感悟等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主體內(nèi)在的精神結(jié)構(gòu)和心靈圖式。對(duì)于傳統(tǒng)文化的教授和學(xué)習(xí),大致可分為三個(gè)層次:第一,講授層次,教育者講授,受教育者理解與記憶;第二,規(guī)范層次,受教育者理解和掌握教育者講授的理論后“被”要求去遵守這種基本規(guī)范;第三,儀式層次,受教育者在有意營(yíng)造的儀式情景中感受傳統(tǒng)文化的本真意蘊(yùn),并主動(dòng)遵守和維護(hù)這種規(guī)范。因此,最有效的傳統(tǒng)文化教授方式是情景化儀式的再現(xiàn),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作為教育過(guò)程的雙主體,在彼此尊重與理解的前提下共同進(jìn)入情境,在輕松和諧的環(huán)境中體驗(yàn)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內(nèi)涵。
3.交互主體性創(chuàng)造傳統(tǒng)文化教育融合式動(dòng)態(tài)教學(xué)儀式
人是實(shí)踐活動(dòng)和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的主體,人們的精神需要推動(dòng)交往的發(fā)生,教育活動(dòng)即師生間的交往活動(dòng)。動(dòng)態(tài)教學(xué)儀式的建立以交往為前提,以“以人為本”為宗旨,教育者需要從知識(shí)的傳授者轉(zhuǎn)變?yōu)橹R(shí)的啟蒙者,受教育者需要從知識(shí)的接收者轉(zhuǎn)變?yōu)橹R(shí)的探索者和經(jīng)典內(nèi)容的實(shí)踐者,從而使傳統(tǒng)文化教育理論更具實(shí)踐性和創(chuàng)新性。受主體間性理論的啟發(fā),構(gòu)建新型的“師—生”二元本位動(dòng)態(tài)教學(xué)儀式模式,拋棄和掙脫以師為本位或以生為本位的傳統(tǒng)窠臼,需要教師與學(xué)生、學(xué)生與學(xué)生、教師與文本、學(xué)生與文本之間的對(duì)話與交往。教師與學(xué)生的對(duì)話與交往是建立在教育關(guān)系上的對(duì)話與交往,教師應(yīng)采取適當(dāng)措施消除師生間的隔閡,引導(dǎo)學(xué)生成為教育的主體。學(xué)生與學(xué)生的對(duì)話與交往是“我—你”關(guān)系的平等對(duì)話與交往,呈現(xiàn)出緊密性和更強(qiáng)的包容性;教師與文本的對(duì)話與交往要求教育者具有精湛的文本解讀能力,對(duì)文本開(kāi)掘與創(chuàng)新,并引導(dǎo)受教育者抵達(dá)文本深層的意義世界;學(xué)生與文本的對(duì)話與交往是動(dòng)態(tài)教學(xué)儀式的最基礎(chǔ)部分,受教育者的感官和思維對(duì)文本的把握與吸收,直接影響課堂效果的優(yōu)劣[2]。教師、學(xué)生、文本三者之間具有緊密的耦合關(guān)聯(lián)性,只有從應(yīng)然與實(shí)然、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等多層面清醒認(rèn)識(shí)到三者的重要關(guān)聯(lián),才能使動(dòng)態(tài)教學(xué)儀式相得益彰[3]。
(二)主體間性視域下傳統(tǒng)文化教育面臨的挑戰(zhàn)
1.交互主體性要求傳統(tǒng)文化教育革新教育理念
學(xué)校的教育過(guò)程即文化的傳遞過(guò)程,而文化的傳遞需要先進(jìn)教育理念的統(tǒng)領(lǐng)。文化在教育中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應(yīng)樹(shù)立教育發(fā)展,文化先行的教育理念。顧明遠(yuǎn)先生曾指出:“教育有如一條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頭和不斷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這條河的表面形態(tài),而摸不著它的本質(zhì)特征。”[4](P439)另外,在傳統(tǒng)的師生關(guān)系理念中,“尊師重道”早已成為傳統(tǒng)文化教育甚至整個(gè)教育領(lǐng)域的教學(xué)信條,而主體間性理論所蘊(yùn)含的多主體共存的理念勢(shì)必挑戰(zhàn)和推翻教師“居高臨下”的地位和授課方式,革新傳統(tǒng)教育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角色定位,從而影響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實(shí)踐和理論傳播。傳統(tǒng)教學(xué)中“一視同仁”的教育理念使教育者始終保持一種固定的教育模式教育全體學(xué)生,沒(méi)有任何創(chuàng)新性的改變,而交互主體性中“此在”與“共在”的核心內(nèi)涵則要求教育者因材施教,不可一概而論。
2.交互主體性要求傳統(tǒng)文化教育轉(zhuǎn)型教育方法
即使施教者也深諳單向說(shuō)教式、灌輸式的授課方式不利于受教育者理解和運(yùn)用知識(shí),但受制于種種現(xiàn)實(shí)原因,此類(lèi)授課方式仍然以主流的形式散布于課堂之中,并且常常被當(dāng)作評(píng)價(jià)教學(xué)質(zhì)量高低的重要指標(biāo)。主體間性理論提倡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互動(dòng)交往,并以師生間彼此接受與認(rèn)可的程度作為評(píng)價(jià)教育質(zhì)量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現(xiàn)有的教學(xué)方法不能有效為這種教育模式服務(wù),甚至成為提高教育時(shí)效的掣肘。另外,傳統(tǒng)的教育方式局限于以線下授課為主,通過(guò)批評(píng)和說(shuō)服教育來(lái)糾正受教育者的思維偏差,帶有強(qiáng)烈的主觀判斷與是非對(duì)錯(cuò)觀念,難以得到受教育者的認(rèn)可和服從,而主體間性傳統(tǒng)文化教育擅于通過(guò)線上與線下相結(jié)合的方式引導(dǎo)和關(guān)注受教育者的心理變化,更容易獲得受教育者的認(rèn)同與理解,從而消弭受教育者內(nèi)心的抵觸情緒。
3.交互主體性要求傳統(tǒng)文化教育轉(zhuǎn)變教育內(nèi)容
從認(rèn)識(shí)論的視角出發(fā),傳統(tǒng)文化教育是一種思維導(dǎo)向教育,現(xiàn)存教育內(nèi)容并未注重思維的塑造與引導(dǎo)。第一,傳統(tǒng)教育內(nèi)容的側(cè)重點(diǎn)在于知識(shí)的理解與記憶,主體間性傳統(tǒng)文化教育則放眼于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注重獨(dú)立人格與問(wèn)題意識(shí)的培養(yǎng),凸顯人的本體性和價(jià)值性,因此勢(shì)必會(huì)給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內(nèi)容帶來(lái)沖擊。第二,隨著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的快速發(fā)展,新事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不斷博取青年人的眼球,而傳統(tǒng)文化教育內(nèi)容更新緩慢,顯然處于被動(dòng)落后的位置,瀕臨被時(shí)代拋棄的危險(xiǎn)。主體間性傳統(tǒng)文化教育,擅于對(duì)傳統(tǒng)文化教育內(nèi)容及時(shí)補(bǔ)充與創(chuàng)新,將縱向的歷史與橫向的現(xiàn)實(shí)相結(jié)合,賦予傳統(tǒng)文化以時(shí)代特色,偏向于實(shí)現(xiàn)儀式化教育的共境,以凸顯傳統(tǒng)文化的實(shí)用性和價(jià)值性,因而更容易使受教育者喜愛(ài)和接受,從而真正發(fā)揮教育的育人功能。
二、主體間性視域下傳統(tǒng)文化儀式化教育問(wèn)題的現(xiàn)實(shí)困境
(一)傳統(tǒng)觀念的深厚根基阻礙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主體間性轉(zhuǎn)向
傳統(tǒng)觀念的深厚根基正成為阻礙主體間性觀念變革的首要因素,轉(zhuǎn)變傳統(tǒng)觀念應(yīng)是邁出去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實(shí)現(xiàn)主客間的“實(shí)體論”向主體間的“關(guān)系論”轉(zhuǎn)換是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理想訴求,近代的主體性哲學(xué)局限于認(rèn)識(shí)論領(lǐng)域,只關(guān)注了主體間的認(rèn)識(shí)關(guān)系,隨著教育理論的深入發(fā)展,對(duì)教育困境的深刻反思,要求教育中要重點(diǎn)關(guān)注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共同成為教育活動(dòng)的主體,教育文本也應(yīng)成為教育活動(dòng)的主體。從存在論的視角來(lái)看,存在是解釋性的,而解釋活動(dòng)的基礎(chǔ)是理解,理解只能在主體之間進(jìn)行,因此文本不是客體,而是主體[5]。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講求天人合一,實(shí)現(xiàn)人與世界萬(wàn)物的視界融合,傳統(tǒng)儒家思想曾清晰表述過(guò)人與自然萬(wàn)物互為主體的關(guān)系,如孟子“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wàn)物與我為一”的觀念等。傳統(tǒng)主客對(duì)立的觀念深深存在于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潛意識(shí)之中,以致主體間的觀念、授課方式和評(píng)價(jià)體系只作為一種“門(mén)面”存在于某種特定的場(chǎng)合之中,很大程度上成為學(xué)校完成政策法規(guī)的任務(wù)、彰顯學(xué)校辦學(xué)成效的一種形式,并未發(fā)揮實(shí)際性的教育效用,傳統(tǒng)的教育觀念與教育方式始終作為主力軍而主宰著教育過(guò)程,主體間性的闕如始終存在。
(二)亞文化影響下價(jià)值觀異變導(dǎo)致傳統(tǒng)文化教育儀式化失衡
亞文化一般是非官方的,處于邊緣和從屬地位反對(duì)主流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種文化形式。文化和亞文化各以其復(fù)雜的形態(tài)存在于其特定的場(chǎng)域之中,它是人和社會(huì)現(xiàn)象存在的一種外在表現(xiàn)。復(fù)雜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潛伏著多種亞文化,每一種亞文化都有其獨(dú)特的價(jià)值和目標(biāo),被主流文化視為越軌的行為對(duì)某一亞文化群體來(lái)說(shuō)可能是可接受的行為,較為強(qiáng)大的亞文化甚至將主流文化的價(jià)值界定為越軌行為[6]。因此,師生間價(jià)值觀的差異往往造成儀式化教育的困境,亞文化中新鮮事物的非主流特色與青少年熱情敏感的性格特質(zhì)交織融合,在社會(huì)上產(chǎn)生一種深刻而持久的獨(dú)特文化景觀。當(dāng)前教育者浸潤(rùn)在主流文化的氛圍中,不了解亞文化的實(shí)質(zhì)與存在形式,對(duì)受教育者缺乏合理的引導(dǎo),使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文化結(jié)構(gòu)出現(xiàn)斷層,無(wú)法進(jìn)行有效溝通。傳統(tǒng)文化教育游離于青少年的亞文化結(jié)構(gòu)之外,極易導(dǎo)致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思維方式的對(duì)立,為價(jià)值觀的異變提供了溫床,這是儀式化教育失衡的重要原因。
(三)受教育者情景再現(xiàn)意識(shí)缺失使傳統(tǒng)文化教育儀式邊緣化
在教育領(lǐng)域,教育者講授與受教育者接收已經(jīng)成為一種主流的教育模式,以致于這種教育模式也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膽?yīng)用到傳統(tǒng)文化教育中。這種主流教育模式的痼疾導(dǎo)致課堂氛圍中潛伏著對(duì)教育者的絕對(duì)服從性?xún)A向,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既定的教育內(nèi)容和授課方式,形成了對(duì)教育者言聽(tīng)計(jì)從的盲目性,無(wú)形中增加了教育者的權(quán)威性和主導(dǎo)性,使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受到壓制,這種固定教育模式的長(zhǎng)期傳遞消磨了受教育者對(duì)儀式化教育的訴求,情景再現(xiàn)意識(shí)的缺失不僅使受教育者自身被邊緣化,更使儀式化教育被徹底忽略。通過(guò)情景再現(xiàn)的方式體悟傳統(tǒng)文化的本真意蘊(yùn)并非天方夜譚,電視節(jié)目中常常可以看到情景化儀式的教育案例,例如2017年在中央衛(wèi)視首播的《國(guó)家寶藏》就是一檔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儀式化教育節(jié)目,通過(guò)演繹劇本重現(xiàn)國(guó)寶故事是節(jié)目的點(diǎn)睛之筆。部分古裝電影、古裝連續(xù)劇也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儀式化教育的再現(xiàn),演員的入戲與切身感悟都已將自身融入文化氛圍之中。因此,師生也可以采取類(lèi)似方式進(jìn)行演練,從而實(shí)現(xiàn)文化精神的情景再現(xiàn)。
(四)代際思維差異阻礙傳統(tǒng)文化教育儀式化變革
當(dāng)前,我國(guó)正處于急劇轉(zhuǎn)型時(shí)期。由于我國(guó)綜合國(guó)力的快速發(fā)展,不同于西方先發(fā)現(xiàn)代化的國(guó)家和地區(qū),我國(guó)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是現(xiàn)代化與后現(xiàn)代化“疊加”在一起的,這種社會(huì)背景和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造成的結(jié)果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巨大差異在不同代群體身上打上不同的烙印[7]。由于不同時(shí)代的人在其生活的年代、社會(huì)環(huán)境氛圍、成長(zhǎng)經(jīng)歷上不盡相同,因而造成他們?cè)趦r(jià)值觀念、思想意識(shí)、性格偏好、行為習(xí)慣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作為95后甚至00后的受教育者,大多表現(xiàn)出思想前衛(wèi)、個(gè)性張揚(yáng)、思維轉(zhuǎn)換頻繁的性格特征,在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出生的他們更加傾向于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表達(dá)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年齡差距往往在20歲以上,教育者更習(xí)慣用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去審視新一代的年輕人,受教育者也難以理解教育者的思維方式與行為習(xí)慣,也就是米德提出的“代溝”概念,代溝存在的客觀事實(shí)決定了師生間儀式化互動(dòng)上的距離感,阻礙著儀式化教育的發(fā)展與變革。
三、主體間性視域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新路徑
主體間性視域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新路徑,即在主體間性框架內(nèi)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儀式化教育,其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內(nèi)容及師生關(guān)系等方面都應(yīng)具有適時(shí)性的創(chuàng)新。
(一)轉(zhuǎn)變傳統(tǒng)觀念,營(yíng)造交互主體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理念
主客傳統(tǒng)觀念的轉(zhuǎn)變是營(yíng)造交互主體教育理念的前提,交互主體教育理念是儀式化教育開(kāi)展的基礎(chǔ)。主體共生理念意味著不同主體之間是一種平等共處、相互依賴(lài)的關(guān)系,他者主體的存在正體現(xiàn)著自身的獨(dú)特性,正如我們追求生物的多樣性一樣,這是一種包容和開(kāi)放的理念,不以消除他者為目的,而是主體間互相尊重和欣賞[8]。傳統(tǒng)教育理念的轉(zhuǎn)變是自上而下的扶正過(guò)程,層級(jí)之間存在明顯的分野:第一,政策制定者要有放眼全局的高度,高屋建瓴地俯瞰整盤(pán)棋,將主體間性理念納入培養(yǎng)目標(biāo)之中,全面鋪展新的教育理念。第二,社會(huì)要有氛圍,積極搭建人性化互動(dòng)交流平臺(tái),大力宣傳民主、平等的儀式化教育理念。第三,學(xué)校要有執(zhí)行力度,深入貫徹執(zhí)行主體間性的教育理念,營(yíng)造和諧的儀式化教育環(huán)境,開(kāi)拓創(chuàng)新儀式化教育的方法和內(nèi)容,努力邁出最艱難的第一步。第四,教師要有溫度,以鼓勵(lì)和引導(dǎo)為主,積極主動(dòng)給予學(xué)生適當(dāng)?shù)闹笇?dǎo)與關(guān)懷,以平等的姿態(tài)與學(xué)生建立和諧的師生友誼。第五,學(xué)生自身要懿度,辯證唯物主義曾指出,內(nèi)因主導(dǎo)著事物的發(fā)展,外因通過(guò)內(nèi)因起作用,政府、社會(huì)、教師等外在因素要想起作用,必須訴諸于個(gè)人的努力來(lái)轉(zhuǎn)化,受教育者自身應(yīng)積極地完成心態(tài)的轉(zhuǎn)化,消除被動(dòng)的理念,主動(dòng)越過(guò)轉(zhuǎn)換途中的叢叢荊棘。
(二)增強(qiáng)民主對(duì)話,消解傳統(tǒng)文化教育代際思維的屏障阻礙
教育主體間“和而不同”的客觀事實(shí)體現(xiàn)出對(duì)話的重要意義,通過(guò)民主對(duì)話消解分歧和差異,意味著教育主體的“博弈雙贏”,更意味著傳統(tǒng)文化教育中的對(duì)話由一方主導(dǎo)走向雙方制衡。
首先,教師應(yīng)創(chuàng)建一種兼容并包、生動(dòng)溫馨的教學(xué)環(huán)境,鼓勵(lì)和提倡受教育者的自由和主動(dòng)發(fā)聲,徹底改變傳統(tǒng)教育課堂中“一言堂”的不和諧局面,使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話語(yǔ)狀態(tài)由“獨(dú)白”走向“對(duì)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受教育者的精神狀態(tài),使“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加具有實(shí)踐意義。
其次,教育者應(yīng)擅于提出具有引導(dǎo)性和開(kāi)放性的問(wèn)題吸引受教育者參與其中,并對(duì)受教育者的觀點(diǎn)和主張進(jìn)行適度的評(píng)價(jià),將關(guān)懷與引導(dǎo)相結(jié)合,以平等的話語(yǔ)權(quán)探討問(wèn)題的本質(zhì),洞悉彼此思維差異的具體點(diǎn)位,在探賾索隱中使教育者產(chǎn)生共鳴,形成思維轉(zhuǎn)換的內(nèi)驅(qū)力,從而消解代際思維屏障的阻礙作用。
最后,對(duì)話的實(shí)質(zhì)是不同思想交融碰撞的過(guò)程,教育者在對(duì)話過(guò)程中要扮演好一個(gè)“主持人”的角色,善于傾聽(tīng)每位學(xué)生的發(fā)言,迅速整合與概括,掌握好對(duì)話的發(fā)展走向,使對(duì)話不過(guò)于偏離預(yù)先設(shè)定的大方向,并沿此方向由淺入深逐次發(fā)展[9]。通過(guò)對(duì)話,教育者的人生觀和價(jià)值觀會(huì)對(duì)受教育者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教育者也可以從受教育者那里汲取新的思維活力,消解代際思維屏障的阻礙,從而實(shí)現(xiàn)教育主體在傳統(tǒng)文化教育中的價(jià)值共性。
(三)重置師生權(quán)重,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教育師生主體的雙向平等
師生權(quán)重的重置并不是推翻尊師愛(ài)生的傳統(tǒng),尊師需要學(xué)生具有程門(mén)立雪的的韌性,愛(ài)生需要教師涵泳教育大家的風(fēng)范[10],這是實(shí)現(xiàn)主體雙向平等的精神基礎(chǔ)。首先,從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身份地位關(guān)系來(lái)看,民主式儀式化教育注重儀式的相對(duì)自由和人權(quán)的絕對(duì)平等,教育者應(yīng)秉承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循循善誘地引導(dǎo)和鼓勵(lì)受教育者的儀式自由,實(shí)現(xiàn)由“復(fù)述性”文本傳遞向“人本化”交往儀式的轉(zhuǎn)變,建立與受教育者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課堂伙伴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從知識(shí)交流向精神交往的轉(zhuǎn)化。其次,從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權(quán)利關(guān)系來(lái)看,雙方的制衡是儀式化教育開(kāi)展的前提,教育者應(yīng)給予受教育者適當(dāng)?shù)臎Q定權(quán),尊重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從而實(shí)現(xiàn)由一方主導(dǎo)到多方制衡的轉(zhuǎn)變。最后,從受教育者潛在的主觀能動(dòng)性來(lái)看,民主式儀式教育強(qiáng)調(diào)在引導(dǎo)和鼓勵(lì)中,充分調(diào)動(dòng)和激發(fā)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dòng)性,教育者應(yīng)積極主動(dòng)關(guān)注受教育者的內(nèi)心情感變化和情感表達(dá),從而易于把握和引導(dǎo)受教育者的思維路徑,一定程度上降低受教育者的抵觸情緒和防范心理,使受教育者的真實(shí)想法浮于水面,并積極主動(dòng)地表露心聲,實(shí)現(xiàn)對(duì)受教育者全方位的指導(dǎo)與關(guān)懷,在這種和諧平等的關(guān)系中極大挖掘受教育者的學(xué)習(xí)潛能。
(四)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意識(shí),構(gòu)建現(xiàn)代傳統(tǒng)文化教育儀式化體系
在主體間性視域下,教育者不僅要將傳統(tǒng)文化知識(shí)融入實(shí)踐之中,還要時(shí)刻關(guān)注受教育者的心理變化及成長(zhǎng)規(guī)律,緊跟時(shí)代發(fā)展的步伐,培養(yǎng)自身的創(chuàng)新意識(shí),革新儀式化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構(gòu)建現(xiàn)代傳統(tǒng)文化教育儀式化體系。
儀式化教育體系的構(gòu)建應(yīng)以實(shí)現(xiàn)以下兩個(gè)目標(biāo)和實(shí)現(xiàn)四個(gè)層次的遞進(jìn)為旨?xì)w。工具理性目標(biāo)與價(jià)值理性目標(biāo),工具理性目標(biāo)即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外在知識(shí)的記憶與運(yùn)用,價(jià)值理性的目標(biāo)即領(lǐng)悟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內(nèi)涵和精神品質(zhì)[11]。實(shí)現(xiàn)受教育者境界的四層遞進(jìn),即文化精髓的統(tǒng)攬觀照,文化理念的初次體驗(yàn),文化內(nèi)涵的理性直覺(jué)和文化意蘊(yùn)的融合升華。
首先,教育者要想順利實(shí)施儀式化教育,就必須把握相關(guān)研究的前沿動(dòng)態(tài),并與受教育者的內(nèi)心偏好相結(jié)合。一方面,教育者要擅于全方位地挖掘和整理,放眼于儀式的多元發(fā)展,通過(guò)文化的理論視角去洞悉社會(huì)的變化和運(yùn)轉(zhuǎn),關(guān)注國(guó)家政策的制定和演變,實(shí)時(shí)解析動(dòng)態(tài)熱點(diǎn)并與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內(nèi)容相融合,增強(qiáng)儀式的象征性,激發(fā)受教育者的激情和動(dòng)力,使受教育主體樂(lè)于參與其中。同時(shí),教育者也要營(yíng)造優(yōu)質(zhì)的學(xué)校文化環(huán)境,重視校園環(huán)境隱性的教化引導(dǎo)作用,力求將優(yōu)質(zhì)的校園環(huán)境熔鑄于受教育者的認(rèn)同理念之中,使學(xué)生在潛移默化中熏陶出主體性品質(zhì),從而形成受教育者主體性品質(zhì)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教育者應(yīng)從實(shí)際出發(fā),以自身所長(zhǎng)和研究興趣為出發(fā)點(diǎn),在充分理解主體間性理論的前提下,積極推動(dòng)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儀式化轉(zhuǎn)變,在師生平等交流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高效完整的儀式化教育過(guò)程。
其次,要實(shí)現(xiàn)儀式化體系的構(gòu)建,需要立足于課堂的重復(fù)演練,完善儀式化教育的理論范式。一方面,教育者自身要為儀式化教育做好充足的準(zhǔn)備,發(fā)揮自身獨(dú)特的教學(xué)優(yōu)勢(shì),根據(jù)受教育者的心理變化不斷調(diào)整、完善授課模式和內(nèi)容,形成自己獨(dú)特的儀式化教育認(rèn)識(shí)和程序。同時(shí),教育者也應(yīng)主動(dòng)與其他教育者交流并觀摩學(xué)習(xí),完善自身的教育經(jīng)驗(yàn),實(shí)現(xiàn)儀式化教育的創(chuàng)新。另一方面,教育者在教育過(guò)程中,要時(shí)刻關(guān)注受教育者的外在情緒反應(yīng)和內(nèi)在情感變化,以受教育者的思維運(yùn)轉(zhuǎn)規(guī)律為出發(fā)點(diǎn),時(shí)刻反省自己的語(yǔ)言和行動(dòng)對(duì)受教育者造成的影響,反思儀式化所折射出來(lái)的教學(xué)理念和教學(xué)啟發(fā),揭露現(xiàn)有教育方式和教育內(nèi)容的不足,并致力于修訂和完善這種不足,批判性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斷實(shí)踐,進(jìn)而完善儀式化教育體系的構(gòu)建。
- 社科縱橫的其它文章
- 文旅融合產(chǎn)業(yè)鏈構(gòu)建與培育路徑研究
- 深度貧困地區(qū)東鄉(xiāng)族自治縣特色產(chǎn)業(yè)扶貧調(diào)查研究
-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城市化對(duì)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作用研究
——基于中國(guó)城市群的經(jīng)驗(yàn)分析 - 社會(huì)公正三維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構(gòu)建研究
- 融入社科聯(lián) 成就社科夢(mèng)
——天水師范學(xué)院社科聯(lián)概覽 - 論新時(shí)代“文明”價(jià)值觀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發(fā)展
——基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論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