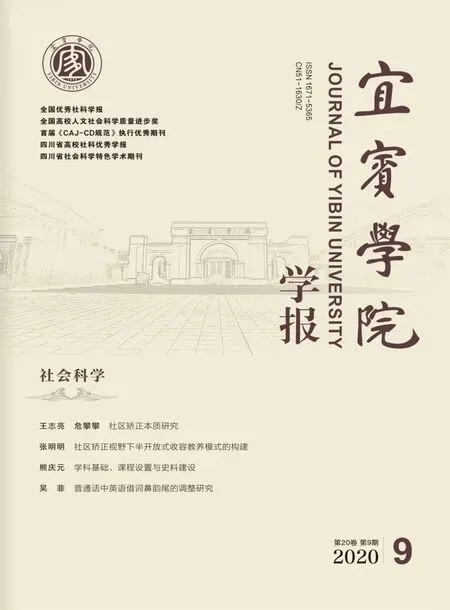學科基礎、課程設置與史料建設
——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若干歷史問題
熊慶元
(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0)
按照通常的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其起源可以上溯到1917年“五四”文學革命,距今已百年有余,其尾聲則下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從時間范圍來說,中國現代文學共計三十余年,時間跨度并不算長,但在這短短三十余年的時間里,中國現代文學卻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學科特性,也留下了非常豐富的歷史材料。迄今為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和史料建設方面的討論并不少見,但對于該學科的史料建設同學科自身特殊的歷史形成過程之間的關系,學科史料建設發展的情況同相關教學研究工作歷史演進的關系等問題,相關的討論仍有待展開。本文將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基礎、課程設置和史料建設等方面的情況,就這一學科建設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討論。
一、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形成的歷史機制
眾所周知,一門學科的建立離不開相關史料文獻的匯集整理,并且在相當程度上,學科的邊界也限定了其史料文獻的范圍。比如,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立,中國古代文學的史料范圍才能進而得到確立。中國古代文學相關的史料文獻雖然先于中國古代文學這一學科的建立,但在學科建立之前,這些史料文獻并不能直接被視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史料文獻。我們知道,如今的學科劃分方式,其本身是一個現代的產物,是一種歷史建構的結果。在現代學科建制出現之前,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諸如文學、歷史、政治這一類的學科界別。在中國古代,文與史的界限并不分明。中國傳統的經典分類體系,如經、史、子、集“四部之學”這類的典籍分類方式,也并不等同于我們今人所謂的文學、歷史、政治、經濟等范疇之別。比如,在中國古代歸入史部的“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在今天,可以同樣放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被作為文學經典來加以講述。因此,盡管今天的古籍匯集和整理工作,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有對傳統史籍整理方式的繼承,但如上所述,很多時候,現代的學科建制也不可避免地,甚至是深刻地,介入了古代文史典籍的匯集整理,不僅在方法上,同時也是在觀念上改造甚至重塑了古籍整理的工作。
正如今天中國古代文學的史料整理不能脫離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制的歷史進程來進行考察,同樣,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發掘與整理,也需要放在這一學科自身生成、發展的歷史脈絡中來加以觀照。從史料形態來說,現代和古代是不同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有其自身鮮明的特點,報刊等近現代傳播媒介對現代文學史料形態的塑造即是一例。但在筆者看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真正的獨特性并不在于傳播媒質的古今差異,而主要還是由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立的歷史特殊性造成的。我們知道,在現有的學科劃分方式上,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或中國現當代文學)同是劃歸中國語言文學這個一級學科之下,二者屬于平行的二級學科。但實際上,無論是學科內容所涵蓋的歷史時長,還是史料文獻的完整和豐富程度,中國現代文學都遠不及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之成為中國語言文學這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從而與中國古代文學相平行,主要不是由于其歷史之悠遠、史籍之浩繁,其學科地位的確立,關鍵在于其所包孕的深厚的文化—政治內涵。換句話說,中國現代文學,就其歷史意義而言,是并不亞于中國古代文學等其他二級學科的。
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等學科的建立,主要取決于學科自身的容量,因而符合學科建立的內在要求的話,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的建立,雖有學科自身的發展需要,但其學科化的過程卻似乎與政治有著更為密切的關聯。作為一門學科,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歷史,可以說是相對晚近的,而建國初期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出版,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形成史上一個標志性的事件。1951年,開明書店率先出版了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一書的上冊,本書的下冊此時尚在寫作之中,直到1953年才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上下兩冊的出版一般被看作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化的開端,自然也就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開山之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討論中國新文學的史著雖時有出版①,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新文學”卻尚未出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史也隨之進入新的階段,因此,為此前的時期修史的任務也就被很自然地提了出來。這時,將“新文學”研究從以往古代文學的學科領域中分離出來同樣也就顯得順理成章。
當然,以一本文學史著作來界定一個新興學科的形成,依據并不充分。《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出版之所以會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制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是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新文學發展的整個歷史語境的變化密切相關的。此書的出版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在同一時期,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和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第一卷)這類新文學史的論著也陸續出版(前者1952年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后者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盡管1949年后出現的這些著作延續了“新文學”這一說法,但它們與1949年之前出版的新文學史著作已表現出明顯差異。從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開始,“新文學史”著作不僅延伸了新文學史的時間下限(比如,從此前很多新文學史截止的1930年代下延到1949年),同時,這些著作還將新文學史的時間線做了閉合處理,將“五四”文學革命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間的這段文學史確定為新文學史,也就是說基本確立了新文學史完整的時間范圍。更重要的是,這些著作的出版并不僅僅只是補充了此前的新文學史著述,它們還是順應建國初期大學擬開設新文學史課程這一訴求的現實產物。也即是說,1950年代初期《中國新文學史稿》等新文學史著作的出版,實際上內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化的歷史語境,著作的歷史敘述、時代觀念的調整同當時教育內容、教育方式的變革相適應,從而構成了新興學科形成的內在動力。
不過,這里需要特別強調一點,“新文學”的說法畢竟不同于“現代文學”。將1949年《中國新文學史稿》等新文學史著作的出版及其與“新文學”課程教學的相輔相成關系視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化進程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源起),并不意味著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這一階段已經形成。孫向陽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形成,首先是源于“現代文學”這一概念的浮現。他注意到,1950年代中期以來,“‘新文學史’紛紛更名為‘現代文學’。最先以‘現代文學史’命名的文學史論著是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1955年)。”[1]孫向陽進而引用洪子誠對“當代文學”概念的界定來說明“新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現代文學’對‘新文學’的取代,是為‘當代文學’概念出現提供‘空間’,是在建立一種文學史‘時期’劃分方式,為當時所要確立的文學規范體系,通過對文學史的‘重寫’來提出依據”[1]。換句話說,“現代文學”概念的出現,并不只是對“新文學”的簡單易名,而是包含著深刻的文化—政治意涵:“從‘新文學史’到‘現代文學史’的名稱變化,既是一種文學‘進化’的結果,也體現出一種文學史觀的‘現代’轉型”,“這種改變……包含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涵義”[1]。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化,其本身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而不只是學科自身自然發展的結果。“現代文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被納入新的學術體制,其背后有清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所以,“現代文學”學科化實際上是一個政治事件。政治—學科化之間的這種特殊的歷史關聯,同時也深刻塑造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研究方式,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等方面也都體現出了自身獨特的學科特點。
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教學中的課程設置
“現代文學”這個概念是1950年代中期出現的,在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一書出版后,陸續出現了一些書名中帶有“現代文學”的著作。正如《中國新文學史稿》等一系列新文學史著作的出現實與50年代新文學史教學的訴求相平行,同樣,現代文學史論著的出現,其功能之一也是為了配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學。按照孫向陽的說法,標志著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成立的事件,是高等教育部在1957年審定頒布了《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將這一事件確定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誕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教學大綱“以官方的名義正式把1919-1949年的文學命名為‘中國現代文學’”,并且將1919年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原點這一做法,也與《中國新文學史稿》將新文學史的起點定在1917年的做法不同[1]。因此,孫氏指出,“‘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本質上已經有別于‘中國新文學’”[1]。
從學科史的角度來說,孫氏的說法并沒有什么問題。但實際上,教學大綱的制定不是從1950年代中期才開始的,早在50年代初,基于課程講授的現實需要,類似的“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就已經出現。將“中國新文學史”明確規定為各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課程是在1950年,當時教育部通過的《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下文簡稱《草案》)中就指出: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中國新文學史”的任務在于“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1]。隨后,教育部組織了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改革小組,由中國語文系小組負責擬定中文系各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其中負責“中國新文學史”課大綱草擬工作的是老舍、李何林、王瑤和蔡儀(原定人選中還有陳涌,但陳因忙于他事而未能參加)。經過前后兩次討論,他們最終確定了《〈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下文簡稱《大綱》),計劃以此作為新中國成立后這門課程的基本框架。很快,《大綱》的內容就在1951年7月的《新建設》刊出,不久即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史研究》一書②。僅僅兩個月后,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一書的上冊便出版問世,成為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的底本。
我們發現,《大綱》《中國新文學史研究》和《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的相關內容似有某種一致的傾向,即它們都重在突出無產階級對“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領導地位以及“新文學”的“新民主主義”性質。顯然,推重和強調政治與文學的關系深刻地影響著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文學史寫作,從歷史上看,它幾乎是作為某種寫作范式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被迅速固定下來的。以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為例。該書上下兩冊雖然在寫作時間、出版年份上存在先后,但其內容仍是前后一貫的,書中以“新民主主義”為綱、突出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影響的做法(即《草案》中所謂“新觀點、新方法”)一直被后來的文學史家廣為沿用。也就是說,盡管伴隨著“現代文學”這一概念的浮現而形成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其形成是在1950年代中期,但實際上,中國現代文學史被視為中國現代革命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分支,則是從1950年代初期“新文學史”的編纂與相關的教學活動開始就一以貫之的。
從上述極為簡要的梳理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出現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既是建國初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化這一歷史要求下的必然產物,同時,它也促進了現代文學學科化的形成③。如上所述,1950年代初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化進程,其與當時整個社會語境的歷史變遷息息相關,因此,突出無產階級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領導地位便有其歷史的意義。不過,這種歷史地形成的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史書寫方式,在此后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定型,幾乎成為經典的文學史書寫范式而被一直沿用。而這一現象,在相當程度上也和教育的代際承傳有關。
從當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教學來看,本科的核心課程設置基本是以現代文學史和現代文學作品選為主,這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制之初的設計是基本一致的。早在1950年代初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甫定之際,將現代文學史和現代文學作品選作為中文系本科專業核心課程的做法即已存在。前文已經提到,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出版后,一度是用作1950年代初“新文學史”教學的底本的,而按照陳平原對1950年代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學情況的介紹,除王瑤以外,當時擔任現代文學史教學工作的還有吳組緗,并且,吳組緗在講授現代文學史方面的課程外,同時還任教“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的課[2]。可見,50年代初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初成之時,現代文學史和現代文學作品選就已經是中文系的本科核心課程。另外,在講述作家作品和文藝思潮時有非常明顯的側重點,比如,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凸顯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的歷史意義,作家側重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在現代文學的學科教學中,課程內容上的這種偏重,也得到了長時間的沿用,甚至在今天的學科教學中,也很常見。不過,盡管存在這種延續,改革開放前后,現代文學學科的文學史教學和作品選讀課程也還是出現了一些變化。
改革開放以后教學上的變化,大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文學史觀的變化引起的文學史講授方式的改變。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現代文學史觀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和現代文學學科自身演進方向的轉變有關。隨著新時期的到來,現代文學學科領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表現之一就是學術視野的拓寬,現代文學研究相應地也開始轉變研究范式,以往研究者對現代文學史的認知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這種轉變大致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此前現代文學史偏重講述革命史的做法有所調整,啟蒙史觀開始出現,尤以錢理群、吳福輝等人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一書的出版為代表(此書初版于1980年代后期,此后一直被作為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本科課程通用的核心教材之一);一是這一時期各種形態的“大文學史觀”相繼出現,比如陳思和強調“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注重突出中國現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黃子平等人提出“20世紀文學史”的說法,試圖貫通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界溝,而王曉明等人更是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的要求。
文學史觀方面的上述變化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講授方式都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文學史教學中對現代文學的啟蒙內涵的強調,在比重上有明顯的上升。同時,這種變化也以另一種形式體現出來,即文學史在講述重要的作家作品時,新增了一些此前未納入文學史或在文學史中被忽略的作家作品,比如沈從文、張愛玲等人及其作品,在改革開放之后的文學史著作及相應的文學史教學中,得到了更多篇幅的講述,講授的課時也明顯有所增加。隨著文學史講授方式的變化而出現的對沈從文、張愛玲等現代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發現,使得文學史的教學內容更為豐富,而這種變化也同樣體現在作品選讀課的講授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現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教學上的這種變化可以說是鮮明而重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總體上看,這種變化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挑戰195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教學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后本科生的現代文學教學活動中,1950年代形成的核心課程教授模式仍有其潛在影響。1980年代以來現代文學史觀的變化及其引致的文學史書寫模式的轉變,盡管提供了此前被主流歷史敘述遮蔽的某些空間,但無論是啟蒙史觀的出現,還是沈從文、張愛玲等作家作品的重新發現,實際上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相關課程教學中論述焦點的側重和歷史敘述的邏輯,它們在削弱現代文學學科建立之初所形成的歷史敘述的偏向的同時,更多的對前者構成了一種有效的補充。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以后現代文學相關的本科核心課程教學中,啟蒙史觀的介入并沒有挑戰長久以來的革命史敘述模式,對革命文學、進步作家、經典作品和重要文學事件的講述仍然構成了這些課程的重心,只不過在教學的比重上,啟蒙史觀的介入相當程度地緩解了革命史講述模式的偏重性,使得相關的課程講授,在學科內容方面顯得更加平衡。當然,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仍然給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在學科教學之外,一個更為重要的變化,實際上發生在現代文學的史料建設方面。
三、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建設及其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史料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19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這套大型史料叢書的出版即是一個有力的佐證。這套叢書的編纂主要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牽頭的,參編者包括了10余家出版社,以及70多所高等院校與科研機構,可謂是舉全國學術界之力共同促成的一項重大的史料工程。不過,改革開放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方面的影響,并不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突變過程。早在現代文學初成之際,收集、整理當時相關的文學材料的做法就并不少見。1930年代中期,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面世,較為系統地總結了從“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實績,而更早的時候,朱自清1929年編寫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也已初具新文學史的雛形。只是這個時候,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尚未形成,當時的材料大多是同時代的材料,從上文援引諸例可見,當時的相關文學史料多是以“新文學”名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隨著現代文學學科的形成,相關現代文學史料的鉤沉、整理工作得到了更為長足的發展,而現代文學史料方面的這些工作大多又與相應的教學活動相關聯,并且在之后的一段時期內都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延續。
盡管在教學(1950年代初主要是高校本科教學)中,史料并不一定是必須的(1950年代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高校中的史料類課程基本都是輔助性的,供有興趣的學生選修,有些高校甚至都未能開設相關的史料類課程),但伴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作品選讀等核心課程的設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匯集、整理工作仍在自然地發生和展開(這些課程在講授過程中,顯然會在一定范圍內觸及諸多的文史材料)。1950年代所形成的教學模式對史料鉤沉方面的影響,首先體現在主流史料的極大豐富,比如與“五四”時期啟蒙文學、1930年代左翼文學、1940年代解放區文學相關的史料的挖掘、勾稽工作得到了相當的進展,《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出版便是一個重要的文學/文化事件。但誠如前文所指,1950年代教學模式對革命史的倚重有其自身的偏重性,主流史料的極大豐富,實際上,就史料構成而言,相應的也與這種教學模式的偏重性息息相關。我們發現,1950年代以來的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主要還是圍繞和革命史相關的材料展開,其他史料的發現和研究仍相對顯得薄弱和滯后。
現代文學史料收集、整理方面的上述特點,到改革開放以后開始出現一定的變化。盡管新時期以來現代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對此前的路徑仍有所依賴,但隨著前述改革開放以來現代文學史觀的調整,一些此前不受關注的史料也開始浮現。上文提到,沈從文、張愛玲這些此前未被納入主流文學史敘述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改革開放后被重新發現并給予了新的歷史闡釋,這種變化同樣影響到改革開放以后現代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對這些作家作品及其相關史料的鉤沉、輯佚和整理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④。此外,這一階段對通俗文學的關注度也明顯上升,除了此前在左翼文學和革命史的脈絡里對蘇區和解放區通俗文藝的關注之外,這一時期對“五四”以來其他通俗文學作品及其文化形態的關注日漸增多,由此也引發了相關史料的發現、收集和整理⑤。這些史料的發現、收集和整理顯然大大推進了此前的史料工作,但總體來看,它們大多仍是局部的,整體性有嫌不足。究其緣由,筆者認為,這相當程度地與教學的需要相關: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新史觀的出現,自然地對新史料的發現提出了要求;但另一方面,由于前述史觀的“補充”性質,即它并未從根本上挑戰當時的現代文學史教學模式,新史料的發現因此也只能作為對當時既有史料的某種程度的補充。
不過,教學需要并不是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缺乏整體性的唯一原因,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之缺乏整體性,一定程度上也與學科發展的歷史過程、史料自身的特性以及史料意識的不夠清晰等因素有關。前文提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收集、整理的偏重性,這種偏重性,如前所述,顯然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形成的特殊歷史過程相關。由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有著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它更多是基于1950年代伊始具體的政治—文化關系形成的,而非基于充分的史料基礎。而實際上,就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自身的布局、構成而言,它也有自身的特點。劉勇和張悅對此有過說明:“現代文學由于戰爭炮火、政治紛爭等諸多因素,一些史料可能已經被銷毀,也有一些史料即便存在,也可能永遠不能再見天日”,他們進而指出,“材料的短缺和難以辨析,使得很多研究都難以推進”[3]。可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完整性的缺乏,除了緣于前述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立過程的特殊性之外,相當程度地也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本身的缺乏有關。趙普光曾指出:“判斷一個學科的成熟與否,其史料建設的完善程度是重要標準”[4]。因此,完善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構成,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和演進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而要完善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建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在重視史料建設之外,應相應地形成與學科自身相適應的史料學意識。
盡管如前所述,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匯集、整理工作幾乎與新文學同時展開,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在1950年代初的幾年間也已基本完成,但長久以來,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意識卻并未成形。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歷史來看,真正形成史料學意識,也就是基于現代文學是一門獨立學科而強調史料學建設,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出現。1989年,樊駿曾撰文指出史料學建設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重要意義[5]。而在更早的時候,馬良春就已提出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想法。1985年,馬良春在《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一文中明確指出:“要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工作,改變過去的自發的、零散的狀態,使整個資料工作形成一個適應現代文學史研究需要的完整體系”[6]。此后,不少學者開始投身于建立、完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工作,朱金順、劉增杰、陳子善、解志熙等人在鉤沉輯佚、校讎勘誤、匯集整理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極具代表性,限于篇幅,不加贅述。但實際上,隨著1990年代初新的學術規范的引入和學術評價機制的變化,在傳統的文史研究方式隨之發生變化的同時,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設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尤其是在研究范式轉換過程中,隨著強調新理論新方法新分析手段和研究模型的層出不窮,加上學術評價機制的特性,傳統的史料編輯工作遇冷,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工作也始終未能完成(比如,謝泳在2008年再度撰文,重提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7])。可見,如今建設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工作雖仍在進行之中,但從馬良春首倡至今凡三十余年,建立和完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工作仍有待更為深入的展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建設與具體的學科基礎、課程設置的關系及其若干相關問題,本文所論仍然有限,但囿于篇幅,無法再作深論,總之,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建設,無論之于相應學科的發展還是相關的課程教學,都仍有其緊迫性和必要性,需要予以更多的關注和重視。
注 釋:
① 如1949年前首部正式出版、具有系統規模的“新文學”史作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年9月由北平杰成印書局出版),第一部現代文藝思潮方面的專史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1939年9月由生活書店出版)等。
② 與《大綱》一同被收入此書的還有另外五篇論文,分別是:李何林的《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左聯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學》《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新文學》,張畢來的《1923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丁易的《中國文藝第一次和兵農的結合》(《中國新文學史研究》,新建設雜志社,1951年)。
③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出版后,其他一些同類文學史著作陸續出現,代表性的有張畢來的《新文學史綱》(作家出版社,1955年)、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和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
④ 1980年代,中國文壇曾一度出現了“沈從文熱”,相關情況可參見謝尚發的《80年代初的“沈從文熱”》一文(載于《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4期)。
⑤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史料發掘、整理和研究,尤以范伯群的著述為代表。范伯群的學術研究始于新文學作家論,改革開放前后開始轉向通俗文學研究,此后編著有《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以及《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等,這些著述有力地推進了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及相關史料的發掘、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