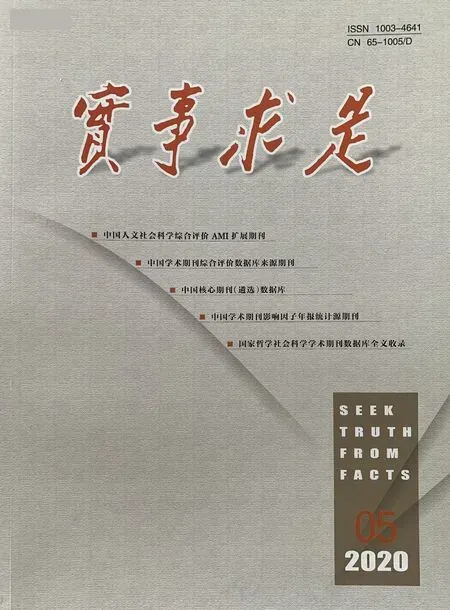奧康納與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比較及啟示
呂明洋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 北京 100872)
作為《資本主義的實質是社會主義》雜志的創始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發起人,詹姆斯·奧康納(以下簡稱“奧康納”)與其最親密的合作伙伴喬爾·科威爾(以下簡稱“科威爾”)在生態社會主義研究領域提出了諸多富有洞見性與創新性的理論觀點,極大豐富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內涵。雖然奧康納和科威爾同處于一個學術共同體,科威爾也受到了奧康納思想理論的影響,但是二人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既存在聯系又存在區別。奧康納與科威爾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的深刻抨擊、批判以及對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鞭辟入里的剖析為認識與解決現今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參考和借鑒,也為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值。
一、關于生態環境危機產生的根源
奧康納首先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視為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科技的飛速發展以及物質生產能力的大幅提升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化進程,社會生產力逐漸演變成資本的生產力,資本家越來越多地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以及調控、管理生產過程,最終導致本應屬于勞動者共同所有的社會化產品成為了資本家的私人產品,歸資本家占有與支配。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所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即是第一重矛盾的具體表現。在此基礎上,奧康納又創新性地提出了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同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從經濟的維度對勞動力、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空間,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環境的自我摧殘性的利用和使用”是第二重矛盾產生的根源。[1](P248)資本家只顧自身利益而全然不顧他人利益,為了達到獲取更多利潤的目的,他們將商品的生產成本轉移到外在的自然條件上,最終導致了自然環境資源遭受破壞。因此,他認為資本主義必然要對其行為負責,雙重矛盾必然帶來雙重危機。雙重危機包含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兩個方面。一方面,資本主義為了進行資本積累而大肆壓榨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率的不斷提高使勞動者購買勞動階層再生產的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下降,這便導致了剩余價值再生產過程的停止,進而促使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爆發。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經濟發展過程中,利潤是經濟活動的目標。資本主義自身的擴張并沒有嚴格的限制,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它完全忽略了自然條件的有限性,將自然視為經濟生產過程中的“水龍頭”與“污水池”,既毫無節制地對自然資源進行開發,又毫無顧忌地把生產出來的廢棄污染物排向自然。然而,自然系統有其獨特的建構原則,自然的生產能力是存在一定限度的,“由于資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價值,因此,它只有通過經濟危機的形式來觸及到生態維度上的局限性”。[1](P289)
經濟危機同生態危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復雜局面最終導致了社會危機的到來。其一,經濟危機爆發后,生產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削減生產成本,這就可能使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減少對環保成本的投入而重新使用那些對生態環境具有污染性、破壞性的技術或產品,也可能導致生產成本低卻對生態環境有害的新技術的產生。“經濟危機還與降低資本流通時間的努力聯系在一起,這反過來會使得企業更加不關注工人的健康、所出售商品的環境以及衛生影響、城市條件及基礎設施的可持續性存在等等。”[1](P293)其二,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所需原材料的缺少無疑會降低所得利潤,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其三,生態危機發生后,包括生態保護運動在內的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不斷呼吁改善生活環境、保護森林資源、提高土壤質量、創造良好衛生條件、保衛城市空間等,這些要求的實現會提高商品的生產成本、降低資本自由流動的可能性,從而影響資本的積累。雙重危機共存于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中,最終形成惡性循環并愈演愈烈。
科威爾則痛斥資本是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他將資本視為自然的敵人以及人類的劊子手,認為“資本不僅直接降低了生態的地位,還制造了大量可操縱的、異化的、負債累累的人”。[2](P17)正是由于資本具有求利性的本質特征并不斷膨脹才使得違背生態原則的生態危機產生與惡化,科威爾由此打開了生態批判的資本視界。他立足于馬克思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相互矛盾理論,指出資本的存在標志在于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交換價值是至上的,使用價值服從于交換價值。資本將全部的有用之物轉化成使用價值并不斷擴大使用價值的范圍以實現商品生產一般化,與此同時,它還不斷貶低使用價值,力圖達到交換價值征服使用價值的目的。滿足需要并不是商品生產的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交換金錢或其他商品,要想買其他商品就需要賣更多商品,商品由此失去了使用價值而只殘留著交換價值。他認為資本增長實質上是交換價值增長。逐利生產不僅加快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步伐,也加快了資本的流通速度,資本的無限擴張及其不斷降低生產條件的趨勢帶來的即是自身的反生態性。“每一資本單位都是‘不增長就滅亡’;每一個資本家都必須不斷拓展市場擴大利益,否則就會失去其在資本主義中的等級地位。在經濟發展以消耗其他一切為前提的機制下,通過不斷擴大領域追求利益,是自然的不斷貶值,不可避免地帶來生態危機。”[3](P101)因此,資本應當為生態危機負責。
科威爾還指出“資本主義是人類的癌變”。[2](P18)資本主義的增長是一種癌性增長,它造成了窮富兩極分化,擾亂了世界體系,“致癌病毒”不斷自我復制、自我擴張,消耗著生態系統,損壞了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與此同時,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生產方式并不具備修復生態的能力。在奧康納著重闡發的雙重危機理論基礎上,科威爾提出了“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正在歷史性地走向崩潰”的結論。“用一種重生的精神和對生命的尊重來直面這種苦難,遠遠好過屈服于垂死的資本主義所指向的寒冷黑暗的死亡結局”,[7]因此建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成為一種必然選擇——恢復使用價值是生態社會主義的邏輯訴求,克服勞動異化、使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構成了生態社會主義的基礎。“資本和未來只能二者選其一。如我們選擇了后者,那么資本主義就必須被廢止或者用另一種生態友好型社會制度來替代。”[3](P131)
二、關于生態環境危機深化的路徑
奧康納在討論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發生發展過程時借鑒與延伸了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將資本主義城鄉的二元對立擴展至全球發達和欠發達國家與地區的不平衡發展。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人要想生存需要同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即新陳代謝。“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至死亡而必須與之交往的、人的身體。”[5](P95)無論是人抑或動植物,都是依靠同自然條件的物質聯系與能量轉換來維持自身的生命活動,如果新陳代謝循環出現斷裂,那么必將導致生態系統的破壞與失衡,引發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背景下,城鄉之間的二元分離中斷了人與土壤的物質交換和代謝:土地的營養物質以衣食形式輸送到城市供人們消費與享用,而人們使用后卻是以垃圾的形式排走,并不能返還土地以補充其營養,損害了肥沃土壤的生長能力。“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條件。”[6](PP552~553)而工廠向農村轉移、化肥的大量投入等一系列惡行亦加劇了新陳代謝的斷裂。
奧康納詳細闡釋了城鄉對立所致的新陳代謝斷裂對人和土地之間物質變換的惡劣影響,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對于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及引發的危機。與此同時,他在馬克思“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的基礎上以經濟學視域進一步考察了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在奧康納看來,不平衡發展通常表現為“歷史性生成的工業、農業、礦產業、銀行、商業、消費業、健康、勞動關系以及政治結構等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平衡狀況”。[1](P301)從政治經濟角度看,不平衡發展表征了工業、金融、商業資本在一些領域相較于其他領域積累速度更快,聚集成更大的集團或聯合體,并具有更大的政治力量;從社會經濟角度看,不平衡發展導致了工業資本在所有權與控制力方面的集中化趨勢同空間結構上的集中化趨勢相聯系。不平衡發展使得對能源與生產資料等自然資源的榨取集中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廉價的原材料降低了資本主義生產成本,促進了資本積累,而又使對自然的攫取變本加厲,逐漸形成了惡性循環并加劇了全球性生態危機。發達和欠發達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社會、政治形態相結合的聯合發展,一方面使欠發達國家與地區的人們向發達國家與地區遷移、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大量涌入城市,對遷出地和遷入地的生態環境都造成了破壞;另一方面也使發達國家與地區的污染伴隨著資本和技術輸出轉移至欠發達國家與地區。因此,聯合發展亦加重了不平衡發展。不平衡發展與聯合發展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征,致使全球性生態危機加速蔓延。
科威爾則從經濟增長對于能源資源使用造成影響的角度出發探討了生態環境危機深化的過程。他認為,導致生態危機的元兇是資本和資本主義制度,“資本融解了時間和空間,融解了生態整體性的連接點;同時,資本也塑造了喪失神圣感的人類。生活在貨幣符號之下的人類成為數量和自私無情的奴隸”。[7](P200)資本主義生產奉行經濟至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目的是追求和實現經濟增長。資本主義競爭亦導致了資本為謀求競爭的勝利而不計生態成本,忽視了自然系統,造成了生態危機。“資本選擇不顧一切地破壞生態,特別是,這種激情不惜一切代價渴望勝利。這種無情的競爭機制是系統的核心,這就保證只有非常自私和無情的人才能達到更高的資本層次。”[3](P69)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革新必然會推動經濟發展,但也會使生態危機發生速度加快、發展范圍擴大。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工業體系所需能源主要來自石化燃料,而石化燃料是不可再生的,即便利用發達的科技手段以提高能源資源的可更新性與利用率以及降低廢料的污染性,也僅能起到緩解作用而無法完全避免環境和生態危機。雖然人們在極力尋找替代能源,但也無法實現大規模的轉化,無法滿足現代社會日益增長的無限需求。核燃料是石化燃料的唯一替代品,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與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核泄漏事故已經為人們敲響了警鐘。技術在資本逐利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使得資本產生技術崇拜,而將環境問題理解為技術問題是機械、庸俗的唯物主義觀點,建立在孤立思維之上并脫離社會關系的技術本身具有反生態性特征。“科技進步論忽略了考察科技創新的作用只能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予以考察這一事實。”[8]因此,唯有實現對能源資源使用的制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放緩腳步,進而緩解生態環境的壓力。科技產品的投入使用加劇了污染程度,而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淪為了發達國家和地區轉嫁危機的重災區。
三、關于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方式
在構建生態社會主義愿景方面,奧康納堅持改良型生態社會主義,而科威爾則批判了生態改良主義思潮,提出了革命性生態社會主義的構想,指出改良主義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日臻嚴重的生態危機。
奧康納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樹在于,他從生產條件與雙重危機理論出發,勾畫出具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意蘊的生態社會主義圖景。他認為,傳統社會主義忽視了生產性正義的訴求而導向分配性正義。分配性正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致力于生產與積累的利、弊的平等分配,它同社會化生產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是相脫節的,根本不可能實現。相反,著眼于“能夠使消極外化物最少化、使積極外化物最大化的勞動過程和勞動商品(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生產性正義將“質”而非“量”放在突出位置,[1](P538)并將需求最小化,降低了自然的破壞程度。因此,社會主義應注重對資本主義的定性批判,包括對應用在生態學社會主義社會規則的生產性正義的關注。“生產性正義的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生態學社會主義。”[1](P538)生態學與社會主義具有互補性:一方面,社會主義需要生態學,生態學能夠使生產力變得更明晰,遏制對自然生態的解構與破壞,它強調交互性,給予自然內部以及社會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以極其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生態學也需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能夠使生產關系變得更明晰,終止市場統治與商品拜物教,它強調民主計劃,給予人類之間的社會交換以關鍵作用。資本積累所致的經濟和生態危機這一現實條件使得生態學與社會主義的“聯姻”成為可能。
奧康納主張“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動”,[1](P476)建立“第五國際”。在他看來,資本主義體制內部具有能夠自行運轉的反饋機制,既可以靠自身直接調節,也可以間接通過社會運動加以改變。生態環境保衛戰及為環境立法等方式能夠起到規范生產過程、促進社會轉型的作用,達到實現發展與緩解危機的雙重效果。因此,他提出了在不觸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將傳統社會國有化轉換為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改良方案。這種方案缺乏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反思,實際上為資本主義作了辯護,其所倡導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生態“資本主義”。
科威爾選擇了一條與奧康納截然不同的實現路徑。他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遏制資本的無限擴張,修復與重建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拋出了極具震撼力的問題——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科威爾指出生態社會主義必須實行以生態為中心的生產,推翻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求利觀念、消除交換價值而實現使用價值,維護自然的內部平衡與內在價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和內在價值形成了三角結構,這種結構能夠打破資本的垂死掙扎。”[7](P203)作為“事物的本性”,內在價值屬于自然的本質價值,是一個“反政治經濟學(Anti-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它是科威爾基于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同生態自然相敵對的立場而提出的,其旨趣在于向被交換價值所征服的使用價值回歸,為生態系統完整性而奮斗。“如果生態社會主義指出使用價值的斗爭是為了抑制資本主義的生態滅絕,如果內在價值能夠使自然界成為一個整體,那么,生態社會主義就可以被視為一種同盟。”[2](P20)這個“同盟”的主體即是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及內在價值,而對立面則是資本主義。
在科威爾看來,生態中心化生產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出的商品沒有交換價值的附加利益,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得到了充分發揮,彰顯了勞動自由及對勞動者的認可,因而是一種愉悅、快樂、滿足的生產。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異化勞動被克服,人的勞動實現了自由與解放,逐步走向了“生產者的自由聯合體”。由此可見,科威爾的生態中心化生產思想繼承與發展了奧康納的生產性正義思想,他將社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有機結合,綜合了生態社會主義與生態自治主義的建構原則,突出了生產的價值訴求,亦拓寬了美國生態社會主義的研究視野。同時,科威爾并沒有遵循綠色和平運動的非暴力原則,主張如果社會制度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資本對生態的破壞到了無藥可施的地步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措施。他還提出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政黨以領導革命實踐,推動生態社會主義全球化與國際化。生態社會主義所直面的是世界各個角落的生態危機,是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出的“斗爭”道路,是一種從現實性指向可能性的“預示”。然而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缺少社會變革的可行性方案,實質上是一種理想主義,具有鮮明的烏托邦色彩。
四、聯系和啟示: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
作為同處于20世紀90年代的生態社會主義的杰出代表人物,奧康納與科威爾為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理論為人類解決生態危機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盡管其理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們的生態思想中所蘊含著的人文精神和人本思維以及致力于人的存在價值和美好生活的實現等,都是可以為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理論所借鑒的,如“生態社會主義最最重要的是為了生命,致力于生命的延續和繁榮。這就是生態社會主義存在性的核心意義”。[4](P198)新時代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始終關心人民幸福、關注人民福祉、注重人民未來,著力構建美麗中國,放眼于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這種人文關懷映襯出其與奧康納和科威爾的生態思想的理論融通性。由此可見,奧康納與科威爾的生態思想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理論在理論原則、價值理念、精神旨趣、追求目標等方面具有互通性與契合性。奧康納與科威爾的生態思想為新時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全球性視角下生態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范式借鑒。
第一,注重引導全社會樹立科學的生態價值觀。無論是奧康納的“生態理性”還是科威爾的“人類自然”概念都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因此,生態價值觀強調從系統和整體的角度出發,以生態思維方式深刻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科學詮釋人類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取向、理念、尺度及標準,在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中開啟“生態文化啟蒙”。“培育全社會的生態文明意識,創新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開創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正是生態文化啟蒙的宗旨所在。”[9]在新時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應全面貫徹綠色發展理念,不斷賦予生態價值觀以新的時代內涵,在夯實生態價值觀的基礎上使其真正落實到人們的實踐中去。例如,通過現代傳媒等創新性方式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以強化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在物欲橫流的社會中著重樹立綠色、健康、理性、科學的消費觀念;動員全社會參與生態環境“保衛戰”,組織豐富的環保公益活動等,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精髓與真諦潤物無聲地融入到人們的行動之中,為生態文明建設貢獻思想力量。
第二,大力倡導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人類是生產和生活的主體,其不合理的生產活動與生活習慣必然會造成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奧康納強調生產性正義,科威爾強調生態中心化生產,這啟發生態文明建設還應在社會生產方面下功夫。在“堅持保護優先”原則的基礎上著重整治污染企業,加強環保企業的投入,不斷優化產業結構,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經濟后盾。同時還應提高與改善環保技術以促進資源的循環利用,注重生產的節約性和環保性,實現資源的再利用、減量化與可循環,進而推動經濟與生態的雙贏。奧康納和科威爾都認識到了使用價值的重要性,提升了使用價值的地位,這意味著同生態文明建設相適應的生活方式亦至關重要,其關涉人們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因此,應鼓勵人們養成健康環保的生活方式與綠色消費習慣,反對消費主義價值觀。“正是由于顛倒了需要、商品、消費和幸福的關系,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不僅造成了人自身的異化、人與人關系的異化,而且也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10]同時,應積極發揮人們在生態環保中的監督作用和積極性,凝聚各方力量以形成生態文明建設合力。
第三,不斷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奧康納和科威爾對于資本主義制度都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建設生態社會主義才是改善生態環境、緩解生態危機的有益探索。制度是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根本所在。近年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確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快車道,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將不斷展現在世人面前”,[11]但仍需應對好諸多挑戰、把握好重要環節。例如,在對能源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的過程中,應堅持科學開發、合理利用的原則,建立健全生態環保管理體制;國家雖已建立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但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主體作用仍有待加強,應進一步完善中央和省級環境保護督察體系;就我國現狀來看,生態環保法規需要進一步完善,尤其是要建立嚴格的執法機制,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以健全的制度為保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密切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不斷開創生態文明建設新局面、譜寫美麗中國建設新篇章。
第四,積極構建生態文明共同體。奧康納主張“組織一起國際性的激進綠色運動”,[1](P476)并寄希望于“第五國際”,提出“保護第一”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而科威爾主張通過“自由聯合的勞動”走向完整的共同體,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政黨以實現“紅”“綠”結合,在“協作”與“合奏”中構建生態社會主義“聯盟”。奧康納與科威爾所提出的方案和構想中蘊含著“眾行遠”的深刻智慧,這啟示新時代的中國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應當著力使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走出中國、邁向世界,建構生態文明視域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21世紀初的今天,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狹義上的社會文化概念,而是應明確包含人與自然關系、社會與自然關系的維度或層面。”[12]生態文明共同體不僅激發和喚起了我們對于自然環境興衰攸關人類共同利益的認知意識、對于人類賴以生存的共同家園的情感認同、對于保衛與重構生命(地球)共同體的自覺行動,同時也推進了一種全球系統性與整體性的社會生態轉型以及文明性重建。因此,新時代的中國在遵循“自立”和“立他”雙重旨趣基礎上應繼續發揮凝聚共識、引領示范、搭建平臺、匯集力量、交流對話等重要作用,講好中國“綠色故事”、傳播中國“綠色聲音”、分享中國“綠色經驗”,在不斷建設綠色中國、美麗中國的實踐中充分彰顯“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的理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