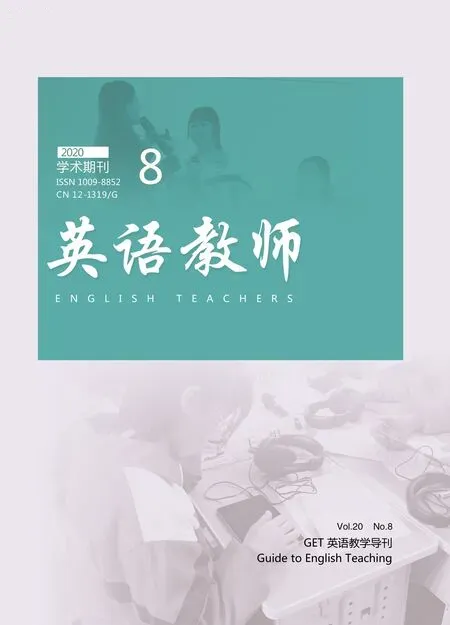譯者行為批評視域下漢語鄉土語言英譯的翻譯態度研究
——以《紅高粱家族》中外譯本諺語翻譯為例
任 俊
引言
“鄉土語言”是指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傳、通俗精練,并流傳于民間的語言表達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周領順 2016a)。它作為一個專業術語,始于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漢語‘鄉土語言’英譯實踐批評研究”的成功立項和周領順(2016a)《鄉土語言翻譯及其批評研究》一文。隨著翻譯領域的不斷發展,學者們也感受到了鄉土語言英譯的難度。鄉土語言中包含的文化底蘊難以在目的語中達到相應的表達效果。業界對其翻譯也未確定統一標準,相關學術研究多集中在翻譯策略研究這一角度。
葛浩文作為一名漢學家,在中國文學作品外籍譯者群中享有盛譽,翻譯了大量中國鄉土文學作品,包括以莫言小說為代表的《紅高粱家族》《蛙》等十多部。針對葛浩文譯作的相關學術研究眾多,但從譯者對比這一角度入手的數量較少。中國譯者鄧世午、于大波于20世紀80年代曾譯過《紅高粱家族》(節選)、《亞細亞瀑布》等作品,相比較于葛浩文譯本,中國譯者的譯本并未引起較多注意。下面將對比分析《紅高粱家族》的外國譯者葛浩文和中國譯者鄧世午、于大波兩個英譯本(以下簡稱葛譯本、鄧于譯本),探尋其中譯者行為與翻譯態度的差異,從而為對比翻譯研究提供借鑒,推動中國文化的傳播和進步。
一、《紅高粱家族》譯介情況
《紅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一部長篇小說,故事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描述了“我”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在抗日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英雄故事。《紅高粱家族》(葛譯本)于1993年在美國出版,廣受贊譽,被視為《紅高粱家族》官方譯本。但實際上,《紅高粱家族》首譯本為中國譯本,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由中國譯者翻譯并收錄在《中國當代軍事文學作品選》(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一書中,并由當時中國作家協會所屬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于1989年出版,這也是莫言作品首次被譯為英語。馬士奎(2018)提到,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有能力翻譯作品的人十分有限,中國譯本由新華社英文組的兩名記者鄧世午和于大波翻譯,過程十分艱難。我國資深翻譯家胡志揮(2012)先生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發文詳細說明了《紅高粱家族》首個英譯本問世的艱難歷程。《紅高粱家族》作為鄉土文學的典型代表,其中涵蓋眾多鄉土語言表達。下面聚焦于《紅高粱家族》第一章中的兩個英譯本鄉土語言翻譯的對比分析,以期為以后的翻譯提供啟示。
二、譯者行為與譯者翻譯態度的關系
(一)譯者行為批評理論與“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
翻譯實踐歷史悠久,而翻譯理論的研究并不多見。隨著“社會轉向”等思潮的到來,“譯者”這一角色在翻譯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針對譯者行為進行考察、分析逐漸成為翻譯研究的核心問題。周領順(2014)開創的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指出,“譯者行為”是指“社會視域下譯者的語言性翻譯行為和社會性非譯行為的總和”。譯者行為批評綜合考慮翻譯內和翻譯外因素,為譯文合理性提供新的分析視角,也為翻譯活動作出更加科學、全面的解釋和支撐,是翻譯批評學科的進一步細化,將翻譯批評推進到了翻譯內、外相結合的翻譯社會學研究階段。在此基礎上,為構建全面、客觀、科學的翻譯評價體系,周領順(2014)進一步提出“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求真”是“務實”的基礎,“求真”是譯者使譯文達到忠實的必要過程,是確保翻譯之為“翻譯”的根本;“務實”高于“求真”,求真為本,務實為用。這一評價模式為譯評者提供了一種動態譯者行為評價模式,同時譯者也可用作自身的翻譯準則。下面基于此評價模式分析中外譯者翻譯《紅高粱家族》的不同翻譯策略,探究譯者翻譯態度的差異性,從而深化對翻譯行為的認識,豐富翻譯批評的廣度和深度。
(二)譯者行為與譯者翻譯態度的關系
“翻譯是復雜的文化交流活動,承擔著精神交流的中介作用,譯者的作用不可忽視。作為橋梁,翻譯的首要職能是溝通。因此,面對作者和讀者,面對出發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譯者應采取怎樣的態度和溝通方式,是翻譯研究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許鈞 1997)譯者的身份和態度在整個翻譯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譯者的態度代表著譯者個人內在的一種心理傾向,可以說是一切翻譯行為的心理觸發點,能夠影響翻譯行為、評判翻譯質量,甚至決定翻譯理論研究的道路與方向(屠國元、袁圓 2015)。譯者采取不同的翻譯態度會外化成不同的譯者行為,或忠實于原文,或向讀者靠攏,在譯文中會存在清晰的譯者行為軌跡;反之,譯者留下的行為軌跡也可作為歸納其翻譯態度的重要依據。因此,譯者行為與譯者翻譯態度即外化和內化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具體體現,后者是前者的內在傾向。
目前,譯學界針對譯者翻譯態度的具體文本分析數量較少,將譯者行為批評理論與譯者翻譯態度結合起來,并對中外譯者兩個譯本進行對比屬于首例。與譯者翻譯態度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譯者翻譯態度和策略之間的關系探討(如張琦2015;方莉 2006;劉滿蕓 2002);二是譯者的文化態度對翻譯產生的影響(如趙志敏 2012;袁秀鳳2002;王岫廬 2014);三是結合具體文本分析譯者的文化態度(如張季紅 2016;程福干 2015)。因此,開展譯者翻譯態度對比,對為鄉土語言譯介提供借鑒、指導具有重要意義。
三、譯者翻譯態度影響因素下中外譯者行為求真度與務實度對比分析
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強調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在整個過程中需作出各種策略的選擇和轉換。這樣譯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其翻譯態度發生變化并產生相應的譯者行為。首先,翻譯活動始終脫離不了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社會環境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社會規范、準則的要求和約束,各種思想觀念的宣傳和教育,風俗習慣的潛移默化和文化的熏陶等方式進行”(樂國安 2009)。社會環境中的文化因素是譯者需要面臨的一項困難和挑戰,這種困難和挑戰來自歷史、地域、風俗和宗教信仰等諸多方面(屠國元、袁圓 2015)。由于中外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在譯介的過程中難免會對譯者和讀者造成一定的障礙。中外譯者在差異較大的文化背景下對翻譯產生不同的認知,對原文的處理方式必然大有不同。除了文化因素會對譯者行為產生影響外,譯者自身也有較多因素影響其翻譯態度。翻譯目標是翻譯的基礎和前提,為具體的翻譯活動指明方向。譯者出于一定的翻譯目的,在翻譯活動中朝著翻譯目標努力。讀者在譯文中隨處可見譯者的痕跡。“鄉土語言”作為鄉土文化的結晶,譯者的審美傾向對該類表達也有一定影響。
下面將從影響譯者翻譯態度的文化及個人因素對葛譯本和鄧于譯本的鄉土語言英譯進行分析。通過影響因素對比譯者行為,再總結出譯者的翻譯態度,從而豐富翻譯實踐內容,推動中外文化交流。
(一)文化差異
鄉土語言作為地方民俗文化與風土人情的結晶,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色。因此,譯者在進行譯介時不僅要做到意思轉換,還要朝著翻譯效果一致而努力。
例1:他問:“你沒送他點見面禮?”
葛譯本:“You didn’t give him anything to grease the skids?”
鄧于譯本:“Didn’t you give him some gift on the first meeting with him?”he asked.
例2:父親聽到奶奶說:“買賣不成仁義在,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
葛譯本:Father heard Grandma say,“Even if you can’t agree,you 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r.This isn’t the time or place to fight.Take your fury out on the Japanese.”
鄧于譯本:Father heard my grandma saying:“Friendship still exists after the failure of business deals.Here is not a place to fight.G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f you want to show your gallantry.”
例3:那天他喝了個八成醉,玲子闖進去,正如飛蛾撲火,正如羊入虎穴。
葛譯本:He was pretty drunk that day,and when Lingzi burst into his room,it was like a moth drawn to a fire,or a lamb entering a tiger’s den.
鄧于譯本:That day he was more than half drunk.Lingzi had come like a flying moth darting into the flame,a lamb entering a lion’s den.
例1中的“見面禮”本義為“初次見面贈送的禮物”,原文中中年人問羅漢大叔是否給監工準備了“見面禮”,意為行個日后方便,不受欺負。葛譯本為grease the skids,根據 Farlex Dictionary of Idioms中指出grease the skids意為to work to prepare something for success,葛浩文在翻譯時采取務實策略,在目的語中找到相應意思的表達進行套譯,避免造成目的語讀者的理解障礙。而鄧世午、于大波則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保留了原文特色。
例2中的“買賣不成仁義在”出自《紅旗譜》,意為“雖然買賣沒有做成,但彼此間的感情還存在,不會為了這點事兒傷了和氣。”葛浩文在翻譯時結合原文具體語境,針對“余司令”和“冷支隊”劍拔弩張之時“奶奶”出來調和氣氛說的這句話進行了轉換,采取歸化策略,更加便于目的語讀者的理解,同時將原文的具體意義表達了出來。鄧世午、于大波明顯采取異化策略對原文進行直譯,保留了原文信息的完整性,對于個別詞語選擇了簡化翻譯,更加方便了讀者理解。
例3中使用成語“飛蛾撲火”和“羊入虎穴”。“飛蛾撲火”意為飛蛾撲向火焰,自取滅亡;“羊入虎穴”或“羊入虎口”表示較弱的一方處在危險的情況之中。葛浩文和鄧、于在處理“飛蛾撲火”時都采取求真策略進行翻譯,向原文靠攏,將意思完整保留;同時達到了良好的譯介效果,給目的語讀者帶來了閱讀新意。對于“羊入虎穴”,葛浩文譯為a lamb entering a tiger’s den,鄧世午、于大波則譯為 a lamb entering a lion’s den,二者的差別在于對“虎穴”的英譯:葛浩文直接按照字面翻譯,而鄧世午、于大波處理為a lion’s den。中文中的老虎多含褒義,象征勇敢威猛;英語中的老虎多含貶義,象征邪惡。中文中的老虎和英語中的獅子具有相同寓意。出于以上考慮,再結合具體語境,原文中的“虎”更偏向于邪惡的意思,故而鄧世午、于大波作出的調整與原文意思相悖。
葛浩文作為外國譯者,處理鄉土語言首先是挖掘其真實含義再采取異化翻譯策略。他說:“為求忠實,我首先試圖忠實于作者的語氣,尤其是在對話中。”(Goldblatt 1980)對于文化信息濃厚并難以在目的語讀者中達到相同效果的表達,葛浩文在自身理解的前提下采取歸化策略,甚至在部分翻譯上進行省略,因此他理解有偏差時會造成誤譯的現象。鄧世午、于大波在翻譯時同樣受到中外文化差異的制約,出于為讀者的考慮,翻譯時部分沒有保留原文特色,直接采取讀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達進行處理。
(二)翻譯目標
譯者的翻譯目標會直接影響譯者的翻譯態度,或向原文靠攏,或為讀者翻譯,是翻譯活動內部或外部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還會直接反映在譯者行為上,通過行為上的傾向也能總結出譯者的翻譯態度。
例4:奶奶雖然想過上馬金下馬銀的好日子,但更盼著有一個識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熱的好女婿。
葛譯本:Grandma pon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mount to the jingle of gold and dismount to the tinkle of silver,but what she truly longed for was a good husband,handsome and well educated,man who would treat her gently.
鄧于譯本:Grandma was glad to live a life of plenty,but she also longed for a handsome and attentive husband who was well-educated.
例5:中年人說:“您老,犯不著跟這根糟木頭生氣。”
葛譯本:“Reserve one,”the man said,“that stinking blockhead isn’t worth getting angry over.”
鄧于譯本:The middle-age man said:“Sir,you needn’t get angry with such a useless person.”
例6:余司令摳起一塊土坷垃,投到方六的臉上。
葛譯本:Commander Yu picked up a dirt clod and tossed it in his face.
鄧于譯本:Yu throw a stone at Fang Liu who was snoring.The stone hit his face.
例4的俗語“上馬金下馬銀”指待遇豐厚,生活豐裕。原文結構對稱,節奏押韻,葛浩文在翻譯時將其處理為mount to the jingle of gold and dismount to the tinkle of silver,對文化信息濃厚的詞語表達采用求真的手法,生動地保留了原文特色,保持結構、節奏與原文的一致。鄧世午、于大波則處理為live a life of plenty,清楚地表達出俗語所蘊含的真實含義,在目的語讀者中引起共鳴,最大限度地減少文化障礙,但在一定限度上丟失了原文的韻味。
例5中“糟木頭”原意指木頭腐爛,爛木頭,引申為沒有用的人或物。葛浩文在翻譯時側重于“木頭”二字的翻譯。中文中的“木頭”包含形容人腦袋不靈光、死板之意,因此葛浩文將其譯為stinking blockhead,考慮到原文在讀者群中不易被接受,因此在更高程度上堅持務實策略。鄧世午、于大波作為中國譯者在理解原文意思時更加順暢,將“糟木頭”譯為a useless person,在更大程度上貼合原文原意,堅持求真策略。
例6中“土坷垃”是方言,本義為“土塊”,葛浩文翻譯為dirt clod,雖然未與其字面意思完全一致,但與原文含義基本無差,所以采取求真策略,在意義對等的基礎上達到了在目的語讀者間相同的效果。鄧世午、于大波直接翻譯成stone,采取務實策略對原文簡化,但其意思與原文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超務實,這也證明了譯者為讀者所做出的努力。
葛浩文說:“作者是為中國人寫作,而我是為外國人翻譯。翻譯是個重新寫作的過程。”明確指出他為外國人即目的語讀者群服務,在翻譯過程中以求真為主,向西方讀者傳播中國文化,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受到讀者的歡迎;同時采用務實策略,如意譯、省譯等,這是堅持以讀者為中心,為讀者考慮的具體體現。鄧世午、于大波承擔《紅高粱家族》的翻譯工作,本著推動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高國際影響力的宗旨,在鄉土語言等特色表達的翻譯上采取歸化策略,期望在目的語讀者中產生相同的表達效果,引起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學的重視。中外譯者雖在翻譯過程中采取的翻譯策略有所差異,但都受到了翻譯目標的影響。
(三)審美傾向
審美傾向是譯者對翻譯結果的美學期待。翻譯的過程同時也是審美的過程。譯者的審美傾向體現在譯者對原文的理解及譯文的表達上。鄉土語言作為中國特色文化的組成部分,對于中外譯者來說,使譯文能夠達到和原文一致的表達效果還是具有較大挑戰性的。
例7:奶奶說:“……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車打了,然后你們就雞走雞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葛譯本:“...then go out and destroy the Jap convoy.After that,chickens can go their own way,dogs can go theirs.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don’t mix.”
鄧于譯本:“...and ambush the Japanese trucks the day after tomorrow.After that,you two just mind your business.”
例8:父親早就知道……,但這些人住在村里時,攪得雞飛狗跳,仿佛滿村是兵。
葛譯本:Father knew all alone that...But when they were quartered in the village,they had stirred things up so much,with chickens squawking and dogs yelping,that you’d have thought it was a garrison command.
鄧于譯本:My father had long known that...But when they lived in the village,their disturbing activities even frightened the chickens and dogs as if there were soldiers throughout the village.
例7中“雞走雞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作為一個典型的諺語表達,意為各自管理各自的事情,互不侵犯。在翻譯時,葛浩文處理為chickens can go their own way,dogs can go theirs.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don’t mix。譯文完整地再現了原文含義,保證了文本的正確性。在此基礎上,譯者也充分展現了原文的語言風格和魅力,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對原文意義和風格求真,達到了理想的譯文審美效果。鄧世午、于大波在翻譯時也出于對讀者理解的考慮,對于文化內涵深厚的表達采取異化策略,傾向于譯文在目的語國家的譯介與接受情況,對原文信息的保留程度有所取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譯文審美效果較弱。
例8的“雞飛狗跳”屬于成語翻譯類,對于此類表達生動的成語,譯者在處理上也有所不同。“雞飛狗跳”形容把雞嚇得飛起來,把狗嚇得到處亂跳,驚慌得亂成一團。葛浩文處理為chickens squawking and dogs yelping,在意思與結構上都與原文保持一致,在“求真”的基本層做到了完全對等;同時形象地表達出了原文中的畫面感,給讀者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間,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且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符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迎合了譯者的審美傾向。鄧世午、于大波譯成frightened the chickens and dogs,采用務實策略將成語表達簡化,一切以在目的語國家獲得理解為首要任務,因此兩位中國譯者的審美傾向以簡潔為主,將所有認為會在目的語讀者群中造成溝通障礙的表達簡化翻譯,在原文韻味上有所取舍。
譯者的審美傾向包括對原文的理解及處理,同時包括對目的語國家讀者群喜好的把握。葛浩文翻譯鄉土語言時以原文的“鄉土味”為重,在表達上可以明顯看出葛浩文對原文含義的保留,但他自身也提到“希望能做到既保留文化特色又保持譯文的流暢。但很多時候不能兩者兼得,所以必須作出選擇”(Goldblatt 2012)。這種選擇往往是以讀者為中心的。葛浩文在對譯文處理存在障礙時,出于對相同語言讀者的了解而采用他們易于接受的表達。鄧世午、于大波作為與原文相同語言的譯者,在鄉土語言的譯文處理上卻沒有濃厚的“鄉土味”,雖然在對原文的理解上比漢學家要更加深刻,但在處理譯文時過多地考慮目的語讀者的喜好,大多數情況下簡化翻譯,原文的表達之美在譯文中沒有較多保留,傾向于簡潔的譯文表達,以不給目的語讀者造成任何理解偏差。
四、結論
在譯者行為批評視域下對文本進行分析,清晰地對比出外國譯者與中國譯者翻譯同一鄉土文學作品時,在處理方式上存在較大差異。本研究在“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的指導下,結合影響譯者翻譯態度的因素對鄉土語言英譯進行對比分析,可以看出,漢學家葛浩文的翻譯態度總體上是以保留原文特色為主,存在理解障礙時向讀者靠攏,采用歸化策略保證譯文的質量,以提升讀者的閱讀興趣。中國譯者的翻譯態度是以讀者為中心的,在鄉土語言翻譯上大多采用務實策略進行簡化處理,甚至有些處理為“超務實”,一切為目的語讀者服務。在譯者翻譯態度的影響因素下對譯者行為進行對比,突出譯者行為之間的差異,也證明了這些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翻譯態度本身主觀性較強,難以直接定義,從譯者行為出發對譯者的翻譯態度進行總結概括,以事實為依據,更加科學、客觀,從而對譯者形成更加客觀、全面和科學的認識。針對鄉土語言的翻譯,翻譯學界并沒有統一的標準,但周領順曾提出“最理想的譯者模式是作者、漢學家譯者和中國譯者三者相結合的模式”(周領順、丁雯 2017)。對比不同身份下譯者行為的差異,總結出譯者不同的翻譯態度,有助于提升鄉土文學作品的翻譯質量,也能給譯評者提供新的思考路徑和研究方法。鄉土語言英譯也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有著緊密聯系,其成功譯介能提升全體國民的文化自信,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供指導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