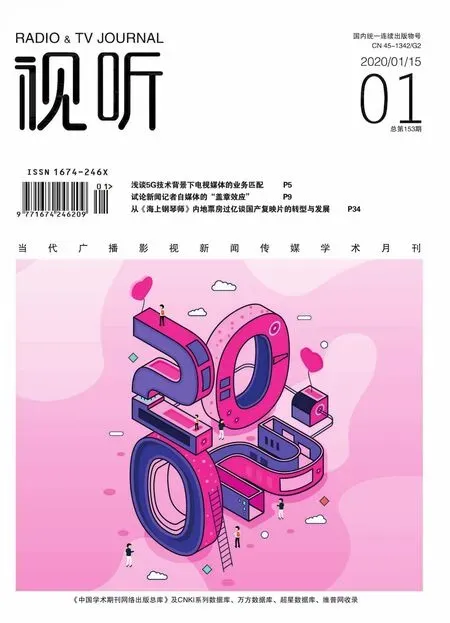快時代與慢綜藝
——對綜藝同質化現象的反思
□ 劉 莉
消費社會的來臨使人和物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文化藝術也不例外。千篇一律的電視節目扎堆出現,沖擊著觀眾的視聽感官,在人們逐漸疲勞之時,節奏舒緩的慢綜藝起到了一定的治愈作用。
一、快時代背景
(一)快節奏下的文化焦慮
經濟發展之后,“快節奏”成為了一個常見的詞匯。以消費社會為例,人們迅速而頻繁地進行消費,成為了當今的常見現象。二戰后,隨著加爾布雷斯宣稱人們開始進入“非常豐裕且豐裕程度還在不斷增長的”社會①,學者們開始以消費為中心描繪世界圖景。從表面看來,大眾被商品所包圍,但由于商品是符號的體現,所以在消費社會中,大眾其實是被符號所淹沒的。體現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物品的符號價值大行其道,形成了對人的支配,人們便會更加期待從其他方面得到滋養和熏陶,例如文化藝術。
(二)快綜藝下的審美疲勞
被符號價值所支配的人們渴望一片寧靜之地,但是在傳媒藝術時代,人們卻仿佛又掉進了一個新的漩渦。尼爾·波茲曼的著作《娛樂至死》的封面上展現了這樣一個畫面:一家四口圍坐在沙發上觀看電視,然而四個人都是沒有腦袋的,這意味著他們只是電視節目的被動接收者。這一具有諷刺意義的畫面其實是當代大眾的真實寫照,影視藝術中缺乏新意千篇一律的內容缺乏思辨性,長期觀看此類內容的觀眾也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
放眼當今的電視綜藝市場,的確如此。當一檔節目開創了先河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之后,電視節目制作人們便會如法炮制出上百個相同性質的節目。在這場商業資本的狂歡中,人們在不停地角逐利潤,迎合大眾的胃口,于是同類型的綜藝節目層出不窮。但是在快節奏的時代背景下,競技類真人秀中的對抗、競技等內容一開始會讓觀眾耳目一新,但當同質化的節目完全占據了熒屏,觀眾便會不可避免地感到麻木。大眾狂歡熱潮下,人們開始渴望重拾傳統文化,社會文化和價值審美從膨脹走向內斂②。
(三)快傳播下的信息過剩
信息轟炸之下,人們只能選擇部分內容進行簡單解讀。從媒體的角度來講,他們所營造出來的媒介生態是以吸睛效應等作為導向的,追求的是一種審美驚顫。媒體之間的競爭愈發激烈,他們為受眾提供海量的信息,配以奪人眼球的宣傳手法,渴望服務對象的駐足停留。從受眾的角度來講,作為被爭奪的對象,他們無時無刻不面臨著媒介壓力,需要做出選擇。然而在每一個快速的選擇過后,受眾對該信息所體現出來的價值卻很少會進行解讀。正如盧卡奇所認為的那樣,在人類與機械的關系中,本應該是人類處于主導地位,但是到頭來卻變成人類被機械所支配。這種形式讓我們的內心變得麻木,只有進行創新的思考與嘗試,才有可能擺脫這種快節奏下人被逐漸物化的局面,讓人們回歸內心的本真。
二、慢綜藝分析
在受眾面臨與日俱增的媒介壓力時,慢綜藝的出現便宛如一場及時雨,讓受眾從競技的疲累中暫時地解脫出來。所謂慢綜藝,是相對于競技類快綜藝而言的,節目嘉賓之間沒有激烈的身體對抗,而是將日常生活展現在鏡頭之下。2009年,挪威推出了鐵路紀錄片《卑爾根鐵路的分分秒秒》,其拍攝的方式十分簡單——將攝像機放置在窗邊,由起點站開始,到終點站結束,記錄一路上的風景點滴。這部紀錄片一經推出便獲得了意外成功,“慢電視”自此開始被人們關注。近年來,由于市場的變化和受眾的轉型等原因,慢綜藝開始集中出現,不僅收獲了高收視率,也在網絡上引發了熱烈討論。
(一)節目形式
嚴格說來,慢綜藝節目并不是一種新的節目類型,而是一種新的制作理念。針對當前受眾普遍存在的文化焦慮、審美疲勞等問題,慢綜藝著重通過人設、體驗等元素來滿足受眾,用情感內核去打動受眾疲憊的心靈。
慢綜藝具有體驗感的主題設置是其頗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例如湖南衛視《向往的生活》的節目內容十分簡單,只是嘉賓與主持人在農家小院里做一日三餐,但是這簡單的一日三餐卻能體現出洗去鉛華的真實。每一位嘉賓到達蘑菇屋之前需要點菜,主人公們據此做出一頓飯。素顏出境的明星們沒有臺詞,也沒有劇本,甚至會出現嘉賓在床上呼呼大睡幾小時的情況,節目中鏡頭大體上也負責真實記錄。但正因為如此,明星們接地氣的一面才被表現出來,從而在簡單中升華,展現出煙火氣息。性格各異的嘉賓展現出來的內容是有人情味和性格邏輯的,觀眾們從中往往可以觀照自身,從而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農家小院中,被逐漸治愈。
可以看出,慢綜藝對體驗、人設等元素的運用十分充分。一方面,觀眾是旁觀者,與節目存在一定的審美距離;另一方面,觀眾又是體驗者,他們將自己的親身經歷代入到節目中,產生一種自己也被治愈了的滿足感。
(二)敘事方式
在真實的主題設置之下,慢綜藝在情節展示上也是以真實自然為主,再輔以個別的亮點。在《向往的生活》中,節目組在屋內安裝隱蔽攝像頭,最大限度地還原了主人公從日出到日落的生活場景。燒柴生火做飯之后沒過多久,又要開始為下一頓飯忙碌,明星們多次素顏出鏡,在做飯的間隙絮絮叨叨地聊著天。作為觀察類綜藝,其所營造出來的“生活在別處”的意象深深地吸引著忙碌的都市人,當本真在這樣的生活中被表現出來時,觀眾便會自然而然地認為這就是他們“向往的生活”。田園的生活節奏變慢,人們便會注意到天上的星星,留下充足的時間去等待一顆流星劃過,讓自己的心靈得到凈化。正如電視觀察者楊智帆所說:“《向往的生活》用一種清新的田園風光,向大家展示著農村生活前所未有的魅力。”③
在浩如煙海的素材中,節目組通過“減法藝術”,只留下必要的內容。貫穿節目整體的溫暖的色調、踏實舒心的氛圍、萬籟俱寂時天上的繁星點點,村落里可愛的中華田園犬小H 等,都是節目的動人之處。在點菜做飯等重復事件中,注重人物之間的互動,聚焦人物情感,使節目變得豐富而濃郁。
(三)價值取向
慢綜藝所體現出來的正是一種歸隱的價值取向。而這種歸隱與陶潛不同,更多是一種內心的安寧。忙碌的都市人哪怕內心再疲憊,也很少會去真正選擇“采菊東籬下”的生活。他們需要在忙碌的間隙能有休息的機會,尋找到片刻的寧靜。所以慢綜藝所傳達的歸隱,更多指的是內心。在略顯重復的日常生活中去發現許多亮點,一道賽螃蟹,雖然做法簡單,但是其中所夾雜的孫紅雷和黃磊之間的回憶,讓人不自覺地動容。夜晚室外難以拍攝的情況下,嘉賓們依然堅持等待流星出現,在其出現的那一刻,他們手舞足蹈,眼含淚花。正如何炅所認為的那樣,農村的星星比城市里更亮,是因為這里更慢。人們愿意花上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去虔誠地等待一顆星星,只為在它出現的那一刻體驗到透徹心扉的舒適感。通過一道賽螃蟹,或是一顆流星,人們觀照自身,觀照自己與物之間的關系,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加懂得生活乃至生命的意義。例如《親愛的客棧》以“慢下來,去生活”作為標語,點明節目主旨,《向往的生活》將節目立意直接體現在標題上,都是在傳達一種遠離喧囂、回歸自然的意境。雖然肉身置身于田園生活中的時間是有限的,但在這有限的時間中,我們卻會回到自己的內心深處,感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體味出一種無限的境界。所謂慢,并不是指情節的拖沓與重復,而是內心的節奏放慢,在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中,關注生活體驗與人情冷暖,展現出一種從容的心態。
三、慢綜藝反思
在慢綜藝集中爆發的當下,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是否所有慢綜藝都重在傳遞人文價值,帶來內心的從容?如果不是,那么它們出現的原因是什么?阿多諾認為,我們無法用具體的概念來定義藝術,因為其本身就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自由灑脫,難以掌控。不論是在風景優美的地方開一家旅社或餐廳,還是在野外建造一所全新的房子,都是在一個遠離都市喧囂的地方完成一件系統的事,立意都是符合慢綜藝的設定的。但是透過許多節目的內容,我們卻發現其往往落入了簡單重復之嫌,只是在所謂慢綜藝的表面行走,而并沒有觸及其內核的歸隱取向,而這才是慢綜藝最打動人的地方。雖然打著慢綜藝的旗號,但其實許多節目依然馬不停蹄,不論是前期的策劃,還是節目中嘉賓的身份轉換等,都沒有慢下來的感覺。
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電視處于產品時代。所謂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為主,觀眾、廣告商等客戶的需求是節目制作需要重點考慮的因素,在商業資本狂歡的背景下,商家們為了攫取利潤,總是會選擇迎合大眾的口味。在文化工業的條件下,藝術的獨創性成為商家投資的契機④,如果一種制作理念被認為是新穎的、有個性的、符合大眾口味的,那么在科技的推動下,其會被迅速地復制生產,進入商品流通市場。久而久之,同質化現象便愈發嚴重。慢綜藝原本是為了讓浮躁疲憊的都市人得到放松,使其內心多一處棲息之地,然而在文化工業大背景下,卻陷入了又一種死循環中。不難看出,目前的慢綜藝一定程度下正處于發展的瓶頸期。由于其內容及形式不能設置得太復雜,并且要在日常簡單的內容中做出新意,不能與以往的慢綜藝重復,所以慢綜藝的策劃難度本身是很高的。所以策劃要名副其實,慢慢探索,放慢制作的步伐,在確定好整體的愿景、使命、價值觀后,以獨有的模式開啟節目,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節目風格,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同質化的桎梏,延長節目的生命周期。
四、結語
史伯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意為不同性質的事物彼此和諧才能生世間萬物,實現發展,如果只存在同一性質的事物,則無法繼續發展。消費社會下,被符號價值淹沒的人們一度喘不過氣來,所以忙碌的他們擅長尋找精神寄托。“慢”這個概念在民謠、詩歌等領域得到展現之后,又來到了綜藝的門前。然而,如果只是參與商業資本的角逐,那么慢綜藝很難打動觀眾的心。節目制作者只有讓自己慢下來慢慢地雕琢,在具有新意的節目模式下用心發現亮點畫面,再通過感性剪輯深化節目內涵,才能使觀眾感到溫暖,才能真正將慢綜藝與其他節目區分開來,賦予其真正的意義。
注釋:
①營立成.“物”的邏輯VS“人”的邏輯——論鮑德里亞和鮑曼消費社會理論范式之差異 [J].社會學評論,2016(05):65-77.
②姚文放.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的“癥候解讀”[J].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04):88-98+196.
③陳文旭.阿多諾“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的困境與啟示[J].教學與研究,2014(11):102-109.
④殷俊,劉瑤.“慢綜藝”:電視綜藝節目的模式創新[J].新聞與寫作,2017(11):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