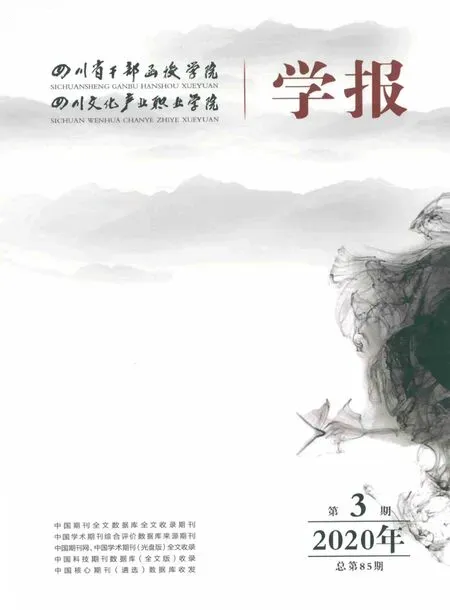中法文學作品中風塵女子形象的選擇與建構
——以《賣油郎獨占花魁》和《茶花女》為例
◇周怡佳◇
風塵女子,是非常特殊的女性職業群體,“風塵女子又稱煙花女子、青樓女子,指的是自愿或被迫走上歌妓或藝妓道路、淪落風塵的女子,一般是命運比較坎坷、值得人同情的妓女,是對妓女的美稱。”①張倓:《論“三言”中風塵女子的正面形象》,《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在中法文學的不同歷史時期,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對風塵女子這一類具有特殊性、爭議性、反叛性的文學形象的選擇與建構,其在文學闡釋層面中擁有著獨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張力。風塵女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經歷不同的世事,生發不同的故事,但都是男權社會中被極度他者化的角色,因此她們具有了文化視野的可比性。
本文將對中法文化背景中風塵女子社會文化境遇和風塵女子文學形象的社會意義進行比較,并以中國明代馮夢龍《醒世恒言》中“王美娘”莘瑤琴和法國19世紀著名作家小仲馬《茶花女》中“茶花女”瑪格麗特這兩位風塵女子形象為例,論述不同文化背景中作家對風塵女子形象的選擇與建構問題。
一、中法風塵女子社會文化境遇比較
(一)中國古代風塵女子:從事賤業的賤民階層
1.男權社會中女性被逼無奈的職業選擇
中國古代社會是典型的男權(主要體現為父權和夫權)社會,“男尊女卑”思想代表著當時的社會主流價值觀。為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需要,儒家禮教制定了“三從四德”,使之成為女子必須遵循的基本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三從四德”是 “三從”與“四德”的合稱。“三從”指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指婦德、婦言、婦容、婦紅。在這樣的社會語境塑造下,女性的婚姻觀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性觀念是從一而終、保貞守節。
為適應穩定家庭、免除男性后顧之憂的需要,儒家強調“內外有別”原則,在社會分工上凸顯了嚴重的性別歧視。絕大多數女性被先在地剝奪了社會職業選擇的自由,只能完全從屬于家庭,具體負責諸如相夫教子、奉養公婆、操持家務等事項。女性作為家庭主婦,沒有社會職業,沒有經濟收入,只能依附男性,使得女性處于卑微服從的地位,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女性的社會職能被單純界定為以“夫榮妻貴”為旨歸的“相夫教子”。
這就使得中國古代女性的職業化道路異常艱險和曲折,只有極少數女子在迫于無奈時才會選擇自己謀生的職業道路。事實上,中國古代女子的社會職業選擇范圍非常狹窄,且大致可以分為三類:(1)生產性職業,主要包括以補貼家用為目的織女、繡女等職業。在繡坊從事紡織物和繡品的生產,是典型的產業女工。(2)專業性職業,主要包括“三姑六婆”九類①元代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三最先提出“三姑六婆”這一概念,“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作為中國古代的專業職業女性群體,她們在各個歷史時期遭到不同程度的污名化誤讀。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鄭重為其正名,指出她們為在宗教信仰、醫療生育與買賣中介等方面為女性提供的服務,是當時其他男性相關從業者所無法代替的②引自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她們可謂是古代中國最初的專業技術女性。(3)卑賤性職業,主要指娼妓行業,包括色妓、歌舞伎或藝伎等,主要以提供色情服務、歌舞表演和才藝表演為生。這個職業是中國古代四大賤業之首③中國古代四大賤業為倡、優、皂、卒。娼:娼妓;優:從事表演類活動的人;皂:衙門里的衙役;卒:兵丁。,受歧視程度最高。在倡優皂卒四者之中,娼妓地位最為低賤,作為中國古代提供色情服務的特殊職業女性群體,她們還需承受道德家們的唾棄和攻訐。中國古代男性一方面坦然享受風塵女子的色情服務,另一方面又義正言辭批評她們水性楊花,不守婦道。
風塵女子從事娼妓賤業,往往并非自愿,而是被逼無奈或生計所迫。妓女按服務場所可細分為宮妓、營妓(軍妓)、官妓、家妓、民妓。其中,宮妓、營妓(軍妓)和官妓三類多因父祖或丈夫犯重罪而被牽連而被罰入宮中、教坊司或軍中充當女伎,是罪罰強迫。家妓、民妓兩類則多因家道中落或家中貧困自愿或被迫賣身為妓,是生計所迫。總之,風塵女子是中國古代男權社會中女性無可奈何之下的一種被動職業選擇,如蒲松齡《聊齋志異·鴉頭》妓女鴉頭所言“妾委風塵,實非所愿”,自述其淪落風塵,實在是迫不得已,有難言苦衷。在當時的三類女性職業中,風塵女子最受輕賤。
2.賤籍制度下風塵女子群體的“落籍從良”追求
中國古代風塵女子的產生由來已久。劉向《戰國策》記載“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語·齊語》記載:“齊有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通國用,管仲相桓公時,立此法,以富國。”管仲通過向妓女征稅確立了妓女的合法地位,這應是史書記載的最早期的官辦妓院。這說明早在戰國時期妓女就已經是合法職業。但合法化的身份帶來的是歧視性待遇。“古代中國為身份社會,舉凡政治權力、生活待遇都與身份相關。其最突出的表現是在法律上明確規定良賤身份作為定罪量刑的要件。在戶籍制度上,賤民階層專門立有賤籍。列入賤籍即被剝奪參政權利,最為典型的是不能參加科舉、不能為官。”①李若暉:《賤籍與身份社會》,《光明日報》2016年8月1日。賤籍之人社會地位極低,且世代傳承,不得隨意變更,倍受社會歧視和壓制。賤籍主要包括奴籍(奴婢)、樂籍(娼優)和軍籍(皂卒)。娼妓群體和樂戶都入樂籍,風塵女子就成了樂籍女子。
中國古代普通女性的人倫關系基于其與家庭中男性的關系,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三從”依附關系確定了女性的身份,她們作為男性的女兒、妻子和母親而獲得正統社會的身份認同。但無夫無子的風塵女子們飄零于家庭之外,也就被排除在人倫秩序之外,成為另類的、邊緣的、他者的存在。風塵女子想要重新獲取正統社會的認同,唯一的選擇就是回歸家庭,通過某個男性來重新確定其身份。因此,身處賤籍的風塵女子最大的夢想就是能擺脫賤籍身份,其理想的出路就是擇一“良人”為其贖身②良人,古代女子對丈夫的稱謂之一,亦指出身為“良家子”之人,在漢代,良家子指從軍不在七科謫內者或非醫、巫、商賈、百工之子女。后世泛指非賤籍出身、家世清白的子女。,然后嫁與其為妻妾,從而實現“落籍從良”,消除或脫出“樂籍”,加入良籍,最終實現社會階層和社會身份的改變。“落籍從良”也因此成為風塵女子皮肉生涯中望梅止渴的精神目標,圍繞“落籍從良”而起的種種引誘、試探、考驗就成為風塵女子日常生活的最核心內容。但由于現實利益、家族觀念等因素影響,這一追求在現實中極少能夠成功。唐代名妓魚玄機《贈鄰女》“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句就反映了她才貌雙全卻無人可將芳心托付的深切遺憾。
正因如此,“落籍從良”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妓女題材作品的重要議題。在文學虛構中,文人筆下的風塵女子往往能因自己的才情、才能、品性得覓良人、脫籍從良,如《李娃傳》中的李娃就成功收獲圓滿愛情且獲封汧國夫人,這多是出于對現實的補償心理。
(二)19世紀法國風塵女子:淫賤和墮落者
19世紀的法國,尤其是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性交易尤為普遍。“在現代化的巴黎都市中,妓女總計約12萬之多(根據攝影家馬克西姆·杜坎1872年估算的數字),這使巴黎成為 19世紀下半葉當之無愧的娛樂之都和尋求性歡愉的向往之地。在這個時代,對于‘妓女’這一職業,存在很多用來指稱的特定俚語,足以顯示當時妓女的多樣化:‘賤婦’‘貪婪’‘淫蕩的維納斯’‘魷魚’‘夜宵’‘柏油瀝青’‘游街的人’……每類妓女皆有其勝人之處,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引誘‘顧客’。”③吳晶瑩編譯:《頹廢與欲望——19世紀法國藝術中的妓女形象》,《世界藝術》2016年第1期。這個風塵女子群體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活躍于上層社會的交際花。“妓女也有等級之分,其中社會地位最高的便是所謂的‘高級妓女’(courtesan)。她們雖然身居社會底層,卻借助外表維持著一些來自社會上層的顧客。這其中包括富有的銀行家、作曲家以及知識階層,由此,她們也順勢成為巴黎社會的交際花,對于生活講求優雅,對于藝術別有激情。”①吳晶瑩編譯:《頹廢與欲望——19世紀法國藝術中的妓女形象》,《世界藝術》2016年第1期。許多交際花通過上流社會的文學沙龍結識各方人士,并往往在與文藝界的接觸之后成為文藝創作的原型。“阿波尼娜·薩巴蒂埃擁有一個著名的文學沙龍,她是波德萊爾創作《惡之花》的重要原型之一,法國唯美主義文學家泰奧菲爾·戈蒂耶還曾為她寫過一封露骨的情書。同樣,亨利·熱爾韋的作品則以女同性戀妓女瓦爾黛絲·德拉比涅為創作靈感。當時她是眾多藝術家極為熱衷的交往對象,也是左拉小說《娜娜》的靈感來源。”②吳晶瑩編譯:《頹廢與欲望——19世紀法國藝術中的妓女形象》,《世界藝術》2016年第1期。
另一類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妓女。勞爾.阿德勒在其社會史著作《巴黎青樓:法國青樓女子的日常生活》中描繪了她們的形象,“她們等待天黑。有的蹲在屋子里,打扮成嬰兒模樣或者披著透明的薄綢,有的站在紅色門牌號碼燈照亮的百葉窗后面,或者埋在客廳的沙發里,她們耐心等候,夜晚將是長的,蹬著高幫短靴,露出開口很低的臉褡,涂紅了嘴唇,描黑了眼圈,她們來到街上,邁著既淫蕩又快樂的步子,走到市中心。她們尋找亮點,熱鬧的咖啡館,正在營業的餐館。她們略微提起裙子,拋擲媚眼。偶爾她們叫住行人,用嬌滴滴的聲音談起金錢和愛情。”③〔法〕勞爾·阿德勒:《巴黎青樓》,施康強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第1頁,第200頁。在書的最后,他寫道,“妓女就其定義而言就是沒有故事的,為什么要嘗試讓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呢?我企圖做的,無非是為她們的故事的片段做一點貢獻。”④〔法〕勞爾·阿德勒:《巴黎青樓》,施康強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第1頁,第200頁。
這兩類妓女的現實處境看似天塹之別,卻同屬社會最底層,同樣遭受歧視,“在世界各民族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把娼妓視為淫賤和墮落者的看法幾乎是驚人的一致。”⑤聶紺弩:《聶紺弩雜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第316頁。
二、中法風塵女子文學形象的社會意義
(一)中國古代文學中的風塵女子形象
中國古代妓女大致可分為色妓與藝妓兩類。前者主要靠出賣色相為生,后者則主要從事藝術表演活動。前者被視為純粹的性交易商品,幾乎不見諸文學作品。后者則因色藝雙全、風流雅致而成為古代文學的重要題材之一。
藝妓因為家中男子的宦海沉浮、家道中落或生計艱難等種種原因而被迫走出傳統女子的后宅生活,進入到男性公眾視野,成為一定意義上的社會公眾人物。相比古代社會中其他女性職業如織女、繡女及三姑六婆而言,風塵女子,特別是其中的當紅人物,社會化程度相對較高,在上流社會拋頭露面的機會較多,往往是某些圈子的公眾人物,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她們中的一些人大多本來已有較高文化素質和才藝修養,且妓院經營者為提高其身價,也愿意對其在聲色才藝方面進行大力培養,反而迫使她們掙脫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庸常束縛,有機會成長為能歌善舞、能詩善畫、才華出眾、色藝雙全的一代名妓。如名列唐代四大女詩人之列的薛濤和魚玄機、宋代名妓李師師、清代名妓陳圓圓等。她們擅長吹彈歌舞、琴棋書畫之類的技藝就是她們的職場競爭力所在。她們本人及相關文人的詩文書畫作品均能大大炒高她們的身價,如以一曲《金縷衣》名世的杜秋娘。
這些集美貌和才華于一身的藝妓兼具如花容顏、風流才情與高潔情懷,最得達官貴人和文人名士的歡心,最能滿足他們“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的男性情懷,也因此最受古代文人青睞。漢代《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出現的“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字句;南宋時期徐陵所編詩歌總集《玉臺新詠》和北宋郭茂倩所編著的樂府歌辭集也出現對風塵女子只言片語的記載,但尚無對風塵女子形象的描繪和塑造;而在之后的唐傳奇、宋詞、明清小說中,風塵女子形象進一步豐滿鮮活起來。風塵女子與男性的交往和情感糾葛衍生了諸多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前者如柳如是與錢謙益的忘年戀情,后者如梁紅玉與韓世忠的抗金故事。前者可參考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后者可見南宋以來以韓梁事跡為訴說對象的眾多文學作品。這些故事演繹成的通俗文學作品,因為娛樂性而廣受市民歡迎,其中的風塵女子形象也廣為人知。
總體而言,各朝代對風塵女子形象的塑造不僅描繪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風塵女子群體生存狀態,也反映了各個時代女性解放的演進之路。如在“從良”問題的選擇上,唐傳奇《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和《鶯鶯傳》中的崔鶯鶯尚會對現實妥協,明代馮夢龍的“三言”“二拍”中的杜十娘卻已經有了為捍衛愛情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不屈意志,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二)19世紀法國文學中的風塵女子形象
法國奧賽博物館曾舉行過一場特殊的展覽 “盛衰記:1850-1910年間的妓女形象”(Splendor and Misery: Images of Prostitution 1850-1910)。該展覽首次向公眾展示了1850-1910年間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中所呈現的19世紀的“巴黎妓女”社會群像。風塵女子題材的巨大魅力可見一斑。該展覽名稱取自巴爾扎克同類題材的文學作品《交際花盛衰記》(The Splendors and Miseries of Courtesans,1838-1847)。無獨有偶,在19世紀的法國文學作品中,風塵女子的形象也被屢屢呈現。
在此之前,法國文學中少見風塵女子形象。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再到啟蒙運動前后,期間法國文學的主人公一直是男性為主:文學作品濃墨重彩、大肆描繪的對象是英雄、騎士、人文主義者和啟蒙主義者等法蘭西民族精神的代表。而19世紀法國文學的理想均源自對當代社會現實的關注:浪漫主義要求關注當下而非古代,自然主義要求呈現細節的真實,現實主義則強調記錄當代社會現實并關注底層人民的生活。風塵女子作為社會底層的另類形象,集中了最多類型和最大程度地壓迫,從而吸引了19世紀法國作家較多的關注和書寫。
總體而言,19世紀法國文學集中呈現了兩類妓女形象:一類是活躍于上層社會的交際花如艾絲苔(巴爾扎克《交際花盛衰記》)、娜娜(左拉《娜娜》)和瑪格麗特(小仲馬《茶花女》);另一類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妓女,如芳汀(雨果《悲慘世界》)、愛麗莎(龔古爾兄弟《妓女愛麗莎》)和羊脂球(莫泊桑《羊脂球》)。
(三)風塵女子文學形象的社會意義
1.身份與性格反差
概觀中外文學,諸多文本中顯示的風塵女子形象并不與傳統思維里那種低賤、下流、無恥的形象掛鉤,“妓女”的社會身份往往與其文學形象形成斷裂式反差,割裂了常識,產生了巨大的張力。在中外作家的筆下,風塵女子極具人格魅力。她們美麗嬌艷、知書達理、才華橫溢、心地善良,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嬉笑怒罵都源自家常,與常人無異,甚至在摸爬滾打中,形成了更為高尚的情操。
作家在對人物形象進行選擇建構時企圖傳達的是譏諷、冷眼、含蓄的控訴,是無聲的質問。現實生活都化為虛無,主流價值皆為謬誤,反而從鄙俗的東西中尋找安慰。
2.身份與命運沖突
“妓女”的身份,本就是施加在社會群體上的“有色眼鏡”,根深蒂固地附帶著社會層面取向的是非判斷與意義辨定。“在她們身上,肉體損耗了靈魂,感官了燒毀了心,放蕩麻木了情感。別人對她們講的話,她們早已熟知,別人使用的手段,她們全領教過,就是被她們激發出來的愛情,也已經被她們出賣了。”①〔法〕小仲馬:《茶花女》,李玉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73頁。這是對她們這一群體的慣常評價,人們的成見,是隔開風塵女子與其向往的生活的高墻。“宿命論”于她們而言是可笑又可怕的老生常談,意味著人在冷酷的現實面前無力擺脫命運的捉弄。
尼布爾《人的本性和命運》中闡釋了基督教的人性觀,靈和肉的二元,人的存在是在靈肉之間的平衡狀態。人最容易陷入兩種罪惡:驕傲之罪,即認為自己可以趨向靈的存在;情欲之罪,即人忘卻自己,耽于肉體感官的享受。風塵女子就是這樣靈與肉間矛盾的存在,作家往往把她們塑造成交際花與純潔多情處女的結合體,從而她們人物形象演變為西西弗斯式的英雄。
3.環境小說的色彩
小說作品中風塵女子往往是作為“花魁”存在,作為泄欲的工具和賺取錢財的傀儡,處在燈紅酒綠的風口浪尖,總與上流社會、王公貴族周旋。她們的命運走向與上層虛偽社會緊密相連,中外作品在對風塵女子的刻畫描寫,全然就是上流社會的風俗畫卷,將紙醉金迷展現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這樣的文明使人們產生了欲念、惡習與虛榮心,容易上癮,輕易戒不掉。而正是在這特定環境中引發的內在沖突,決定著風塵女子的全部命運走向。勒內基拉爾《流浪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提出“三角欲望”,現實中的欲望不直接,需要介體轉折欲望。風塵女子是骯臟欲望的介體。上層對情欲無休止的渴求、對權力的掌握,風塵女子在其中承擔了某種符號意義,作為一種象征,面對不合時宜的迷狂、匱乏的信仰與拜物教、主體的分裂,她們注定要與黑暗社會一起沉淪崩潰。
三、個案分析:莘瑤琴與瑪格麗特的形象建構
《茶花女》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代表作。這一長篇小說講述了一個青年人與巴黎上流社會一位交際花曲折凄婉的愛情故事。而同是描繪名妓愛情的明代小說《賣油郎獨占花魁》卻洋溢著喜劇色彩。本文將比較分析《茶花女》和《賣油郎獨占花魁》中名妓瑪格麗特與莘瑤琴的形象,以探究不同風塵女子形象的選擇與建構。
(一)莘瑤琴與瑪格麗特的不同選擇:抗爭或屈服
同為描繪名妓愛情追求的小說,《茶花女》和《賣油郎獨占花魁》的結局卻大相徑庭。《茶花女》中的瑪格麗特是犧牲成全、黯然離開、凄苦離世,《賣油郎獨占花魁》莘瑤琴卻是精心策劃、如愿以償、終成眷屬。選擇的不同決定了結局的差異:意料之中的悲劇和脆弱的圓滿。下面是依據風塵女子的特殊身份對其結局進行分析推敲。
1.瑪格麗特:意料之中的悲劇
瑪格麗特的悲劇不是其個人偶然的悲劇,是社會、時代的悲劇,是對社會認可的控訴。等級制及其衍生各種扭曲的價值觀,這種東西讓人變形。而同時,單純用社會悲劇來解釋不夠,是人性的悲劇,基于人性糾纏于自然與自我的悲劇。
首先,這是性格悲劇:瑪格麗特善良、柔弱、順從而富有犧牲精神,這通常預示著她浪漫的幻想與追求多流于妥協;其次,這是社會悲劇:社會習俗與不可撼動的“貞節觀”深深影響著社會中的每個人,無論是阿爾芒的父親抑或是瑪格麗特本人都認同了風塵女子的卑賤,所以阿爾芒的父親的懇請能夠得到瑪格麗特的配合;再次,這是命運悲劇:瑪格麗特在天命思想與偶然因素間進行的劇烈思想斗爭,最終向社會主流價值判斷妥協,選擇了黯然分手;最后,這更是生命悲劇:人的正常本能和欲望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悲慘結局。
瑪格麗特愛慕的阿爾芒是個紈绔子弟,沖動任性、做事不計后果。他的不孝順、不理智是將自己愛情推向矛盾高潮的直接原因。勒德戈爾蒂埃說:“同樣的無知,同樣的朝三暮四,同樣的缺乏個人反抗,這使得他們聽命于外界環境的暗示,缺乏來自內心的暗示。”總之,讓瑪格麗特毀滅的不僅僅是欲望,其自身的精神匱乏和社會道德綁架也是重要推手,而阿爾芒的不可靠更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將瑪格麗特推上絕路。
悲劇最終就會指向失去意義、暗無天日地繼續沉淪和死亡這兩種結局,無法保障生命的價值,那么人就應該自殺,如同加繆談到的“哲學自殺”。以上兩者結局,死亡顯得更為幸運,通過死亡尋求自我救贖,阿爾芒在人去樓空的大宅中,意識到瑪格麗特的“死亡已經凈化了這個富麗而淫穢的場所的空氣”。生活是一種過渡,向死亡的過渡。對人生意義最大的懷疑,只有死亡才能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義問題,也只有死亡,才能使她們得以爭取到世俗以外的價值,得以反抗壓迫。在這場愛情博弈中,瑪格麗特凄苦離世,“她將在祭壇上為資產者的體面獻身。”她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鬧得滿城風雨,她死后也就越是無聲無息。她就像某些星辰,隕落時和初升時一樣暗淡無光。
2.脆弱的圓滿
風塵女子的故事少有善終,中國古代文學講述秦樓楚館女性的作品層出不窮,其中或多或少也有大團圓的結局,而故事往往帶有傳奇的色彩,邏輯上禁不得推敲,更有甚者將主人公定為魑魅魍魎,才使其得以成功游離于傳統禮制的邊緣。
《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秦莘二人終成眷屬的圓滿結局并不偶然,是莘瑤琴精心選擇和謀劃的必然結果:莘瑤琴在遭受凌辱之后,放棄追求達官貴人翩翩公子,而選擇了來自下層階級且其貌不揚的賣油郎秦重。這個選擇保證了秦重不會鄙夷其身份地位。作為一個賣油郎,是一個小本經營、挑擔走街的商販,他的為人無可挑剔,是個人盡皆知的老實好人。他經濟狀況窘迫,社會地位較低且才貌欠佳,并非白馬王子,看似并非良配,但他對莘瑤琴的追求是一個男子對所戀女子的單純而熱烈的追求,他并不把莘瑤琴看作是性交易商品、玩物和男權附屬品,而是當作具有獨立人格的人來尊重。這正是其貌不揚的他能打動莘瑤琴,使她重新相信愛情的真正原因。而莘瑤琴則維系著傳統美德與從良的決心。鴇兒劉四媽評風塵女子從良行為:“有個真從良,有個假從良,有個苦從良,有個樂從良,有個趁好的從良,有個沒奈何從良,有個了從良,有個不了的從良,”王美娘(莘瑤琴)即是“真從良”“樂從良”“趁好的從良”“了從良”①馮夢龍:《醒世恒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7頁。,她省吃儉用,并不奢侈放縱,早早存夠了贖身所需花銷,能夠不為外在因素而迷亂,反而清醒地認識到秦重那極為難得的人品,“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隱惡揚善,千百種難遇此一人。”①馮夢龍:《醒世恒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2頁。莘瑤琴的精心策劃、秦重的全力配合,加之并無王公貴族的死纏爛打、老鴇的坑蒙拐騙等令人唏噓的情節,故事在機緣巧合下拼湊出了令人艷羨的結局。
3. 小結:性別話語與男權社會中的他者建構
比對瑪格麗特和莘瑤琴的不同結局,有兩個構成要素非常引人注目。第一,阿爾芒是上流社會的公子哥,而秦重只是普通百姓賣油郎。故事最終還是對階層做出了妥協,安排女主人公不是向上索求,而只是向下尋覓。第二,區別于阿爾芒的避重就輕,懦弱無能,秦重勤勞能干善良踏實,男性主人公的品行變得至關重要。“通過對瑪格麗特風塵妓女哀怨命運的分析,說明在男權社會里,被置于‘第二性’的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②蘇屹峰:《論《茶花女》悲劇的成因》,《武漢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9期。以上兩個因素反映了女性獲得善終與否,決定權最后竟然還是在男性手里。喜劇結局的獲得在于男性的妥協而非女性的追求。兩位作者建構風塵女子這一形象,都不約而同以男性為基點,頌贊其人格的高尚美好并非目的,而只是工具,作者寫作活動中選擇和建構風塵女子形象并非是為其聲援,只是各取所需曲線救國罷了。
(二)讀者接受角度下看風塵女子形象的塑造
《賣油郎獨占花魁》出自馮夢龍“三言”中的《醒世恒言》。“三言”擁有龐大的讀者群。“這并非認為小說的讀者只是以生員為主的科舉考生,另一方面,如同磯部氏發表的資料所示,地位相當高的人也是其讀者;可以肯定當時馮夢龍小說的讀者包括以生員為主的科舉考生和商賈這兩個層面的人。”③大木康:《關于明末白話小說的作者和讀者》,吳悅摘譯,《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2期。“三言”收錄的作品來源之繁、覆蓋之廣、內容之雜,同時也都經由了馮夢龍的主觀過濾,是自然主義的人文理想與傳統儒家雙重解構與建構的博弈。 “三言”在建構明代風塵女子形象時,對她們的美貌和才藝只是簡單提及,重點寫她們身上的高貴品質,挖掘她們的獨特內涵,在重建風塵女子形象的同時不忘加入道德倫理的訴求。因此《賣油郎獨占花魁》的喜劇色彩更多了些“勸人”意味。勸人向善,勸人忠厚老實,平添了家國情懷。
和《醒世恒言》相比,《茶花女》在創作動機上就有很大不同。“小仲馬為自己的‘純真愛情’辯白,對父親說‘我希望一舉兩得,即同時拯救愛情與倫理。既贖了罪,也洗滌自身的污穢,任何權威都不可能指責我選擇了一個婊子當小說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請進法蘭西文學院,他們也無法說我頌揚過淫蕩。’”④〔法〕波羅·德爾貝什《茶花女與小仲馬之謎》,沈大力、董純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第1頁。由此可見,小仲馬的《茶花女》為他自己私心所寫的。當時通俗小說已經逐漸流行,小仲馬寫作的目的是受到關注。妓女題材更具爭議性,悲劇更具沖擊力,更能讓讀者記住他的故事,記住他小仲馬這個人。因此,無所謂結局悲喜。而實質上,根據他與瑪麗·杜普萊西的真人真事,也注定了《茶花女》的悲劇。小仲馬以為自己在以現實主義的身份批判,可是社會批判的基本形式應該是諷刺而不是悲劇。他就像小丑,努力扮出旁人喜歡的樣子,甚至可能自己都沒意識到。而實際上,這個題材新穎又刺激,《茶花女》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小仲馬以倫理的權威自居,高舉社會道德這桿大旗,用懺悔的語氣,把這愛情和自己的野心神圣化。
結 語
風塵女子聚合了種種極端矛盾特質:社會地位極其低下、才藝修養極致高超、妝容衣著極盡精美、工作環境極度奢華,等等。而她們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不論是官妓、家妓和私妓,其地位存在著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即集卑賤與優裕于一身。”①李劍亮:《唐宋詞與唐代歌妓制度》,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5頁。她們社會地位低賤尤甚于奴仆,卻與達官貴人密切相交;她們姿容秀麗,最能討男性歡心而又備受男性鄙視;她們才華出眾,最得文人追捧卻又屢遭文人抨擊。這些特質使她們區別于當時的普通女性,同時也使她們飽受非議,成為道德衛士的唾棄目標。這種極端反差的處境對她們的心理、情感和婚戀均產生特殊影響,“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同時也是女性失落于社會家庭和泯滅自我的歷史。尤其是作為私有制和男權中心的產物——風塵女子,她們在這個維系生存的社會里摸索掙扎,她們的整個生命與奢靡的環境、放縱的男性融為一體,其生存方式、內心情感、愛情婚戀及命運結局有許多特異之處,所以風塵女子題材一直都是中國文學中的重要母題。”②林夢如:《“三言”“二拍”之風塵女子形象研究》,青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31頁。這一論斷同樣適合于19世紀法國的風塵女子文學形象。
風塵女子在泥淖里,散發著人性的光輝。她們的卑微社會地位與獨特人格魅力及高尚品行間形成巨大反差。她們在遭遇了最徹底的情感欺騙與剝奪后,還依然懷有對幸福的期許;在遭受了最沉重的社會倫理壓迫后,還愿意犧牲、隱忍與成全。正是這種弱者的高貴、卑微的光輝、黑暗中的光明賦予了風塵女子獨特品格,她們的形象也因此成為了大量文學作品的書寫對象,其在文學闡釋層面產生著獨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張力。中法文學均選擇用這樣最黑暗的身份來進行最神圣的話語表達。風塵女子形象的選擇與建構背后,預示著肆虐的、殘酷的惡旁往往也有孱弱的良善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