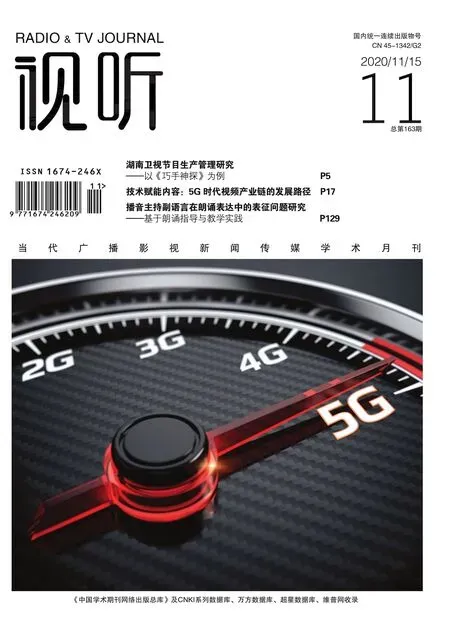韓國電影《恐怖直播》的鏡頭語言分析
□ 江佳玉
一、引言
電影《恐怖直播》是由韓國80后導演金秉宇自編自導,韓國演員河正宇主演的犯罪懸疑劇情片,總投資35億韓元(約人民幣2000萬元)。該電影于2013年7月31日上映,獲得了當年電影票房排名第6的好成績,也使得金秉宇導演斬獲第34屆韓國電影青龍獎的最佳新人導演獎。
該影片豆瓣評分高達8.8,且已有接近46萬人進行評分,主要講述了遭遇職場和離婚危機的廣播電臺Daily Topic節目主持人尹英華接到揚言要炸掉首爾麻浦大橋的“恐怖分子”樸魯圭的電話,并通過直播連線的方式與其周旋的故事。這部長達98分鐘的電影基本就在一間新聞直播間里進行,如何在有限的小空間內塑造影片大格局的立意,利用多種鏡頭語言以快節奏的方式為觀眾打造緊張、刺激的觀影體驗,是本文重點討論和研究的內容。
在視聽語言中,鏡頭是主要的、基本的視覺意義構成的語言單位,其在電影中有著舉足輕重的表現力。電影《恐怖直播》鏡頭語言豐富,利用多類鏡頭的急速切換,特別是運動鏡頭、特寫鏡頭、長鏡頭等多種鏡頭語言的使用推進了跌宕起伏的劇情,讓影片的敘事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內更加流暢和飽滿。
二、特寫鏡頭:推進影片敘事
所謂特寫鏡頭,就是指電影中拍攝人物的面部等人體的某一局部或一件物品的某一細節部分等鏡頭。特寫鏡頭往往兼顧了敘事和寫意兩種功能,在呈現人或物細節的同時傳遞某種感情,推動情節發展。特寫鏡頭畫面大面積的主體呈現,讓觀眾關注到影片想要表達的劇情細節、影片主旨與內涵。在《恐怖直播》中,導演通過大量的人物特寫與物體特寫鏡頭推動著劇情的快節奏敘事。
(一)人物特寫——展現角色心理變化
《恐怖直播》這部小成本影片可以說是演員河正宇一個人的“獨角戲”。特寫鏡頭較多的影片對演員的演技也是一種挑戰和考驗。有限的空間、有限的角色,在這樣的情況下,導演用了大量的人物特寫鏡頭來刻畫角色心理變化,進一步塑造人物形象。
影片從尹英華在直播間里與聽眾連線開始,導演一開始就給予了男主人公大量的特寫鏡頭。最初,觀眾看到的是一位不修邊幅的30歲大叔,其胡子拉碴的面容、戴著墨鏡的散漫、隨意的發型等細節無不展現了主人公落魄、失意的狀態。并且,特寫鏡頭中的人物形象也和尹英華與妻子離婚、被上司設計貶職的后續情節相契合。當尹英華得知自己可以利用與“恐怖分子”樸魯圭連線直播的方式獲得咸魚翻身機會時,特寫鏡頭與大量跟鏡頭組合,對主人公快速換裝、與上司談判決策等內容進行拍攝。而當人物特寫鏡頭再次拉近,尹英華的眼神從最初的黯淡無光變成了犀利深邃,整個人也從一開始的頹廢疲憊變得神采奕奕。在無形鏡頭語言之下,影片通過對發型、面貌、衣著等特寫鏡頭讓一個訓練有素、輕車熟路的專業新聞主播形象呈現在觀影者眼前。
隨著劇情的推進和人物矛盾沖突的日益加劇,尹英華的角色心態進一步發生了轉變。比如,當自大狂妄的警察局局長來到直播間與“恐怖分子”樸魯圭進行連線談判時,在局長不斷輸出咄咄逼人、冷漠無情的話語的同時,導演頻頻切換尹英華的面部特寫。觀眾可以從其面部表情的變化看出男主人公對局長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對民眾訴求的冷漠、敷衍態度的不贊成。這些特寫鏡頭下,微表情的變化也為后面主人公站邊“恐怖分子”一方的劇情走向做出了鋪墊與暗示。
(二)物體特寫——補充細節敘事
除了人物特寫,影片還多次運用物體特寫來呈現劇情細節、鋪墊影片線索,進一步保障影片敘事邏輯的完整性。比如通過對話筒、調音臺、耳機、攝像機、電話等多種新聞直播間元素的特寫鏡頭來強調“恐怖直播進行中”的場景和主題。同時,通過各種物體元素與主人公尹英華之間的互動,比如男主熟練地操作調音臺與話筒,用紙筆記錄關鍵信息等畫面內容,也可以從側面烘托出尹英華作為一名前黃金檔新聞主播的專業素養。影片多次對主人公正在記錄或已經記錄完成的手稿進行物體特寫,通過對紙上具體文字的特寫,如“樸魯圭”“工地工人”“麻浦大橋恐怖襲擊”“獨家”等字樣,既是在側面表露主人公當下的想法和思考邏輯,同時在提示觀眾情節的發展和關鍵線索。
三、運動鏡頭:增強身臨其境的真實感
電影是一門“動的藝術”。電影藝術中的運動鏡頭,是指通過攝影機的連續運動或連續改變光學鏡頭的焦距所拍攝到的鏡頭。電影《恐怖直播》中,為了配合快節奏的劇情,讓觀眾擁有沉浸式觀影體驗,導演運用了大量運動鏡頭的推、拉、搖、移、跟、升降等多種形式來展現人物沖突,推進劇情發展,增強觀眾觀影時的真實感和體驗感。
(一)電影中的跟鏡頭分析
攝影機始終跟隨一個主體被攝物移動的鏡頭被稱為跟鏡頭。被攝物始終保留在畫面內,且攝影機與被攝物始終保持勻速運動。影片多次用到該類運動鏡頭語言來帶領觀眾了解主人公尹英華第一視角下的其他人物的形象、事發進展等。
影片一開始,尹英華以為揚言要炸掉麻浦大橋的來電只是一場惡作劇,便隨意地掛掉了樸魯圭的來電。隨著窗外的幾聲巨響,以及直播間外其他工作人員不知所措的反應,導演選擇用跟鏡頭的手法讓觀影者與主人公一起快速走到窗邊目睹麻浦大橋的爆炸現場。同時,這一跟鏡頭配合著手持攝影技巧增強了影片的紀實感,讓觀眾的體驗感和真實感更強,易與處于事件中心的主人公產生情感與情緒共鳴。
影片第二個經典跟鏡頭是尹英華拿著自己的公文包走出錄影棚前往衛生間為后面的出鏡新聞直播做準備。這一段較長的跟鏡頭選擇從主人公的后方和側面視角進行拍攝,一路上,他既穿過了忙碌的工作區域,也通過透明窗戶看到了麻浦大橋上的救援情況。跟鏡頭中,尹英華一邊以“獨家新聞”為籌碼和局長談判,一邊麻利迅速地打領帶、刮胡子、抓發型。這些鏡頭畫面既體現了主人公從容冷靜的遇事態度,也映射了其只關心自己利益的冷漠麻木。同時,跟鏡頭配合抖動性較強的手持攝影方式,也增加了電影的紀實感和真實感,仿佛把觀影者也帶到了緊張刺激的事發現場,跟隨著主人公一起進行新聞直播前的分秒必爭的準備工作。
(二)電影中的搖鏡頭分析
搖鏡頭是指攝影機在移動車或三腳架上拍攝一個畫面時,攝影機的機位不做位移,只有機身進行上下、左右旋轉運動,是運動鏡頭的一種。“搖鏡頭既可以使得畫面顯得特別真實,而且能使觀眾在與攝影機一同移動的時候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體驗。觀眾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切東西,一樣不漏。”①《恐怖直播》通過一些搖鏡頭的使用,展現主人公所處的環境與場景,抓住人物微表情與造型細節變化,給予觀眾沉浸式的觀影體驗。
片中,當尹英華目睹身旁的警察局局長身亡后,導演給予其長達1分鐘左右的360度環繞搖鏡頭,結合人物特寫拍攝與十幾秒的“耳鳴”配音效果,讓觀眾仿佛置身于爆炸現場。同時,這一組特寫跟鏡頭集中于人物面部進行拍攝,將主人公目睹死亡后的恐懼、震驚、脆弱等情緒收錄于畫面中。無論是臉上濺射的鮮血、慌張的神色,還是其泛紅的眼眶,尹英華內心的無助和害怕一一被捕捉。在跟鏡頭的處理下,觀眾意識到這場戲是重要的分水嶺,讓主人公終于明白,這一場新聞直播并非可以讓自己東山再起的機會,也并非可以掌控,而是讓自己踏入了一場無法脫身的泥潭。
四、長鏡頭:深化電影主題
長鏡頭的拍攝與運用是導演們對電影敘事進行的探索,被稱為電影敘事的實驗與藝術觀念創作的手段。“所謂長鏡頭,乃是連續拍攝的具有一定長度的深焦距鏡頭,從而能在一個統一的時空里相對完整地展現動作或事件。”②
結尾長達29秒的長鏡頭是整部影片中最具有畫龍點睛作用之處。從近景景別過渡到特寫,鏡頭在晃動中層層推進,推向尹英華的面部特寫。從男主角眼神與表情中最初的面對死亡與混亂的心力交瘁,到按下引爆開關的憤懣悲情與毅然赴死,整個長鏡頭都聚焦在主角個人的面部,雖然觀眾無法直觀看到大廈的坍塌,但是可以從尹英華背后的窗口景色變化和愈發傾斜的鏡頭畫面拍攝方式,感受到大廈的倒塌。在坍塌的一瞬,窗外的建筑愈發清晰,表明大廈正在倒向政府官員所在地——國會大廈。自此,畫面一黑,影片到此戛然而止。在這個精彩的特寫長鏡頭之下,電影將人物的情感和心理變化清晰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有目睹死亡的痛苦和悲傷,有對自己成為“替罪羊”的無助脆弱,還有對韓國政府冠冕堂皇、欺騙大眾的憤怒等等。所有的情緒涌上心頭,男主引爆大廈之舉的劇情走向也并非意料之外,這樣的結局處理方式反而讓觀影者有刺激痛快的觀影體驗。
五、結語
“一句道歉就這么難嗎?”這是電影結尾的一句臺詞,也是“恐怖分子”在生命的最后對尹英華和政府提出的疑問。在這一場“恐怖直播”中,故事直觀地反映了韓國現行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下貧富兩極的矛盾,既有上層階級的冷漠,更體現了潛藏在人性之中的自私。當底層勞動者無法通過正常渠道表達合理訴求的時候,除了沉默,他們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往往就是破壞。
《恐怖直播》是一部反類型的類型片。它講述的是恐怖襲擊的人為災難,卻沒有大場面的災難和營救等畫面,只有在演播廳里的小場景。在有限的空間格局內,導演通過運用成熟豐富的鏡頭語言和精湛的敘事技巧為觀眾呈現了一個跌宕起伏的快節奏故事。同時,隨著劇情的推進,也引發了觀眾對眾多社會現實問題的思考,比如媒體究竟為誰服務,政府的尊嚴與百姓的生命之間誰更重要……這部影片其實對政府和媒體而言都是一次非常深刻且有意義的拷問。
注釋:
①[匈]貝拉·巴拉茲.電影美學[M].何力 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78.
②潘秀通,萬麗玲.長鏡頭辨析[J].當代電影,1990(01):29-42.
——以《在一起》中的《救護者》單元為例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