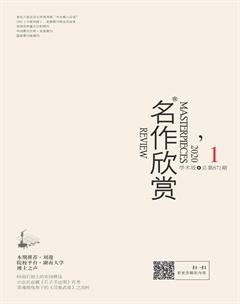論《絕秦書》中“桃源夢”的幻滅
摘要:絳帳文化傳統(tǒng)孕育出的周克文致力于將周家寨營造成一個以儒家思想文化傳統(tǒng)為底色的世外桃源。與兄弟、兒子的沖突,已使得周克文桃源夢的實現(xiàn)之路坎坷曲折,在饑荒中被徹底打破。作家無意于以此高唱一曲文化哀歌,而是希望現(xiàn)代化的高速列車能多一點文化底色。
關(guān)鍵詞:《絕秦書》 絳帳文化 桃源夢
一、絳帳傳統(tǒng)孕育的桃源夢
“絳帳”在小說中是指與周家寨相距僅數(shù)里的地名,東漢通儒馬融曾在此開館講學,因帳子為絳色而得名,盧植、鄭玄也求學于此。“絳帳”在小說中與其說是地名的實指,毋寧說是以仁義禮智信、修治齊平、忠節(jié)孝悌為主要內(nèi)容的儒家歷史文化精神的象征。因此,作家以與絳帳相距不遠的周家寨為故事展開文本空間并非隨意為之,而是賦予它巧妙的歷史隱喻,并賦予其歷史文化內(nèi)涵。
絳帳傳統(tǒng)在周克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周克文的啟蒙老師西府老秀才是漢儒馬融的數(shù)十代嫡傳弟子,因此,周克文承續(xù)了一整套儒學文化思想。這種歷史文化傳統(tǒng)所具有的“文化特質(zhì)……在諸意義的來源中占有優(yōu)先的位置”①。周克文也常通過文脈承續(xù)的方式實現(xiàn)自我認同和價值建構(gòu)。周克文將全家聚集的場所取名“明德堂”,“明德”二字語出《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正如剛回村的周立功所理解的那樣,“明德堂”承載著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寄寓著他爹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立善存仁是人生最大的責任”②。可見,周克文深受儒家精神的影響。此外,周克文三個兒子的名字源于《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既是周克文的個人追求與人生愿望,也是他對兒子們寄托的希望與期許。
但周克文又喜歡讀陶淵明、王維、孟浩然等人的田園詩,有周家寨其他村民缺少的超俗情懷。種樹是周克文保持這一獨特秉性和個人價值確認的重要方式,“周克文莊前屋后、旮旯犄角都栽了樹”,他栽樹“是田園詩讀多了,老把周家寨朝桃花源的樣子弄”。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是他與世俗抗爭而虛構(gòu)出的浪漫化的理想世界,是詩人的生活理想與社會政治理想。③在桃花源中,陶淵明通過桃源人的生活環(huán)境、生活方式、待客之道等表現(xiàn)桃源人安閑自足、怡然自得的生活。與陶淵明不同的是,周克文是用一整套儒家價值體系來支撐他的桃源夢,他種樹也是為了重構(gòu)《寡人之于國也》中所描繪的大同圣境。對周克文而言,桃源夢只是遮蔽其孔孟大同理想之軀體的華麗外衣而已。因此,周克文雖然喜讀田園詩,欣賞田園詩的隱逸精神,但他僅止步于精神上的向往。
作為遠近聞名的秀才和周家寨的族長,周克文幾乎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向接觸的人傳授他所理解的儒家精神,也不失時機地傳播他所理解的仁義思想。“傳統(tǒng)導向的社會利用口述家史、神話傳說與歌謠等形式來傳播其相對穩(wěn)定的價值觀。”④周克文顯然把口述史、神話傳說和歌謠作為其傳授價值觀念的有效方式。旱地龍搶劫明德堂時,周克文用盜跖和虬髯客的故事給土匪講盜亦有道,讓土匪明白土匪之道也有高低之分;教村民識字則從馬融到絳帳講學的歷史和逸聞趣事講起;他還借祈雨之機整治鄉(xiāng)風。周克文到縣城時,看見洋人施粥時讓災民拜耶穌,便效仿洋人的做法,讓災民在孔子像前磕頭作揖,直到記住其名諱才給飯吃。周克文對孔子及其思想學說敬若神明,讓災民拜孔子像的目的則是要災民通“王化”(天子的教化)。周克文這一系列看似古怪,實則有跡可循的舉動,都是為了讓災民成為通孔孟精神的“君子”。
二、家庭沖突與桃源夢的裂痕
在周克文努力打造世外桃源似的周家寨時,作家以縱橫的方式展開敘事:橫軸是周克文、周拴成兩兄弟的瑣碎矛盾及由此展開的賭氣暗斗,縱軸則是劇變時代下激烈的代際沖突。由兄弟矛盾及父子沖突構(gòu)成的家庭沖突對周克文“人人皆可為堯舜”的桃源夢帶來巨大的挑戰(zhàn)。
周克文、周拴成兄弟倆的矛盾圍繞“家業(yè)”和“族長”兩方面展開。在家業(yè)方面,周拴成在分家的時候就在盤算侍養(yǎng)老人與產(chǎn)業(yè)之間的性價比,分家后雖然僅得很少一部分土地,但他一直精心侍弄土地,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超越兄長周克文,揚眉吐氣。與鹿子霖和白嘉軒旗鼓相當?shù)牟┺牟煌芩┏稍谂c周克文的較量中幾乎一直處于劣勢。如果說在家業(yè)方面周拴成能夠經(jīng)過不斷打拼趕超周克文,那么在權(quán)力方面,他卻無法通過努力來獲得族長這一頭銜。盡管如此,他還是大膽地向族長發(fā)起了挑戰(zhàn),比如越俎代庖地組織了只有族長才有資格主持的耍社火、祈雨等活動。農(nóng)耕社會的競爭機制不健全,個人出路較為狹窄,主體意識較強的人會不自覺形成“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會力量的原則”,“以抵抗無法承受的壓迫”。所以,周拴成以傳統(tǒng)的方式去挑釁族長的權(quán)威和穩(wěn)固的社會秩序,尚未有接受現(xiàn)代價值的覺悟。
如果說周克文、周拴成兩兄弟的矛盾是傳統(tǒng)文化內(nèi)部不同力量之間的博弈,那么周氏父子的代際沖突則是不同的主體身份認同以及文化認同之間的沖突。在考察科舉廢除對讀書人的影響時,程美寶認為“晚清廢除科舉制度,并沒有馬上廢除‘士大夫這個身份及其附屬的意涵,廢科舉所標志的,其實是‘士大夫這個觀念的分裂”,“中國年輕一代受過教育的精英分子……不得不重新定義自己……為自己營造一個有異于傳統(tǒng)士大夫忠君衛(wèi)道的自我形象,這個新的自我形象的內(nèi)涵,更多的是對學術(shù)獨立的追求,對民眾的關(guān)懷,以及對國家前途的憂心”⑤。程美寶顯然是以“傳統(tǒng)士大夫忠君衛(wèi)道的自我形象”作為參照系來討論“中國年輕一代受過教育的精英知識分子”對自我形象的想象和他們的價值追求。但程美寶的討論僅止于此,并未繼續(xù)探討新舊兩代知識分子因定位不同而產(chǎn)生的矛盾糾葛。而作者張浩文將新舊知識分子間的矛盾糾葛在周克文、周立功父子間展開,從小說美學角度看,這種處理方式既能集中凸顯新舊文化的沖突,又能讓尖銳緊張的沖突因父子血緣關(guān)系得到舒緩。
周克文對最得意的兒子周立功給予厚望,把未完成的志業(yè)都寄托在兒子身上,但事與愿違,受新學哺育的周立功雖然理解周克文的理想與追求,卻竭力在思想上與父親捍衛(wèi)的孔孟之道劃清界限,并試圖以新學取而代之,父子之間由此產(chǎn)生了激烈的沖突。大學畢業(yè)后,周立功為追隨梁漱溟和晏陽初等人所倡導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毅然回到周家寨辦掃盲班,教村民識字。周克文對周立功這項惠及村民的事極為支持,不僅將教室設(shè)在周家寨祠堂,而且還唱戲替兒子拉學生。兒子教村民識字時,周克文還上臺講授,比教學效果,這些似乎都表明了父子之間的共識與默契。周氏父子第一次思想觀念上明顯的交鋒是在過年的行禮方式上:周克文堅持行跪拜禮,周立功堅持行鞠躬禮。父子二人都知道,方式的不同是新舊觀念沖突的展現(xiàn):周克文把這事提升到禮數(shù)人倫的高度,周立功也把它當作鄉(xiāng)村建設(shè)移風易俗的破冰之旅。在周立功到夜校講婚姻法,導致單眼的媳婦逃跑后,周氏父子再次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周克文氣急敗壞地要去打周立功,并關(guān)掉了周立功的夜校。面對兒子的挑戰(zhàn)和進攻,周克文以靜制動,老練沉著,沒有絲毫左支右絀;但周立功在和父親的對陣中,總是從攻變守,倉皇失措,最后只得落荒而逃。
面對兄弟的挑釁、兒子的挑戰(zhàn),周克文并非總是神閑氣定、恪守初衷,比如因一時置氣,他竟然讓同胞兄弟夫婦倆餓死在饑荒中。兄弟出殯,周克文為兄弟摔孝盆固然需要勇氣,但與其說是出于寬恕與仁義,毋寧說是他對自己過失的贖罪。然而,悲劇已然發(fā)生,周克文的舉動并不能讓亡者復生,只為求生者心安,他的過失也不能因此豁免。面對兒子用現(xiàn)代工業(yè)理論為其描繪的發(fā)家藍圖,周克文曾一度神往,也因此在拯救饑荒與投資工業(yè)之間舉棋不定。兄弟、父子之間的矛盾,已經(jīng)讓周克文及其倡導的孔孟之道顧此失彼,加之他對圣賢之道的猶豫,建立在此基礎(chǔ)之上的桃源夢也就發(fā)生了動搖。
三、饑荒與桃源夢的破滅
約緒·卡斯特羅在《饑餓地理》中寫道:“饑餓殘害人類,不僅在身體方面使身材變小,肌肉萎縮,皮膚損傷,而且影響他的精神,他的心理狀況和他的社會行為……沒有別的災難像饑餓那樣地傷害和破壞人類的品格。”⑥與大多數(shù)描寫“自然災害及其導致的災荒在其他作品中大多是以故事背景的形式出現(xiàn)”不同,《絕秦書》中的“饑荒是推動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的敘事動力”⑦。饑荒使人直面生存的困境,拷問人性的高貴與卑劣、缺失與堅守;饑荒是洪水猛獸,無情地撕扯掉人們偽善的外衣,也讓周克文堅守的人倫道德?lián)u搖欲墜,最終轟然倒塌。
《絕秦書》淋漓盡致地描寫了饑荒年代人性的復雜,批判了道德缺失的丑陋,贊揚了在饑荒中堅守人性的偉大。兔娃媽為方便賣身,將兔娃推進二十余丈深的枯井,最終用石頭將兔娃砸死在井中;周寶根為求一己之安,帶走所有家當導致雙親餓死;彩蓮死前為見父母最后一面,幾乎爬了一天一夜才到娘家,卻未得到父母接待,餓死門外;單眼父子為了吃到肉,將人殺死。相反,豬娃的二爸和嬸娘為了給大哥家留下香火,將親生兒子狠心拋棄;二爸為了讓侄子與妻子活下去,一直未吃東西,最后餓死;嬸娘為了照顧和養(yǎng)活豬娃,下嫁周寶根,受盡各種折磨;周拴成夫婦掛念尚未歸來的周寶根,一直到死也還想著為兒子守家看院。他們在饑荒中用實際行動踐行著仁義的真諦。
周克文是《絕秦書》中刻畫得最為成功的人物,饑荒年代,他在施粥救災和投資工業(yè)發(fā)家致富之間猶豫掙扎,后來終于選擇施粥救災。即使兩個兒子接連喪命,他仍然堅持施粥救災,樹立起一座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豐碑。作為方圓百里德高望重的名儒宿老,周克文帶領(lǐng)幾十個村的饑民包圍縣城,迫使政府暫停征糧。弟弟周拴成與其妻被餓死后,周克文意識到災情比他想象中要嚴重。他到縣城為民請命,反被狡猾的孫縣長將了一軍。回家后,他試圖躲在家里,但“明德堂”三個字又使他反省自己的行為。看到洋人施粥讓中國人念洋經(jīng)、信耶穌,他意識到“洋教毀我圣賢,亂我綱常,斷我文脈”,如果繼續(xù)這樣下去,他視之如命的倫理綱常將在周秦故地上消失。他將施粥救災視為拯救人心,“辦不辦工廠只關(guān)乎錢,收不收人心卻關(guān)乎道統(tǒng)。錢可以少掙一些,可作為士紳,他不能看著孔孟之道在這里斷了根啊,這是剜他的心頭肉。道統(tǒng)散,天下就散了,那還得了”。收回人心,賡續(xù)中華文脈的確比幫助兒子辦工廠重要得多。為此,三兒子周立言從鳳翔運糧回周家寨途中,被劉風林手下打死;緊接著,周立功又因為糧食死在了劉風林手上。至此,施粥賑災之于周克文而言具有收人心、承道統(tǒng)、救人命等多重意義。周克文的義舉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土匪旱地龍義務留下來負責維持飯場秩序。在打敗了洋人之后,周克文贏得了洋人的尊重,挽救了道統(tǒng)和人心。
不幸的是,周克文的放粥招來了“吃大戶”(舊時饑民聚眾奪取富家食物或去富家吃飯的行動)的人,他們蝗蟲似的氣勢猶如沙塵暴,來勢洶洶,所到之處寸草不留。他們淹沒了粥棚,踢翻了圣人牌位,擠破了絳帳鎮(zhèn),踏平了周家寨。周克文苦心經(jīng)營的道統(tǒng)人心還未立正,就被“吃大戶”的洪流沖散了。尾聲部分,周立德回到周家寨.一切幾乎都換了模樣,“他向街上人打聽明德堂,那些人都說著他聽不懂的外鄉(xiāng)話”。周立德此時面對的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非”。周克文連同他孜孜以求的桃源夢,早在二十年前的饑民浪潮中消逝了。
雖然有論者頗具感傷色彩地將周克文稱作“關(guān)中大地最后一個鄉(xiāng)紳”⑧,但作者張浩文似乎并不想借此高唱一曲文化哀歌,而是對鄉(xiāng)土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做出文化反思。國家和社會在匆匆登上現(xiàn)代化的高速列車時,帶上一點自己的歷史文化,讓一場不知終點的現(xiàn)代旅途增添一點傳統(tǒng)文化的底色,或許才是作家真正的希冀。
①[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夏鑄九、黃麗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本文有關(guān)該書引文均出白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張浩文:《絕秦書》,太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頁。(本文有關(guān)該小說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范子燁:《(桃花源記)的文學密碼與藝術(shù)建構(gòu)》,《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
④陳忠實:《關(guān)于(白鹿原)的答問》,見《(白鹿原)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頁。
⑤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第18頁。
⑥轉(zhuǎn)引白高建國、趙曉華主編:《災害史研究的理論與方 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頁。
⑦張?zhí)脮骸睹駠四隇幕牡摹熬刻烊酥H”之作——評張浩文的(絕秦書)》,《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2期。
⑧李瑩:《關(guān)中大地最后一個鄉(xiāng)紳的消失——評張浩文的(絕秦書)》,《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12期。
作者:劉金玲,海南師范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萬向: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