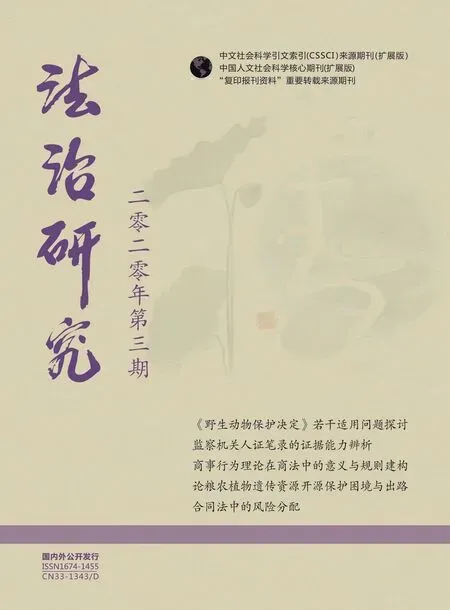《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若干適用問題探討*
葉良芳
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第十六次會(huì)議通過并公布了《關(guān)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dòng)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dòng)物陋習(xí)、切實(shí)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jiǎn)稱《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自即日起施行。從非典疫情到新冠疫情,濫食野生動(dòng)物的陋習(xí)讓人類接連付出慘痛的代價(jià)。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就是保護(hù)人類自己。此次新冠疫情的爆發(fā)再一次給人們敲響警鐘。疫情當(dāng)前,既要反思如何從源頭補(bǔ)齊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存在的短板,又要站在全局高度平衡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與利用的關(guān)系。《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聚焦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的突出問題,在《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等相關(guān)法律修改之前,先及時(shí)明確嚴(yán)厲打擊非法野生動(dòng)物交易和全面禁食野生動(dòng)物等最為緊迫的事項(xiàng),有利于從源頭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衛(wèi)生風(fēng)險(xiǎn),切實(shí)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在宏觀上以全面禁食野生動(dòng)物為導(dǎo)向?qū)ο嚓P(guān)法律的未來修改指明了思路和方向,在微觀上確立了加重處罰制度、參照適用制度、全面禁食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鑒于《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在相關(guān)制度和規(guī)則方面較現(xiàn)行法律存在重大變化,因而有必要探討其內(nèi)在的設(shè)計(jì)機(jī)理,以便準(zhǔn)確地予以適用。
一、關(guān)于“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
《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1條規(guī)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和其他有關(guān)法律禁止獵捕、交易、運(yùn)輸、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必須嚴(yán)格禁止。”“對(duì)違反前款規(guī)定的行為,在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基礎(chǔ)上加重處罰”。該條規(guī)定恢復(fù)了立法實(shí)踐中陳年擱置的加重處罰的“罰則”,其正當(dāng)性何在,具體應(yīng)當(dāng)如何適用,值得探討。
(一)“加重處罰”罰則溯源
加重處罰,顧名思義,是指在法定最高限以上處罰。在新中國(guó)刑事立法領(lǐng)域,關(guān)于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始見于1951年《懲治反革命條例》。該條例第4條第2款規(guī)定:“其他參與策動(dòng)、勾引、收買或叛變者,處十年以下徒刑;其情節(jié)重大者,加重處刑。”1952年《懲治貪污條例》也有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并與從重處罰并列適用。其第4條第1款規(guī)定:“犯貪污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從重或加重處刑:一、對(duì)國(guó)家和社會(huì)事業(yè)及人民安全有嚴(yán)重危害者;……。”1979年刑法在制定過程中,其第33稿第64條曾有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即“對(duì)于個(gè)別罪行嚴(yán)重、情節(jié)惡劣、懷惡不悛的犯罪分子,如果判處法定刑的最高刑還是過輕的,經(jīng)過最高人民法院核準(zhǔn),可以在法定刑以上判處刑罰”。但1979年刑法正式頒布時(shí),取消了這一規(guī)定。1979年刑法施行期間,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頒布了一些單行刑法,又恢復(fù)了加重處罰制度。例如,1981年《關(guān)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以下簡(jiǎn)稱《勞教決定》)第2條第2款規(guī)定:“勞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從重或者加重處罰;刑滿釋放后又犯罪的,從重處罰。刑滿后一律留場(chǎng)就業(yè),不得回原大中城市。”第3條規(guī)定:“勞教人員、勞改罪犯對(duì)檢舉人、被害人和有關(guān)的司法工作人員以及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的干部、群眾行兇報(bào)復(fù)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規(guī)定,從重或者加重處罰。”1983年《關(guān)于嚴(yán)懲嚴(yán)重危害社會(huì)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以下簡(jiǎn)稱《治安決定》)第1條規(guī)定:“對(duì)下列嚴(yán)重危害社會(huì)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規(guī)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1.流氓犯罪集團(tuán)的首要分子或者攜帶兇器進(jìn)行流氓犯罪活動(dòng),情節(jié)嚴(yán)重的,或者進(jìn)行流氓犯罪活動(dòng)危害特別嚴(yán)重的;……。”1997年刑法在總則中不再規(guī)定加重處罰制度,在附則中明確宣告《勞教決定》等單行刑法失效,意味著這些單行刑法涉及的加重處罰規(guī)定不再適用。
在行政立法領(lǐng)域,加重處罰制度也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從有限設(shè)定到絕對(duì)排除的立法過程。1957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規(guī)定:“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從重或者加重處罰:一、后果較重的;二、屢經(jīng)處罰不改的;三、嫁禍于人的;四、拒絕傳問或者逃避處罰的。”第22條第3款規(guī)定:“連續(xù)實(shí)行同一種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從重或者加重處罰。”但是,1986年和1994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均取消了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2005年《治安管理處罰法》更是明文禁止加重處罰。該法第94條規(guī)定:“公安機(jī)關(guān)不得因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的陳述、申辯而加重處罰。”2012年《治安管理處罰法》完全保留了這一規(guī)定。1996年《行政處罰法》第32條第1款規(guī)定:“行政機(jī)關(guān)不得因當(dāng)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2009年和2017年《行政處罰法》對(duì)該款規(guī)定亦完全保留。不過,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是,行政法律雖然沒有規(guī)定加重處罰,但卻有執(zhí)行罰的規(guī)定。例如,2017年《行政處罰法》第51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jī)關(guān)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繳納罰款的,每日按罰款數(shù)額的百分之三加處罰款……。”又如,2015年《稅收征收管理法》第64條規(guī)定:“納稅人、扣繳義務(wù)人在規(guī)定期限內(nèi)不繳或者少繳應(yīng)納或者應(yīng)解繳的稅款,經(jīng)稅務(wù)機(jī)關(guān)責(zé)令限期繳納,逾期仍未繳納的,稅務(wù)機(jī)關(guān)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的規(guī)定采取強(qiáng)制執(zhí)行措施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外,可以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當(dāng)然,執(zhí)行罰不同于狹義的行政處罰,也不能將其視為加重處罰的一種方式,因?yàn)槠溽槍?duì)的是行為人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內(nèi)容的事實(shí),是對(duì)“新”的違法行為的處罰,而非對(duì)“舊”的違法行為的處罰。
(二)“加重處罰”罰則的方法論釋疑
對(duì)于任何不法行為(行政違法或刑事犯罪),在配置處罰(行政處罰或刑罰)時(shí),都應(yīng)遵守一個(gè)基本原則(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dāng)原則),都應(yīng)與該行為的危害程度相適應(yīng)。對(duì)于法律既定的“罰則”,執(zhí)法機(jī)關(guān)或司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給予絕對(duì)的尊重——假定“立法規(guī)定的罰則都是合理的”,而不能突破罰則的最高限給予處罰,否則便僭越了立法機(jī)關(guān)專享的立法權(quán)。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但是,立法機(jī)關(guān)能否設(shè)立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或者在法律中明確授權(quán)執(zhí)法機(jī)關(guān)或司法機(jī)關(guān)在法定最高限以上給予處罰呢?
對(duì)此,學(xué)界向來存在爭(zhēng)議。以1979年刑法草案第33稿第64條的設(shè)定為例。贊同者認(rèn)為,刑法草案分則對(duì)各種犯罪設(shè)定的法定刑,在通常的情況下是適合的,但考慮到我國(guó)過渡時(shí)期階級(jí)斗爭(zhēng)的規(guī)律和特點(diǎn),在各種犯罪中總還會(huì)有少數(shù)很特殊的情況和問題,如果法律上不解決這些特殊問題,就不利于審判機(jī)關(guān)在實(shí)際工作中對(duì)復(fù)雜的犯罪區(qū)別對(duì)待。如果為了解決這些特殊問題而擴(kuò)大法定刑幅度,就勢(shì)必在分則條文中過多地增加死刑、無期徒刑,也容易導(dǎo)致在處理一般案件上產(chǎn)生量刑輕重懸殊的現(xiàn)象,不利于國(guó)家法制的統(tǒng)一。另外,既然給法院以減輕處罰的機(jī)動(dòng)權(quán)力,也應(yīng)給以加重處罰的機(jī)動(dòng)權(quán)力。反對(duì)者認(rèn)為,第一,有了這一條,等于分則每一條的法定刑上面都打開了缺口,這就降低甚至喪失了設(shè)立法定刑的意義;第二,從邏輯上說,因加重幅度沒有限制,刑法分則每條都可能加重到死刑,與少規(guī)定死刑的初衷相悖;第三,設(shè)立了這一條,法律本身規(guī)定下來的法定刑就不能算數(shù),被告人隨時(shí)有被加重處罰的可能,不利于鞏固和加強(qiáng)法制;第四,把加重處罰和減輕處罰相提并論是站不住腳的;第五,即便將核準(zhǔn)權(quán)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也難免有司法權(quán)超越立法權(quán)的嫌疑。①參見高銘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fā)展完善》,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58~59頁。
上述觀點(diǎn)之爭(zhēng),從立法權(quán)力來看,贊同者的主張是能成立的。鑒于立法權(quán)的至上性,無論是以法典或者單行法的形式,設(shè)定“從重處罰”這一特殊的罰則,都具有效力上的現(xiàn)實(shí)性和權(quán)源上的合法性。但從立法技術(shù)考察,結(jié)論并非那么容易得出。這其實(shí)涉及如何提升具體犯罪的刑罰問題,即是采用法定刑升格模式(通過立法給具體犯罪增設(shè)一檔或數(shù)檔法定刑)還是加重處罰模式(授權(quán)司法者在具體犯罪的法定刑的最高限以上適用刑罰)來提升法定刑的幅度。從法律的明確性要求來看,法定刑升格模式針對(duì)具體個(gè)罪而設(shè),刑種和刑度明確清晰,顯然更為可取。而加重處罰模式,往往針對(duì)類罪甚至所有犯罪而設(shè),且可加重的刑種和刑度都極為概括,除非情況特別緊急,否則都不應(yīng)采用。這可能是立法實(shí)踐中加重處罰模式通常備而不用的原因。
《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1條規(guī)定激活了沉寂已久的加重處罰模式。之所以采用這一模式,參與立法的同志作了如下說明:“全面修訂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需要一個(gè)過程,在疫情防控的關(guān)鍵時(shí)刻,由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盡快通過一個(gè)專門決定,既十分必要又十分緊迫。”②《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dòng)物交易 革除濫食野生動(dòng)物陋習(xí)——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法工委有關(guān)部門負(fù)責(zé)人答記者問》,載新華網(wǎng),http://www.hn.xinhuanet.com/2020-02/25/c_1125621609.htm,2020年2月28日訪問。該說明雖然沒有直接針對(duì)加重處罰制度的規(guī)定,但間接回答了這一制度的激活背景。亦即,在當(dāng)前疫情防控這一緊急狀態(tài)下,召集全國(guó)人大專門討論《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等法律的修改已經(jīng)缺乏現(xiàn)實(shí)可能性,但“以最嚴(yán)格的法律條文禁止和嚴(yán)厲打擊一切非法捕殺、交易、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行為”又迫在眉睫,需要立法先行,不得已恢復(fù)加重處罰模式。
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要避免為人詬病,關(guān)鍵在于適用對(duì)象的明確性。有學(xué)者結(jié)合立法規(guī)定,將加重處罰提煉為兩種:一種是罪行的加重,指具體犯罪法定刑幅度的升格;另一種是刑罰的加重,指著眼于刑罰本身的加重。③參見張波:《新中國(guó)從重和加重處罰的考察》,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年第1期。這種劃分是有啟示意義的,但將二者的區(qū)別限定于能否改變刑種(如將最高刑由有期徒刑升格為無期徒刑,或者由無期徒刑升格為死刑)則不甚妥當(dāng)。筆者認(rèn)為,罪行的加重,是指因具體犯罪行為又具有其他特別情節(jié)要素,使行為的危害性增大,因而加重處罰的情形,如脫逃后實(shí)施犯罪、犯罪后果特別嚴(yán)重、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劣的。而刑罰的加重,是指具體犯罪行為的情形不存在特殊性,行為的危害性也沒有變化,僅因特殊時(shí)期為增加刑罰的威懾效應(yīng)而加重處罰的情形。上述1979年刑法草案第33稿第64條即屬于一般性的刑罰的加重,這是要絕對(duì)杜絕的。但上述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中出現(xiàn)的個(gè)別性加重的規(guī)定,由于針對(duì)的是特別對(duì)象或特殊情形,屬于罪行的加重,則具有相對(duì)的合理性,質(zhì)疑的聲音也沒有那么強(qiáng)烈。現(xiàn)行刑法中雖然也有一些加重犯的規(guī)定,但也均是針對(duì)具體情形而設(shè),并非抽象性不加區(qū)別地普遍加重,如刑法第133條關(guān)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刑法第263條關(guān)于具有特定八種情節(jié)的搶劫罪加重處罰的規(guī)定。1996年《行政處罰法》第32條更是明確規(guī)定,“行政機(jī)關(guān)不得因當(dāng)事人申辯而加重處罰。”《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1條規(guī)定針對(duì)的是“獵捕、交易、運(yùn)輸、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具體行為,對(duì)象相對(duì)明確,這應(yīng)屬于個(gè)別性加重而非一般性加重。但與之前的立法例不同的是,該規(guī)定沒有對(duì)加重處罰附加“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多次實(shí)施”“暴力抗拒執(zhí)法檢查”等情節(jié),有過于寬泛之虞,這是在適用時(shí)需要特別警惕的。
(三)“加重處罰”罰則的具體適用
實(shí)踐中,在適用《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的“加重處罰”罰則時(shí),應(yīng)當(dāng)注意把握以下幾點(diǎn):
第一,加重處罰應(yīng)當(dāng)僅限于“獵捕、交易、運(yùn)輸、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行為,除此之外的行為(無論是上游行為還是下游行為)均不得適用。例如,《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50條是關(guān)于“為出售、購買、利用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獵捕工具發(fā)布廣告”行為的罰則,雖然這一廣告行為也與獵捕、交易、運(yùn)輸、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目的行為密切相關(guān),但畢竟不是目的行為本身,因而不得適用加重處罰。
第二,加重處罰應(yīng)當(dāng)以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的處罰為基礎(chǔ),即不能不考慮具體不法行為的危害程度而一律突破法定最高限予以處罰。例如,《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44條規(guī)定:“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三款規(guī)定,以收容救護(hù)為名買賣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的,由縣級(jí)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主管部門沒收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違法所得,并處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價(jià)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將有關(guān)違法信息記入社會(huì)誠(chéng)信檔案,向社會(huì)公布;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假設(shè)行為人違反本條的前段規(guī)定,構(gòu)成行政違法,則決定對(duì)其處罰時(shí),不能當(dāng)然地適用十倍以上的罰款,而應(yīng)首先根據(jù)本條的罰則規(guī)定,結(jié)合其具體行為的危害程度確定一個(gè)罰款數(shù)額,比如三倍的罰款。再根據(jù)《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的“加重處罰”規(guī)定,決定最后的處罰,比如四倍的罰款。
第三,加重處罰應(yīng)當(dāng)有處罰種類的限制,即不能變更不法行為的性質(zhì)而適用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處罰。例如,《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49條規(guī)定:“違反本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使用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或者沒有合法來源證明的非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為食用非法購買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的,由縣級(jí)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主管部門或者市場(chǎng)監(jiān)督管理部門按照職責(zé)分工責(zé)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和違法所得,并處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價(jià)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假設(shè)行為人違反了本條的前段規(guī)定,構(gòu)成最嚴(yán)重的行政違法,應(yīng)當(dāng)處十倍的罰款,在對(duì)其處罰時(shí),也只能在行政違法行為的“罰則”之內(nèi)加重(如適用十二倍的罰款),而不能將其行政違法行為升格為犯罪行為,進(jìn)而適用本條的后段規(guī)定,予以刑罰制裁。
第四,加重處罰應(yīng)當(dāng)有“格”的限制,即不能無限制地加重。正如減輕處罰有“格”的限制一樣(原則上在法定處罰幅度的下一個(gè)處罰幅度內(nèi)裁量處罰),加重處罰也應(yīng)當(dāng)有類似的限制,即原則上只能在法定處罰幅度的上一個(gè)處罰幅度內(nèi)裁量處罰,特殊情形下在不改變處罰性質(zhì)(行政處罰或刑罰)時(shí)可以變更處罰種類。對(duì)此,時(shí)任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法制委員會(huì)副主任王漢斌同志曾有如下說明:“至于如何加重判刑,不是可以無限制地加重,而是罪加一等,即在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判處。如法定最高刑為十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判處十年以上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為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判處無期徒刑;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的,可以判處死刑(包括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④王漢斌:《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法制委員會(huì)關(guān)于加強(qiáng)法律解釋工作等三個(gè)決定(草案)的說明》,載高銘暄、趙秉志主編:《新中國(guó)刑法立法文獻(xiàn)資料總覽》,中國(guó)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570頁。在具體適用時(shí),行政處罰和刑罰在“加重”的程度方面會(huì)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不同的行政處罰之間嚴(yán)厲程度沒有刑罰那么明顯,因而在“格”的識(shí)別上更要仔細(xì)辨別。例如,刑罰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這五個(gè)主刑之間完全呈現(xiàn)一種階梯序列,而行政處罰的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cái)物、責(zé)令停產(chǎn)停業(yè);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zhí)照、行政拘留等彼此之間的級(jí)差則相對(duì)不夠清晰。這是因?yàn)椋塘P的主刑除死刑這一生命刑外都是自由刑,而行政處罰則是訓(xùn)誡刑、財(cái)產(chǎn)刑、資格刑、自由刑等混合規(guī)定在一起。因此,在判斷行政處罰的法定最高限時(shí),尤其要結(jié)合法條規(guī)定的具體處罰種類對(duì)比分析。
第五,加重處罰應(yīng)當(dāng)有時(shí)效的限制,即原則上只能在疫情防控期間適用。行為的危害性,既是一個(gè)客觀存在,也是主體主觀認(rèn)知和體驗(yàn)。同樣的行為,在緊急狀態(tài)下和非緊急狀態(tài)下,其社會(huì)危害程度是有差別的。《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之所以規(guī)定加重處罰,正是考慮到在疫情防控期間,實(shí)施獵捕、交易、運(yùn)輸、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行為,較非疫情防控期間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風(fēng)險(xiǎn)性。因此,在疫情結(jié)束之后,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不用或者少用“加重處罰”規(guī)定。如果認(rèn)為現(xiàn)有法律的罰則嚴(yán)厲性不夠,則應(yīng)及時(shí)啟動(dòng)立法程序予以修改。
二、關(guān)于“參照適用”的規(guī)定
《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2條第3款規(guī)定:“對(duì)違反前兩款規(guī)定的行為,參照適用現(xiàn)行法律有關(guān)規(guī)定處罰。”這里的“前兩款規(guī)定”,即“全面禁食”的規(guī)定(下文詳述)。對(duì)于違反全面禁食的行為,該款設(shè)立了“參照適用”這一罰則。
(一)“參照適用”罰則溯源
“參照”,是指參考并仿照;“參照適用”,就是指參照之后照此辦理。在法律規(guī)范中,“參照適用”則是指參照相關(guān)法條辦理。類似的表述還有,“應(yīng)當(dāng)參照”“可以參照”“參照”“比照”等。我國(guó)向來有“比附援引”的法律傳統(tǒng),如《唐律·名例律》規(guī)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yīng)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yīng)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在新中國(guó)刑事立法領(lǐng)域,參照適用的立法例可以追溯至《懲治貪污條例》。其第12條規(guī)定:“非國(guó)家工作人員勾結(jié)國(guó)家工作人員伙同貪污者,應(yīng)參照本條例第三、四、五、十、十一各條的規(guī)定予以懲治。”1979年刑法既規(guī)定了個(gè)別性參照適用,也規(guī)定了普遍性參照適用(類推制度)。其第138條第1款規(guī)定:“……凡捏造事實(shí)誣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參照所誣陷的罪行的性質(zhì)、情節(jié)、后果和量刑標(biāo)準(zhǔn)給予刑事處分……”該條沒有給誣告陷害罪配置獨(dú)立的法定刑,僅指出可以參照適用的量刑標(biāo)準(zhǔn)。第79條規(guī)定:“本法分則沒有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但是應(yīng)當(dāng)報(bào)請(qǐng)最高人民法院核準(zhǔn)。”該條更是直接創(chuàng)設(shè)了罪名和刑罰的參照適用,而且適用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所有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之后,一些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也有參照適用的規(guī)定。如1990年《鐵路法》第60條第2款規(guī)定:“攜帶炸藥、雷管或者非法攜帶槍支子彈、管制刀具進(jìn)站上車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指私藏槍支、彈藥罪——筆者注)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1993年《紅十字會(huì)法》第15條規(guī)定:“在自然災(zāi)害和突發(fā)事件中,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紅十字會(huì)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zé)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指妨害公務(wù)罪——筆者注)的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zé)任;阻礙紅十字會(huì)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zé)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的,比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的規(guī)定處罰。”但是,1997年刑法對(duì)誣告陷害罪配置了獨(dú)立的法定刑,同時(shí)取消了類推制度。2009年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關(guān)于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將《計(jì)量法》等多部法律中的刑事責(zé)任條款,如“依照刑法第×條的規(guī)定”“比照刑法第×條的規(guī)定”,統(tǒng)一修改為“依照刑法有關(guān)規(guī)定”。自此,在刑事立法中,已經(jīng)不再有參照適用的罰則。
在行政立法領(lǐng)域,參照適用的立法模式則一直存在。例如,1982年《食品安全法(試行)》第6條規(guī)定:“食品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過程必須符合下列衛(wèi)生要求:(一)保持內(nèi)外環(huán)境整潔,采取消除蒼蠅、老鼠、蟑螂和其他有害昆蟲及其孳生條件的措施,與有毒、有害場(chǎng)所保持規(guī)定的距離;……對(duì)食品商販和城鄉(xiāng)集市貿(mào)易食品經(jīng)營(yíng)者在食品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過程中的衛(wèi)生要求,由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參照本條另行規(guī)定。”1990年《國(guó)旗法》第19條規(guī)定:“在公眾場(chǎng)合故意以焚燒、毀損、涂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國(guó)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情節(jié)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guī)定,由公安機(jī)關(guān)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1991年《國(guó)徽法》第13條規(guī)定:“在公眾場(chǎng)合故意以焚燒、毀損、涂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國(guó)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情節(jié)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guī)定,由公安機(jī)關(guān)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2011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條規(guī)定:“車輛在道路以外通行時(shí)發(fā)生的事故,公安機(jī)關(guān)交通管理部門接到報(bào)案的,參照本法有關(guān)規(guī)定辦理。”2019年《建筑法》第83條第1款規(guī)定:“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動(dòng),參照本法執(zhí)行。”1989年《行政訴訟法》第53條第1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guó)務(wù)院部、委根據(jù)法律和國(guó)務(wù)院的行政法規(guī)、決定、命令制定、發(fā)布的規(guī)章以及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省、自治區(qū)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jīng)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jù)法律和國(guó)務(wù)院的行政法規(guī)制定、發(fā)布的規(guī)章。”2014年《行政訴訟法》第63條第3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規(guī)章。”2017年《行政訴訟法》對(duì)該款予以完全保留。
以上僅就立法領(lǐng)域而言,但在司法領(lǐng)域,則無論是刑事審判還是行政審判,均存在參照適用的情況。這集中表現(xiàn)在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目前推行的案例指導(dǎo)制度方面。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案例指導(dǎo)工作的規(guī)定》第7條率先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指導(dǎo)性案例,各級(jí)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shí)應(yīng)當(dāng)參照。”2010年和201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案例指導(dǎo)工作的規(guī)定》沒有明確各地人民檢察院辦理案件是否應(yīng)當(dāng)參照指導(dǎo)性案例,只是要求“人民檢察院參照指導(dǎo)性案例辦理案件,可以引述相關(guān)指導(dǎo)性案例作為釋法說理根據(jù),但不得代替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作為案件處理決定的直接法律依據(jù)”。但201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案例指導(dǎo)工作的規(guī)定》第15條明確規(guī)定:“各級(jí)人民檢察院應(yīng)當(dāng)參照指導(dǎo)性案例辦理類似案件,可以引述相關(guān)指導(dǎo)性案例進(jìn)行釋法說理,但不得代替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作為案件處理決定的直接依據(jù)。”
(二)“參照適用”罰則的方法論釋疑
從立法技術(shù)來看,“參照”和“依據(jù)”“參考”是含義不同的。“依據(jù)”,是指依照進(jìn)行。依據(jù)的對(duì)象是針對(duì)待決事項(xiàng)的法律規(guī)范,具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可直接援引適用。“參考”,是指參合、考量。參考的對(duì)象是學(xué)理解釋、習(xí)慣、政策、參考案例、法院內(nèi)部的統(tǒng)一裁判尺度要求等,這些都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也不能作為裁判的法律依據(jù)。“參照”,是指參酌考量,再?zèng)Q定是否適用。參照的對(duì)象是針對(duì)其他事項(xiàng)的法律規(guī)范,對(duì)其他事項(xiàng)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對(duì)待決事項(xiàng)則為效力待定。因此,參照與依據(jù)、參考之間的主要區(qū)別在法律效力上,參照介于依據(jù)與參考之間,其法律效力小于有直接法律強(qiáng)制力的依據(jù),但大于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參考,其有著弱法律約束力。⑤參見紀(jì)長(zhǎng)勝:《“參照”的法理與適用》,載李鳳章主編:《產(chǎn)權(quán)法治研究》2017年第2輯,上海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頁。
根據(jù)不同的標(biāo)準(zhǔn),可以對(duì)參照適用進(jìn)行不同的劃分。(1)根據(jù)參照對(duì)象的適用強(qiáng)度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加強(qiáng)型參照、一般型參照和選擇型參照。加強(qiáng)型參照,是指在“參照”一詞之前增加“應(yīng)”“應(yīng)當(dāng)”等詞語修飾,以加強(qiáng)語氣,強(qiáng)調(diào)所參照的法律規(guī)范的約束力效果;選擇型參照,是指在“參照”一詞之前增加“可”“可以”等詞語修飾,以減弱語氣,表明對(duì)所參照的法律規(guī)范可以適用也可以不適用;一般型參照,是指在“參照”一詞之前不加任何修改語,在法律約束力的效力強(qiáng)度上介于加強(qiáng)型參照和一般型參照之間。(2)根據(jù)參照的形式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規(guī)范類參照和案例類參照。規(guī)范類參照,是指參照的對(duì)象是法律法規(guī)、政策、辦法等;案例類參照,是指參照的對(duì)象是最高司法機(jī)關(guān)發(fā)布的指導(dǎo)性案例或者其他案例等。根據(jù)全國(guó)人大法工委《立法技術(shù)規(guī)范(試行)(一)》的解釋,“參照”一般用于沒有直接納入法律調(diào)整范圍,但是又屬于該范圍邏輯內(nèi)涵自然延伸的事項(xiàng)。這里的“參照”顯然僅指規(guī)范類參照,即法定授權(quán)式的法律擴(kuò)展適用,而非案例的比照適用。(3)根據(jù)參照的程度不同,可以將其劃分為完全型參照和部分型參照。完全型參照,是指參照的對(duì)象是整個(gè)法律規(guī)范,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效果;部分型參照,是指參照的對(duì)象是法律規(guī)范的一部分,即法律效果部分,行為模式則并不參照。1979年刑法規(guī)定的類推制度是典型的完全型參照,現(xiàn)行刑法第180條第4款規(guī)定的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則屬于部分型參照(僅指出法定刑需援引適用)。
在刑事立法領(lǐng)域,規(guī)范類參照、完全型參照(類推制度)是嚴(yán)格禁止的,可以允許的只有案例類參照和部分型參照。刑事立法之所以取消類推制度,最根本的原因是刑事類推和罪刑法定原則在本質(zhì)上是對(duì)立的,極易導(dǎo)致罪刑擅斷,不利于人權(quán)保障。“毫無疑問,刑事類推對(duì)于成文法的局限性確是一劑良藥。但是,刑事類推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標(biāo)準(zhǔn),本身潛藏著司法擅斷的危險(xiǎn)性”。⑥陳興良:《罪刑法定的當(dāng)代命運(yùn)》,載《法學(xué)研究》1996年第2期。另外,刑事立法技術(shù)的提高也是一個(gè)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國(guó)刑法自頒布以來,經(jīng)過多次修改和補(bǔ)充,“可以說,相當(dāng)完備、相當(dāng)周密。尤其是嚴(yán)重的罪行,已無無法可依之虞。因此再規(guī)定類推制度,實(shí)無必要,而且這樣做只會(huì)因小失大、得不償失”。⑦同注①,第174頁。總之,類推制度有利于強(qiáng)化刑法的適應(yīng)性,但卻蘊(yùn)含著司法擅斷的危險(xiǎn);罪刑法定容易導(dǎo)致刑法的僵化,但卻有利于人權(quán)保障。兩相權(quán)衡,廢除類推制度利大于弊。在行政立法領(lǐng)域,參照適用的立法模式則相當(dāng)普遍,不僅案例類參照、部分型參照大量存在,規(guī)范類參照、完全型參照也不鮮見。《行政訴訟法》確立的“參照規(guī)章”規(guī)則就是完全型參照的適例。之所以設(shè)立這一規(guī)則,時(shí)任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副委員長(zhǎng)、法制工作委員會(huì)主任王漢斌同志作了如下說明:“憲法和有關(guān)法律規(guī)定國(guó)務(wù)院各部委和省、市人民政府有權(quán)依法制定規(guī)章,行政機(jī)關(guān)有權(quán)依據(jù)規(guī)章行使職權(quán)。但是,規(guī)章與法律、法規(guī)的地位和效力不完全相同,有的規(guī)章還存在一些問題。因此,草案規(guī)定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時(shí),參照規(guī)章的規(guī)定,是考慮了上述兩種不同的意見,對(duì)符合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規(guī)章,法院要參照審理,對(duì)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規(guī)原則精神的規(guī)章,法院可以有靈活處理的余地。”⑧王漢斌:《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行政訴訟法(草案)〉的說明》,載全國(guó)人大網(wǎng),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9-03/28/content_1481184.htm,2020年2月29日訪問。參照規(guī)章,意味著在法律、行政法規(guī)、條例等缺位的情形下,完全可以根據(jù)部門規(guī)章和地方政府規(guī)章來處理行政事項(xiàng)。如此規(guī)定,應(yīng)是基于行政事項(xiàng)的廣泛性和行政行為的效率性的需要。
(三)“參照適用”罰則的具體適用
《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規(guī)定,對(duì)違反全面禁食規(guī)定的,“參照適用現(xiàn)行法律有關(guān)規(guī)定處罰”。但問題是,現(xiàn)行《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等法律并未有相關(guān)的關(guān)于全面禁食的罰則規(guī)定,因而,這里的“參照適用”實(shí)際只能是“類推適用”。但也不能簡(jiǎn)單地認(rèn)為,這里的“參照適用”就是完全型參照。事實(shí)上,如果考慮到?jīng)Q定對(duì)行為模式(全面禁食的違法性)是有明確規(guī)定的,而只是未明確規(guī)定行為的法律效果(處罰的種類和幅度),而決定本身又屬于廣義的法律,因而本款規(guī)定屬于“法律規(guī)定了行為模式但僅指出援引處罰”的情形,應(yīng)該歸類于部分型參照。
雖然這一立法“類推”在權(quán)源上沒有問題,但在具體適用時(shí)仍應(yīng)援引最相類似的條款。目前的法律體系上,最可能被參照適用的應(yīng)是《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49條的規(guī)定,即“違反本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使用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或者沒有合法來源證明的非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或者為食用非法購買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的,由縣級(jí)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主管部門或者市場(chǎng)監(jiān)督管理部門按照職責(zé)分工責(zé)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和違法所得,并處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價(jià)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需要注意的是,該條規(guī)定的“構(gòu)成犯罪的”,僅限于“為食用非法購買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的情形,《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2條第1、2款規(guī)定的全面禁食行為能夠刑事入罪的,亦應(yīng)限定于此。這是因?yàn)椋谭ㄊ墙^對(duì)禁止完全型參照的,部分型參照也僅存在有限的適用空間。根據(jù)2000年《立法法》第7條第2、3款的規(guī)定,“刑事、民事、國(guó)家機(jī)構(gòu)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由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定和修改。“除應(yīng)當(dāng)由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制定和修改;在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閉會(huì)期間,“對(duì)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定的法律”,由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進(jìn)行部分補(bǔ)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第8條規(guī)定,“犯罪和刑罰”,只能制定法律。《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雖然屬于廣義的法律,但與《立法法》提及的“基本法律”“其他法律”還是不能等同的。因此,筆者認(rèn)為,它可以創(chuàng)設(shè)行政罰則,但不能增設(shè)新罪。具體而言,《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2條第1款的禁食行為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行政違法行為,即便再嚴(yán)重,也不能上升為刑事犯罪;第2款規(guī)定的禁食行為,則應(yīng)區(qū)別對(duì)待:如果涉及的野生動(dòng)物系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可以刑事入罪;如果是其他陸生野生動(dòng)物,則只能予以行政處罰。
關(guān)于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現(xiàn)行刑法規(guī)定的罪名主要有:第341條規(guī)定的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罪,非法收購、運(yùn)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制品罪和非法狩獵罪。前兩個(gè)罪名的行為類型必須是“獵捕”“殺害”“收購”“運(yùn)輸”“出售”行為,行為對(duì)象必須是“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或其制品”;第三個(gè)罪名的行為對(duì)象可以是“任何野生動(dòng)物資源”,但行為類型必須是“狩獵”,行為情狀必須是“在禁獵區(qū)、禁獵期或者使用禁獵的工具、方法”。由此可見,現(xiàn)行刑法并未將食用行為犯罪化,也沒有將所有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納入刑罰調(diào)整的范圍。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三百一十二條的解釋》規(guī)定,“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是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購買的,屬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非法收購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的行為”。據(jù)此,“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購買”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的,可以以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罪論處。這一立法解釋雖然明確“食用”等目的不影響非法收購的認(rèn)定,但并未擴(kuò)張非法收購的對(duì)象范圍。總之,根據(jù)現(xiàn)行刑法的規(guī)定,《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禁止的兩類行為尚難以犯罪論處。如果要將這兩類行為以犯罪論處,則必須要修改刑法。首先,必須擴(kuò)大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罪,非法收購、運(yùn)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制品罪的對(duì)象范圍,將“珍貴、瀕危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修改為“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其次,必須取消非法狩獵的情狀規(guī)定,即禁止在任何區(qū)域、任何時(shí)間、以任何手段狩獵野生動(dòng)物。再次,必須增設(shè)“食用野生動(dòng)物罪”,即將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行為以犯罪論處。顯然,這些修改牽涉面極廣、力度極大,有無違背刑法謙抑性原則,是將來立法修改時(shí)需要充分論證的。
另外,無論是參照適用罪刑規(guī)范,還是參照適用行政處罰規(guī)范,都應(yīng)是一般型參照,而非加強(qiáng)型參照。換言之,對(duì)于《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2條規(guī)定的禁食行為,執(zhí)法機(jī)構(gòu)或司法部門在辦理案件時(shí),雖然通常情況下應(yīng)當(dāng)首先考慮追究行政違法責(zé)任或刑事犯罪責(zé)任,但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酌情對(duì)待決個(gè)案不予行政處罰或刑罰處罰。
三、關(guān)于“全面禁食”的規(guī)定
《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2條第1、2款規(guī)定:“全面禁止食用國(guó)家保護(hù)的‘有重要生態(tài)、科學(xué)、社會(huì)價(jià)值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dòng)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yǎng)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全面禁止以食用為目的獵捕、交易、運(yùn)輸在野外環(huán)境自然生長(zhǎng)繁殖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該兩款關(guān)于全面禁食規(guī)定,極大地拓展了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的處罰范圍,但也是最具爭(zhēng)議的條款,值得深入探討。
(一)沒有例外:“全面禁食”規(guī)定的涵射范圍
全面禁食規(guī)定,是一個(gè)全新的罰則設(shè)定。《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30條:“禁止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使用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沒有合法來源證明的非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為食用非法購買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據(jù)此,該法堅(jiān)持的是有限禁食原則。具體而言,其禁止的是兩類行為:一是制售食品行為,且使用的食材必須是“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或者“沒有合法來源證明的非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二是為食用而非法購買的行為(“購買”而非“食用”行為),且購買的對(duì)象必須是“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此外,《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28條⑨《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28條規(guī)定:“對(duì)人工繁育技術(shù)成熟穩(wěn)定的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經(jīng)科學(xué)論證,納入國(guó)務(wù)院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名錄。對(duì)列入名錄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可以憑人工繁育許可證,按照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主管部門核驗(yàn)的年度生產(chǎn)數(shù)量直接取得專用標(biāo)識(shí),憑專用標(biāo)識(shí)出售和利用,保證可追溯。”“對(duì)本法第十條規(guī)定的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名錄進(jìn)行調(diào)整時(shí),根據(jù)有關(guān)野外種群保護(hù)情況,可以對(duì)前款規(guī)定的有關(guān)人工繁育技術(shù)成熟穩(wěn)定野生動(dòng)物的人工種群,不再列入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名錄,實(shí)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應(yīng)當(dāng)依照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和本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取得人工繁育許可證和專用標(biāo)識(shí)”。還引入了人工繁育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名錄制度,對(duì)列入名錄的野生動(dòng)物,可以憑人工繁育許可證,進(jìn)行出售和交易。因此,《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處罰的是制售、購買行為,而非食用行為,且制售、購買的對(duì)象是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和未列入名錄、人工繁育的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以及沒有合法來源的非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但對(duì)列入名錄、人工繁育的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和有合法來源的非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及其制品,則不在禁止之列。⑩據(jù)統(tǒng)計(jì),目前有國(guó)家一級(jí)保護(hù)陸生野生動(dòng)物98種、國(guó)家二級(jí)保護(hù)陸生野生動(dòng)物308種,還有重要生態(tài)、科學(xué)、社會(huì)價(jià)值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1591種以及昆蟲120屬的所有種等都納入保護(hù)范圍。但是,蝙蝠、鼠類、鴉類等約1000種陸生脊椎野生動(dòng)物尚未列入保護(hù)范圍。總體而言,《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對(duì)“野生動(dòng)物”和“人工繁育的動(dòng)物”作了區(qū)分,采取的是分級(jí)保護(hù)原則。?參見葉良芳、應(yīng)家赟:《人工馴養(yǎng)繁殖的野生動(dòng)物屬于刑法的規(guī)制范圍嗎?》,載《安徽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第2期。
《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則采取全面禁止原則,將以往對(duì)獵捕、販賣、運(yùn)輸、加工等供應(yīng)鏈的單向打擊,延伸到對(duì)食用需求的消費(fèi)鏈的雙向打擊,編織了一張野生動(dòng)物全鏈條保護(hù)網(wǎng)。具體而言,《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在保留《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著眼于處罰銷售環(huán)節(jié)的同時(shí),另外增設(shè)兩項(xiàng)處罰消費(fèi)環(huán)節(jié)的規(guī)定:一是全面禁食所有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包括“三有”陸生野生動(dòng)物和人工繁育、人工飼養(yǎng)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二是全面禁止以食用為目的獵捕、交易、運(yùn)輸行為,行為對(duì)象為所有在野外環(huán)境自然生長(zhǎng)繁殖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簡(jiǎn)言之,所有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水生野生動(dòng)物除外),無論是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還是非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的,是純野外環(huán)境生長(zhǎng)繁育的還是人工飼養(yǎng)繁育的,一律禁止食用。值得注意的是,《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3條第1款規(guī)定:“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動(dòng)物,屬于家畜家禽,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畜牧法》的規(guī)定。”根據(jù)該款規(guī)定,野生動(dòng)物只要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則視為家畜家禽,可以交易、食用。但這也不能算是為全面禁食開了一個(gè)小口子,因?yàn)榱腥胄笄葸z傳資源目錄的“野生動(dòng)物”,嚴(yán)格地說,已經(jīng)不再屬于野生動(dòng)物了。?關(guān)于“野生動(dòng)物”和“非野生動(dòng)物”的區(qū)分,《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采取的是“環(huán)境區(qū)分法”,即在野外自然環(huán)境生長(zhǎng)的,為野生動(dòng)物;在人工控制環(huán)境生長(zhǎng)的,為非野生動(dòng)物(人工繁育的動(dòng)物)。《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則改采“目錄區(qū)分法”,即任何未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包括人工繁育但未列入名錄的,均為野生動(dòng)物;列入名錄的,包括人工繁育但列入名錄的,均為非野生動(dòng)物。綜上,《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傳遞了一個(gè)強(qiáng)烈的信號(hào):野生動(dòng)物不能吃,能吃的不是野生動(dòng)物。就此而言,全面禁食規(guī)定可謂是史上“最嚴(yán)禁食令”。
(二)公共衛(wèi)生:“全面禁食”規(guī)定的制定根據(jù)
全面禁食規(guī)定之所以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食用問題作了近乎一刀切的規(guī)定,最根本的原因是基于維護(hù)公共衛(wèi)生安全的需要。眾所周知,近年來,H7N9禽流感、埃博拉病毒、塞卡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等重大公共衛(wèi)生事件,均與野生動(dòng)物存在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性。例如,2003年的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就是蝙蝠,蝙蝠感染了果子貍后又傳給人類。一些野生動(dòng)物感染病毒后并無不適,但如果傳染給人類,可能產(chǎn)生新毒株,進(jìn)而致病致死。人類食用這些野生動(dòng)物或侵害其棲息地,則加大了接觸和傳播病毒的機(jī)會(huì),給疫情爆發(fā)提供了可能性。此次新冠疫情的爆發(fā),雖然尚沒有明確其自然宿主和中間宿主,但種種跡象表明,它與食用野生動(dòng)物脫不了干系。中國(guó)疾病預(yù)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報(bào)告就認(rèn)為:“新型冠狀病毒可能于2019年12月初從湖北省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chǎng)的某種野生動(dòng)物外溢及其市場(chǎng)環(huán)境污染感染人,進(jìn)而造成人與人之間傳播。”?《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進(jìn)展和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載中國(guó)疾病預(yù)防控制中心網(wǎng)站,http://www.chinacdc.cn/yyrdgz/202001/P020200128 523354919292.pdf,2020年3月1日訪問。中國(guó)-世界衛(wèi)生組織聯(lián)合考察組的報(bào)告也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種動(dòng)物源性病毒。目前的全基因組基因序列系統(tǒng)進(jìn)化分析結(jié)果顯示,蝙蝠似乎是該病毒的宿主,但中間宿主尚未明顯。”?《中國(guó)—世界衛(wèi)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聯(lián)合考察報(bào)告》,載國(guó)家衛(wèi)健委網(wǎng)站,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2002/87fd92510d094e4b9bad597608f5cc2c.shtml,2020年3月1日訪問。因此,如果沒有食客對(duì)吃野味的口腹之欲的無止境的貪求,就不會(huì)有這次新冠疫情的發(fā)生;如果能夠斬?cái)嗍晨团c野生動(dòng)物之間的緊密接觸,就能避免將來類似衛(wèi)生事件的重演。基于這一認(rèn)識(shí),《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的立法目的也應(yīng)作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即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立法的價(jià)值目標(biāo)不應(yīng)僅限于“維護(hù)生態(tài)平衡和生物多樣性”,而應(yīng)同時(shí)納入“保障公共衛(wèi)生、公眾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內(nèi)容。?2020年1月22日,19位中科院院士、高校教授聯(lián)名呼吁,由全國(guó)人大緊急修訂《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將公共健康安全的內(nèi)容納入到野生動(dòng)物利用的條款中。參見《19位學(xué)者呼吁全國(guó)人大緊急修訂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載財(cái)新網(wǎng),http://www.caixin.com/2020-01-24/101508072.html,2020年3月1日訪問。
公允地說,立法者的上述認(rèn)識(shí)是完全符合客觀實(shí)際的。科學(xué)研究表明,人類主要疾病,絕大多數(shù)可以追蹤到脊椎動(dòng)物的源頭,包括靈長(zhǎng)類動(dòng)物、嚙齒類動(dòng)物、兔形目動(dòng)物、有蹄類動(dòng)物、鳥類等。不少脊椎動(dòng)物宿主含有各種病毒,僅蝙蝠身上就宿生有1000多種病毒。世界衛(wèi)生組織將在人類和脊椎動(dòng)物之間傳播的疾病定義為人畜共患傳染病,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表明,在175種被認(rèn)為是“新發(fā)”疾病中,75%是人畜共患傳染病,如鼠疫、瘋牛病、口蹄疫、猴天花、狂犬病等。獼猴(國(guó)家二類保護(hù)動(dòng)物)有10%~60%攜帶B病毒。它如果撓人一下,甚至吐一口水,都可能致人感染,而生吃猴腦者感染B病毒的可能性更大。慘痛的事實(shí)一再警示人類,野生動(dòng)物是一個(gè)潛在的危及公共衛(wèi)生的風(fēng)險(xiǎn)源,對(duì)此再也不能無動(dòng)于衷了。從環(huán)境資源的角度,也許生態(tài)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動(dòng)物福利論和反動(dòng)物福利論還可以唇槍舌劍地大辯一場(chǎng),但從公共衛(wèi)生的角度,敬畏大自然、拒食野生動(dòng)物,卻是不容辯駁的安全需要。
不過,認(rèn)識(shí)到野生動(dòng)物的衛(wèi)生風(fēng)險(xiǎn)是一回事,如何防范其風(fēng)險(xiǎn)又是另一回事。不少人認(rèn)為,野生動(dòng)物在端上餐桌之前都經(jīng)過烹、煮、燉、烤、炒等高溫處理,即使體內(nèi)潛藏有病毒,也早已經(jīng)被殺死,不存在傳播的可能性。因此,沒有必要禁食野生動(dòng)物。這一觀點(diǎn)即使能夠成立,也不能否證禁止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正當(dāng)性。食用野生動(dòng)物的消費(fèi)環(huán)節(jié)也許沒有病毒傳播的風(fēng)險(xiǎn),但在前端的制售(獵捕、運(yùn)輸、交易、宰殺)環(huán)節(jié)卻存在極高的傳播風(fēng)險(xiǎn)。而“沒有買賣就沒有殺戮”,制售環(huán)節(jié)和消費(fèi)環(huán)節(jié)是一種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正是由于數(shù)量眾多的食客存在,才催生了龐大的野生動(dòng)物產(chǎn)業(yè)鏈。而以往的治理經(jīng)驗(yàn)表明,僅靠規(guī)制生產(chǎn)、銷售等前端環(huán)節(jié),預(yù)防效果是差強(qiáng)人意的。因?yàn)橐粋€(gè)完美的野生動(dòng)物交易市場(chǎng)是不存在的,由于受科學(xué)技術(shù)水平的制約,再加上病毒演變的復(fù)雜性,總會(huì)存在一些檢疫檢驗(yàn)盲區(qū)和漏洞。而人一旦被傳染病毒,其帶來的破壞力是不可估量的。為此,有必要溯源規(guī)制,掐斷野生動(dòng)物產(chǎn)業(yè)鏈的源頭——旺盛的消費(fèi)需求。這樣,前端堵截和后端死守雙管齊下,才是最保險(xiǎn)和最有效的預(yù)防策略。
(三)關(guān)聯(lián)制度:“全面禁食”規(guī)定的實(shí)現(xiàn)保障
“法律首先產(chǎn)生于習(xí)俗和人民的信仰”,?[德]薩維尼:《論立法和法學(xué)的當(dāng)代使命》,許章潤(rùn)譯,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對(duì)于一個(gè)有著豐富飲食文化的民族而言,“全面禁食”無疑是一個(gè)革新除弊的規(guī)則創(chuàng)新。要使這一規(guī)則真正發(fā)揮實(shí)效,實(shí)現(xiàn)改變民眾飲食觀念、重塑民眾飲食文化的意圖,沒有相應(yīng)的配套制度是根本不行的。立法者顯然十分清楚這一點(diǎn),因而確立了若干配套規(guī)定。在此,著重闡述三項(xiàng)配套制度: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制度、養(yǎng)殖戶補(bǔ)償制度和宣傳教育制度。
首先,是建立和完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制度。《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3條規(guī)定:“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動(dòng)物,屬于家畜家禽,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畜牧法》的規(guī)定。”“國(guó)務(wù)院畜牧獸醫(yī)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制定并公布畜禽遺傳資源目錄。”該條規(guī)定堅(jiān)持了立法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tǒng)一,既貫徹了全面禁食野生動(dòng)物的精神,又從實(shí)際出發(fā),將對(duì)家畜家禽業(yè)的負(fù)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一方面,全面禁食是“零容忍”原則,沒有例外,這有利于實(shí)踐執(zhí)行;另一方面,列入目錄的野生動(dòng)物不再屬于野生動(dòng)物,可以為人類所用,包括食用、藥用,這有利于合理利用資源。對(duì)此,參與立法的同志作了如下說明:“比較常見的家畜家禽(如豬、牛、羊、雞、鴨、鵝等),是主要供食用的動(dòng)物,依照畜牧法、動(dòng)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規(guī)管理。還有一些動(dòng)物(如兔、鴿等)的人工養(yǎng)殖利用時(shí)間長(zhǎng)、技術(shù)成熟,人民群眾已廣泛接受,所形成的產(chǎn)值、從業(yè)人員具有一定規(guī)模,有些在脫貧攻堅(jiān)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按照決定的規(guī)定,這些列入畜牧法規(guī)定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動(dòng)物,也屬于家畜家禽,對(duì)其養(yǎng)殖利用包括食用等,適用畜牧法的規(guī)定進(jìn)行管理,并進(jìn)行嚴(yán)格檢疫。”?《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dòng)物交易 革除濫食野生動(dòng)物陋習(xí)——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法工委有關(guān)部門負(fù)責(zé)人答記者問》,載新華網(wǎng),http://www.hn.xinhuanet.com/2020-02/25/c_1125621609.htm,2020年2月28日訪問。
事實(shí)上,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在2005年《畜牧法》中即有規(guī)定,該法于2015年修正,關(guān)于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完全保留。但是,該法的立法目的,主要側(cè)重于對(duì)畜禽遺傳資源的“保護(hù)”,對(duì)其“利用”的目的極不明顯。這集中體現(xiàn)在該法第12條第1款和第13條第1款的表述上。前者內(nèi)容為:“國(guó)務(wù)院畜牧獸醫(yī)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公布國(guó)家級(jí)畜禽遺傳資源保護(hù)名錄,對(duì)原產(chǎn)我國(guó)的珍貴、稀有、瀕危的畜禽遺傳資源實(shí)行重點(diǎn)保護(hù)。”后者內(nèi)容為:“國(guó)務(wù)院畜牧獸醫(yī)行政主管部門……省級(jí)人民政府畜牧獸醫(yī)行政主管部門……分別建立或者確定畜禽遺傳資源保種場(chǎng)、保護(hù)區(qū)和基因庫,承擔(dān)畜禽遺傳資源保護(hù)任務(wù)。”另外,該法也沒有與《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法》第28條規(guī)定的人工繁育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名錄制度進(jìn)行必要的銜接。還有,《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模糊、更新不定期、公布不規(guī)范,并沒有發(fā)揮應(yīng)有的指引作用。2003年8月4日,林業(yè)部等12個(gè)部門聯(lián)合發(fā)文,公布了《商業(yè)性經(jīng)營(yíng)利用馴養(yǎng)繁殖技術(shù)成熟的陸生野生動(dòng)物名單》(以下簡(jiǎn)稱《商業(yè)名單》),將梅花鹿等54種陸生野生動(dòng)物納入其中,可以從事經(jīng)營(yíng)利用性馴養(yǎng)繁殖和經(jīng)營(yíng)。實(shí)操中,這一名單成了判斷野生動(dòng)物能否食用的“白名單”,而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卻成了不折不扣的“畜禽遺傳資源保護(hù)名單”。這次《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賦予畜禽遺傳資源目錄以確定可供食用的野生動(dòng)物的“白名單”功能,基本是可行的,但應(yīng)明確其與人工繁育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名錄和《商業(yè)名錄》的關(guān)系(替代、補(bǔ)充抑或整合),并根據(jù)人工繁育和檢疫檢驗(yàn)技術(shù)的發(fā)展,不斷調(diào)整更新具體名單。?2020年2月28日,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出臺(tái)六項(xiàng)措施貫徹落實(shí)《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其中,第2項(xiàng)措施為:“加快制定畜禽遺傳資源目錄。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畜牧法》的規(guī)定,將比較常見的家畜家禽(如豬、牛、羊、雞、鴨、鵝等)等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依照畜牧法的規(guī)定進(jìn)行管理。”總體而言,對(duì)于人工馴養(yǎng)繁殖的動(dòng)物,可以采取分類管理、區(qū)別利用的原則:對(duì)于猴子、黑猩猩等動(dòng)物,基于與人類的近親性,無論是多少子代,都不得納入名錄;對(duì)于蝙蝠、果子貍等動(dòng)物,基于確知的高度衛(wèi)生風(fēng)險(xiǎn),也不得納入名錄;對(duì)于鵪鶉、梅花鹿等動(dòng)物,如果養(yǎng)殖技術(shù)成熟、檢疫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則可以逐步納入名錄。
其次,是建立養(yǎng)殖戶補(bǔ)償制度。《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7條第2款規(guī)定:“國(guó)務(wù)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應(yīng)當(dāng)采取必要措施,為本決定的實(shí)施提供相應(yīng)保障。有關(guān)地方人民政府應(yīng)當(dāng)支持、指導(dǎo)、幫助受影響的農(nóng)戶調(diào)整、轉(zhuǎn)變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給予一定補(bǔ)償。”該款規(guī)定明確全面禁食之后,要給養(yǎng)殖戶一定的經(jīng)濟(jì)補(bǔ)償。這充分考慮到全面禁食規(guī)定對(duì)養(yǎng)殖業(yè)的沖擊和影響,較好地做到了價(jià)值權(quán)衡。人類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的馴養(yǎng)繁殖,起始于初民時(shí)期,一直延續(xù)至今,歷經(jīng)千年,綿延不絕。人類所有的家畜家禽均來源于自然界中的野生物種;為了穩(wěn)定獲取肉類或者毛皮,人類不斷馴化新的野生動(dòng)物。在傳統(tǒng)的食用養(yǎng)殖動(dòng)物以外,人類以食用為主要目的而馴養(yǎng)繁殖的動(dòng)物種類越來越多。尤其是在中國(guó),傳統(tǒng)飲食文化催生形成了規(guī)模龐大的食用特種動(dòng)物養(yǎng)殖產(chǎn)業(yè)。據(jù)《中國(guó)野生動(dòng)物養(yǎng)殖產(chǎn)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報(bào)告》(2017年中國(guó)工程院咨詢研究項(xiàng)目)數(shù)據(jù),2016年我國(guó)食用野生動(dòng)物產(chǎn)業(yè)的直接從業(yè)者約626.34萬人,總產(chǎn)值1250.54億元。其中兩棲爬行類養(yǎng)殖從業(yè)人員101.7萬人,年產(chǎn)值506.48億元;爬行動(dòng)物養(yǎng)殖從業(yè)人員501.13萬人,年產(chǎn)值643.22億元;鳥類養(yǎng)殖從業(yè)人員14.73萬人,年產(chǎn)值76.56億元;獸類養(yǎng)殖從業(yè)人員8.77萬人,年產(chǎn)值24.28億元。禁食野生動(dòng)物,不得不在商業(yè)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間進(jìn)行權(quán)衡。這種權(quán)衡雖然不是零和博弈,但必須對(duì)二者進(jìn)行價(jià)值位序排列。立法機(jī)關(guān)根據(jù)疫情時(shí)期的特殊情勢(shì),將安全利益置于商業(yè)利益之上,是符合緊缺利益優(yōu)先原則的。
但是,全面禁食規(guī)定畢竟對(duì)養(yǎng)殖業(yè)主造成巨大的經(jīng)濟(jì)損失,對(duì)此,不能完全由其個(gè)人承擔(dān)。《行政許可法》第8條第2款規(guī)定:“行政許可所依據(jù)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準(zhǔn)予行政許可所依據(jù)的客觀情況發(fā)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jī)關(guān)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jīng)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cái)產(chǎn)損失的,行政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依法給予補(bǔ)償。”這一規(guī)定與《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7條第2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對(duì)此,野生動(dòng)物主管部門及各地方政府應(yīng)當(dāng)全面地貫徹落實(shí),不能只注重執(zhí)行禁令,而忽視對(duì)“受影響的農(nóng)戶”的指導(dǎo)、幫助、支持以及補(bǔ)償。(1)獲得補(bǔ)償是養(yǎng)殖戶的法定權(quán)利,給付補(bǔ)償是行政機(jī)關(guān)的法定義務(wù)。如果撤回行政許可而拒不給予補(bǔ)償,則屬違法。(2)補(bǔ)償對(duì)象是養(yǎng)殖戶,即《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所指的“受影響的農(nóng)戶”,一般是人工繁育許可證的被許可人。(3)承擔(dān)補(bǔ)償義務(wù)的機(jī)關(guān)是作出并撤回行政許可的機(jī)關(guān)。根據(jù)相關(guān)規(guī)定,國(guó)家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動(dòng)物的人工繁育、經(jīng)營(yíng)利用的審批權(quán)限屬于省級(jí)政府的林業(yè)等主管部門,撤回行政許可的補(bǔ)償義務(wù),也應(yīng)當(dāng)由作出審批決定的機(jī)關(guān)承擔(dān)。(4)補(bǔ)償不是“行政賠償”,不適用《行政賠償法》的程序和標(biāo)準(zhǔn)。行政賠償?shù)那疤幔侵感姓C(jī)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quán)而對(duì)相對(duì)方合法權(quán)益造成損害;而撤回行政許可系依據(jù)《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實(shí)施,?當(dāng)然,如果撤回行政許可的決定本身違法,即根據(jù)《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和相關(guān)法律的規(guī)定,本不應(yīng)撤回而強(qiáng)行撤回的,則屬于“因行政行為違法而給相對(duì)方合法權(quán)益造成損害”的情形,應(yīng)屬于行政賠償?shù)姆秶2⒉贿`法。(5)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一般應(yīng)等于或低于實(shí)際損失數(shù)額,預(yù)期收益不屬于補(bǔ)償范圍。行政補(bǔ)償?shù)臉?biāo)準(zhǔn)以實(shí)際損失為限,具體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確定。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中的預(yù)期收益、貸款利息等均不屬于補(bǔ)償范圍。
再次,是強(qiáng)化教育宣傳制度。《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第5條規(guī)定:“各級(jí)人民政府和人民團(tuán)體、社會(huì)組織、學(xué)校、新聞媒體等社會(huì)各方面,都應(yīng)當(dāng)積極開展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和公共衛(wèi)生安全的宣傳教育和引導(dǎo),全社會(huì)成員要自覺增強(qiáng)生態(tài)保護(hù)和公共衛(wèi)生安全意識(shí),移風(fēng)易俗,革除濫食野生動(dòng)物陋習(xí),養(yǎng)成科學(xu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這一規(guī)定可謂點(diǎn)中了問題的死穴,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牛鼻子。處罰是外部強(qiáng)制性約束,只能治表;只有內(nèi)心確信濫食野生動(dòng)物的危害,才能治本。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濫食野味之所以久盛不衰,與不良的飲食亞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有學(xué)者分析了在物質(zhì)財(cái)富豐富、飲食種類繁多、花色品味多樣的今天,一些人仍執(zhí)著于嗜食野生動(dòng)物的原因。“從收益最大化角度來看,這主要因?yàn)槭仁骋吧鷦?dòng)物的‘飲食文化’在現(xiàn)代社會(huì)里逐漸被衍生出其他的含義,如炫耀、滋補(bǔ)、獵奇心理,滿足了現(xiàn)代人的消費(fèi)需求,同時(shí)這些含義所形成的嗜食‘亞文化’又隨著改革開放的火車頭廣東在全國(guó)迅速擴(kuò)散”。?鄭風(fēng)田、孫瑾:《我國(guó)部分地區(qū)嗜食野生動(dòng)物的成因探析》,載《消費(fèi)經(jīng)濟(jì)》2005年第5期。
為此,必須動(dòng)員全社會(huì)的力量,加大教育宣傳的力度,講清講透濫食野生動(dòng)物的危害性,重塑健康的飲食文化:(1)濫食野生動(dòng)物,將嚴(yán)重破壞生物多樣性,危及人類有限的生物資源。由于存在大量的食用需求,對(duì)野生動(dòng)物大規(guī)模的濫捕亂殺屢禁不止,已經(jīng)嚴(yán)重危及了種群的生存,許多野生動(dòng)物已經(jīng)瀕臨滅絕的邊緣。(2)濫食野生動(dòng)物,不僅存在個(gè)人健康隱患,而且還存在引發(fā)公共衛(wèi)生安全的風(fēng)險(xiǎn)。在全球化的今天,濫食野生動(dòng)物再也不是純粹個(gè)人的私事,而是必然涉及公共利益。“那些可能帶有病毒會(huì)危害人類生命的野味,個(gè)人的感官享受有時(shí)會(huì)造成全人類的災(zāi)難,原本屬于個(gè)人無關(guān)緊要的行為,有可能導(dǎo)致自己和他人的毀滅”。?於賢德:《誘惑與危險(xiǎn)——“非典”陰影下的野味飲食文化反思》,載《廣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05年第1期。(3)濫食野生動(dòng)物,是對(duì)野生動(dòng)物營(yíng)養(yǎng)價(jià)值和藥用價(jià)值錯(cuò)誤認(rèn)識(shí)的結(jié)果,是一種飲食迷信。在傳統(tǒng)食藥同源的“進(jìn)補(bǔ)”文化里,山珍野味被視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食用野生動(dòng)物被認(rèn)為有助于延年益壽。但實(shí)際上,盡管食物的種類繁多,但營(yíng)養(yǎng)素的種類通常只有蛋白質(zhì)、脂類、維生素、水等六類。野生動(dòng)物與家禽家畜相比,在蛋白質(zhì)、碳水化合物、能量等主要指標(biāo)上相差無幾甚至更低。“吃啥補(bǔ)啥”“以形補(bǔ)形”更多的是食用者的一廂情愿,并無任何科學(xué)根據(jù)。(4)濫食野生動(dòng)物,是一種不文明的飲食文化,是虛榮心和獵奇心理的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一些人對(duì)野味趨之若鶩,并非真的認(rèn)為野味有特殊的營(yíng)養(yǎng)價(jià)值或者藥用價(jià)值,而是一種炫富擺闊的心理作祟,甚至是一種權(quán)力腐敗的結(jié)果。
四、結(jié)語
新冠疫情是重大突發(fā)事件,《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決定》應(yīng)當(dāng)歸屬于緊急狀態(tài)立法。它明確了當(dāng)前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及公共衛(wèi)生安全等領(lǐng)域中最需解決的問題,及時(shí)彌補(bǔ)了相關(guān)法律的短板,為疫情防控攻擊戰(zhàn)取得最后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這雖不是未雨綢繆,但也絕非亡羊補(bǔ)牢,而是暗室逢燈,非常必要。在緊急狀態(tài)下,立法偏好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下猛藥治沉疴,大幅度限制公民的行動(dòng)自由,加大對(duì)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均有其歷史必要性和合理性。不過,對(duì)于病毒的危險(xiǎn)性,人類既不應(yīng)輕描淡寫,也不應(yīng)談虎色變,而應(yīng)理性地積極應(yīng)對(duì)。人類的生活史,其實(shí)是一部病毒史。地球上的病毒,數(shù)量多得不可計(jì)數(shù),遍布于各種生物身上。可以說,人類都寄居在病毒星球,野生動(dòng)物就是這些病毒的蓄水池。?參見[美]內(nèi)森·沃爾夫:《病毒來襲:如何應(yīng)對(duì)下一場(chǎng)流行病的暴發(fā)》,沈捷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頁。人類身上也寄宿著大量的病毒,許多病毒對(duì)人體并無危害,而是可以和平共處。因此,可怕的不是已知病毒的存在,而是對(duì)新型病毒潛在風(fēng)險(xiǎn)的“無知”。相信隨著病毒學(xué)、檢疫學(xué)、藥理學(xué)等學(xué)科的發(fā)展,人類必將不斷填充對(duì)新型病毒認(rèn)知的盲區(qū),提高對(duì)其風(fēng)險(xiǎn)的防控能力。申言之,對(duì)于新型病毒,即使不能確定其有無風(fēng)險(xiǎn),也不能無視其潛存的可能性;相反,“我們恰恰需要保持警惕,這樣才能在它們有機(jī)會(huì)進(jìn)入我們這個(gè)物種之前就采取措施,阻止它們的腳步”。?[美]卡爾·齊默:《病毒星球》, 劉旸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