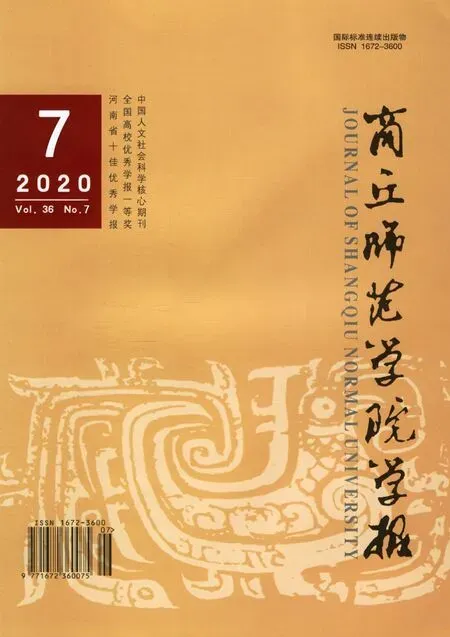隔離與斷裂:加繆荒誕哲學(xué)觀照下的《仁慈》
王 麗
(河南大學(xué) 大學(xué)外語(yǔ)教研部,河南 開封 475001)
托尼·莫里森(1931—2019)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非洲裔女作家,其作品在世界范圍內(nèi)都享有盛譽(yù),然而非洲裔作家的只言片語(yǔ)都會(huì)被理解為種族的、政治的,或是性別的,而非藝術(shù)的,或者說從來不被以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這已成為套在非洲裔作家心頭難言的枷鎖。莫里森在小說《秀拉》前言中寫道:“黑人是,抑或不是這樣的”——一語(yǔ)道破非洲裔作家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以及文學(xué)批評(píng)方面的困境[1]12。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國(guó)外評(píng)論界主要從三個(gè)角度對(duì)莫里森的作品進(jìn)行解讀。第一,莫里森和女性主義;第二,莫里森和美國(guó)黑人文學(xué)的傳統(tǒng);第三,莫里森和白人經(jīng)典作家之間的對(duì)比研究。我國(guó)對(duì)莫里森的研究也多從性別、種族、文化、主題、敘事、審美等方面進(jìn)行。而作為一位偉大的藝術(shù)家,莫里森的創(chuàng)作不僅關(guān)切自己的民族、種族,更是以其高超的藝術(shù)表達(dá)、創(chuàng)作技巧、故事情節(jié)、語(yǔ)言文化體現(xiàn)了文學(xué)作品的世界性,從而引起世界范圍讀者的共鳴。本文擬從文本細(xì)讀入手,以加繆荒誕哲學(xué)的視角考察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仁慈》對(duì)人與自身、他人和世界關(guān)系思考的幾重意蘊(yùn)。
一、《仁慈》與荒誕哲學(xué)
在《仁慈》中,雅各布的農(nóng)場(chǎng)聚集了印第安人麗娜(Lina)、白人契約勞工威拉德和斯考利,還有黑人奴隸佛羅倫斯,成為各種底層人物聚集的避難所。他們的遭遇展現(xiàn)了美國(guó)底層社會(huì)的生存狀況,凸顯了一幅17世紀(jì)末美洲殖民地和拓荒時(shí)期的社會(huì)生活畫卷。從1607年到1733年,英國(guó)在北美建立了13個(gè)殖民地,構(gòu)成了殖民地特有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社會(huì)的上層由以總督為首的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或種植園奴隸主組成,中層為小土地所有者、小工廠主、技師和自耕農(nóng)等,底層是白人契約奴和黑人奴隸。1776年7月4日,美國(guó)革命通過《獨(dú)立宣言》以及由此導(dǎo)致的一系列立法,建立了一個(gè)全新的國(guó)家。《獨(dú)立宣言》基于天賦人權(quán)和社會(huì)契約論,認(rèn)為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然而對(duì)于殖民地時(shí)期的底層人民來說,尤其是對(duì)于黑人奴隸來說,所謂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只是一紙空談。底層人民對(duì)美好生活的憧憬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殘酷之間形成鮮明的對(duì)立,而毫無緣由的磨難則使人物產(chǎn)生巨大的荒誕感。
荒誕(absurdity)一詞源于拉丁文的“absurdusm”,意為“不合曲調(diào)”(out of tune),特指音樂中的不和諧。在《新牛津英語(yǔ)辭典》里,荒誕是指“滑稽的和極端無理性的狀態(tài)和特征”[2]7。在西方文化中,荒誕也被廣泛運(yùn)用于文學(xué)和哲學(xué)中,意為愚蠢和形成觀念時(shí)不合邏輯的推理。作為文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母題,自古就有志怪小說、寓言、神話等很多作品對(duì)荒誕進(jìn)行表現(xiàn)。從古希臘到文藝復(fù)興,有許多哲學(xué)家如亞里士多德、蒙田、培根和霍布斯等都對(duì)荒誕進(jìn)行了探討。20世紀(jì)以來,越來越多的人用“荒誕”來描述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人類生存狀況,“荒誕哲學(xué)”就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yīng)運(yùn)而生。從存在主義先驅(qū)克爾凱郭爾、尼采、胡塞爾到海德格爾、薩特,以及雅思貝爾斯、馬塞爾、梅勞·龐蒂、高茲等,每一位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都有自己的理論側(cè)重和觀點(diǎn)。其中丹麥哲學(xué)家索倫·克爾凱郭爾是“荒誕主義”的鼻祖。1957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加繆在其作品《局外人》《鼠疫》以及《反抗者》等作品中無不表達(dá)出他對(duì)“荒誕”的哲學(xué)思考。加繆認(rèn)為,荒誕本質(zhì)上是人與人、人與世界的一種聯(lián)系和紐帶,人一旦意識(shí)到荒誕,就永遠(yuǎn)和它聯(lián)系在一起了,只有死亡才能宣告荒誕的終結(jié)。莫里森則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展開了同樣的哲學(xué)思考:在小說《仁慈》中,莫里森將背景設(shè)置在17世紀(jì)80年代的美洲大陸,塑造了一個(gè)人與自身、與他人和所處世界相隔離的荒誕場(chǎng)景,并通過人物的坎坷命運(yùn)探尋上述關(guān)系的荒誕本質(zhì),表達(dá)了生活在科技高度發(fā)達(dá)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人對(duì)死亡的焦慮和對(duì)自身生存狀態(tài)和命運(yùn)的關(guān)切。
二、人與自我的分裂
對(duì)于加繆來說,最荒誕的事情莫過于人不認(rèn)識(shí)自我。“我將永遠(yuǎn)成為我自己的陌生人。”[3]18加繆將這種體驗(yàn)描述為:“在鏡子里突然看到有陌生的人朝我們走來,或在我們自己的相冊(cè)里重新見到親切而令人不安的兄弟,這還是荒誕。”[4]85人無法認(rèn)識(shí)自我,看到鏡子里和相冊(cè)里貌似熟悉實(shí)則陌生的自我時(shí),親切與不安油然而生。
在《仁慈》中,掃羅就是這樣一個(gè)典型。作為一個(gè)船長(zhǎng)的女兒,她從小生活在海上,然而一場(chǎng)海難卻打破了她既定的生活,將她拋棄在她從未接觸過的世界。兩個(gè)遇難的死尸隨著波浪撞擊海岸的場(chǎng)景、沉船的殘骸、寒冷的海風(fēng)使這個(gè)從未上過岸的女孩感到自己被已知的世界遺棄了。正如加繆對(duì)荒誕感的描述——“在被突然剝奪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陌生的陸地生活和對(duì)海上幸福生活的記憶使她產(chǎn)生了巨大的荒誕感。而“這種放逐是無可挽回的,因?yàn)閷?duì)失去故土的懷念和對(duì)天國(guó)樂土的期望被剝奪了。這種人與其生活的離異、演員與其背景的離異,正是荒誕感”[3]4-5。假裝對(duì)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她試圖通過不去回憶過去來保護(hù)自己,而想象中的雙生子(Twin)成了她唯一交流、傾訴的對(duì)象。當(dāng)佛羅倫斯來到這個(gè)莊園時(shí),掃羅很高興能結(jié)交這樣一位年齡相仿的朋友,但是卻受到了雙生子的阻攔。雙生子是她想象中的朋友,更是她分裂的自我。掃羅面對(duì)荒誕和沒有人性的世界選擇了將自己禁錮在一個(gè)密閉的空間,只有她分裂的自我竊竊私語(yǔ)。而當(dāng)她想沖破這個(gè)禁錮時(shí),另一個(gè)自我就會(huì)百般阻撓。在這個(gè)她無法理解的世界里,掃羅將自己與外部完全隔離,同時(shí)也將自己一分為二,看不清自己究竟是誰,也不知究竟是為什么而生。
在荒誕中,人與自身是斷裂和沖突的,因?yàn)樗乃f和所思不一致,他得到的和他內(nèi)心渴望的不一致。佛羅倫斯在尋找黑人鐵匠的路上途經(jīng)寡婦伊靈家,在那里受到幾個(gè)白人的詢問。她黝黑的皮膚使這幾個(gè)白人感到十分震驚,甚至懷疑她是魔鬼的奴才。更令他們難以接受的是她居然會(huì)說話,并且有一封女主人的信來證明自己的身份。這一切使這幾個(gè)白人不知所措,最后佛羅倫斯被勒令脫光衣服接受他們的審視。在他們審視的眼神中,佛羅倫斯沒有看到仇恨、害怕或是厭惡,而是一種視她為異類并且得不到認(rèn)可的距離。就連豬在吃食時(shí)抬眼看她的眼神都比這些人的眼神更親近一些。在這些白人眼里,他們是不承認(rèn)佛羅倫斯的人性的存在的。在他們的“凝視”下,她感到一些珍貴的東西在離她而去,她被一分為二:一方面,自己本質(zhì)上與白人并無二致;另一方面,在白人的眼中只能看到動(dòng)物般的自我。生活在被母親拋棄的噩夢(mèng)之中,佛羅倫斯對(duì)黑人鐵匠的迷戀溢于言表,然而她卻又一次被拋棄,最終使她對(duì)愛和尊重的渴望化為泡影。
對(duì)荒誕的感受一是來自人類認(rèn)識(shí)能力的有限,二是源于人類豐富的想象。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受罰推石上山,但他把巨石推到山頂時(shí)卻只能眼望著巨石從山頂滾落谷底。他只能如此周而復(fù)始地做著這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后現(xiàn)代文學(xué)如小說《變形記》以及荒誕派戲劇對(duì)荒誕的反思和表現(xiàn),則不得不使人重新反思人與自身、與世界、與他人之間的關(guān)系。荒誕派戲劇以存在主義為哲學(xué)基礎(chǔ),否認(rèn)人類生存的意義,認(rèn)為人與人根本無法溝通,世界對(duì)人類是冷酷的、不可理解的,重在借荒誕的手法直接表現(xiàn)荒誕,表現(xiàn)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人們對(duì)人類社會(huì)絕望的情緒。而加繆則利用西西弗這一神話原型,以荒誕感為出發(fā)點(diǎn)對(duì)之進(jìn)行全面系統(tǒng)化地探討,最終將荒誕由一個(gè)概念提升到哲學(xué)的高度——“一個(gè)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釋的世界也不失為一個(gè)親切的世界。但相反,在被突然剝奪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這種放逐是無可挽回的,因?yàn)閷?duì)失去故土的懷念和對(duì)天國(guó)樂土的期望被剝奪了。這種人與其生活的離異、演員與其背景的離異,正是荒誕感”[4]79。當(dāng)人們重新審視自己機(jī)械的生活時(shí),荒誕感便油然而生。然而對(duì)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本質(zhì)的追問并沒有結(jié)束。從荒誕感的產(chǎn)生開始,人們“日常的鏈條給打斷了,心靈再也找不到銜接鏈條的環(huán)節(jié)了”[4]84。
三、人與人之間的隔離
在加繆看來,荒誕的本質(zhì)還表現(xiàn)在人與人之間的隔離感——“某些日子,見到一個(gè)女人,面孔熟悉,如同幾個(gè)月或幾年前愛過的女人,重逢之下卻把她視同陌路”[4]85。不僅愛人成為陌路,加繆筆下的人物面對(duì)至親故去也無動(dòng)于衷(1)加繆為文學(xué)史提供的典型人物就是《局外人》中的莫爾索(Meursault)。莫爾索拒不偽裝自己的真實(shí)感受,在遭遇重大事件時(shí)沒有表現(xiàn)出人們通常“應(yīng)有”的樣子而顯得與周圍格格不入,由于絕對(duì)忠實(shí)于自我的感受而成為世人眼中的“局外人”。,而《仁慈》中人與人之前也呈現(xiàn)這樣的荒誕關(guān)系。大衛(wèi)·蓋茨在《紐約時(shí)報(bào)》的書評(píng)《原罪》中這樣寫道:“《仁慈》沒有《寵兒》的可怖的激情,沒有《愛》英勇的獨(dú)創(chuàng)性,但是它卻有著對(duì)美國(guó)歷史最深入的挖掘。深入到一個(gè)美國(guó)南部剛剛頒布法令將白人和一切其他種族的人徹底割裂開的時(shí)代,與此同時(shí),美國(guó)北部已經(jīng)開始迫害那些被認(rèn)為懂巫術(shù)的人。”[5]小說對(duì)人與人之間疏離關(guān)系的刻畫,進(jìn)一步印證了世界的荒誕。其中黑人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敵對(duì)關(guān)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仁慈》中,所有的人物之間都呈現(xiàn)一種隔閡和對(duì)立的關(guān)系: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情人都無法逃脫互為異己的關(guān)系。
農(nóng)場(chǎng)的女主人瑞貝卡,從未感受到父母的關(guān)愛,因?yàn)樗麄儭氨舜酥g以及對(duì)待孩子都是漠不關(guān)心,把自己的熱情都投入到宗教活動(dòng)中了”[6]74。“已經(jīng)十六歲了,她知道她的父親會(huì)為了不再養(yǎng)活她而把她嫁給任何人。”[6]7正如她預(yù)料的那樣,父親把她嫁給了一個(gè)從未謀面的遠(yuǎn)在美國(guó)的男人,僅僅是因?yàn)檫@個(gè)求婚者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他所能提供的經(jīng)濟(jì)補(bǔ)償。盡管被尊為“先生”,農(nóng)場(chǎng)主雅各布在幼年卻是一個(gè)“邋遢的孤兒”[6]12。他一出生母親就死了,父親將他扔給了親戚就不知所蹤。在孤兒院長(zhǎng)大的雅各布從小遭受著世人的白眼,沒有得到過一絲父母的關(guān)愛和家庭的幸福。苦難的童年讓雅各布無法抑制對(duì)孤兒和流浪者的憐憫之心。而這一“仁慈之心”使他收留了孤兒掃羅和佛羅倫斯,成就了小說中一個(gè)伊甸園般的農(nóng)場(chǎng)。
小說的主人翁佛羅倫斯不知生父是誰,小小年紀(jì)又被母親賣給了農(nóng)場(chǎng)主雅各布。“賣女為奴”這一場(chǎng)景在小說中和佛羅倫斯的回憶中反復(fù)出現(xiàn),而在她的夢(mèng)中,她的母親想告訴她什么,可是她卻把眼睛挪開了。這一夢(mèng)境暗示她的母親想要解釋為何將她賣掉,而佛羅倫斯卻拒絕傾聽,更是拒絕原諒她的母親。在尋找黑人鐵匠的路上,佛羅倫斯在一個(gè)饑寒交迫的雨夜里,敲開了村莊里唯一一家亮著燈的房子,并在這里得到了一天的食宿。如果說雅各布的農(nóng)場(chǎng)像一個(gè)小小的伊甸園,那么這個(gè)經(jīng)歷使佛羅倫斯看到了“伊甸園”之外的各色人物。在這個(gè)房子里住著寡婦伊靈、她的女兒簡(jiǎn)和一個(gè)躺在籃子里病得抬不起頭說不出話的小孩兒。作者通過佛羅倫斯的眼睛刻畫出這幾個(gè)怪誕人物的外貌和言行:寡婦伊靈身材高大,長(zhǎng)著一雙綠眼睛,身著棕色長(zhǎng)袍,紅色的頭發(fā)從她的白帽子的邊緣處露了出來。這些顏色的搭配給人以強(qiáng)烈的視覺震撼,使人感覺非常不協(xié)調(diào)。奇怪的是她們雖為母女,外表卻極不相似。簡(jiǎn)的“兩只眼睛像黑炭一樣,并不像寡婦的眼睛”[6]107。而更為可怖的是,“她的一只眼睛向別處看去,另一只卻目光直視一眨也不眨,像一頭母狼的眼睛”。簡(jiǎn)盡管看起來和佛羅倫斯年齡相仿,但她的嗓音卻低沉得像男人的嗓音。最使人難以理解的是寡婦伊靈每天都鞭打簡(jiǎn)的腿,用流淌的鮮血來向白人證明簡(jiǎn)不是魔鬼,她歪斜的眼睛沒有魔法。當(dāng)佛羅倫斯的信被白人扣留,伊靈去尋求地方治安官的幫助時(shí),簡(jiǎn)偷偷地把佛羅倫斯放走了。分別之際,佛羅倫斯終于鼓足勇氣問道:“你是魔鬼嗎?”,簡(jiǎn)那“捉摸不定的眼神”突然變得堅(jiān)定,笑著回答道:“是的。”[6]114她們使人難以理解的交談、怪誕的行為、近乎可怖的外貌構(gòu)成了一幅幅恐怖的畫面,其中缺失的唯獨(dú)是母女的親情和家的溫馨。當(dāng)劇中人和局外人試圖去理解這個(gè)荒誕的世界時(shí),就感覺更加的荒誕和不可理喻。
除了父母和孩子的關(guān)系,小說中所涉及的夫妻關(guān)系也相當(dāng)生疏。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瑞貝卡的父母彼此互不關(guān)心之外,還有兩對(duì)夫妻關(guān)系也是非常疏離的。首先是在雅各布去馬里蘭州處理一個(gè)壞賬時(shí),他和鄉(xiāng)紳德奧爾特加的家人一起用餐。令他感到驚奇的是這對(duì)夫妻“從來不相互對(duì)視,除了當(dāng)對(duì)方在看其他地方時(shí)偷偷地掃一眼對(duì)方”[6]19。這種疏離和冷漠溢于言表,充分顯示出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其次,雅各布和瑞貝卡的關(guān)系在表面上看要比德奧爾特加夫婦的關(guān)系好,但是,他們也是缺乏溝通,無法理解對(duì)方的內(nèi)心。在結(jié)婚伊始兩人就無感情可言,雅各布是為了管理農(nóng)場(chǎng)之需,所以想娶一個(gè)“不信教的育齡婦女,順從但不奴顏婢膝,受過教育但不驕傲,獨(dú)立但有教養(yǎng)”[3]20,而瑞貝卡正是最佳人選。妻子對(duì)于他來說只是生兒育女、操持家務(wù)的工具,甚至是他的財(cái)產(chǎn),而“他是絕不會(huì)接受任何譴責(zé)的”[6]20。當(dāng)他們第一次見面時(shí),他看到瑞貝卡從船上“拿著寢具、兩個(gè)箱子和一個(gè)沉重的背包掙扎著跳下梯板時(shí),他知道了他的財(cái)富”[6]20。從此,他們就決定建立起一個(gè)工作關(guān)系——“他是不會(huì)給她任何溺愛的,就是他給了她也不會(huì)接受”[6]86。盡管是一個(gè)勤勞的主婦,作為一個(gè)沒有財(cái)產(chǎn)的女人,她永遠(yuǎn)都是弱者,都要依靠她的丈夫。在他們的孩子一個(gè)接一個(gè)死去之后,雅各布決定出遠(yuǎn)門做生意,夫妻的交流愈來愈少。從他們夫妻關(guān)系可以看出,囿于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規(guī)約和白人女性對(duì)丈夫精神和物質(zhì)的雙重依賴,最終破壞了夫妻間的平等對(duì)話,從而導(dǎo)致女性失去主體意識(shí)和獨(dú)立精神。
在《西西弗神話》中,加繆將情人間疏離的關(guān)系描述為:“正如有些時(shí)日,我們?cè)谝粡埵煜さ拿婵紫驴吹搅艘粋€(gè)陌生人,而這個(gè)人恰恰是我們幾月前或幾年前愛過的。”[3]13在《仁慈》中,莫里森也描述了一個(gè)連情人都彼此陌生的荒誕世界。通過麗娜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佛羅倫斯對(duì)黑人鐵匠一見鐘情,當(dāng)麗娜提醒她說“你是他的一片葉子”時(shí),佛羅倫斯固執(zhí)地說“我是他的樹”[6]61。黑人鐵匠是她唯一的庇護(hù)和生命唯一的意義,然而她除了知道他是從新阿姆斯特丹來的一個(gè)自由黑人之外,對(duì)他一無所知。當(dāng)雅各布新房子的門做好了之后,黑人鐵匠便不辭而別。然而佛羅倫斯依然執(zhí)迷不悟,癡癡地盼望鐵匠的歸來,直到女主人也染上天花,佛羅倫斯被派去尋找黑人鐵匠,她經(jīng)歷了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旅途。而對(duì)于這個(gè)旅途來說,重要的不是過程中她孤身一人所經(jīng)歷的千辛萬苦和危機(jī)重重,而在于在找到鐵匠并且作出她一生中第一次自己的選擇以及這選擇的結(jié)果。“我們談了很多事情,并且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想要留下。……我留在這兒永遠(yuǎn)和你在一起。再也再也不和你分離。……和你在一起我的身體是愉悅的安全的有歸屬感的。”[6]136-7這個(gè)決定卻在她心里未敢道出,因?yàn)樽鳛橐粋€(gè)黑人奴隸,她從未掌控過自己的命運(yùn)。她和黑人鐵匠交流并非在平等的主體之間進(jìn)行,她只是一個(gè)聆聽者,甚至無法說出自己心里如此重要的決定。正常情況下人們會(huì)說:“我們談了很多事情,但是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可是她卻用了“并且”而非“但是”,充分說明一直以來的從屬地位使她習(xí)慣于隱藏自己的想法,這句話看似輕描淡實(shí)寫,則一語(yǔ)道破他們之間不對(duì)等的關(guān)系。
四、人與世界的不和諧
荒誕本質(zhì)是一種分離和對(duì)立,是人類存在的根本特征。“荒誕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離。”[4]106《仁慈》展現(xiàn)了一個(gè)無理性的荒誕世界,然而在這個(gè)世界中,人們卻試圖尋找一個(gè)物質(zhì)充盈、宗教自由的幸福生活。這一時(shí)期的北美處于殖民地時(shí)期,也是美國(guó)的奠基時(shí)代。早期移民懷揣著對(duì)幸福、自由、富裕和宗教自由的夢(mèng)想來到這片處女地,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戰(zhàn)爭(zhēng)、屠殺、疾病和瘟疫。當(dāng)農(nóng)場(chǎng)主雅各布來到弗吉尼亞繼承遺產(chǎn),這片土地和他想象的大相徑庭。在他的眼中,“1682年的弗吉尼亞仍是一團(tuán)糟”,“在這兒,沒有人可以跟得上為了上帝、國(guó)王和土地的戰(zhàn)爭(zhēng)”[6]11。在這樣一片混亂的景象中,獨(dú)自旅行一定要小心謹(jǐn)慎,因?yàn)橐磺卸急┞对诨囊爸小K^荒誕,是根據(jù)存在于他的動(dòng)機(jī)和等待著他的現(xiàn)實(shí)之間的不成比例來斷定的,是根據(jù)我能抓住它的實(shí)際力量和他企圖達(dá)到的目的之間的矛盾來斷定的[4]84。人們期待的美好生活的美夢(mèng)卻被現(xiàn)實(shí)世界打破,荒誕感油然而生。
雅各布的農(nóng)場(chǎng)在小說中是孤苦無依的人物的避難所,甚至有評(píng)論家認(rèn)為它象征著人類的伊甸園,而伊甸園之外的世界則通過小說人物的旅途展現(xiàn)出來。例如小說第二章以對(duì)雅各布的旅途的描述開始:“這個(gè)男人踏著浪,小心翼翼地跨過沙灘來到岸邊。迷霧和大西洋上植物腐敗的臭味籠罩著海灣,使他的腳步放慢……和他所熟知的英國(guó)的霧以及他現(xiàn)在住的靠北的地方的霧不一樣,這里的霧像是被太陽(yáng)點(diǎn)著了一樣,將世界變成密實(shí)的、炙熱的金子。當(dāng)人們?cè)噲D穿過它時(shí),就像在睡夢(mèng)中掙扎一樣。”[6]9這個(gè)雅各布眼中,“密實(shí)的、熾熱的金子”般的世界正如加繆所描述的“厚實(shí)的”世界。旅途中的“迷霧”正如站在人和世界之間的荒誕本質(zhì),使人們迷失生活的方向。同時(shí),這個(gè)世界還是“寂靜的”,正如《寂靜的春天》一文中的描述,世界一片死寂,毫無生機(jī),象征著世界的無理性與殘酷,對(duì)人類的存在毫無憐憫、無動(dòng)于衷。
“荒誕產(chǎn)生于人類呼喚和世界無理性之間的對(duì)峙。”[4]94在小說中,荒誕就表現(xiàn)在人們對(duì)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充滿苦難、死亡的沉寂的世界之間的對(duì)峙。隨著殖民擴(kuò)張的進(jìn)一步深化,印第安人的生活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種族滅絕的大屠殺和瘟疫使印第安人的人口銳減。同時(shí),非洲黑人作為奴隸被賣到美洲,受到種種非人的虐待。小說中印第安人麗娜的家族就被瘟疫所吞噬,黑人奴隸佛羅倫斯的母親為了保護(hù)女兒不再受到身體的摧殘而把她賣給相貌善良的雅各布,因?yàn)椤霸谶@里作為一名女性,就像一個(gè)敞開的、永遠(yuǎn)無法愈合的傷口。即便結(jié)了痂,膿血還在下頭”[6]163。而白人女性的未來不外乎仆人、妓女和妻子。通過這些事件,人與世界的沖突展露無遺。薩特認(rèn)為,“根本的荒謬證實(shí)了一項(xiàng)裂痕——人類對(duì)統(tǒng)一的渴求與精神和自然之間的斷裂;人類對(duì)永生的渴求與生存有限性之間的絕緣;人類對(duì)其構(gòu)成本體的‘憂慮’和奮斗的徒勞之間的破裂;偶然、死亡、生命和真理之難以征服的多元論,以及現(xiàn)實(shí)的無法理解——這些就是荒謬的極端”[7]107。
隨著科技的迅猛發(fā)展,人類開始質(zhì)疑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超驗(yàn)的實(shí)體,例如宗教和上帝。工業(yè)革命不僅僅推動(dòng)了社會(huì)生產(chǎn)力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變化,而且使人類的生活和思想產(chǎn)生了巨大的改變。哥白尼通過他的劃時(shí)代巨著《天體運(yùn)行論》,告訴人類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引發(fā)了哥白尼的革命,從此撼動(dòng)了教會(huì)以神為中心的宇宙學(xué),改變了人類對(duì)世界的認(rèn)識(shí)。當(dāng)人們?cè)俅螌徱暿澜纾l(fā)現(xiàn)它已不再是人類的天堂。在人的眼中,世界是“厚實(shí)”的:“瞥見一塊石頭有多么的奇妙,都叫我們無可奈何;大自然,比如一片風(fēng)景,可以根本不理會(huì)我們。一切自然美的深處都藏著某些不合人情的東西,連綿山丘、柔媚天色、婆娑樹影,霎時(shí)間便失去了我們所賦予的幻想意義,從此比失去的天堂更遙遠(yuǎn)了。世界原始的敵意,穿越幾千年,又向我們追究。”[4]85這個(gè)曾經(jīng)被人類“征服”的世界以巨大的反作用力給人類以沉重的打擊,面對(duì)這個(gè)沒有人性的世界,人像其他動(dòng)物一樣無助和脆弱,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總之,小說《仁慈》描繪了一個(gè)充滿對(duì)立與分離的荒誕場(chǎng)景,深刻揭示出荒誕作為一種焦灼和不安的感受,表現(xiàn)為人與世界、人與他人和人與自身的斷裂和矛盾。人被拋于世上實(shí)屬偶然,當(dāng)人們?cè)噲D去了解和探尋這個(gè)世界時(shí),人們不能得到更多,而是與之愈發(fā)敵對(duì)和疏離,死亡是唯一已知的事實(shí)。與此同時(shí),無論人們?cè)馐茉鯓拥耐纯啵@個(gè)世界都是“寂靜無聲”的。盡管人們彼此需要,但是從根源上人們又相互疏離。更可怕的是,在這個(gè)沒有實(shí)質(zhì)意義的世界里,人們不了解自己,更找不到生存的證據(jù)。然而莫里森和加繆并非要借此宣揚(yáng)這樣一種悲觀的思想,而在于在揭露世界荒誕本質(zhì)的基礎(chǔ)上呼喚一種更加和諧的關(guān)系——只有人與他人、世界建立一種良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關(guān)系之后,才能找到自己內(nèi)心的平靜,并在荒誕之中建立自身生存的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