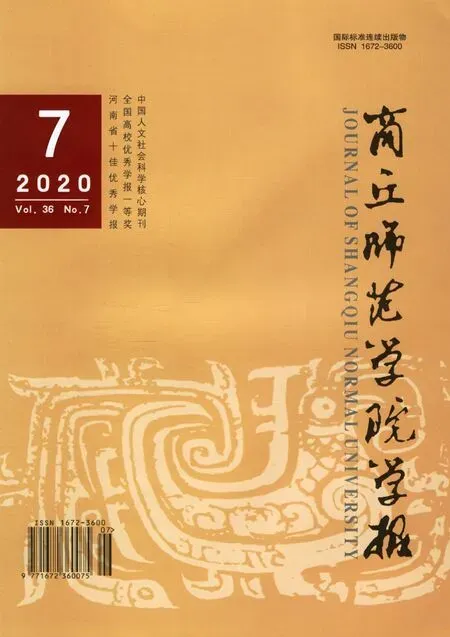《老子》與《太一生水》關系再檢討
吳戰洪 王紅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太一生水》是1993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1]1之郭店楚簡的一組簡文,“本組簡共存14枚。竹簡兩端平齊,簡長26.5厘米,上下兩道編線的簡距為10.8厘米。其形制及書體均與《老子》丙相同,原來可能與《老子》丙合編一冊。篇名為整理者據簡文擬加”[1]125。其釋文曰:
1.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輔]也,是以成寒熱。寒熱復相輔也,是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輔也,成歲而止。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者,寒熱之所生也。寒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陰陽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時,周而又[始,以己為]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為萬物經。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埋,陰陽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謂[□,不知者謂□。]
2.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強,責于[□;□于弱,□于□]。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以道從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長。圣人之從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傷。天地名字并立,故訛其方,不思相[當: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于東南,其上[□以□。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2]41-42。
李零注:“‘大一’,釋文讀‘太一’。案‘大一’是‘太一’的本來寫法。”[2]42驗之古音:“大”上古音為月部定紐[3]25,“太”上古音為月部透紐[3]126,二字同韻部,定紐透紐為旁紐[4]26,27,二字上古音近同而義通;證以字書:《說文·水部》:“泰,滑也。從廾水,大聲。”段玉裁注:“后世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則作太,如‘大宰’俗作‘太宰’,‘大子’俗作‘太子’,周‘大王’俗作‘太王’是也,謂‘太’即《說文》‘夳’字,‘夳’即‘泰’,則又用‘泰’為‘太’,輾轉繆,莫能正。”[5]565知“大一”與“太一”“泰一”義同。
“君子知此之謂[□,不知者謂□。]”李零注:“‘知此之謂’下一字是褒義詞,‘不知者謂’下一字是貶義詞,后面有章句號。”[2]42余佳認為,“君子知此之謂”后當補為“道”[6],筆者以為似不當。因為,其一,如李零所說,殘壞二字義相褒貶,第一字若補為“道”,第二字應當補為“非道”,如帛書《老子》第53章曰:“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猒飲食,資財有余。是謂盜竽,非道也哉。”[7]443即“道”與“非道”反義對文,而“不知者謂”后只殘一字,故補“非道”不當。其二,據釋文“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青昏”指天地,下文詳說),知在《太一生水》中,“道”為天地之共字,若補為“道”字,則“君子知此之謂天地”,不僅與下句“不知者謂天地”義相矛盾,更與前文義脈相斷:“君子知此”,即謂君子當知太一創生萬物之機理及歷程乃天地不能夷滅之真理與存在,或謂自然物象與客觀規律是天地陰陽都無法易除的,如帛書《老子》第24章曰:“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況于人乎!”[7]451而謂“君子知自然物象及客觀真理是天地都無法改變的就是天地”,此說甚為不辭,故補“道(天地)”實不當。
帛書《老子》第55章曰:“知常曰明。”[7]444《爾雅·釋詁》:“恒,常也。”[8]15帛書《老子》第1章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7]448河上公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自然長生之道也。”[9]1謂“常(恒)道”為“自然長生之道”,一如帛書《老子》第25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451第59章曰:“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7]444《呂氏春秋·重己》曰:“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10]35高誘注:“視,活也。”陳奇猷案:“生者有視,死則無視,故高謂視為活也。”[10]41然則“知常(恒)曰明”,即可謂“知自然長生之道曰明”;又帛書《老子》第16章曰:“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兇。”[7]450“明”“妄”反義對舉,以狀“知常(道)”與“不知常(道)”之德操品質或行為結果,其語義背景與《太一生水》近似,然則“君子知此之謂[□,不知者謂□]”,二殘壞字亦當補如“明”“妄”者為當,下文即引為“君子知此之謂明,不知者謂妄”。
“伐于強,責于[□;□于弱,□于□]。”李零注:“即所伐所責者為強者、盛者或眾者,所助所益者為弱者、劣者或寡者,意思正好相反。”[2]43其說大體為當,然由第1章太一創生萬物的意義看,《太一生水》作者似不反“眾者”,又“寡者”未必為“弱者”“劣者”,故下文即引作“伐于強,責于盛;助于弱,益于劣”。“天地名字并立,故訛其方,不思相[當: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于東南,其上[□以□。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李零注:“‘不足于上’,前三字與‘高以強’相反,可能是虛而空、空而曠一類意思,其下字當韻腳,很可能是‘空’或‘曠’字。”[2]43其說有理:據釋文“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乃天地對舉生發,“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于東南,其上□以□”,兩組對句正各承應前文天地對舉生發之文勢而立言,知“其上□以□”乃以摹狀上天情態。《淮南子·天文訓》曰:“道始于虛霩(廓),虛霩(廓)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11]165-166知古人認為天由清陽之氣生成,非絕然為“空”,而氣終由“始于虛廓”的“道”生成,然則“道”及其所生之“氣”皆有“虛”之德質,一如《莊子·人間世》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12]130然則“虛廓”義足摹天。“廓”與“曠”義近,《詩·何草不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曰:“曠,空也。”[13]949即如今之“空曠”“開闊”義,正可形況于天,且“曠”“強”上古音皆為陽部[3]73,104,故下文即引為“地不足于東南,其上虛以曠”。
以上對《太一生水》釋文之主要異文字(“大”“太”)、殘壞字進行了辨析、增補,以便于下文征引與論說。
一、研究情況簡述
若論最先對《老子》與《太一生水》之關系進行辨析研究者,就目前的資料看,恐怕莫早于郭店楚墓的墓主人或是在其授意下的竹簡抄錄者。李學勤論曰:“郭店一號墓的考古學文化性質與時代,是明確的。這座墓在楚都郢所屬墓地范圍之內,當地楚墓的序列已較清楚,可以說明這座墓位于戰國中期后段。……郭店一號墓不會晚于公元前300年,作為公元前4世紀末的墓是妥當的。竹簡的制作抄寫時間,自然還會更早一些,至于簡文的著作時代,可能就還要早了。”[14]1劉祖信研究說:“從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文獻記載的先秦埋葬制度推測:一棺一槨的葬具是‘士’,但此墓中的隨葬品十分精巧,是此類楚墓中不多見的,估計墓主人家族地位較高。”[14]14尹振環亦論曰:“從出土刻有‘東宮之不(杯)’的耳杯看,極可能是東宮太子之師,因為其隨葬器物品繁多,數量也較大,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周制,也可說明墓主人的特殊地位。”[15]1-2又如尹振環論曰:“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說:‘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人。’學皆在官時,‘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胥徒,或仍供灑掃為仆役焉’。學問之事,即為政之事,學問的掌有者,必是貴族王公。欲學者,必須以吏為師,學成后又必須服務于所學之統治者。”[16]106戰國中期后段之前有關《老子》與《太一生水》關系的研究狀況于典籍無所見,而《老子》與《太一生水》自戰國中期后段抄成下葬,至公元1993年冬出土,其間兩千余年中寢藏地下,對墓中簡文的研究自無可能,而其間亦無對《老子》與《太一生水》下葬抄錄竹簡之原著間學理關系的研究著述傳世(原著可能早已亡佚)。可見,說最早對《老子》與《太一生水》之學理關系進行研究者(甚或是碩果僅存的古代研究者)為郭店楚墓之墓主人,或者是在其授意下的竹簡抄錄者,這是有歷史依據的;雖然他們的研究實跡文獻無載,然在竹簡下葬之前,其當是對包括《老子》《太一生水》在內的諸簡牘進行了研讀、辨析及整理、抄編,而將《太一生水》與《老子》丙組以相同書體及竹簡抄錄,是否表明簡文的抄編者認為《太一生水》與《老子》同屬道家文獻呢?是否表明其認為《太一生水》就是《老子》的一部分呢?
自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簡》始,學術界才真正意義上開始了對《太一生水》的研究,其研究過程與成果均直接或間接指向了《老子》與《太一生水》間學理關系。學者大多認同《太一生水》與《老子》一樣,都為道家著作,然于二者主要字詞義涵及思想要旨、成書前后、統屬關系諸方面則歧見紛呈。
如《郭店楚墓竹簡·前言》曰:“《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時期所稱的‘道’。該文主要論‘太一’與天、地、四時、陰陽等的關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1]1既認為《太一生水》為道家著作,則作者所謂“太一”就是先秦時期所稱的“道”,精確言之,即可謂:“太一”等同于《老子》之“道”。而王春則認為:“將《太一生水》中的‘太一’解為‘氣’或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講的‘元氣’,能夠從整體上協洽該篇的思維邏輯,并使一些學者們爭論不已的問題得到簡單明了的解決。”[17]從老子“道生萬物”的理論視角考量,“氣”或“元氣”亦當為“道”所創生,換言之:“氣”或“元氣”不是“道”,然則王春當認為“太一”非為《老子》之“道”。又有學者如余佳者,認為“太一”為“神”[6],則“太一”創生萬物實即“神創生萬物”,此顯殊異于老子“道生萬物”說,故余佳亦當主張“太一”非為“老子”之“道”,而《太一生水》自非為道家著作了。僅此一例即可見學者對《太一生水》重要字詞意義的理解不同,而這些不同在更深層次上體現了學者對《太一生水》與《老子》間某種學理關系的認知,故要辨明二者學理關系,切實把握《太一生水》與《老子》中重要字詞真義,細微辨析其成詞先后、意義關系,對厘清《太一生水》與《老子》之學理關系至為重要。
李零論說:“《太一生水》和《老子》是什么關系?李學勤先生說,它是《老子》后學對《老子》的解說和發揮(《荊門郭店楚簡所見關尹遺說》),這對我們很有啟發。”[2]52據知,李學勤顯然認為《太一生水》是道家著作,且成書晚于《老子》。再如步瑞蘭、劉鵬認為:“從考古工作角度看,《太一生水》應為丙組內容即《老子》的一部分。”[18]鄒安華論曰:“令人不解的是《郭店楚墓竹簡》不知為何故,將《太一生水》篇單獨立篇,并未歸入竹簡《老子》之列,但在說明中指出該篇‘可能與《老子》丙合編一冊’,將理應是開頭部分的《老子》丙篇放到了末篇,應是末篇的甲篇放在了首篇。”[19]2其于所著《楚簡與帛書老子》中,即本此認知而將《太一生水》分列為所修訂之《荊門郭店楚墓竹簡〈道德真經〉》的書首前三篇[19]1-19。更有甚者,將《太一生水》視為郭店楚簡道家文獻的“總綱”之作,如譚寶剛認為,“《太一生水》被判定為道家的作品已經成為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太一生水》不僅是道家創始人老聃的作品,而且是整個郭店楚簡道家著作的總綱。嚴格地說,《太一生水》應置于郭店楚簡道家著作之篇首,同簡其他內容則是對《太一生水》的引申和闡發”[20]。無論是鄒安華實將《太一生水》置于楚簡《老子》之首,還是譚寶剛主張“《太一生水》應置于郭店楚簡道家著作之篇首”,其實質上即認定《太一生水》不僅于創作時序上早于《老子》,而且在思想內涵方面與《老子》是融合一體的。又如李剛論曰:“通過對《太一生水》與《老子》丙本內容的分析比較可知,二者具有相同的旨歸,只是《太一生水》在以天道明人道方面補充了《老子》丙本在天道論述方面的不足,繼而在理論上闡明了天道無為與圣人無為而治之間的聯系,進一步完善了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在上承老子之學的同時,《太一生水》又在一定程度上啟迪和影響了后來以《黃帝四經》《鹖冠子》等典籍為代表的黃老之學。”[21]作者顯然認為,《太一生水》為道家著作,成書晚于《老子》,具有承前啟后的學術價值。可見,對《太一生水》與《老子》思想內涵的不同理解,致使學者在二書的統屬關系、成書先后諸方面爭鳴不止。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太一生水》非全部為道家文獻,如蕭漢明認為:“說《太一生水》此處受老子影響則可,以為通篇皆屬道家著作則恐難說通。”[22]謂《太一生水》晚出于《老子》,并非純粹道家著作。有的學者則認為《太一生水》為神仙家言:如劉書惠認為,“長沙子彈庫《楚帛書》與郭店簡《太一生水》內含豐富的創世神話情節”[23];又如張思齊論曰:“既然我們承認在道教中‘太一’是神,而且道教中的其他神系的諸神也是神,那么就必然面對一個有趣的問題:神生成神。”[24]視《太一生水》為神仙家語的學者,應當認為《太一生水》不是道家著作,且于思想內涵上與《老子》相牴牾而與其不相統屬。此再明深辨具體情節內涵對探明《太一生水》與《老子》學理關系之重要性。
綜上,今人對楚簡《太一生水》與《老子》關系研究雖多有創見,然“疏辨妄斷”的瑕疵易見:如認為“太一”即《老子》之“道”;不辨楚簡《老子》丙組與甲、乙組內容關系,僅以《太一生水》可能與楚簡《老子》丙組同抄一冊,就認為《太一生水》屬于且早成于楚簡《老子》;因“太一”可指“神”名而認定《太一生水》為神仙家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又李零指出:“出土竹簡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雜亂無章地抄寫(有時甚至會用零章碎句湊字數,用來填補空白)。這和我們今天碰到的情況是一樣的。當然,情況可能更復雜,有些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是精心安排;有些看似很有條理,其實卻是隨意為之。因為我們很難了解古人的內心活動。”[2]52雖如此,李零還是精考簡文、辨析眾說而精心校訂出了楚簡《太一生水》的“釋文”,從而為學術的進步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足見對簡文的學術探究,終歸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文本審辨上來。或鑒于前述李零所言之研究困境,學者引述論辯多有幽邈難實、臆測無本之說。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借鑒其研究方法、經驗及可靠的成果結論,遵循語言嬗變及思想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通過文本細讀(李零校訂之楚簡《太一生水》釋文,尹振環校注之楚簡《老子》甲、乙、丙組釋文,高明勘校復原之帛書《老子》甲本釋文。成書于春秋末的楚簡《老子》與成書于戰國中期的帛書《老子》乃目前存世最為近古的兩種傳本,近古固葆真,簡本簡古,而帛書對簡文進行了加工改造及補充潤色,正可參引辨校)以辨析字詞意義、思想內涵間的差異與聯系,進而剖析、裁定前人研究之是非得失,力求對《太一生水》與《老子》間主要學理關系作出切實有效的解讀與判斷。
二、學理關系辨析
(一)抄錄體例之視角
李零論曰:“《太一生水》與《老子》丙組,簡形、簡長和字體都很相近,很多學者認為,它們原來是合抄在一起,而且簡文合抄,必有內容聯系。這是合乎情理的考慮。”[2]52其說確然嗎?
李零于《郭店楚簡的字體和形制》中說:“我們分析簡文是否屬于同一類,首先是靠字體和形制,而不是內容。”[2]6據李零研究,楚簡《老子》甲組、乙組、丙組與《太一生水》用的同是“第一種字體”[2]6,且甲組與乙組簡體形制大體相同:“《老子》甲組:最長簡(簡長32.3厘米),兩道編(編距13厘米),簡端梯形。《老子》乙組:長簡(簡長30.6厘米),兩道編(編距13厘米),簡端平齊。”《老子》丙組與《太一生水》簡體形制則完全相同:“中短簡(簡長26.5厘米),兩道編(編距10.8厘米),簡端平齊。”[2]4據此體例,知抄錄者當認為《太一生水》同《老子》一樣屬于道家文獻。
又如尹振環說:“(1)楚簡《老子》之‘甲’‘乙’原合編于一冊,‘丙’居另一冊。可見‘丙’不能與‘甲’‘乙’平起平坐,只能作為附錄。……(3)‘丙’組竹簡比‘甲’‘乙’要短五、六厘米,而其長度、線槽間距、‘形制與書體’均與《太一生水》篇相同,‘原來可能合編一冊’(《郭店楚簡墓竹簡·太一生水》篇前說明)。如果原來是‘完整’的楚簡《老子》的一部分,為什么另居一冊呢?(4)‘丙’內容、簡數都少,而且從與‘甲’重復的章看,文句也有所不同。文字既有所增加,加之字體不同,顯然晚于‘甲’‘乙’。因此,‘丙’極可能是抄留備用之文。又因為‘乙’之竹簡數不及‘甲’之一半,所以必然有缺失,焉知這些缺簡不就是‘丙’中其他非重復的章?”[15]14據知,楚簡抄錄者當認為:《太一生水》作為道家文獻,與楚簡《老子》丙組之文獻性質、價值、地位相同,乃為晚出于楚簡《老子》甲、乙組之“附錄”,故以同一字體及相同形制之竹簡抄錄,以此區別于甲、乙組;若如此,其固不屬《老子》本有。
楚簡抄編者對《太一生水》與《老子》的研究情況于籍無載,借助李零、尹振環二學者的研究成果,可推知楚簡抄編者的學術主張為:《太一生水》與《老子》同屬道家文獻,晚出于《老子》。此結論是否能于二書之具體文本內涵得證呢?
(二)萬物創生論之視角
道家貴崇萬物創生機理及過程的探究,如帛書《老子》第42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7]442尹振環引河上公、《說文》、董仲舒諸說,注曰:“所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是說天地人的形成應追溯到混沌不分的‘一’,進而到‘道’。它的結論是‘負陰抱陽,中(沖)氣以為和’。”[16]52又詳如蔣錫昌注《老子》之萬物創生之機理曰:“《說文》:‘沖,涌搖也。’此字老子用以形容牝牡相合時,搖動精氣之狀,甚為確切。‘氣’指陰陽精氣而言。‘和’者,陰陽精氣互相調和也。《莊子·田子方》:‘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沖氣以為和’,言搖動精氣以為調和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萬物生育之理,乃所以釋上文生生之義者也。”[25]280-281可見,《老子》之“道生萬物說”的本質乃“氣化生成論”。
“道生一”云云于楚簡《老子》甲、乙、丙組中俱無載,然有類似思想的表述,如尹振環校訂楚簡《老子》第24章(甲組第37簡)之“訂文”曰:“反也者,道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15]266《說文·亡部》:“亡,逃也。”段玉裁注:“亦假借為有無之無,雙聲相借也。”[5]634“逃”義于文不協,故“生于亡”本當為“生于無”,審“反也者,道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無)”,旨在發道“行反用弱”而終生萬物之理,“無”當指大道。《晉書·王衍傳》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26]814即以“無”代指《老子》之“道”。“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一如帛書《老子》第42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7]442“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一如帛書《老子》第62章曰:“道者萬物之主也,善人之寶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也,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雖有拱之璧以駪駟馬,不若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謂求以得,有罪以免與,故為天下貴。”[7]445“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一如帛書《老子》第32章:“道恒無名,樸雖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雨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7]452司馬遷說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27]1704。《莊子·在宥》云:“睹無者,天地之友。”[12]405張默生注曰:“無者無為,若睹此無為之道者,則德合天地,故稱為天地之友。”[28]289亦以“無”指代“無為之道”。筆者曾有論曰:“于行為觀念層面上講,‘無’指道法自然而制私控欲,無悖物理,無妄舉動的處世哲學,如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此處‘無身’,斷不當解為‘沒有身體’,‘無’乃自然無為之簡稱,老子本義乃謂以自然無為之德規治身心,進而消災遠禍;再如老子言‘無為’,不是說什么事都不干,而是指要因循萬物自然本性,不因私利物欲而費精竭神,縱欲妄為……”[29]可見,楚簡《老子》謂萬物“生于無”,實即“生于道”,帛書《老子》承襲了這一理念而進行了較為具體的發揮。而萬物“生于道”可謂“生于無”,實乃于大道玄虛無形而功德自成之特質處立言之,如春秋早期的管子于《管子·內業》曰:“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30]933又如帛書《老子》第14章:“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忽恍。隨而不見其后,迎而不見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7]449-450第21章:“道之物,唯恍唯忽。”[7]451

王弼本[32]136、河上公本[9]196“器成之”作“勢成之”“器”上古音為質部溪紐[3]102,“勢”上古音為月部書紐[3]120,質部月部旁轉[4]20-23,書紐相當于審[三]紐[3]6,溪紐和審紐于聲不協[4]26-28,則二字緣韻部近同而可通假,然孰為本字孰為借字呢?據尹振環于《帛書老子再疏義》中考證:戰國、秦、漢初無“勢”字而代之以“埶”[16]350-353,“因此從字形、字例看,無疑‘埶’為‘勢’之古體字”[16]352。又尹振環研究認為:“簡本、帛書《老子》的成書時代不同,一在春秋末,一在戰國中期,并非出于一人之手。”[15]171故帛書《老子》制作時因無“勢”字,當或以古體“埶”字代之,或以近音“器”字借之,“埶”上古音為月部疑紐[3]156,“器”上古音為質部溪紐[3]102,質部月部旁轉[4]20,23,疑紐溪紐準雙聲[4]26,27,故“埶(勢)”、“器”上古音近同而可通用。王弼為三國魏人,《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作者,舊題多為漢人河上公,然高明考辨說:“今據帛書《老子》甲、乙本勘校,書中訛誤尤多,不僅非漢人所為,而且晚于王弼。”[7]2然則王弼、河上公其時“勢”字當已創用,故其注中用之,王弼注曰:“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因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32]137河上公注:“道生萬物。德,一也。一主布氣而畜養之。一為萬物設形象也。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9]196知河上公實乃認為“一”即為“道”,如河上公注“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9]196據王弼、河上公注知:道雖為萬物創生總根源,但畜養、形成萬物者還有德、物、勢。“勢”古有形勢、態勢之用義,如《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王弼注:“地形不順,其勢順。”孔穎達正義:“地勢方直,是不順也。其勢承天,是其順也。”[33]27王弼注“形”“勢”對舉互文,“勢”有“形”義可知,“地勢”可謂地之形勢或態勢,地為物之大者,如《莊子·在宥》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12]402然則“勢”可謂為物之形(勢)或態(勢),前引河上公注可明此義;如此,“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勢成之”,二句形式對仗而義無復贅,同明萬物創生之過程乃為“生于有(為有形之德、物、勢所化育輔佐),生于無(終為玄虛無為大道創生)”之“雙創生模式”。此種創生模式與《太一生水》之宇宙生成說有何學理關系呢?
《太一生水》第1章所述及的太一創生萬物說,歷述太一漸次創生水、天、地、神明、陰陽、四時、寒熱、濕燥、歲,其內容遠較《老子》之道生萬物說翔實繁富,其“反輔”“復相輔”之雙向創生過程及機理,亦遠較《老子》單向創生說復雜進步,這表明其作者同老子一樣,極重視對天地自然萬物之道的體悟,如帛書《老子》第47章曰:“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7]442其謂太一創生萬物之過程及機理,“君子知此之謂明,不知者謂妄”,如前述,這體現出其作者有如老子般對知行自然之道的清醒與自覺,如帛書《老子》第16章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云云,各復歸于其根。歸根曰靜,靜,是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兇。”[7]450又《太一生水》之“反輔”“復相輔”之運作模式,正契合《老子》“反也者,道之動”[7]442之道德要旨。尹振環說:“思想認識過程是由淺入深,由簡到繁,由具體到抽象的。”[16]229則《太一生水》之“太一創生萬物說”顯較《老子》道生萬物說為深為繁;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老子》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創物說貌似“抽象”而不如《太一生水》之創生過程具體。然誠如前引蔣錫昌所言:“老子一二三,只是以三數字表示道生萬物,愈生愈多之義。”非是老子不想具體與深刻,實乃當時之認知水準使然,此種認知情態老子于文似有暗示,如帛書《老子》第1章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恒無欲也,以觀其妙;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7]448劉笑敢論曰:“本章只有第一句明確講到道,且不是‘直接’講宇宙論或本體論問題,而是提出道之可言不可言的問題。……萬物起源既有無名之始,又有可名之母。無名即不可道、不可名,也就是超越于人類之有限生命與感知能力的。有名即可道、可名,也就是人類可以通過感性、知性或理性來認識與描述的。萬物起源演變既有無名而不可知的一面,又有可知而有名的一面,二者乃一體之兩面,相反而為一,因而是玄之又玄。萬物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從無名之始到有名之母,人類既知那里確有一個共同根源,又不知其究竟,因而只能以比喻的方法稱之為眾妙之門。”[34]97其說切實有理,故于《老子》中玄虛之言,不可盲目臆斷拔高而虛譽以“抽象”。又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可明《老子》道生萬物的本質乃“氣化生成”,以今觀之亦屬“抽象”,然“氣化生成”之思想至少在老子之春秋時代即有之,管子為春秋早期人,《管子·內業》曰:“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房玄齡注:“氣得道,能有生。生則有心,故思也。思則知(智)生也。成智則理足,故止也。”[30]937又如孔子與老子同處春秋末期,《孔子家語·禮運》記孔子言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35]192《太平御覽》注曰:“太一,謂元氣也。”[36]1然“氣化生成”的思想似或更早出,如《周易·系辭》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韓康伯注:“精氣煙煴,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游魂為變也。游魂,言其游散也。”[33]266-267又如徐整所撰載三皇以來事之《三五歷記》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溟涬始牙,蒙鴻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又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36]1(黃劍華研究曰:“因為《藝文類聚》中引用了徐整《三五歷紀》,后人又根據《隋書·經籍志》中說徐整是三國時期吳國的太常卿,便將兩條資料整合在了一起,推斷《三五歷紀》就是三國時期吳國徐整所撰,這個推斷雖有疑問,但也有一定的依據和道理。”[37])可見,《老子》之“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之“氣化生成”思想,其時并非抽象玄學,當為學術常識,故由思想認知之一般規律審視《太一生水》與《老子》之萬物創生說,前者當晚出于后者;而今若謂《老子》晚出于《太一生水》,“道生萬物說”乃為對“太一創生說”的形上總結,是否有其學理依據呢?
《說文·一部》:“一,惟初大(太)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5]1據知:“一”為“太極”之“初”,大道功德建立于“一”。《莊子·天地》記夫子(老子)曰:“德成之謂立。”[12]416張默生注曰:“此德發為事功,方可謂之立。”[28]295“道立于一”亦表明“道”之地位在“一”之上。“一”創生出天地萬物。《周易·系辭》曰:“生生之謂易。”孔穎達《正義》曰:“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后生次于前生,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33]271《列子·天瑞》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38]6,然則許慎謂“(太)一”為“大(太)極”之“初”,可謂即等同于《列子·天瑞》“氣之始也”的“太初”,相當于《周易·系辭》之“太極”,一如《周易·系辭上》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孔穎達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33]289孔氏既謂《老子》之“一”為太初或太一,即以“太一”為老子之“道”的創生物,此是否有學理依據呢?《漢書·律歷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39]964孟康注曰:“元氣始起于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一也。”[39]965直謂“太極(太初、太一)”為“元氣”,乃“天地人混合為一”之物態。又《漢書·律歷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39]985“太極”與“元氣”對舉互文,即謂“太極(太初、太一)”為“元氣”,而《老子》創生萬物之“道”,則可相當于《列子·天瑞》之“太易”,之所以如此比況,是因為《老子》之“道生萬物說”,其本質亦是氣化生成論,道相當于“未見氣也”之“太易”,可謂創生萬物之混元一氣正處于成長匯聚階段;“太一(太極)”相當于“氣之始”之“太初”,可謂創生萬物之混元一氣得以初具形質,大道好生之德得以澤被萬物,大道創生之功得以立于天下,一如許慎《說文》所云“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可見,于氣化生成萬物的理論范疇審之,“太一”當為大道所創生,在此基礎上審視《太一生水》之“宇宙生成論”,其可謂是“有(萬物)生于有(太一或元氣)”之“單創生模式”;而《老子》之“道生萬物”,一如前述,則為“有生于有,生于無”之“雙創生模式”;今若謂《老子》晚出于《太一生水》,“道生萬物說”是對“太一創生說”的形上涵蓋,焉得將《太一生水》之“單創生模式”總結為“雙創生模式”?
綜上辨析,由“氣化生成”之萬物創生的理論視角看,《太一生水》可歸為道家文獻,其成書當在《老子》之后,其“太一生成說”對《老子》“道生萬物說”進行了創生模式的簡化、創生機理的深化、創生過程的細化。
(三)“天道貴弱”之視角
《太一生水》第2章曰:“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強,責于盛;助于弱,益于劣。”其要旨可以“貴弱反強”涵蓋之。《老子》中似乎也有類似的表述,如帛書《老子》第9章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7]449第79章曰:“天之道,猶張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7]447然則“貴弱反強”思想于《太一生水》與《老子》中是否內涵等同呢?它們之間又存在什么樣的學理關系呢?
首先必須明白:《太一生水》之“天道”與《老子》之“天之道”,學理內涵并非等同。在《太一生水》中,“道”乃天地之共字,如《太一生水》第2章曰:“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李零說:“學者(包括我)以為簡文的兩個‘其’字都是代指上文的‘天地’,即把‘道’理解為它們的另一個‘字’,‘青昏’理解為它們的另一種‘名’。”[2]50然據李零說:“他(裘錫圭)認為,‘道’既無名,這兩個‘其’字都不能指上文的‘天地’,而是指上一章的‘太一’。‘青昏’只能讀‘請問’。”[2]50據知:裘先生是將《老子》“無名之道”等同于《太一生水》之“道”了,如帛書《老子》第32章曰:“道恒無名,樸雖小,而天下弗敢臣。”[7]452又“青”“請”上古音同為耕部清紐[3]107而可通假,“昏”上古音為文部曉紐[3]52,“問”上古音為文部明紐[3]135,二字同韻部,曉紐明紐于聲不協[4]26-28,則“昏”“問”韻部相同而可互借,然“請問”于文句中實無前后語義背景支撐,當以李零謂“道”為天地之共字為是。《爾雅·釋天》曰:“春為蒼天……秋為旻天……”郭璞注:“萬物蒼蒼然生。……旻猶愍也,愍萬物雕落。”[8]165《說文·艸部》:“蒼,草也也。”段玉裁注:“引伸(申)為凡青黑色之稱。”[5]40則“蒼天”可謂“青天”。“萬物雕落”,其態如日落之昏冥。《說文·日部》:“昏,日冥。”段玉裁注:“冥者,窈也;窈者,深遠也。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引伸(申)為凡暗之稱。”[5]305“萬物雕落”,則其態色自昏暗,故“旻天”可謂“昏天”,有“昏暗深遠之天”義,天昏則地自暗。又《說文·冥部》:“冥,窈也。”段玉裁注:“窈各本作幽,唐玄應同,而李善《思玄賦》《嘆逝賦》,陶淵明《赴假還江詩》三《注》皆作窈。許書多宗《爾雅》、毛《傳》,《釋言》曰:‘冥,窈也。’”[5]312帛書《老子》第21章曰:“道之物,唯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忽呵,中有物呵。幽呵冥呵,中有情呵。”[7]451第25章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451即謂天地皆法則于道,故天地固有“幽暗深遠”之特質,即可謂為“昏暗天地”。又如《莊子·逍遙游》曰:“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后乃今將圖南。”[12]8-9《莊子·田子方》中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12]785“青天”與“黃泉”對舉,“黃泉”即昏暗幽深之地下。又如《周易·系辭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孔穎達正義曰:“‘象’謂懸象,日月星辰也。‘形’謂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而成昏明,山澤通氣而云行雨施,故變化見也。”[33]258天象之日月星辰“運轉以成昏明”,地形之山川草木生長而有青黃,則統兼言之,“青昏”可狀“天地”萬象之運作大況。綜上,“青昏”于義確可指代“天地”而為其別名,則前文引“道亦其字也”,據前后句語意關聯,“其”自當指代“天地”,句義謂“道”于《太一生水》中為天地之同字;《儀禮·士冠禮》賈公彥疏:“云‘子,男子之美稱’者,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今請賓與子加冠,故以美稱呼之也。”[40]49謂“道”為天地共字,可謂比附于人之尊稱,一如老子尊“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7]451可見《太一生水》作者對自然天地之貴崇,其道心由此可鑒。
帛書《老子》第25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451從遞相師法的句式來看,《老子》之“天地”皆效法于“道”,或謂“天地”之德質源出于“道”,“道”之地位崇高而統攝天地,用老子的話說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7]451。《說文·之部》:“之,出也。”[5]272然則《老子》“天之道”之義可謂“天德出自大道”;據前分析,《太一生水》之“天道”本義乃為“天地”或“天地之德”;可見,“道”于《太一生水》與《老子》中特質不同,于《老子》中可謂“無名”之道,于《太一生水》則可謂“有名”之道。《老子》中并未有“天道貴弱”的表述,只是說:“弱也者,道之用也。”[7]442如前引嚴靈峰說,“道之用”即是“道之德”,而“道之德”乃“法自然”之結晶。筆者曾有論曰:“‘道法自然’之‘自然’當解為自然界(自然物、自然規律、自然德性),方為至當,他解均因悖《老》文實際而有失精準。作為《老子》主要論道方式,‘道法自然’本質是老子借助自然物象或自然規律來譬喻、闡發、強化大道內涵。作為《老子》重要濟世方略,‘道法自然’本義為世人(主要為統治者)唯漸次取法自然天地萬物自律自營、無私無欲、善生利物、貴柔尚虛等善德,方可德配大道圣德,終使世道人心歸復到初創之際的質樸自然狀態。”[41]“‘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應解讀為君王民人要通過‘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的層進修養,體悟大道真諦,最終回復到創生之初的真樸狀態,即自然物界自律自適的生命境界,這其間的每一個過程均是向質樸自適之自然物態師法取則的返璞歸真。”[41]故從此意義上講,老子似無意創設“天道貴弱”思想:一者,天道非是通常意義上的“軟弱”,如《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33]10又《周易·系辭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孔穎達正義曰:“天以剛陽而尊,地以柔陰而卑,則乾坤之體安定矣。乾健與天陽同,坤順與地陰同,故得乾坤定矣。若天不剛陽,地不柔陰,是乾坤之體不得定也。”[33]257故于自然“常道”言之,當是“天道貴剛,地道貴弱”,老子既倡“道法自然”,亦當是贊同“天剛地弱”這一主張的,如帛書《老子》第42章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7]442第32章曰:“天地相合,以雨甘露。”[7]452可知老子亦是認同天地陰陽德殊而和合雨露,故老子當不會悖于自然常理而輕發“天道貴弱”之論。二者,如前引筆者所論,《老子》“法自然”之道所取法者,乃為“自然天地萬物自律自營、無私無欲、善生利物、貴柔尚虛等善德”,而非“懦弱無能”之劣德。前文所引《老子》中對“天之道”的相關論述即可明此理。又如帛書《老子》第8章曰:“上善似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居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7]449第66章曰:“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樂推而弗厭也。非以其無爭與,故天下莫能與爭。”[7]445-446三者,如前引述,作為《老子》“法自然”之道的重要德質,“弱”之內涵亦絕非淺俗意義上的“軟弱無力”,如帛書《老子》第28章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恒德不離。恒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復歸于樸。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恒德不忒。”[7]452錢穆論其要旨曰:“人若喜雄、白、榮,便該守雌、黑、辱。雌、黑、辱有獲得雄、白、榮之道。若牢居在雄、白、榮的位上,反而要墮入雌、黑、辱的境遇了。”[42]422此看似“懦弱”的處世方式,實源于老子對自然界“物極必反”“相反相成”諸規律的體悟,以及將此體悟于人生諸事上加以落實或應用,其終極目的是成濟事功且消災遠害,誰能否認其非為老子基于“道法自然”理念而創設的更高層次的“強勝”德術呢?如帛書《老子》第63章曰:“圖難乎其易也,為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細,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圣人猶難之,故終于無難。”[7]455然審《太一生水》所言曰:“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強,責于盛;助于弱,益于劣。”其顯然認為“天道”所貴之“弱”為通俗意義上的“軟弱”“卑劣”,其義與《老子》之“弱”則有云泥之別。
據上辨析,從“天道貴弱”要義審辨之,《太一生水》當非為《老子》固有內容;由于彼此對“弱”之內涵理解殊異,故《老子》不可能后出而對《太一生水》“天道貴弱”思想進行了繼承或總結;又鑒于老子無意于創設“天道貴弱”思想,故亦談不上其書后出而對《太一生水》進行改造的問題了。綜上可推知:《老子》書當早于《太一生水》,《太一生水》作者極可能是僅拘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遞相師法的文句形式及“弱也者,道之用也”之斷語,在未從文本全局審辨詞句義理的情況下,經“斷章取義”而出“天道貴弱”之說,此至少表明《太一生水》作者是尊崇老子思想主張的。又如《太一生水》第1章曰:“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埋,陰陽之所不能成。”“此”指前文所述之太一創生萬物之過程及機理,“成”義與“殺”“埋”不協,疑“成”當為“乘”之借字。“乘”上古音為蒸部船紐[3]16,“成”上古音耕部禪紐[3]16,蒸部耕部旁轉[4]20,23,船紐相當于床[三]紐[3]6,床紐禪紐為鄰紐[4]26,28,然則“乘”“成”上古音近同而可通假。《說文·桀部》:“乘,覆也。”[5]237“覆”義與“埋”近同。又“乘”有“踐踏”義,《墨子·節葬下》:“已葬,而牛馬乘之。”[43]182“乘”有“欺陵”義,如《漢書·禮樂志》:“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39]1039顏師古注:“乘,陵也。”[39]1041“乘”之“踐踏”“欺陵”義與“滅”得通,則“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埋,陰陽之所不能成(乘)”之要義如前文所述:太一創生萬物之過程及機理是天地陰陽都無法埋沒與滅除的,何況人哉?足見《太一生水》作者同老子一樣,具有對自然創生過程與機理的誠篤信仰及精心體悟,故其書雖晚出于《老子》,而楚簡抄編者視之為《老子》“附錄”而與丙組以同字同簡抄之。
(四)“激進反強”之視角
《太一生水》第2章緊承“天道貴弱”后曰:“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強,責于盛。”《說文·刀部》:“削,鞞也。”段玉裁注:“凡侵削、削弱皆其引伸(申)之義也。”[5]178《說文·人部》:“伐,擊也。從人持戈,一曰敗也,亦斫也。”段玉裁注:“《詩》‘勿翦無伐’《傳》,‘鉦人伐鼓’《傳》皆曰:‘伐,擊也。’《禮記·郊特牲》‘二日伐鼓何居’,鄭曰:‘伐猶擊也。’《尚書》‘不愆于四伐五伐’,鄭曰:‘一擊一刺曰伐。’《詩》‘是伐是肆’,《箋》云:‘伐謂擊刺之。’按此伐之本義也,引伸(申)之為征伐。”[5]318-319《說文·貝部》:“責,求也。”段玉裁注:“引伸(申)為誅責、責任。”[5]281《說文·言部》:“誅,討也。”段玉裁注:“凡殺戮,糾責皆是。”[5]101可見,《太一生水》“貴弱”之“天道”具有明顯的“激進反強”之情感色彩;與其有相似言語表述的帛書《老子》第79章曰:“天之道,猶張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7]447《爾雅·釋詁下》:“按,止也。”郭璞注:“按,抑。”邢昺疏:“按、抑、替、廢皆止住也。”[8]38《說文·手部》:“損,減也。”段玉裁注:“《水部》曰:‘減者,損也。’二篆為轉注。”[5]604可見,較之《太一生水》“削”“伐”“責”所體現的對盛者、強者之主動的斥責、擊殺之激進態度,《老子》“抑”“損”之意義與語氣都要平順、和緩多了,且老子旨在以天道之自然均平、公正無私,批斥人道的貪暴無度、私欲橫流,呼吁統治者法天道師圣王而無為治世,并非宣泄“激進反強”之私憤;再者,前引成書于戰國中期的帛書《老子》第79章于成書于春秋末期之楚簡《老子》甲、乙組中均無載,可知其中“抑”“損”諸貌似具“激進反強”情感色彩的字詞實乃后人增益。可見,二者之“天(之)道”的具體內涵與性質是不同的,其所透顯的《老子》與《太一生水》作者之道德情懷或處世德術是殊異的。《莊子·天下》述關尹、老聃德行曰:“常寬容于物,不削于人。”[12]1338王叔岷注:“案削猶刻也。《呂氏春秋·孟冬篇》‘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高《注》:‘削,刻也。’常寬容于物,故不刻削于人也。”[12]1343二者德行對立,其書固不相屬。《太一生水》為何有此“激進反強”思想呢?
前引尹振環認為,簡本《老子》成書于春秋末期,帛書《老子》成書于戰國中期。在帛書《老子》中有明顯具有“激進反強”思想的文句,如第19章曰:“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7]450此于尹振環校訂之楚簡《老子》甲組第1簡“訂文”作“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復稚子”[15]173。尹振環“辨析”認為,文本差異乃不同時代環境使然,其論曰:“它說明老聃那時還沒有否定(或公開否定)圣、仁、義,因為他對仁義中的自利性、市易性、虛偽性尚發現得不多。同時客觀上也暴露得不夠充分,但他對智、辯、慮中的偽詐與自利卻深惡痛絕,他幾乎將智、辯、慮與偽、詐等同起來,明確地反對‘智’‘辯’‘慮’。……到了戰國,情況大變。《荀子·非相》說:‘故君子必辯。’由‘棄辯’到‘必辯’,可見時代不同。太史儋(尹氏認為,楚簡《老子》為春秋末的老聃所作,帛書《老子》為戰國時的太史儋所作,其說可商,然其于《楚簡老子辨析·簡本、帛書〈老子〉之不同時代印證十一》中,對帛書、楚簡《老子》之春秋、戰國時代特征考論翔實,足可信從)不再提‘棄辯’‘棄慮’,但修改為‘絕圣棄智’‘絕仁棄義’。可見,簡本、帛書《老子》的成書時代不同,一在春秋末,一在戰國中期,并非出于一人之手。”[15]170-171即認為:“到了戰國,統治階層及智者群的欲望無限膨脹,‘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矯情飾欲已經司空見慣,追求功名利祿已屬常情。”[15]172動亂現實,促發成書于戰國中期的帛書《老子》具有愈發濃烈的“激進反強”之思想內容。《太一生水》作為戰國中期后段之楚墓文獻,是否可能因成書于戰國時代而打上“激進反強”的時代烙印呢?
劉笑敢論曰:“古文字研究表明,‘無’字雖然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但早期表示有無之無的,主要是‘亡’字,而不是‘無’。到了戰國末年,‘亡’‘無’的使用才有了分工,‘亡’專指‘死亡’‘逃亡’,‘無’專指有無之無(劉翔1996,231-243)。龐樸先生也曾經指出在表達有無之無的字中,‘亡’字使用最早(龐樸1995,273),竹簡甲乙本多數情況下以‘亡’代‘無’,正是早期版本的一個特征。竹簡丙本用‘無’,對照抄寫字體,當晚于竹簡甲乙本。”[34]105這與前引尹振環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足可信從。又尹振環《帛書老子再疏義》載述:帛書《老子》甲本“學不學,而復眾人之所過”[16]150,尹振環辨析曰:“果然楚簡《老子》甲篇不是‘學不學’,而是‘教不教’。不過,丙篇相同的章(顯系后出),已是‘學不學’了。‘教不教’是說要教那常人所不教的東西,指的是對下之教,‘學不學’是要學那常人所不能學的東西,指的是‘圣人’。”[16]151據前引尹振環研究:楚簡《老子》成書于春秋末期,帛書《老子》成書于戰國中期,楚簡《老子》丙組既為“學不學”,則其抄據母本當為帛書《老子》(即丙組晚出于帛書《老子》)而后出于楚簡《老子》甲、乙組。又據前引李零的研究結論(楚簡文獻是否同類首以字體與簡制而非以內容判定)、尹振環研究成果(楚簡《老子》丙組為“抄留備用”之“附錄”,成書晚于甲、乙組),而楚簡《老子》丙組與《太一生水》字體與簡制完全一致,此至少表明其時抄編者(甚或其時之學術界)認為《太一生水》在文獻性質、價值地位、甚或成書時間諸方面(依李零說,不必思想同容方面相同或相近)與楚簡《老子》丙組是相同(或謂“同類”)的,若如是,則《太一生水》與楚簡《老子》丙組成書晚于楚簡《老子》甲、乙組且同為其“附錄”。又據前引尹振環研究發現,楚簡《老子》之甲、乙原合編于一冊,丙居另一冊,再鑒之楚簡《老子》丙組及《太一生水》為后出“抄錄備用”之“附錄”,故尹振環所說成書于春秋末期的楚簡《老子》當為楚簡《老子》甲、乙組;又據前引李學勤研究認為郭店楚墓立于戰國中期后段,再如前述:楚簡《老子》丙組晚出于成書于戰國中期的帛書《老子》,然則作為與楚簡《老子》丙組“同類”之《太一生水》的成書時代當在戰國中期(前段可能性較大,因楚簡為抄本,所據母本成書當更早些),此是否有學理依據呢?
李零說:“(《太一生水》)‘陰陽’‘四時’‘寒熱’‘濕燥’相輔成‘歲’,則與《鹖冠子》的術語相近。”[2]41黃懷信《鹖冠子匯校集注·前言》考證認為,《鹖冠子》的最終完成,就當在公元前243至公元前236年間[44]7。時在戰國晚期,郭店楚墓立于戰國中期后段,《太一生水》固不可能在《鹖冠子》成書后借鑒之,故其成書當早于《鹖冠子》,又二者于術語及學理思想方面有承繼、改造之處,故成書時間當距不遠,試引證之如下。
《鹖冠子·夜行》曰:“四時,檢也。”黃懷信注引吳世拱曰:“《管子·山權數》:‘時者,所以記歲出。’《左》閔二年《傳》:‘時,事之征也。’”[44]25較之《太一生水》純狀歲之形成之自然歷程,《夜行》則向社會生活領域引申之。《鹖冠子·夜行》曰:“陰陽,氣也。”黃懷信注:“陰陽,萬物之所生。氣,無形之物。”[44]25而《太一生水》中“陰陽”則為“太一”所生,鹖冠子將其改造成創生萬物之本。《鹖冠子·道端》曰:“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獨知也。”黃懷信注引吳世拱曰:“精,謂五行。”引張金城曰:“謂精神互變,乃始成寒暑之時也。”黃懷信注:“言氣候變化,由多方因素造成,以比大事之變。”[44]91據注知,其“寒溫(熱)”成因顯與《太一生水》所述迥異,且其基自然物理而發人世道理的言說模式及內容,顯較《太一生水》純述自然創生過程、機理為進步與深化。《鹖冠子·度萬》記龐子問鹖冠子曰:“圣與神謀,道與人成。愿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44]134鹖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頗則神濕,神濕則天不生水。音□(缺文符號,黃懷信疑作‘斯(嘶)’)聲倒則形燥,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勢,萬物無以成類。”[44]135-137《鹖冠子·度萬》又曰:“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黃懷信校辨眾說,注曰:“五氣,謂寒、熱、風、燥、濕,張(金城)引《子華子》說是。端,正也。四時不成,謂春不成生、夏不成長、秋不成熟、冬不閉藏,此亦比人君言。”[44]145其“濕(水)”“燥(火)”及“歲”(四時為一歲)之成因顯與《太一生水》殊異或不盡相同,如前述:其本自然以說人事的話語模式及內容,亦較《太一生水》為進步與深化。《度萬》又記鹖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時,拔陰陽,移寒暑;自流并生,萬物無害,萬類成全,名尸氣皇。”[44]162-163黃懷信注:“名,名號。尸,主、占。氣皇,即羲皇伏羲氏,此以代三皇。”[44]163-164《鹖冠子·泰鴻》中又借“泰(太)一”之言曰:“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刻鏤未萌,離文將然者也。”[44]226“天也者……醇化四時”云者,即謂“四時(一歲)”為天所“醇化”而成,其顯與《太一生水》的“成歲”歷程不類;又《太一生水》謂“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亦與《鹖冠子·泰鴻》之“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不盡符契。可見,李零說“(《太一生水》)‘陰陽’‘四時’‘寒熱’‘濕燥’相輔成‘歲’,則與《鹖冠子》的術語相近”,甚是。然《太一生水》與《鹖冠子》在論年歲之時令氣象時,僅是諸“術語相近”而已,《鹖冠子》并未像《太一生水》般詳細描述天地及一年中各時令氣象的自然化成歷程,這似與鹖冠子“假自然以明世理”的論說模式有關,鹖冠子或無意探究天地及時令氣象的生成過程及機理。
綜上,從術語相近及內容有所繼承、改造、深化的角度看,《太一生水》與成書于戰國末期的《鹖冠子》當時距不遠,極有可能是戰國中期的作品而于戰國中期后段抄編而下葬,若如此,《太一生水》就可得與帛書《老子》一樣浸染時代之戰亂特征,而具“激進反強”之思想內容。此是否有具體的文本內涵作支撐呢?
先來看《太一生水》可能與之同抄一冊的楚簡《老子》丙組是否有“激進反強”的主張。如前引述:其成書雖晚于楚簡《老子》甲、乙組,然作為“抄錄”楚簡《老子》甲、乙組而“備用”之“附錄”,其核心思想主張當與成書于春秋末期的楚簡《老子》甲、乙組相(近)同。現將尹振環校訂之楚簡《老子》丙組“釋文”抄錄如下:
(1)太上下智。佑之其即,親譽之其即,畏之其即。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猶乎,其貴言也。成事述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快出,安有大偽;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亂,安有正臣。[15]321-322(丙1、2、3簡)
(2)勢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坪大。[15]325(丙4簡)
(3)樂與餌,過客止。古道之出言,淡呵,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而不可既也。[15]328(丙4、5簡)
(4)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铦襲為上。弗美也。美之,是樂殺人。夫樂殺人,不可得志于天下。故吉事尚左,喪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故殺人眾,以悲哀蒞之;戰勝,以喪禮居之。[15]333-334(丙6、7、8、9、10簡)
(5)為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圣人無為古(故)無敗也;無執古(故)[無失也]。慎終若始,則無敗喜(矣)。人之敗,恒于其且成也敗之[15]193。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是以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15]194(丙11、12、13、14簡)
釋文第(1)尹振環注譯曰:“最好是降低智者的聲望。福佑他們,他們就會接近你,就食于你;親近和贊美他們,他們更會迎合就食于你;他們畏懼你,也會設法接近你。要看不起他們。誠信不足,于是才有不信任。猶猶豫豫呵,使他們慎貴其言。事遂功成,這樣百姓才能說我遵順自然。所以說,大道廢棄,于是才有了仁義;智者們迅速出現,于是才產生大詐大偽;六親不和,于是有了孝慈;國家昏亂,于是有了忠正之臣。”[15]321-322據知,此乃老子為統治者設計的統御“智強”的知識精英之策略,并非強橫以滅除之,而是恩威并施,用其智而限其弊;雖提及“仁義”“大偽”“孝慈”“正臣”,然據上下文義可知,老子對其并非持絕然毀棄之主張。尤要注意“故大道廢”之“故”字,王叔岷曰:“‘故’猶‘所以’也。”[45]160“故”于此為承轉上下,表因果關系的連接詞,老子本義謂:統治者若能修行自然無為大道以治世,妥善對待使用“智強”者,使社會安定、家邦和睦,自然不會出現“大道廢,安有仁義”諸弊害,“故”后諸句云云,宗旨在從反面強化老子于“故”前諸句所表達之“修道治世,善待智者”思想,而非謂要絕棄“仁義”“智慧”“大偽”“孝慈”“正臣”。釋文第(2)尹振環注譯曰:“盛大權勢威力的形象,能使天下的人歸附,歸附而不受到傷害,大地安定平坦通泰。”[15]325,據知,老子對“盛大權勢威力”不是絕然反斥的,前提是其于天下蒼生無害而能和諧安定之。類似思想一如帛書《老子》第61章曰:“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靜勝牡。為其靜也,故宜為下。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過欲兼畜人,小邦者,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大者為下。”[7]444-445釋文(3)講古道特質與功德,毫無“激進反強”之印跡。釋文(4)論道家之用兵德術,主張以悲憫之心而于“不得已”的情況下用兵,老子力倡之戰法為“铦襲為上”,尹振環注譯曰:“最好是鋒利地、輕裝地突然襲擊。”[15]333可見,即便對于強如軍力者,老子亦非絕對排斥,而是主張以道統御而適時用之,一如帛書《老子》第30章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于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居,楚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毋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謂果而不強。”[7]452釋文(5)雖提到“為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人之敗,恒于其且成也敗之”,然其宗旨是為宣揚“無為”“無執”“慎終若始”的圣人之道術作鋪墊,諸不道行徑終將因圣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之功德而返璞歸真。
可見,楚簡《老子》丙組沒有如《太一生水》之“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強,責于盛”所體現的“激進反強”思想;《太一生水》抄錄字體及簡制與楚簡《老子》丙組完全相同,“原來可能與《老子》丙組合編一冊”而為楚簡《老子》甲、乙組的“附錄”,然主要思想竟截然相反,合理的解釋當是其抄錄之各自母本不同:楚簡《老子》甲、乙組成書于春秋末期而無“激進反強”思想,而《太一生水》成書于戰國中期而如帛書《老子》具有之,其時道家著作“激進反強”思想尤烈者莫過于《莊子》。《胠篋》曰:“圣人不死,大盜不止。”[12]354“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與論議。”[12]356-357“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12]357《在宥》曰:“絕圣棄知(智),而天下大治。”[12]385其語勢語義,與《太一生水》之“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強,責于盛”可謂形神兼似!又如尹振環論曰:“簡本‘罪莫厚乎甚欲’,只說欲望的‘厚’‘甚’,即過分過量,而帛本改為‘……大于可欲’,已是任情縱欲了。簡本‘咎莫險乎欲得’,這里的‘咎’,非過失,《說文》‘咎,災也’,所以此句是說可能引發災難的危險性,而帛書改‘險’為‘慘’,危險的災難已變為慘烈的災難。可以想象,這需要多少次災難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才能改寫出這樣一個‘慘’字呵!這也算作簡帛本不同時代的標記吧。”[16]68亦即謂成書于春秋末期的楚簡《老子》無明顯的“激進反強”之語言及情緒,此種內容及情感至戰國中期之帛書《老子》方出現。若如是,則又與前引尹振環校訂楚簡《老子》甲組第1簡釋文“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復稚子”之“激進反強”思想主張相抵牾,這又當如何解釋呢?
尹振環校訂楚簡《老子》甲1簡釋文“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無)有;絕偽棄慮,民復稚子”,與《老子》思想實際多有相違。
(1)老子主張習用自然無為之智,而反對縱欲謀私之智,非絕棄一切智術。帛書《老子》第65章曰:“故以智治邦,邦之賊也;以不智治邦,邦之德也。”[7]445《說文·戈部》:“賊,敗也。”段玉裁注:“敗者,毀也;毀者,缺也。”[5]630《禮記·哀公問》記孔子答哀公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鄭玄注:“德,猶福也。”[46]1735傅奕本正為:“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16]383毀邦敗國之“智”固為縱欲圖私之非道之陋智,令邦得福之“不智”乃當為自然無為之道智。《說文·不部》:“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凡不之屬皆從不。”[5]584據知:“不”本指鳥飛不落之自然現象,一如《莊子·天地》記華之封人言曰:“夫圣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12]430張默生注曰:“宣(穎)云:鶉無常居,言不求安;鷇待母食,言不求飽。彰,跡也。言如鳥之飛行,無跡可見也。”[28]302則“不治”可指老子力倡之“無為而治”道術。
(2)老子不絕然反對言辯,而反對逞智剖判事物而妄興是非。如帛書《老子》第68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7]446既貴崇樸實“不美”之“信言”,自當不排斥“信言”之辯。又如帛書《老子》第2章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惡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恒也。是以圣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7]448即謂天下萬物皆自然對立統一而同生共存,世人不悟此恒常之道而私心逞智,剖判是非,自持一端而爭競不止,故圣人鑒之而無為治之,故老子當主張“棄辨”而非“棄辯”,“辯”與“辨”上古音同為元部并紐[3]8,雙聲疊韻而可通假,《說文·刀部》:“辨,判也。”段玉裁注:“古辨判別三字義同也。”[5]180
(3)老子固反對世俗之巧詐貪利,如帛書《老子》第57章曰:“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盜賊多有。”[7]444第44章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7]442然不得以此謂老子絕對反斥“巧”與“利”。《說文·工部》:“巧,技也。”[5]201帛書《老子》第45章曰:“大巧如拙。”[7]442既言“民利百倍”,就不可斷然謂老子反“利”,如帛書《老子》第7章曰:“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與,故能成其私。”[7]448-449第11章曰:“卅輻同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為器,當其無,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7]449第68章曰:“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弗爭。”[7]446故契符自然之道之“巧”“利”當在老子贊行之列。
(4)老子固反斥縱欲妄為,然貴行自然無(有)為。如前引帛書《老子》第68章,又如帛書《老子》第38章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7]441《韓非子·解老》曰:“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47]372則老子所言“無為”非淺俗所謂“什么都不做”,即乃“無私心雜念之自然作為”義,而于政治層面上的“無為”要義,一如張默生論曰:“道出于自然,用于為政,則天下萬物人事莫不順遂安定,這個道的要義,便是無為。這是哲理在政治思想上的體現。”[28]294《說文·人部》:“偽,詐也,從人,為聲。”段玉裁注:“經傳多假為為偽,如《詩》‘人之為言’,即‘偽言’。”[5]379因“偽”“為”同聲,“為”可假為“偽”,“偽”亦可借作“為”,如《廣雅·釋詁》曰:“偽,為也。”[48]273故若“偽”是“為”之借,就不得斷然說老子主張反斥之。又《說文·思部》:“慮,謀思也。”段玉裁注:“《言部》曰:‘慮難曰謀。’”[5]501帛書《老子》第63章曰:“圖難乎其易也,為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細,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圣人猶難之,故終于無難。”[7]445可見,亦不可謂老子全然反斥謀慮,切乎自然道理者,老子當主張審慎謀之慮之。又“慮”有“亂”意,如《呂氏春秋·恃君覽·長利》記伯成子高言曰:“夫子盍行乎,莫慮吾農事。”[10]1345高誘注:“慮,猶亂也。”[10]1348老子反對悖道而亂為,如帛書《老子》第16章曰:“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兇。”[7]450故于此意義上講,說老子主張“棄慮”為是。又《一切經音義·音廣弘明集》“理攄”條記曰:“褚豬反。《廣雅》:攄,張也。顧野王云:舒也。《說文》:從手慮聲。集作攄,俗字。”[49]2160“攄”發“慮聲”,然則“慮”可通為“攄”;《廣雅·釋詁》:“攄,張也。”[48]28《廣雅疏義》曰:“凡為張大之義,不止弓弦也。”[48]29《廣雅疏證》曰:“《孫子·兵勢篇》云:‘勢如彍弩。’”[48]29則“攄(張)”可形況行事如拉滿弓弩般強勢張揚,一如《莊子·外物》所說“德溢乎名,名溢乎暴”[12]1076。老子顯是反對此種張揚作派的,一如帛書《老子》第22章曰:“企者不立,自是者不彰,自見者不明,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余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裕(道)者弗居。”[7]451第23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7]451故于此意義上講,謂老子主張“棄慮”,本當為“棄攄”。又《老子》中多有贊譽、崇法自然德操、無為治術的表述,如帛書《老子》第29章曰:“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培或墮。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7]452第34章曰:“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為大也,故能成大。”[7]453第66章曰:“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7]445故不加詳辨而妄言老子絕然主張“絕圣”亦是不準確的。如前引述,“絕圣”云云諸道家主張,多出自戰國時如帛書《老子》和《莊子》中,實乃憂憤至極之詞也。
綜上辨析,尹振環校訂楚簡《老子》甲組第1簡釋文“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復稚子”,本當作“繼智棄辨,民利百倍;繼巧棄利,盜賊亡有;繼為棄攄(慮),民復稚子”,其要義為:統治者當繼承自然之智巧及運作態勢,摒棄逞智妄辨、縱欲貪利、逞強張揚諸不道行徑,如此則百姓自然受惠,盜賊自然消亡,民眾自然純樸。此正與老子“道法自然”、師法道圣、返璞歸真諸思想理念相契合,而無如《太一生水》“激進反強”之情感內涵,僅憑此點即可判定楚簡《老子》與《太一生水》不可能為一書;進而檢審楚簡《老子》甲、乙組全部內容,及帛書《老子》絕大部分章節(除第19“絕圣棄智”章、第46“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章),老子諸思想主張無不體現出地“平和、辯證”的特質及悲天憫人之情懷,而無(明顯)“激進反強”之特質,如帛書《老子》第42章曰:“故強梁者不得其死,我將以為學父。”[7]442陳鼓應譯曰:“強暴的人不得好死,我把它當作施教的張本。”[52]235“強暴的人不得好死”似有“激進反強”的意味,然老子之宗旨是“把它當作施教的張本”,這就極大沖淡了“激進反強”的意味。王弼注曰:“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32]118這就化“激進反強”之私憤色彩于虛無了,彰顯了老子修道濟世之大德;王弼注更切合時代背景及老子德操,故較陳鼓應譯注為善。劉笑敢認為:“所有不同版本的《老子》當然有一個共同的最早的祖本,我們姑且稱之為‘初祖本’。”[34]105老子為春秋末代人,則成書于春秋末代之楚簡《老子》雖不可斷定為“初祖本”,想必也是最近者了,其中無“激進反強”之情感內涵,即可明《老子》原本當無此類思想主張,帛書《老子》有關“激進反強”主張實乃戰國時人增益之,而《太一生水》作為楚簡《老子》“附錄”性質的道家著作而有此類“激進反強”思想,理當亦是戰國時代之著述,至少其當較楚簡《老子》甲、乙組晚出。鑒于前之辨析可定:《太一生水》非為楚簡《老子》所固有,其成書當晚于楚簡《老子》。
(五)行事原則及道術之視角
《太一生水》第2章曰:“以道從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長。圣人之從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傷。”《經傳釋詞》曰:“以,語詞之用也。”[53]6《廣雅·釋詁》曰:“以,與也。”[48]254《周易·師·彖》曰:“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孔穎達正義曰:“欲見齊眾必須以正,故訓貞為正也。”[33]51其釋“以”為“齊同”義。《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預注:“左右,謂進退在己。”孔穎達正義曰:“謂求助于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54]433其又詮“以”為“左右(專制)”義。審“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長”,“圣人之從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傷”,體現出一種執意作為而建功全身的理念,故“以”釋為“用”“齊同”“左右(專制)”皆可,而以“左右(專制)”義更與“必托”之語勢相合。《說文·言部》:“托(讬),寄也。”[5]95《春秋公羊傳·桓公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得罪于天子也。……屬負茲舍,不即罪爾。”何休注:“屬,托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托疾止不就罪。”[55]107-108《禮記·檀弓下》記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鄭玄注:“木,槨材也。托,寄也,謂叩木以作音。”[46]322《戰國策·趙策四》記左師觸龍曰:“雖少,愿及未填溝壑而托之。”[56]548注曰:“托,托付、委托。”[56]549則“托”有主動將希望寄托于他物、人以成濟事功之義。“以道從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長。圣人之從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傷”之前句曰:“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則知“道”于《太一生水》中為“天地”之共字,又如前文所述:“其名”即天地之名“青昏”。又“名”與“命”通,《史記·天官書》曰:“兔七命。”《史記索隱》曰:“謂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27]1144《詩·維天之命》曰:“維天之命,于穆不已。”鄭玄箋云:“命猶道也。”[13]1284然則“以道從事者必托其名”,如前述,其要義即謂“思想上依賴且行動上掌控天地之道而行事”。其所托“天地之道”具體內涵除前文所述之“天道貴弱(包括‘激進反強’與‘助益弱劣’兩個主要方面)”外,還有“天地名字并立,故訛其方,不思相當: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于東南,其上虛以曠。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中蘊含之相關思想主張。“天不足于西北……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如前述,要義是說天地各有其“不足”與“有余”。《說文·竝部》:“并,併也,從二立,凡竝之屬皆從竝。”[5]501“從二立”云者,即謂“并”字形況二人等高并列而立之態,則《太一生水》作者所言之“天地名字并立”,顯體現出“天地齊一”的思想主旨,于此意義上講,作者又是認為,天地各具之“不足”與“有余”是齊同均一而無等差區別的。此種宇宙萬物“對立統一而自然并存”的思想,成書于戰國中期的帛書《老子》中多有,如第2章曰:“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恒也。”[7]448第20章曰:“唯與訶,其相去幾何?美與惡,其相去何若?”[7]450第29章曰:“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培或墮。”[7]452而“萬物齊同歸一”的思想于戰國中期莊子的《齊物論》中更是得到淋漓盡致的闡發;實際上,此種宇宙萬物“對立統一而自然并存”的思想,在成書于春秋末代的楚簡《老子》中即有發端,如楚簡《老子》甲組第15、16簡曰:“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也。”[15]215-216除句尾少“恒也”二字,文句與帛書大體相同,而帛書添加“恒也”二字,是否表明是認識進一步深化的結果呢?故而添“恒也”以示強調宇宙萬物“對立統一而自然并存”之規律的普遍性。又楚簡《老子》中雖有“天地”并稱之例,如甲組曰:“道恒無名,仆唯棲,天地弗敢臣”(第18簡)[15]220,“天地相合,以俞甘露”(第19簡)[15]223,“有狀混成,先天地生”(第21簡)[15]229,“天地之間,其猶橐(‘橐’為帛書、今本字,原書字形為‘全包圍’結構:內為‘乇’,外為‘囗’,尹振環注引《龍龕手鑑·口部》解其義為‘小廩也’,即‘小型糧倉’[15]231)籥與?”(第23簡)[15]232而無如《太一生水》“天地名字并立”之對“天地”自身特質更為深刻的表述。驗之典籍,戰國文獻多有“天地”并稱且對其德質深入表述者,如《馬王堆漢墓帛書·六分》:“天下大(太)平,正以明德,參之于天地,而兼復(覆)載而無私也,故王天。”[57]17《鹖冠子·天則》:“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44]33《莊子·逍遙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變),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12]17《莊子·天道》:“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12]472“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12]476“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12]477可見,于對萬物自然規律、天地特質及功德的認知方面,《太一生水》當如帛書《老子》及戰國典籍而對楚簡《老子》有所深化;若如是,則《太一生水》亦當成書于戰國,或至少表明其成書當晚于楚簡《老子》。
對于所貴崇之“天地之道”,《太一生水》作者特別警誡世人曰:“故訛其方,不思相當”:《爾雅·釋詁下》:“訛,言也。”郭璞注:“世以妖言為訛。”[8]36《廣雅·釋詁上》:“方,有也。”[48]8《莊子·秋水》記河伯言曰:“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12]581成玄英《疏》:“方,猶道也。”[58]563《說文·思部》:“思,也。”段玉裁注:“《谷部》曰:‘者,深通川也,引畎澮歫川。’引申之,凡深通皆曰,思與雙聲……謂之思者,以其能深通也。”[5]501《說文·田部》:“當,田相值也。”段玉裁注:“值者,持也,田與田相持也;引申之,凡相持相抵皆曰當。”[5]697則“故訛其方,不思相當”,要義為:故而如果妖言禍亂了天地萬物自然均平之道理,世人將因不能深通且真持天地自然之道而縱欲妄為,此正乃《太一生水》“天道貴弱”“激進反強”“助益弱劣”諸內涵的理論根柢。
綜上,《太一生水》之行事德術可簡言曰:本崇天地,托名有為,成功全身。然則老子之行事道術是否與之相同呢?
楚簡、帛書、今本《老子》均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見取法自然天地之道而行事的思想,于古今《老子》傳本中是一脈相承的,老子倡行此種行事道術的宗旨,一如楚簡《老子》甲組曰:“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厭。”(第3、4簡)[15]177“功述身退,天之道也!”(第29簡)[15]269“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第35、36簡)[15]262又如楚簡《老子》丙組第2簡曰:“成事述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15]322這些語句及思想在帛書、今本《老子》中亦有所載,只是個別用詞或詞序有別,然大義近同,如“功述身退”,高明勘校復原帛書《老子》甲本作“功遂身退”[7]449,王弼本同帛書[32]21,河上公本作“功成、名遂、身退”[9]32,尹振環注曰:“述,功述、申述、記述也。”譯曰:“功勞已經表明,引身退下,天之道呵!”[15]269可見,“成功全身”思想于古今《老子》傳本中源流不斷,然則于行事之宗旨方面,楚簡《老子》與《太一生水》是相同的,然于行事之根本原則及道術方面,二者有相近之處,然差異亦是明顯的:《太一生水》之行事主體是一般的“以道從事者”(可包括統治者、知識階層及庶眾)及“圣人”,依本的是天地“貴弱”“均平”“齊同”諸自然之道,主張主動依托天地之道而積極成事衛生;而楚簡《老子》中只有一處提到統治者師法天地之道而治世,即如楚簡《老子》第14章(甲組第19、20簡)曰:“天地相合,以俞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安。始折有名,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小谷之于江海。”[15]223-224尹振環注“俞”為“應允也”[15]222,然謂“天地相合以應允甘露”,似有違“道法自然”義旨;《說文·舟部》:“俞,空中木為舟也,從亼,從舟,從巜;巜,水也。”[5]403段玉裁注:“凡穿窬、廁牏皆取義于俞。”[5]403又《說文·穴部》:“窬,穿木戶也,從穴,俞聲,一曰空中也。”段玉裁注:“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曹當作槽,者,窬之或體,《玉篇》云‘窬木槽也’是也,與牏古通用。”[5]345又《史記·樂毅列傳》載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27]1899《廣雅·釋詁》:“雜、錯,廁也。”[48]350知“廁”有“雜錯居處”義,然則“穿窬、廁牏”得有“穿越或處于中空之所”義,故“俞甘露”義即形況雨露穿行空中而自由降落之自然現象,正契老子“道法自然”義旨。“天地相合,以俞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安。始折有名,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小谷之于江海”,旨在勸誡統治者師法天地“無私無欲、公正博厚”之自然圣德,如甘露潤化民眾般無為而治,終得使“民莫之令而自均安”,即便因政績卓著而“開始轉向有名望了,那么就要知道適可而止,適可而止不會招來禍殃”[15]224。《說文·止部》:“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阯,故以止為足。”[5]67“知止”即“知足”,老子于此亦誡勉統治者知足制欲而避免人亡政息之劫難。“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小谷之于江海”,尹振環認為此二句是用以喻況“知止不殆”之境界的,其譯曰:“就像道在天下那樣靈應,又如小河大川之水必須流向大海那樣靈應。”[15]224謂“道”必“靈應”及河川“必須流向大海”,一者,有違“道法自然”旨趣;二者,亦不符《老子》反映之社會實況。如楚簡《老子》乙組第3、4簡曰:“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也,無為則無不為。”義如尹振環注譯曰:“學者一天天增多,[功名欲望與偽行偽善也會隨之增大與漫延],因而遵行大道的人會一天天減少,減少再減少,總要回到無私無為上來,無私心無私為,則無所不為。”[15]278老子雖對社會終將返璞歸真抱有信心,然不道妄為的動亂現實他是不能罔顧的。又如楚簡《老子》乙組第9、10簡曰:“上士聞道,勤行于其中;中士聞道,若聞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為道。”[15]294-295可見,對自然無為之道真正篤信實行者,三分僅存其一了!故帛書《老子》感喟曰:“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7]446故尹氏譯注不確,實際上,老子此言“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小谷之于江海”,當旨在揭示前句“天地之道”的內涵淵源,并形象闡明“無為道術”的實施境界,因老子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則天地自當配大道自然之德,或謂天地之道(術)即此“謙下無為,順物自化”之德(術)。《春秋公羊傳·僖公三年》記齊桓公言曰:“無障谷”,何休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55]210《爾雅·釋詁》:“之,往也。”[8]12“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小谷之于江海”,老子以江海喻大道“謙下無為,順物自化”之德,如楚簡《老子》甲組第2、3簡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能為百谷下,是以能為百谷王。”[15]177江海地勢低下乃自然之態,溪流歸往江海亦是順勢無為之行,一如《孟子·告子上》載孟子誡告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59]295又如前引嚴靈峰認為“德”為“道之用”,則老子“自然之道”亦可謂“無為”之行事“道術”,其本質即“順物本性而自然作為”,而非淺俗所謂之“無所事事”。此種“自然無為”的行事道術,在楚簡《老子》乙組第11簡中被譬美為“上德如谷”[15]299,于帛書《老子》被贊譽為“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7]441,義如《韓非子·解老》曰:“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于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于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者德盛。德盛之謂上德。”[47]372可見,在實施“自然無為”之行事道術時,老子是反對心存私念而刻意為之的。老子倡行“自然無為”之行事道術,最終目的是企望統治者能本此“無為而無以為”之大道“上德”修身理政,終使亂世復歸正道,一如楚簡《老子》甲組第31、32簡曰:“是以圣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15]253
再者,《太一生水》主張托道(天地)之名而激進作為,而楚簡《老子》卻貴崇“無名”而自然無為。如楚簡《老子》甲組第18、19簡曰:“道恒無名,仆唯棲,天地弗敢臣。侯王如守之,萬物將自賓。”尹振環注譯曰:“道永遠是無名的,不追求名譽的,它仆從依附棲息于萬物,但是連天地也不敢臣服它。侯王如果遵守道的無名,不求名,萬物將自然歸化。”[15]220老子道論固反對悖道害生之“名利”或“名譽”,如楚簡《老子》甲組第35、36簡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15]262然所求“名利”若契和自然之道,或能以誠樸、知足諸大道圣德規制名利,老子亦是贊同而非絕然反斥的,如前引楚簡《老子》第14章(甲組第19、20簡)[15]223-224可明此義。再者,老子之“道”于稱呼上是可暫而名之的,如楚簡《老子》甲組曰:“有狀混成,先天地生。……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15]229于性質上亦是可以“小”“大”和諧稱名的,如帛書《老子》第34章曰:“道汜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則恒無欲也,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可名于大。”[7]452-453故尹振環謂“道永遠是無名的,不追求名譽的”,實屬不確。又如尹振環楚簡《老子》第9章(甲組第13、14簡)曰:“道恒亡為也,侯王能守之,而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將鎮之以忘名之樸。夫亦將知足,知足以束,萬物將自定。”注譯曰:“道永遠是隱蔽其所為的……將用忘名、質樸鎮定它。”[15]202-203謂“道”“永遠是隱蔽其所為的”,“道”之樸為“忘名之樸”,著實與“道法自然”之義旨相牴牾,且與前述老子之“名利”觀相違,故其說亦不確。實際上,如前引《說文》:“亡”通“無”,“亡為”當為“無為”,一如前引筆者曾論:“無”于《老子》中可借指“道”,“無為”非“無所作為”,而是本道而自然作為;又《說文·心部》:“忘,不識也,從心,亡聲。”[5]510知“忘”“亡”聲同而得通,“忘名”當為“亡(無)名”,義如前文筆者論說,基于前文所述老子之“名利”觀,則“無名”當解作“契符自然無為道義之名(利)”或“以道規制名(利)”。可見,楚簡《老子》之“無名”與《太一生水》之“托名”,二者內涵殊異、對立,故不可能同屬一書。
綜上可知,在楚簡《老子》與《太一生水》中,其行事道術所依本的天地之道的具體內涵不盡相同,而其行事道術(或謂天地之道的執行方式)則差異懸殊(一自然無為,一激進有為)。帛書《老子》第38章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7]441,即謂世人漸次遠離自然道德而歸于仁義禮,而《太一生水》“激進有為”的行事道術即離自然之道益遠,就此點論,二者不當共存一書,且《太一生水》理當后于楚簡《老子》。從行事主體看,楚簡《老子》本天地之道行事者為統治者;而《太一生水》踐行天地之道者為“以道從事者”及“圣人”,據“圣人之從事也,亦托其名”云者,知此二類行事者是不同層次的。在《老子》中,圣人是“天下”之統治者及庶眾的行為楷式,如帛書《老子》第28章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恒德不離。……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恒德不忒。恒德不忒,復歸于無極。樸散則為器,圣人用則為官長,夫大制無割。”[7]452故“以道從事者”可指統治者與庶眾,然則《太一生水》中踐行天地之道的行事主體較《老子》為多,故雖《太一生水》敘述簡略,然其行事道術所涉內涵當較《老子》為深,二者既非屬一書,然則從思想文化史“由簡到繁,由淺入深”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看,《太一生水》亦當晚于楚簡《老子》。
(六)詞語辨析之視角
張岱年在為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作《序》時曰:“他首先考察了內、外、雜篇的先后問題,揭示出內篇之中只有道、德、命、精、神等概念,而沒有道德、性命、精神等復合詞;外、雜篇中道德、性命、精神等復合詞便屢見不鮮了。參照《左傳》《論語》《老子》《孟子》以及《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用詞情況,足證復合詞的出現確實較晚,于是《莊子》書中內、外、雜篇的先后早晚便得到無可爭辯的證明。”[60]1知利用古漢語“單字詞先出,復合詞后出”的規律判定古籍先后順序,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用此方法加之相應的詞義辨析,亦可判定楚簡《老子》與《太一生水》的成書前后及統屬關系。
1.“太一”
“太一”作為合成詞的形式,于楚簡、帛書、今本《老子》中俱無見,然有“太(大)”“一”分用之例。考楚簡《老子》甲、乙、丙組,“大”字出現27次,“太”字出現2次,其意義可分為10類。
(1)指代“道”或為“道”之特質。如第15章:“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15]229第37章:“大道廢。”[15]322
(2)指合乎道德或達道至境之事物。如第32章“大白如辱”,“大方亡(無)隅,大器慢成,大音祗聲”[15]299;第34章“大成若缺”,“大盈若盅”,“大巧若拙,大成若詘,大直若屈”[15]305-306。
(3)“盛大”義。如第38章:“勢大象。”[15]325
(4)“偉大”或“偉大的人、物”義。如第15章:“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15]229
(5)“超過”義。如第3章:“禍莫大于不知足。”[15]180
(6)“極度(危險的、嚴重的)”義。如第23章“甚愛必大費”[15]262;第30章“貴大患若身”,“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15]291;第37章“安有大偽”[15]322。
(7)“重要的”義。如第10章“大小之”,尹振環譯為“大事化小”[15]209。
(8)“大聲地”義。如第31章:“下士聞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為道。”[15]294-295
(9)“最好的或最上乘的”義。如第37章:“太上下智。”[15]321
(10)“太平或安泰”義。如第38章:“往而不害,安坪太。”[15]325
楚簡《老子》諸“大”及意義于帛書《老子》中幾乎都有載,然據尹振環《帛書老子再疏義》載簡、帛《老子》“釋文”知:簡本《老子》比帛書《老子》多“大成若詘”,帛書《老子》比簡本《老子》多“大贏如絀”[16]60。可見,“大(太)”于楚簡《老子》中可指代“道”,然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指“道”。
又據尹振環研究說:“帛書《老子》‘一’字凡十五見,分布于八個章。逐一分析,共有五種含義:(1)是數詞。如‘吾有三寶,一曰慈,……’。(2)表示一貫、合一、始終如一。如‘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圣人執一’。(3)表示天地萬物形成前的渾樸一體。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既然是‘道生一’,可見‘一’就不完全等于‘道’。(4)即‘道’,又似未形之形。雖然絕大多數章之‘一’不是‘道’,但十四章有一處例外。‘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者,其上不徼,其下不昧。繩繩呵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從前面‘混而為一’看,即‘道生一’之‘一’;而從后面的文字看,‘一’又即‘道’。(5)含糊的‘得一’。”[15]85又特論“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云云曰:“如果‘得一’即得道,為什么不直呼為‘道’,偏要模糊其詞轉個彎?如果說‘侯王得一’即‘侯王得道’,那么‘天’‘地’‘神’‘谷’哪有什么得道不得道的問題呢?顯然,在這里,‘得一’是不能簡單地等同為‘得道’的。”[15]85尹振環又考辨《尚書·大禹謨》《尚書·咸有一德序》《周易·系辭下》《管子·水地》《周易·剝》《經典釋文》《老子》及傅奕本、嚴遵本、《韓非子·解老》《素書·原始》、王弼《老子》第38章注,結論曰:“‘得一’,即是利而無害之德的純一、一貫也。”[15]85-86可見,帛書《老子》之“一”只有一處指“道”,而絕大多數不指“道”。而楚簡《老子》僅有一處“一”,即第15章:“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15]229尹振環注譯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也大。國中有四大則安寧平靜,王是安寧平靜中之一呵。”[15]229此“一”為“其中之一”義而非指老子之“道”。
綜上可見:楚簡、帛書《老子》均有“大(太)”可指代“道”,楚簡《老子》中無“一”指“道”而帛書《老子》中僅有一例,故楚簡《老子》中無“大(太)一”合用而義指“道”之可能,帛書《老子》中僅只有一種情況下“大(太)一”合用義可指“道”而絕大多數情況下非是;又如前文所述,從創生意義上講,《太一生水》之“太(大)一”當指“混元一氣”而非指“道”,“道”于《太一生水》中為天地之共字,實為太一所化生,而于《老子》的創生話語體系中,“(太)一”卻為“道”所創生。有學者謂《太一生水》之“太(大)一”就是先秦所稱之“道”或《老子》之“道”,無論是從單字詞構成合成詞之意義組合的概率上看,還是從學理內涵及關聯上看,其論是不準確的。
尹振環有論曰:“李學勤先生認為,《太一生水》為關尹遺說,這有《莊子·天下》所言為證:‘關尹、老聃主之以太一。’可見關尹與老子有關。所以這才將‘丙’與《太一生水》合編成冊以為附錄的吧。”[15]14首先,認為“《太一生水》為關尹遺說”,似不確。據《莊子·天下》言關尹德操曰:“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12]1337-1338其自然無為、謙卑自持、因緣隨化之道術極近老子,而顯與《太一生水》之“激進反強”德術不類,故說“關尹與老子有關”,可從;而謂“《太一生水》為關尹遺說”,則不當。又據尹氏所引李學勤說,則尹氏、李氏似認為《老子》當載有“太一”以代指“道”或相關道論內涵,然如前引證知:楚簡《老子》中無“太(大)一”合稱以指稱“道”之可能,帛書《老子》雖有一例此種可能,然而楚簡、帛書《老子》均無“太(大)一”合用之例,楚簡《老子》成書于春秋末期,老子正處其時,故簡本《老子》極可能是老子親著,以老子至圣而尚不得以“太(大)一”合用以稱闡大道,何況他者?故“太一”合用似當晚于楚簡《老子》成書時,其創用當在春秋末至《莊子·天下》篇作成之戰國末期之間。又《天下》為《莊子》雜篇之末,學界一般認為,雜篇為莊子后學所著,時在戰國末期;然亦有學者認為,《天下》為莊子所著之《莊子》“序言”;嚴靈峰則于《論〈莊子·天下篇〉非莊周所自作》中認為,《天下》一文非莊子所作,“可能是出于荀子的手筆”,“此篇倘非荀卿自作,必系其門人或后學得自荀卿的傳授而寫作的。這可以從先秦所有典籍中,未有討論學術流派比荀子和韓非子兩人更為詳盡,而得到證明”[31]169-207。荀子為戰國末期人,其門人后學得其傳而著書亦當在戰國末期,故《莊子·天下》篇作者可能是借用前人典籍中“太一”成例來概述關尹、老聃道德及學說,甚或即是借用《荀子》中“大(太)一”而為文。“大一”于《荀子·禮論》中兩見,文曰:“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王先謙《集解》曰:“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也。”[61]352《爾雅·釋詁下》:“時,是也。”[8]54《說文·是部》:“是,直也,從日正。”[5]69《爾雅·釋詁下》:“道,直也。”[8]39知“時”可通轉為“道”,“太古時也”可謂“太古道也”。又如《尚書·堯典》曰:“曰若稽古,帝堯”,偽孔安國《傳》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62]25然則《荀子·禮論》“以歸大一”,亦可謂“以歸太古之道”,此義與老子之道論內涵有通,如楚簡《老子》第39章曰:“古道之出言,淡呵,其無味也。”[15]328《荀子·禮論》又曰:“復情以歸大一。”王先謙《集解》曰:“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61]355解“大(太)一”為“質素”,則與老子之“道”相通,如楚簡《老子》第9章曰:“道恒亡(無)為也,侯王能守之,而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將鎮之以忘(無)名之樸。夫亦將知足,知足以束,萬物將自定。”[15]202-203又如帛書《老子》第32章曰:“道恒無名,樸雖小,而天下弗敢臣。”[7]452又如龐樸有論曰:“太一也是楚國神靈名字和天上星星的名字,屈原《九歌》所祀第一尊神,便是東皇太一。王逸《楚辭章句》注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即最高神或上帝,有的地方寫作‘天皇大帝’。而太一作為星,則指眾星之軸北極星,其說載于《史記·天官書》等。星星和神靈之為太一,當亦取其至高無上、天上第一的意思;一般說來,它們得名的時間較早于哲學太一。”“哲學太一在傳世文獻中,常見于《莊子》《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等,與道家的‘道’范疇異名同謂”[63]。屈原為戰國中晚期人,呂不韋為戰國末期人,太史公與淮南王皆西漢人,故其書皆當晚出于戰國末期至漢初,其書中出現“太一”,亦可明前述關于“太一”創用于春秋末至戰國末的說法可信;“太一”作為“星神”而創生宇宙萬物之說于典籍無見,戰國中晚至漢初典籍之哲學意義上的“太一”和“道家的‘道’范疇異名同謂”。又如前述:于創生意義上講,“太一”當指“混元一氣”,而“道”當為“混元一氣”之“正處于成長匯聚階段”,故《莊子·天下》作者可借“太一”以概說老子德行及主張,而《太一生水》作為極可能成書于戰國中期的道家著作,亦可借用(甚或首發創用)“太一”而詳闡其宇宙生成說。
綜上,楚簡、帛書《老子》中只有“大(太)”“一”作單字詞之用例,無“太(大)一”合用的情況,而作為合成詞的“太(大)一”當創用于晚于楚簡《老子》成書的春秋末至戰國末,而《太一生水》“太一”合用,且其極可能成書于戰國中期,故楚簡《老子》成書早于《太一生水》。
2.“神明”
《太一生水》中有“神明”一詞,出于如下語句:“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神明”之義,研究者多有異說:李零引王博論曰:“該篇(《太一生水》)中的‘神明’,李零提到是指一種精神境界。我覺得應是指日月。”[2]47李零認為:“第一,《易傳》中的‘神明’,它在古書中的用法一般都是泛指,其含義與我們常說的‘神靈’差別不大。這種神靈可以是泛指的神,也可以是某種精神境界。”[2]48李小光研究說:“‘神’‘明’皆有光明義,則作為‘太一生水’所論宇宙生成序列中的關鍵一環,是極可理解。”[64]又如趙衛東說:“把《太一生水》之‘神明’讀為‘昏明’,釋為晝夜,既能與《太一生水》獨特的宇宙論系統相諧合,又可以在先秦及其后典籍中找到證據。因此,與以往學者對《太一生水》之‘神明’的解釋相比較,把《太一生水》之‘神明’釋讀為‘昏明’,更能符合《太一生水》之原意。”[65]類似觀點劉文英先已有說,其論曰:“‘神明’大體相當明暗或晝夜這個環節。明暗和晝夜十分相近,完全可以合為一個環節。再從文字訓詁來看,神者申也,申是神的本字,申的初形是電光閃爍之形,這在甲、金文中非常清楚。而電光閃爍只能出現于黑暗之中,所以‘神’可表示黑暗,‘明’則表示光明。因此《太一生水》中的‘神明’應該訓為明暗。明暗的具象即晝夜。從明暗或晝夜的特征及其對偶關系,引出陰陽的特性及其對偶關系,依古人的生活經驗與思維方式來看,應是十分順理而自然的。”[66]魏啟鵬認為:“‘神明’作為源于道、生于天地的精氣,在萬物形成的過程中起著通合萬類的作用。”[67]又如龐樸主張:“所謂神明,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神靈,也不是人的圣明,而是天地的神妙功能。”[63]韓東育認為:“作為老子宇宙生成論鏈條之重要一環,‘神明’不但為老子所創,而且具有百分之百的‘神化’意味。”[68]而所謂的“神化”,即作者認為老子主張“自然神化”。諸說孰是孰非呢?
驗之語境,“神明”當同“天地”“陰陽”“四時(春夏秋冬)”“寒熱”“濕燥”一律為“太一”經由“‘反輔’和‘相輔’兩個化生層次”[69]而創生出的相互具有對立統一關系之兩具體事物(四時之春夏與秋冬亦可謂自然對立統一,如《莊子·天道》曰:“春夏先,秋冬后,四時之序也。”[12]479),故“神明”解為“日月”或“昏明”似更善,他解至少于形式而言乃不確,因為解“神明”為“泛指的神”,或認為“神明”出自老子,有“神化”色彩,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楚簡、帛書、今本《老子》皆不見“神明”一詞,老子的核心思想特質是“貴道德而輕鬼神”,如帛書《老子》第4章曰:“道盅,而用之又弗盈也。淵呵,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呵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也,象帝之先。”[7]448第60章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圣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7]444又老子貴崇“道法自然”,也就談不上“自然神化”的問題了。解“神明”為“精氣”亦不確。《周易·系辭上》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韓康伯注:“精氣煙煴,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游魂為變也。游魂,言其游散也。”[33]266-267然則“精氣”之地位及功德幾于創生宇宙萬物的“太一”(本質乃混元一氣),若“神明”為“精氣”,則文脈淆亂,語義難安,故為不當。解“神明”為“精神境界”“生成序列中的關鍵一環”“天地的神妙功能”,雖不能說與語境完全無涉,然于形式及內涵方面,均與“天地”“陰陽”“四時(春夏與秋冬)”“寒熱”“濕燥”諸“太一”創生物貼合松散,多有“隔靴搔癢”之感。若將“神明”讀為“昏明”,義同“晝夜”,則“明”指“晝”,“昏”指“夜”;如前述:在《太一生水》中天地之別稱為“青(清)昏”,則“青(清)”指“天”,“昏”指“地”,若如此:“昏”(語境中只得代指一種事物)同為“夜”和“地”,這是不合義理的;又若將“神明”詮為“昏明”,則“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亦即“昏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如前文引述,《太一生水》中“昏”可借指“地”,“青(清)”可代指“天”,又如前引《淮南子·天文訓》曰:“道始于虛霩(廓),虛霩(廓)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11]165-166知天由“清陽之氣”升化而成,又《說文·阜部》:“陽,高、明也。”[5]731知“陽”“明”義近同,驗之古音:“陽”上古音為陽部喻紐[3]151,“明”上古音為陽部明紐[3]87,二字同韻部,喻紐明紐古聲不協[4]26-28,知“陽”“明”因古音同韻部而字可互通,故“清陽(明)”亦可指代“天”,然則“昏明(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亦可作“天地者,天地之所生也”,其說自我循環,與《太一生水》“反輔”和“相輔”之創生理路及結果不類,故解“神明”作“昏明(晝夜)”亦不確。
“神明”若解作“日月”,形式上與“太一”所創生之“天地”“陰陽”“四時(如前述:春夏與秋冬可謂對立統一之自然現象)”“寒熱”“濕燥”和諧一律;于意義上看,前引李零征王博認為“神明”當為“日月”,且王博論曰:“《說卦傳》中曾有一句話:‘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東漢的荀爽注云‘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晝照’。即以神為月,以明為日。根據這個解釋看《莊子·天下篇》的‘神何由降?明何由升?’神明指日月的意思就更加顯豁。而且,從本文中的‘神明復相輔也’來看,神明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東西。”[2]47又《莊子·天下》曰:“天地并與?神明往與?”[12]1343“天地”與“神明”對舉,“神明”解為“日月”正與“天地”諧對。“神明”解為“日月”,則《太一生水》中“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義謂天地復相輔生日月也,日月為萬物之皇皇大者,故其說近似天地生萬物之說。《周易系·辭上》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孔穎達正義曰:“性,謂稟其始也。存,謂保其終也。道,謂開通也。義,謂得其宜也。既能成性存存,則物開通,物之得宜。從此易而來,故云‘道義之門’,謂易與道義為門戶也。”[33]274帛書《老子》第5章亦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7]448可見,老子之“道生萬物說”當本“天地化生”之遠古“易道”而創立。又《說文·日部》:“日,實也,大(太)陽之精不虧。”[5]302《說文·月部》:“月,闕也,大(太)陰之精。”[5]313《說文·米部》曰:“精,擇米也。”段玉裁注:“引伸(申)為凡最好之稱。”[5]331又如《莊子·田子方》中記老聃誡諭孔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12]779成玄英疏曰:“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58]713據《說文·米部》及《莊子·田子方》、成玄英疏知,日月乃“出乎天”“發乎地”之陰陽二氣之精華成就之(籠統言之,亦可謂日月為天地化成),此說遠承化生萬物之“混元一氣”的“太一”德質,近合《太一生水》“天地復相輔,是以成神明(日月)”之要義,可明《太一生水》言當有所本。又《說文》記字先秦古義,《莊子》為戰國著作,且“大(太)陰”“大(太)陽”與“至陰”“至陽”義同(《爾雅·釋詁》郭璞注:“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為大也。”[8]9-10),《莊子·田子方》之“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于義可涵蓋《太一生水》之“天地復相輔,是以成神明(日月)”,此是否可明《太一生水》為戰國著說呢?《太一生水》又謂“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神明”若解為“日月”,即謂“日月復相輔以成陰陽(二氣)”,此非與“太一創生說”之氣化生成特質相矛盾,本義是說:日月秉承“太一”化成萬物過程中的“反輔”德質而助益“生己者(發自于天地的陰陽二氣)”——《說文·車部》:“輔,《春秋傳》曰:‘輔車相依。’”段玉裁注:“引申之義為凡相助之稱。”[5]726《爾雅·釋言》:“濟,成也。濟,益也。”[8]92“濟”又有“相助”或“救助”義,如《周易·謙·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孔穎達正義曰:“‘下濟’者,謂降下濟生萬物也。”[33]80《晉書·何樊傳》曰:“攀雖居顯職,家甚貧寒,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26]850然則“神明(日月)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義謂日月又相輔相成,而助益陰陽二氣之旺沛。
綜上辨析,無論從形式論,還是由內涵審,《太一生水》之“神明”當以解為“日月”至善至當。各傳本《老子》俱無“神明”合成詞而有“神”“明”單用之例,其意義若何?
就楚簡《老子》甲、乙、丙組而言,均無“神”字用例,“明”字用例有兩處:一處出自甲組第33、34、35簡:“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終日乎而不憂,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即老,是謂不道。”尹振環注譯曰:“具有渾厚德行的人,好比初生的嬰兒。……他終日無憂無愁,這是因為他非常淳和。淳和叫作常,認識和叫作明智,有益于生命叫作吉祥,任性使氣叫作逞強,事物迅猛就會走向衰老,這叫作不道。”[15]258則“和”指“含德之厚”者修行大道而使元氣充沛、性情平順、身心無憂、生命吉祥之自然和諧、生機無限的狀態或境界,尹振環謂“認識和叫作明智”,即以“明”為“明智”義,而“含德之厚”之“明智”者必“懂得”或“明白”修道而達“和”之境界,故“明”亦當有“知行(為)合一”之義。實際上,“知”即有“為”義,如《呂氏春秋·仲冬紀·長見》曰:“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10]611高誘注:“知猶為也。”[10]615《周易·系辭》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33]259王引之注曰:“家大人曰:‘知猶為也,為亦作也。’”[70]55另一處是見于乙組第10簡:“明道如悖,痍道如類,進道如退。”[15]295尹振環“再疏義”說:“過去釋為光明的(或明顯的)道、前進的道、平坦的(或高尚的)道。如果說‘道’是一種規律,那就無所謂光明的、前進的、平坦的規律。老子一再說:道,恍呵,惚呵,看不見,摸不著,聽不到,無狀無象。因此光明、前進、平坦之道的詮釋難以成立。”[16]42尹振環譯曰:“懂得道的好像違背道,踐踏道的好像保衛道,接近道的好像背離道。”[15]295則“明道如悖”之“明”為“懂得”或“明白”“知曉”諸義。總之,在楚簡《老子》中無“神”字,“明”義指對大道的知行及其結果。
“神”于帛書《老子》共見8處,意義可分為如下3類:(1)一般意義上的“神靈”及其特質。如第39章:“神得一以靈……謂神毋已靈將恐歇……”[7]441第60章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圣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7]444(2)“神圣”義。如第29章曰:“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為者也。”[7]452尹振環“再疏義”曰:“《易·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所以‘器’又是政權、權力、君器之謂。”[16]337注譯曰:“所謂天下,就是神圣的國家權力,這不是哪個為私的人隨意就能得到的。”[16]329(3)指具有生養萬物功德之“道”。如第6章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7]448尹振環“再疏義”曰:“今本《老子》的文字是‘谷神’,在帛書《老子》甲、乙本中,均為‘浴神’。它證明河上公本、孟喜等本作‘浴’是古貌。洪熙煊曰:‘谷、浴,皆欲之借字。’想爾注曰:‘谷者,欲也。’河上公注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可見谷、浴、欲是相通的。而‘玄牝’則進一步點明生養之意。令人費解的是:《老子》為什么不徑直用‘欲’而用‘浴’?可能是用‘浴’以區分名利等非基本需要之‘欲’,同時此‘浴’又不限于貪色之欲,還有天地萬物養育之欲,因而此‘浴’又含有陰陽相吸之義。總之,‘谷神’乃生養之神,古已有之。今天訓‘浴神’為生養之神,更是符合老旨的了。如果道學家是用禁錮的眼光看‘欲’,以致改為‘谷’,那么今天就完全沒有這個必要了。”[16]248-249此“谷神”為“天地之根”,正乃大道德質,如帛書《老子》第25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7]451
“明”于帛書《老子》共見13處,意義可分為如下6類:(1)“潔白光亮”義。如第10章:“明白四達。”[7]449河上公注:“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于天下八極之外。”[9]35(2)“明(睿)智”義。如第16章“復命常也,知常明也”[7]450,第22章“自見者不明”[7]451,第23章“不自見故明”[7]451,第33章“自知者明也”[7]452,第52章“見小曰明”[7]443,第55章“知常曰明”[7]444。(3)“知曉(道)”義。如第40章“明道如昧”[7]441,第47章“不見而明”[7]442,第65章“為道者非以明民也”[7]445。(4)指“道”。如第27章:“是以圣人恒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材,是謂襲明。”[7]451河上公注:“圣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9]110(5)“顯著”義。如第36章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固舉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是謂微明。”[7]453河上公注:“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9]142(6)“智慧”義。如第52章:“用其光,復歸其明。”[7]443朱謙之注:“唯《老子》書中,‘光’與‘明’異義(大田晴軒說)。……言‘明’皆就其內在之智慧而言。……言‘光’皆就外表之智慧而言。”[71]208-209《老子》中雖無“神明”作為合成詞之用例,然道家學人有以“神明”指涉老子之“道”者,如《莊子·天下》述關尹、老聃德操曰:“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12]1337“神明”與“道術”前后對應生發,故《天下》篇作者當認為“神明”與“道”異文同義。又如嚴遵《老子指歸·上德不德篇》曰:“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指精微,性命同于自然,情意體于神明,動作倫于太和,取舍合乎天心。”[72]4“道”“一”“自然”“神明”“太和”“天心”對舉生發,于道家話語范疇看,其義本近同。又如《老子指歸·上德不德篇》曰:“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為宗,太和為祖。”[72]3“元”“始”“宗”“祖”義近同,然則“道”“德”“神明”“太和”義固當同質。又《老子指歸·道生一篇》曰:“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氣,氣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萬物以存。”[72]17《廣雅·釋詁》曰:“因、友、愛,親也。”《廣雅疏義》曰:“《爾雅》《釋文》引《倉頡篇》:‘親,愛也,近也。’”[48]274又“因”有“依順”義,如《莊子·養生主》曰:“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郄,導大窾,因其固然。”[12]105“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對舉互文,“依”“因”同義,成玄英疏曰:“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58]120然則“神明因于道德”義即“神明依順、親近于道德”,然則“神明”于義可代指“道(德)”。道家學人之所以認為“神明”義指“道(德)”,如前所述,蓋因“神”“明”二字(詞)于《老子》中確可形況大道以及對道德的知行。
綜上可見:據楚簡、帛書《老子》中“神”“明”均為單字詞而《太一生水》中“神明”則為復合詞,可知楚簡、帛書《老子》成書先于《太一生水》,而楚簡《老子》成書又先于帛書《老子》,則三者成書時序可定為:楚簡《老子》→帛書《老子》→《太一生水》。又因帛書《老子》成書于戰國中期,而郭店楚墓立于戰國中期后段,故《太一生水》成書時間當為戰國中期(前段可能性較大,因楚簡為抄本,所據母本成書當更早些),于時晚于帛書《老子》。從詞義看:“神明”于《太一生水》中為“日月”,與“神”“明”作為單字詞在楚簡、帛書《老子》中的意義殊異無涉,相同字符而著述賦義迥然不同,可明《太一生水》與《老子》文不相屬。
三、結語
綜上辨析,本文主要結論為:在成書時間方面,楚簡《老子》早于帛書《老子》,帛書《老子》又早于《太一生水》;在文獻性質方面,《太一生水》與《老子》同為道家著作,認為《太一生水》為神仙家言或非為、不全為道家著述的說法不確;在文本內涵方面,《太一生水》于楚簡、帛書《老子》多有繼承、改造,甚有對立生發;在統屬關系方面,鑒于《太一生水》成書較晚,于楚簡、帛書《老子》彼此不相統屬。諸說前人多有爭訟,今辨析裁定如上,然絕非終極的論:一者,筆者學養尚淺,所論必掛一漏萬;二者,學問之路艱遠,不可一步到位,如對《太一生水》第1、2章內容性質、是否同篇諸問題,學界仍存爭議,筆者認為其第2章之“天道貴弱”“激進反強”“天地(自然)齊同”諸思想不出道家言筌、不違道家義趣,故認為其與第1章同篇,并在此基礎上辨析立論。學無止境,術在專攻,權以此文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