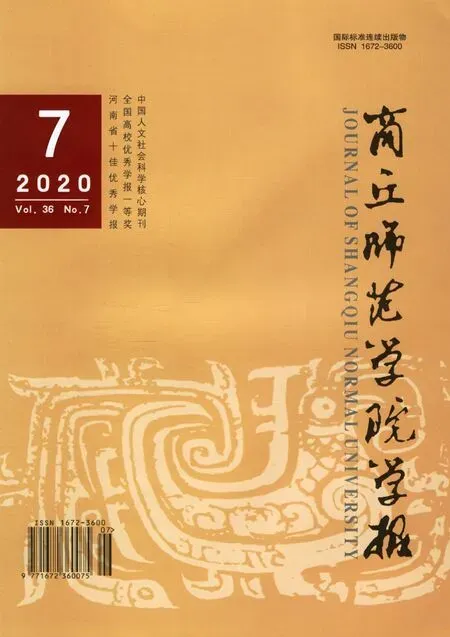從拉鐵摩爾到“新清史”學派:西方中國史研究視角的轉換與“新范式”的漸立
王 建
(肇慶學院 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曾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東亞的歷史舞臺上,中國更是舉足輕重,特別是在古代,中國的發展甚至決定了東亞歷史的走向,其發展進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東亞歷史的主線。基于這些事實,史學界在書寫東亞歷史特別是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關系史時,通常都以中國古代正統王朝為中心,從中原王朝的角度出發考察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關系,中國史學界是如此,國外和西方史學界也是如此。但是自20世紀初以來,在考察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關系史方面,西方史學界部分學者的視角逐漸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為“內亞”概念的引入。在引入這個概念后,西方史學界逐漸出現了一種趨向,即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在考察上述兩者間的關系時,將著眼點放在北方少數民族上。在此基礎上,到了近代,以“新清史”學派的出現為標志,西方史學界逐漸確立了中國史書寫的“新范式”,即以北方少數民族為主體考察某些時段的中國歷史,甚至不將這些時段的歷史當作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而是將其看作是獨立的異族史的一部分。這種傾向應引起我國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對他們的主張,我們必須予以明確、有力的回應,因為很明顯,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歷史研究和書寫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學術話語權的問題,還涉及很多實際的問題。
一、“內亞”概念及其新視角
西方史學界視角轉換和書寫“新范式”確立的進程至少可以追溯到拉鐵摩爾那里,而拉鐵摩爾的影響則在于他對“內亞”概念的發揮與運用,即從“內亞”視角出發形成的一系列獨到的新觀察。在拉鐵摩爾之前,“內亞”概念已經被提出,它出現于19世紀上半期,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洪堡特提出的。之后,這個概念為西方學界所接受,許多學者在解說亞洲地理時都會運用該概念。比如,俄國學者布羅卡蒙斯1900年就運用過這個概念,他認為,亞洲大陸所有內部閉塞的地區都可以被稱作是“內亞”[1]。不過,很長時間以來,“內亞”一詞只是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被使用,并未被引入歷史領域。進入20世紀后,該詞才逐漸為西方歷史學界所接受,而且在歷史學家們的使用過程中,其內涵與外延也發生了變化,它也由一個單純的自然地理概念變為一個含義豐富的歷史地理概念。
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內亞”的提法十分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其含義,更在于其視角。就其本身來說,它的出現頻率雖然很高,但其含義卻十分模糊。關于它所指代的具體范圍,學術界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甚至可以說,學術界對該概念的運用是相當混亂的。不過,大部分學者都同意一點,即這個概念與古代中國有關。“內亞在涉及傳統中國的地理范圍上,最大的區域包括了中國東北地區、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肅、陜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區;最小的范圍則是19世紀中國的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2]很明顯,這個概念涉及許多中國邊疆地區,也自然會將人們的視線引向這些地區,提醒人們注意這些地區在歷史上的作用。可以說,不論這個概念在實際運用中如何混亂,它都代表了一種觀察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關系的新視角,這種新視角才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二、拉鐵摩爾的“內亞”視角
在“內亞”概念的運用和推廣上,許多20世紀的學者都曾發揮過作用,其中拉鐵摩爾的影響尤為顯著。拉鐵摩爾是一個眼光獨到的田野調查者,他曾在中國北部作過廣泛的游歷和考察,足跡遍布新疆、東北等地。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他對古代中國的四個邊疆區即東北、蒙古、新疆和西藏作了深入分析。他認為,上述四個地區在生態環境、歷史發展和民族成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間也存在一定的互動依存關系。在觀察上述地區和審視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上,拉鐵摩爾還提出了一個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中原王朝的歷史循環與草原游牧社會的歷史循環有著密切的聯系,“游牧循環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國循環的結果”[3]377。但他也沒有忽略北方少數民族的作用和影響,他認為,中國的內陸邊疆地區擁有參與歷史的能力,草原民族的參與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在拉鐵摩爾的觀念中,北方少數民族與中原地區的互動在本質上是一種主動參與中國國家構建的活動,在此過程中,北方少數民族也將他們的一些特征打入到中國的肌體中。
拉鐵摩爾的許多觀察都是獨到的,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的視角。可以說,拉鐵摩爾持有一種典型的“內亞視角”,雖然他是從解釋中國歷史的角度出發考察古代中國內陸邊疆地區的,但他的聚焦點無疑是所謂的“內亞”。他集中分析內陸邊疆地區,這實際上是在作一種一分為二的考察。他指出“內亞”各地區間的共同屬性,指出內陸邊疆地區與中原地區缺乏共生的有效機制,這實際上也突出了它們與中原地區的差異。更重要的是,他強調內陸邊疆地區在歷史上的作用,這種強調也在有意無意間突出了上述地區的“主體性”。拉鐵摩爾的“內亞視角”是明顯的,從這種視角出發,他可以得出從許多其他角度難以取得的新認識,但也存在過分強調所謂的“內亞”的傾向。
拉鐵摩爾的很多見解是極富見地的,也并無過多不當之處,其視角也不應受到批評,但仍需引起我們的重視,因為它實際暗含著一種將“內亞”和中原對立起來的傾向。其中的危險之處不在于拉鐵摩爾的論述本身,而在于后來者對他論述的進一步解說。這些解說存在著在與歷史實際脫節的軌道上越走越遠的可能,而且一旦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它們就可能對人產生誤導,甚至會在現實中產生消極作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在拉鐵摩爾之后,“新清史”學派扭曲了他的觀點,對中國歷史發展作出了十分不恰當地解釋。
三、“新清史”學派與西方中國史書寫“新范式”的形成
在拉鐵摩爾等人之后,西方史學界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特別是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關系的解釋在總體上沿著三個方向發展。一個方向是一些人繼承傳統的立場和做法,在書寫中國古代歷史時,將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當作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書寫中原王朝的歷史時一并提及。另一個方向是一些人繼承了拉鐵摩爾的立場,即將所謂的“內亞”地區視作是古代中國的邊疆地區,進而從中原王朝的角度審視其歷史,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強調古代邊疆地區的“內亞特性”。同拉鐵摩爾一樣,在強調與中原地區的差異的時候,他們實際凸顯了邊疆地區在歷史上的作用。也就是說,盡管他們仍在中國的大框架下審視“內亞”,其注意力已更多地投向邊疆地區,其視角也與拉鐵摩爾一樣開始向“內亞”轉移。還有一個方向是一些人則沿著拉鐵摩爾的方向越走越遠,以至于超出了必要的界限,完全偏離了傳統的立場,其典型代表就是所謂的“新清史”學派。
20世紀90年代,“新清史”學派在美國興起。這個學派標榜全球視角,強調清朝歷史發展中滿洲因素的重要性,提倡在相關研究中運用滿文和其他少數民族文字,聲稱其研究多依據滿文史料[4]。應該承認的是,“新清史”學派在許多方面是有其成就的。比如,由于在研究中提倡利用滿、蒙等少數民族史料,他們在歷史細節方面有過不少新發現;其視角也有可取之處,從“內亞”的視角來審視和解釋清朝歷史,無疑也會取得一些從其他角度出發難以獲得的新發現。但在史實考證方面的成就無法掩飾和替代其立場的根本錯誤之處,因為如果對歷史的整體解釋與歷史實際背道而馳,即使其對歷史細節的揭示再正確,也是于事無補的。“新清史”學派的謬誤之處在于他們的基本立場和根本主張,而不在于其對歷史細節的考證。具體來說,就是他們嚴重偏離整體歷史進程的“內亞視角”,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內亞”概念在他們那里實際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概念[5]。“新清史”學派認為自己在學術思想上是追隨拉鐵摩爾的,這或許是因為拉鐵摩爾的視角給了他們以啟發,特別是在重視內陸邊疆地區獨特性、強調北方少數民族的“內亞特性”等方面。但應該指出的是,“新清史”學派與拉鐵摩爾等人是有根本區別的,前者雖然對后者的某些觀點有過繼承,但實際上又作了很大的發揮,以至于其歷史敘述在總體上已嚴重偏離了歷史實際,甚至達到了歪曲、虛構歷史進程的程度。比如,他們刻意突出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的“主體性”,甚至不認為清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總的來看,兩者間最主要的分歧是立場和視角上的分歧,可以說,拉鐵摩爾所持的是一種以中原王朝為中心、側重考察“內亞”的立場和視角,而“新清史”學派的學者則大多持有一種可以稱之為“內亞中心論”的立場。兩者孰對孰錯,不言自明。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的作用雖然不容忽視,但包括清王朝在內的諸中原王朝的主導作用和主體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盡管我們不能同意他們的立場,不得不承認的是,“新清史”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了對傳統范式的突破,在此基礎上,他們還確立了一種中國史研究和書寫的“新范式”。“新清史”學派自出現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隨著該派學者的努力,用“內亞視角”審視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和清朝歷史的學者已變得越來越多,相關研究成果也不斷出現。假如說存在一個用傳統立場解釋古代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關系的學者群體的話,那么“新清史”學派已壯大到能夠向他們發起挑戰的程度,甚至許多原本持傳統立場的學者在該派的影響下也已改換門庭、加入其中。如果追溯一下相關的學術史,其源流也是清晰可辨的。如果說拉鐵摩爾等人代表了視角轉換的開始,那么“新清史”學派的出現就代表了視角轉換的完成。不僅如此,該學派對歷史的解說在某種程度上還標志了一種“新范式”的形成。這種“新范式”的總體特征是,一些人認為自己在書寫中國歷史時尋找到了新的對象,發現了新的“歷史主體”,并用這種新的“歷史主體”來解釋中國和東亞的歷史進程,盡管這種“歷史主體”在實際上并不存在。
“新清史”學派的立場和其所確立的“新范式”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因為它涉及的不僅僅是學術問題,還涉及許多實際問題。它涉及歷史的主體問題,涉及歷史解釋的話語權問題,甚至還涉及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在這方面,有的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問題:“將滿族與中華民族區分開來,將清帝國與中國區隔起來,顯然具有一定的分離主義色彩和濃厚的意識形態嫌疑。”[6]很顯然,如果任由其發展,在很多事情上我們將會陷入被動境地。對此,我國學者必須直面挑戰、勇于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