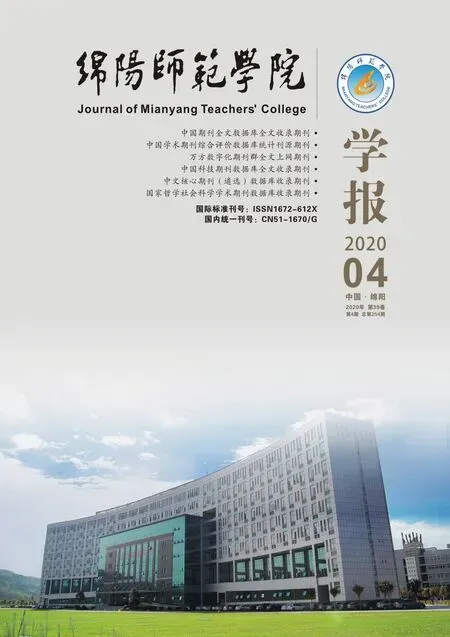“雅俗精神”的當代詮釋
——讀譚玉龍《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研究》
王周孌
(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重慶 400065)
雅和俗是中國古典美學中一對非常重要的范疇。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先民們就具有了雅俗審美意識。表面上看,雅與俗是兩種完全對立的審美標準,但雅與俗的對立關系又不是絕對的,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轉化、相互融合的可能。有些最初帶有“俗”屬性的文藝,伴隨著社會的變革和時代的發展,有可能轉變為雅文藝,而有些“雅”文藝也會因為歷史的變遷,逐漸轉化為俗文藝。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創作中出現了大眾化、商品化傾向,文藝的深度被消解,在雅俗審美觀上呈現出相對主義的傾向,使一些文藝創作者打著“藝術”的幌子創作出一系列滿足大眾低級趣味的作品,不斷挑戰著人們的道德底線。因此,研究雅俗及其關系成為美學、文藝學、藝術學等學科的重要論題。近期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譚玉龍副教授的新著《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研究》。該著是作者以古今中西相結合的視域觀照明代乃至整個中華美學之雅俗精神的研究成果。作者認為,“雅俗之辨”是中國古典美學中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古代審美意識、美學思想和藝術觀念的發展離不開歷朝歷代美學家、藝術家對“雅”“俗”問題的探討與闡發;通過梳理以雅俗為線索的明代審美意識、美學思想的發展,從而更全面地認識中華民族的審美觀念,對當代文藝創作產生新的啟發[1]1。這是作者寫此專著的初衷,書中也凝結了作者對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的獨到見解。
“雅”“俗”審美意識是伴隨著階級的產生而逐漸生成的。它萌芽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成長于夏商時期,確立于“制禮作樂”的周代[1]10-11。在審美意識生成的初期,“雅”就是正統、雅正,往往代表統治階級的文化,而“俗”則與“雅”相對,代表著被統治階級的文化。在“禮崩樂壞”的沖擊下,“雅”“俗”的界限也隨之被解構。面對此種巨變,先秦各家各派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提出各自的救世主張。儒家美學“崇雅尚古”“斥俗貶今”,在文藝風格上倡導“中正平和”的特征,即審美創作和欣賞都要有“節制”,正如《毛詩序》中提到的要“發乎情,止乎禮義”;而道家美學追求超越“雅”“俗”的“超凡脫俗”,追求自然無為、瀟灑自由的境界;兩漢之際傳入我國的佛教,基于眾生平等的理念,試圖打破以階級劃分、等級制度為前提的“雅”“俗”,追求一種“非雅非俗”的境界。由此可見,作者在討論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時,并不是單一靜態地談論各家各派的理論,也沒遵循普遍認為的由雅到俗的發展路徑,而是以動態發展的眼光進行研究,得出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是以“崇雅斥俗”為主線、伴以“超越雅俗”貫穿始終,其間“俗”又興起,逐步形成了“崇雅斥俗”“尚俗貶雅”“超越雅俗”多線發展的態勢的結論。易言之,明代美學形成了儒家“崇雅斥俗”、市民階層“尚俗貶雅”、道教“超凡脫俗”、佛教“非雅非俗”多元共存、四足鼎立的局面[1]286。這是書中的主要結論,也是作者的創新觀點。
作者在討論明代美學思想的“崇雅斥俗”“尚俗貶雅”以及“超越雅俗”時,有著自己新穎的研究視角。
第一,從創作者的角度強調藝術家要有“德”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作者在探索明代書法美學的“雅正”思想時,提到“詩品出于人品”,這一觀點對當代文藝創作有著重要意義。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對文藝工作者的重托: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德行對于藝術家來講非常重要,“明德”也包含職業道德的部分,要把勞模精神、工匠精神貫穿到文化、文藝和社會科學領域。在大眾傳媒時代,受市場化的影響,一味追求商業利潤和收視率的最大化必然會導致部分創作者生產低俗、媚俗的文藝作品,忽視對文化藝術價值屬性的深度挖掘和探索。作者在書中提到,南宋姜夔認為書法之風神取決于八種因素,即“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而“人品”被放在了首要的地位[1]113。無獨有偶,孔子認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2]2481。這就是讓“德”成為文藝之所以為文藝的“本”[1]112。強調創作主體的“雅”對當代文藝建設有重要意義,文藝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更好地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創作更多更好地文藝作品,為黨和人民繼續前進提供強大精神激勵。
第二,作者較為獨到地論述了“醉”的境界。在“明代書法美學之‘超凡脫俗’精神”一章中,作者特別強調一種創作功夫論,即書法為沖破功利、名譽、技法等規矩、束縛的“醉”[1]249。《晉書·姚興載記》記載,阮籍“居母喪,彈琴飲酒”[3]2979。作者認為,這種在“醉”之中的“居喪廢禮”其實是莊子逍遙精神的體現,他齊生死、泯物我,從而進入到與“道”冥合的狀態之中[1]250。“醉”就是道家所追求的通往“圣人”境界的工夫。除此之外,作者還提到“李白”之“醉”是人生美學和藝術美學的雙重境界。杜甫《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4]62從人生美學上看,“醉”讓李白無視權貴,超越時間和空間而成為酒中之“仙”。從藝術美學上看,李白的“詩百篇”是在“醉”的狀態中創作的,“醉”成為李白藝術創作的一種自由的工夫[1]250。作者由談論的“醉”指向了人生美學和藝術美學兩個維度。從人生美學來看,“醉”能超越階級,打破人與人之間的界限,從而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從藝術美學來看,“醉”這種工夫能讓創作者擯棄功利之心,超越技法的束縛,進入自由的創作狀態,從而實現以藝進“道”。“醉”這種工夫不僅體現在飲酒作詩中,還在書法、音樂、繪畫等創作方面發揮著無可比擬的作用,其合理之處對當代文藝創作者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第三,作者由古及今地探索了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的當代意義。作者在論述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與中華美學之雅俗精神的關系時說:“每一新學說、新思想中必定含有前代學說、思想的基因,每一舊學說、舊思想必然對后世新學說、新思想產生影響與啟發。”[1]15這就體現了研究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的當代價值。當前我國的文化生態是“一元主導、多元并存”,即馬克思主義居于主導地位,是主導的意識形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西方合理的文化,這與作者提出的多元共存不謀而和。隨著社會歷史的進步,現代各藝術門類逐漸呈現出“雅”和“俗”共生共榮、相互促進并相互融合的發展趨勢。縱觀有極大影響力的作品無不實現了雅俗共賞的審美構建。正如作者在書中不偏不倚的觀點,并不一味追求“雅”,也不貶低“俗”。這對當代文藝創作者有所啟示,在創作過程中應力求雅與俗的結合,力求實現大眾審美、藝術品味、文化價值的完美融合,在滿足不同審美需求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文藝作品的思想價值和文化內涵。
總之,譚玉龍副教授的《明代美學之雅俗精神研究》旁征博引,邏輯嚴密,論述清晰,不僅提出了具有創建的觀點,還為當代文藝工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