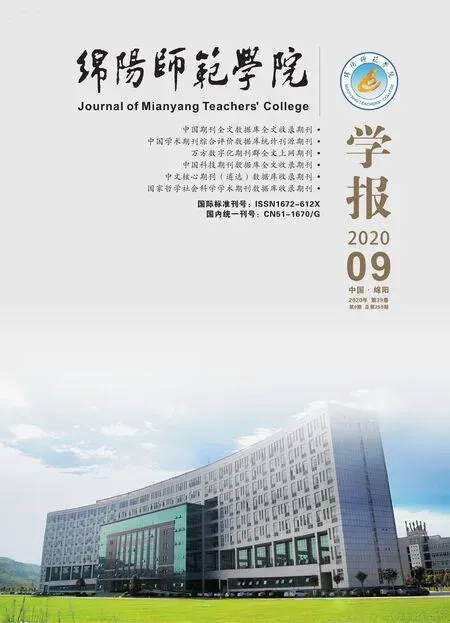戰時中國游記中民族意識的多維表達
茍健朔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 400715)
自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城市相繼淪陷,居住于淪陷區的中國人民滋生出“我城”變為“他城”的失落感,逃離與疏散成為重新發現“我城”、再次尋找主體定位的一種途徑與方式。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月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抗戰”[1]6,重慶成為戰時國都,“西南腹地的大門被突然打開,重慶也由一個邊陲小城一躍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為一個國際大都市”[2]10,“到重慶去”成為一種口號與意識形態歸屬,意味著“回到民族國家的懷抱”[3]。因此,大量“下江人”①融入重慶,進入大后方,遷徙與大后方旅行成為文學寫作的一種流行話語。
由此看出,在逃離淪陷區與戰時國都遷渝的雙重因素下,遷徙、疏離、逃難、旅行成為一種常見社會現象與運動,“八年抗戰,中國的難民遷移大約有1000萬人,其主要流向是自東向西,從沿海和中原遷移到內地。”[4]35“隨著全國各地的作家紛紛來到重慶,在國難之中輾轉于戰時旅途的作家們,不僅個人眼界越來越開闊,而且個人體驗越來越豐富,個人的所見所聞與所感所思,無疑成為進行散文敘事的創作源泉,他們不約而同的采用了游記這一敘事散文體裁來進行個人寫作。”[5]游記書寫因此成為一道獨特的文學現象與文化景觀。
戰時體制下的文學創作與抗戰宣言具有同構性,“拿筆桿代槍桿,爭取民族之獨立。寓文略于戰略,發揚人道的光輝”是通行的標語,“抗戰的文藝”“抗戰救亡”與“抗戰建國”成為文學創作顯性的敘事主題與默契導向。戰時中國的游記書寫作為一種勃興的文學現象,自然被規約于抗戰文化的敘事框架下,作家在人文山川的風景敘事與途中瑣事描寫中融入民族國家觀念,個人文學書寫中嵌入抗戰宣傳與意識動員。
一、屈辱體驗、往事回憶與民族怨恨抒發
盧溝橋事變之后,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繁華的城市被轟炸成為一片瓦礫,文化教育機關被摧殘殆盡,千萬的平民被屠殺,被奴辱,無數的青年婦女在暴力之下忍受野蠻的獸行,求生無路,求死不得;兇暴無人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使得黃河流域淮河流域太湖流域成為慘極人寰的活地獄!”[6]敵人與戰爭摧毀家園,屠殺同胞。因此,指控敵人野蠻行徑與回憶戰前往事成為戰時體制下民族怨恨抒發的兩種敘事策略。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指出:“對國內,我們必須喊出民族的危機,宣布暴日的罪狀,造成全民族嚴肅的抗戰情緒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爭取最后的勝利。對世界,我們必須揭露日本的野心與暴行,引起全人類的正義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7]戰時中國,淪陷區人民飽受日寇凌辱、非日占區同胞時時擔憂敵機轟炸,中國人惶惶度日,受盡屈辱。王西彥《屈辱的旅程》講述了作者由北平前往上海,在火車上遭遇日軍檢查,國人備受侮辱。“帝國武士”的“臉上刻畫著同樣的表情,是驕矜,輕藐,呆板和冷漠”[8]86,他們是“兇殘的野獸”,肆意凌辱國人,而后者只能點頭哈腰或爭相逃跑。日寇“莽撞”,國人“慌亂”,兩幅截然不同的面孔形成強烈的視覺繪像反差,造成作者深刻的屈辱體驗。“我城”變為“他城”,“他者”控制本土與民族,并實行同化策略,國土的淪陷既是政治權力的更替,也是本土民族性的失落,造成主體意識模糊與民族情懷含混,有識知識分子有意繪像,以達到民族怨恨抒發。民族怨恨抒發不止來源于身處淪陷區的中國人民,身在大后方的同胞也時時親身體驗到日寇侵略行徑。居住于昆明的巴金在《廢園外》中指控日寇轟炸暴行,嘆息少女慘亡:“炸彈毀壞了一切,甚至這個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這樣地逃出囚籠,這個少女是永遠見不到園外的廣大世界了。”[9]72由此可見,抒發屈辱體驗成為填充失落情感、呼吁共鳴并引起民族怨恨抒發的一種可行范式。
民族怨恨的抒發緣起于現實危機,日寇侵略促使大批淪陷區的知識分子被迫遠離家鄉,涉入異地。在他們心中,家鄉作為和平美好的回憶與戰時語境下的異地體驗形成對照,知識分子由此產生鄉愁,鄉愁是催化劑,提供抒發民族怨恨的方式并加速其進程。因此,追憶往昔之和平以嘆息現實之戰爭、指控日寇之罪孽成為民族怨恨抒發的一種途徑,在游記中最為廣泛。“老舍喜歡的城市格調,其實是比較固定的,那就是古都北平的類型,與之類似的有成都、昆明、濟南等,這類城市體現出城鄉協調的特性,古樸、寧靜、閑適。”[3]抗戰時期,老舍游歷成都時,也將成都與北平進行下意識的對比,“成都的確有點像北平:街平,房老,人從容”[10]186。在《青蓉略記》結尾,老舍感嘆:“這樣也好,省得看月思鄉,又是一番難過!”[11]124成都印象喚醒北平記憶,兩座城市鏡像造成老舍內心情感錯置,成都成為北平的替代表征,思鄉情緒不請自來。在《檳城三宿記》中,郁達夫也借友人之口,以觀南洋之山而憶廬山,聯想“大好河山,要幾時才收復得來”[12]272,進而作詩“好山多半被云遮,北望中原路正賒”[12]272,懷念故土之情,溢于言表。王平陵在《月下渡江》中,由枯枝“雜居在敗絮爛草里浮來浮去,原來曾在春天里萌過它的新芽”[13]71為線索,聯想“春天是夢的季節,美的季節,花的季節”[13]71,進而慨嘆:“可是,此刻是秋天了!在雜亂中已經是第七個秋天了!”[13]71王平陵將往日和平與現實動亂嵌入“春之江景”與“秋之江景”兩幅風景描寫中,景色融入主觀意識,景色對立與過去、現實對立不謀而合,成為作者懷念過去、追尋和平的一種敘事體現,只可惜,“岸上的喧嘩、煩擾,口角斗毆聲,無情地粉碎我畫似的回憶,我被迫著必須奮勇地重沖入可怕的‘現實’。”[13]71-72沖入現實是必須面對的事實,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壓抑主體的游覽體驗,從另一側面表露出作者對戰爭的不滿與對日寇的怨恨。黃裳在《成都散記》開篇即把杜甫與成都勾連,游逛成都而聯想杜甫晚年被迫離家流浪,客死他鄉,所以“在這位大偉人的晚期的作品中,我找不到什么光與色,除了那一種重重地壓在人心上的衰颯的氣氛”[14]45。古與今進行對話,作者與杜甫企望歸鄉、厭棄戰爭的情感不謀而合,杜甫因此成為一種表意工具。
現世游覽可以喚醒舊時回憶,以今憶昔,表達對現實戰爭與敵人的痛恨。然而,在戰時中國,交通不便,物價飛漲,無論逃離疏散或是遷徙旅游,對于某些作家,都是極為不便的。既然此時不可得,那就回憶彼日所能見。于是,在民族怨恨抒發的催化引導下,“憶舊游”模式得以成形并流行。《旅行雜志》曾特以“憶舊游”為題鼓勵作家創作。閻重樓在《登山·憶舊游》中談到:“看見‘憶舊游’這個題目便不禁勾起我心頭的往事,我感到過去的人生就是一個舊游啊!而且在像我現在所處的這個不能作新游的情況之下,真的我也只能是憶舊游了。”[15]在作者心中,“憶舊游”具有雙重維度:既是憶人文風景之游,又是憶人生歲月之游。兩種維度又互相糾纏,互相嵌入,前者成為后者的載體,這里的人生歲月具有一定的限度,即全面抗戰以前。憶風景以憶和平歲月,成為“憶舊游”模式下一種通行的寫作策略。署名瑯玕的作者在《旅行雜志》上分三次發表《憶舊游》上中下三篇文章,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作者回憶戰前游玩大連、長春、哈爾濱、北平等地,回憶舊時游玩美好以反襯今日之現實,表達對和平的向往與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行文中個人情感頗為濃厚,懷念中滲入無盡的惋惜,正如針對長春感嘆道:“一切的一切,雖然經過了整個八年,我還是記得很清楚,宛然如在昨日,誰想到長春便是今日偽滿的新都呢?”[16]更有甚者,將旅行與抗戰進行意識形態的糅合與等同,羅才清在《致友人書》中談到自己因困于“孤島”無法旅游,遂懷念青島游玩往事,更祝福出游他鄉的友人,定義其所進行的是“偉大的旅程”,最后,發出殷切的希望:“新生的中國能給予我們一個新的旅行的天地的!”[17]“旅行的天地”與抗戰勝利、和平來臨的美好憧憬具有附屬、象征關系,因此,回憶往事與祝福友人成為期望勝利與和平的兩種訴求方式,而旅行則作為中介而存在。
無論今昔對比或是“憶舊游”,都規約于往事回憶的敘事范疇,并共同指向對現實的反襯,以作為民族怨恨抒發的情愫表達。總而言之,處于戰時中國的同胞深受苦難,抒發屈辱體驗以抵抗民族侵略、回憶戰前往事以期待和平,并合力進行民族怨恨抒發自然成為民族意識表達的兩種方式,而游記書寫正是一類適用的載體。
二、錦繡山河、戰時建設與民族身份認同
戰時中國處于烽火狼煙之中,中國人民面對日寇,浴血奮戰,從不屈服。縱觀整個抗戰文學,盡管文學書寫的戰時化愈趨平穩,游記書寫“漸趨悠游”[5],但多數還是無法與抗戰疏離,依舊規約在這宏大的敘事主題中。“文藝家從來因為階級、集團、世界觀、藝術方法論的不同,未能調和在一起”[18]4,而全面抗戰以來,“僅管在階級、集團、世界觀、藝術方法論上大家有著各自的特性然而一個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標——抗敵,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都成為親密的戰友。”[18]4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空前增強,各類黨派、各類社會團體、各類階層,都有一致抗日的決心并付出行動。游記書寫為民族情感表達的去向提供了容置空間,作家在疏離、逃難、遷徙、旅行中,將自己的民族情感寄托在途中所見之中,或是因途中所見而民族情感有極大增強,行途的人文風景及行途本身成為一種工具。佘貴棠在《游覽事業之意義》中首先引培根“旅行為青年人之教育,老年人之經歷”之語為據,并以德國、瑞士、意大利、法國等國為例,強調游覽事業于文化教育有莫大關聯,進而總結:“概括言之,游覽之文化價值固難估計,其開拓胸襟(如國家及國際觀念之培養)蕩滌心目(如情感凈化,心理衛生)增廣見聞(如資源之認識史績瞻禮)之效能,殆為舉世所公認。”[19]旅行與民族文化同構,民族文化是民族情感認同的基礎,因此行途的人文風景與民族情感的產生、增強相輔相成,合力為一種敘事導向,體現主體自身對民族身份的認同、增強對未來必定美好的信心,具體到文本中,則表現在對錦繡山河與戰時建設的描寫中。
中國自古以來地大物博,錦繡山川在文人筆下熠熠生輝。在戰時語境的作家眼中,風景作為接受客體而內含民族情感依托。“川康為新中國太陽的起點,其蘊藏之富,足以支持我國抗戰以達勝利之日;其山水之壯麗,尤足冠甲全國”[20],風景的壯麗美好足以增強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信心,風景作為敘事話語,也參與到抗戰意識的建構中。在《舊游之地》中,朱曼華盡管知道戰亂緊急而無暇“流連風景,玩賞自然”,卻仍強調“中國有廣博的錦繡山河,這些名區勝景,在在使每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感到深深的戀慕”[21],因此仍有回憶的必要。于此看來,將錦繡河山與國民自信建立在一個基準上是常見的文學現象。茅盾在《白楊禮贊》中,以西北白楊的“樸質,嚴肅,堅強不屈”與枝葉團結為標識,既象征北方的農民,也“象征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激蕩用血寫出新中國歷史的那種精神和意志”[22]。白楊被典型化,成為一類對象,以對位民族情感,增強民族身份認同。吳祖光的《小城春色》旨在“記一個逝去的春天”[23]403,將春色與傷兵糅合,共享光明,傷兵作為軍人,在戰時與民族具有一致性,光明既是對春天,也是對傷兵,更是希冀于整個民族。
不僅沿途風景可以參與表意和建構,甚至旅行本身就具有與民族契合的符號意義。莫艾便感嘆道:“我愛山川,我愛原野,我愛自由。祖國都具備了這些,我為什么不去呢?朋友!這是游歷,不是跋涉!顛蕩震旋會堅定我的意志,雨露風霜會鍛煉我的精神!我走了,謝謝你的盛意。”[24]游歷本身作為一種行為被抽象化,主體強烈的民族情感需要在游歷過程中得到依托與釋放,主體情感需急切與客體對象進行對話并雙向認同,游歷“變成我唯一奉行的口號了!當我舒展于萬里的曠野,當我奔馳于削壁的山澗,聽泉聲淙淙,看云沒山巔,我高語,我跳躍,有的是愉快和興奮,那兒找到半點疲倦的影子?”[24]
此外,戰時中國一面在戰火中飽受磨難,一面又浴火重生,戰時人文風景建設是中國人民奮勇抗戰的另一幅面孔。抗戰前北平的風景建設、文化修復促使北平“市面賴以繁榮,民生終以復蘇,游覽事業之發皇,風景建設之重要,相輔而行,相得益彰,此一證也”[25]。由此可見,人文風景與城市建設直接關聯城市繁榮、民生復蘇,并與民族前景息息相關。
重慶特殊的政治地位促使重慶文學“突破了區域文學從地域性到地方性的雙重文化限制,從而使陪都重慶文學在具備區域性的同時又具有全國性”[26]。因此,有關重慶的游記書寫,自然具有典型性與全國性。重慶作為戰時國都,常年遭受敵機轟炸,卻在轟炸后積極恢復,“每一次,轟炸過后半小時,市面就可以照常恢復,就像這三天連天的轟炸,電燈線炸斷了,街上一眼望去如同十幾年前的小縣城里過元宵燈節,太平燈是那樣美觀而有秩序地在每家店鋪門口點燃”[27]23-24。積極的戰時建設自然被敏感的知識分子捕捉,在游記書寫中體現。在《北泉日記》中,鳳子游歷重慶北碚“這么一個新興的小市鎮”后感嘆:“走進內地,愈相信我們支持抗戰的力量;只要物力人力配合得當,不屈膝中途,必能取勝到最后。”[27]25冰心在由昆明前往重慶的飛機上俯瞰重慶,“倚窗下望,我看見林立的頹垣破壁,上上下下的夾立在馬路的兩旁,我幾乎以為是重游了羅馬的廢墟。這是敵人殘暴與國人英勇的最好記錄。”[28]在冰心眼中,重慶是忙的,“我們是疲乏,卻不頹喪,是痛苦卻不悲哀,我們沉靜的負起了時代的使命,我們向著同一的信念和希望邁進”[28],因此“這里有一種心理上的太陽,光明燦爛是別處所不及的”。重慶作為戰時國都,具有民族國家的象征,文藝界眾多作家“到重慶去”,以“擇亦途徑,貢其微力”,在重慶,中國人民不被戰爭擊敗,投入到風風火火的戰時建設之中,作家的民族身份認同感油然而生。
游覽風景與游覽本身的觀念賦予是主體意識對客體對象的一種意象化行為。沿途與沿途風景在民族意識的加工下,參與民族觀念的建構。戰時建設是主客為一體的民族行動,本身內含著豐富的民族意識,戰時建設與戰時動員相互迎合,戰時動員產生戰時建設,戰時建設促進戰時動員的擴大與延展,兩者的合力在游記書寫中呈現。總體來看,無論錦繡山河或是戰時建設,在游記書寫中都是體現民族身份認同的一種路徑,當然,在“抗戰的文藝”主題之下,兩者也同時指向戰時動員、服務抗戰。
三、批判國民、審視傳統與民族精神重塑
日寇侵襲促使民族凝聚力再次登上高點,而這凝聚力是雙向作用的:對外抗敵,對內自省。半殖民地半封建語境下的中華民族藏污納垢,批判國民性與審視傳統文化是五四文學以來照耀整個現代文學的母題。全面抗戰以來,民族的污濁被進一步放大,民族文化重塑成為有識知識分子的方向。梅林在《文協五年來工作志略》中總結道:“一方面我們竭誠的激勵士氣民氣,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揭發各方面的缺點和弱點,以求補救和革新。誠心抗日的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妨礙抗日的是漢奸,我們的善惡分明,也希望使全民族辨清是非……。”[18]29游記作為作家們戰時所見所聞的一股支流,在暴露黑暗與落后方面具有真實性,成為一種可行的敘事體裁。在游記書寫中,圍繞民族精神重塑,也契合“五四”以來的寫作方向,體現在批判國民與審視傳統兩個維度上。
抗日戰爭以來,中國雖然不乏視死如歸的英雄,但懦弱的國民依舊存在。《屈辱的旅程》提供了這兩幅畫面:一幅在日軍面前唯唯諾諾的中國國民的畫面在前文已闡述;另一幅則是“一個四川人就為了行李的放置和幾個廣東學生吵了嘴——好像還要動武的樣子”[8]89。面對侵略的日寇一言不發,而將被壓抑的怨氣撒在自己同胞身上,互相謾罵、盛氣凌人,這使作者感到無以言表的悲哀,屈辱體驗既來自外敵,也取于同胞。倪絅賢在《漢口沙市道上》一文中也對國民性進行批判,“窗口上扒了三四個人,窗前圍了一大堆,叫囂擁擠,充分表現出過人無秩序的習慣,這時才五點四十分,售票處還緊閉著窗門,才恍然到聽差所以要這樣早叫我起來的理由,鐘鳴六下,鈴聲一響售票處窗門開了,稍為平靜一些的騷擾聲,叫囂聲,此時又起了高潮,穿著黑制服的路警,手拿著木棍一聲也不響的望望走走,我不禁對著站上新油漆的新生活標語感嘆著。”[29]民眾的無序、擁擠、吵鬧,路警的不作為,使得這段旅程雜亂,作者不禁擔憂“新生活”指向何處。
在游記書寫中,關于國民性的批判不僅來自民間的眾生群像,也源于達官顯貴,作家們對此類群體的批判更顯冷酷。署名陳志良的作者寫自己由桂林撤退至昆明的親身體驗,感嘆疏散的艱難,既嘲諷“桂林的有權有貨,有錢有勢的人,早已開始喬遷了,他們是天之驕子,所以得天獨厚”[30]。戰時中國,通貨膨脹極為嚴重,階層易位、身價漲跌,使得一些國民以錢為本位,囤積貨物,以期來日發財,這在老舍話劇《歸去來兮》中有淋漓盡致的體現。陳志良也對此類現象進行痛斥“在疏散期間,最感頭痛者,首推囤積戶”[30],“時局愈緊張。逃離的人愈多,交通愈困難,黑市愈高,處處非錢不可,實踐了‘錢能通神’的名言,而且只要有錢,沒有公理法律,更不計情面。‘混水里摸魚’,此之謂也”[30]。抗戰勝敗與經濟流通有莫大關系,因此,訴諸于此類發國難財的國民批判顯得尤為緊急與無情。此外,國民性批判不只滿足于當下,同時也糾察過往。署名瑯玕的作者在《憶舊游》上篇游玩大連、哈爾濱等地之時,對東三省官員提出質問與指責:“我真奇怪,東三省的高級長官,在此時都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在經濟上如何壓迫我們,在政治上如何威脅我們,他們所列舉的事實,非常清楚,所顧慮的事情,后來也都應驗了。可是這些長官在白天盡管發愁,到晚上便有些模糊起來,打牌的還是打牌,跳舞的還是跳舞;而享受的豪華,真使一般人咋舌,做一套西服,太講究式樣了,非一百元金票,不能上身。固然這許多人并不能代表整個東北,但是當時的現象,的確如此;而東北到后來的淪亡,這些人也應連帶負責的。”[31]不僅東北,北平長官更是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可是,在另一方面,有很多闊衙門的長官,每天晚上,照舊度著他們豪華的生活,城南一代,菜館娼寮,卻異常活躍,汽車馬車和包車,擁塞了燈火燦爛的胡同中,如果把他們正當的收入估計一下,他們決沒有這樣大量的金錢來揮霍。至于軍閥更是暢所欲為,予取予求,單是賭錢,輸上十萬八萬也絕不顧惜。”[32]官員如此妥協與頹靡,下層百姓自然缺少反抗的平臺與契機,東北與北平經驗給國民政府與中國人民提供了教訓,作為民族精神重塑的規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語境下,城市想象參與民族國家觀念的建構。城市以獨有的文化特征而相互區隔。抗戰以來,重慶以“抗戰司令臺”的城市身份對其他城市文化進行規訓,進而言之,“抗戰”作為一種文化話語,對城市固有文化進行清理,以達到重塑。在清理模式下,比起上海摩登,北平的傳統文化更成為一面具有典型意義的反思鏡。北平作為舊時都城,是傳統文化凝聚地,“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33],北平作為全面抗戰以來首個淪陷的城市,提供給作家多維度的描寫空間。在游記書寫中,北平文化作為抗戰文化的對立符號編碼而呈現文本,提供了一種審視傳統文化的角度。作為從小生活在北平的地道北平人,老舍在《在成都》《可愛的成都》中多次談及成都與北平類似,卻又強調“只是街平,房老,人從容,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北平的陷落,恐怕就是吃了‘從容’的虧;成都,不要再以此自傲吧”[10]186。在《青蓉略記》中也慨嘆“古跡,十之八九,是會使人失望的”[11]121。“從容”“古跡”與北平文化對位,以北平警示成都,進而反思整個傳統文化。提煉“從容”這一概念進行剖析,筆者發現這不只是老舍的一家之言,“從容”成為審視北平傳統文化的共同話語。年幼時即跟隨父親來到北平的冰心也在《擺龍門陣:從昆明到重慶》中由重慶想象照耀北平記憶,以重慶的“忙”校對北平,“然而這里有一種心理上的太陽,光明燦爛是別處所不及的,昆明較淡,北平就沒有了”[28]。不僅本土作家的城市記憶如此,別處的北京想象也不謀而合,瑯玕在《憶舊游》下篇以外來者的眼光審視北平,“旅行者到了北平,一顆心便自然地舒散下來,并不是不喜歡忙迫,亦不是有什么特別原因使得你舒散,實在是環境勸誘你不得不松弛下來”[32]。
國民性與傳統文化一體兩面,互為歸屬,內含邏輯的同向延伸,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共同熔鑄民族精神的內核。此外,戰時國都與舊時故都文化交纏,戰時民族意識于此具有榜樣效用,審查并規范傳統民族文化,以求重塑。由此看來,抗戰文化與抗戰精神既是一面放大鏡,將民族性的藏污納垢放大,呈現在敘事舞臺中心地帶;又是一種篩選裝置,對民族精神進行過濾與清理,國民性批判與傳統文化審視“首當其沖”。
四、結語
戰時中國混亂的社會動態促使中國人民產生“無家”的漂泊心態,而“無家”的緣起對象是日寇侵略,因此,抵牾與回憶成為游記書寫中引導情感走向的兩種話語,在兩者中進行民族怨恨抒發,以確立主體,表達民族意識。然而,中國與中國人民積淀著五千年歷史文化,中國人民與生俱來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自信空前增強,天然的錦繡河山與人為的戰時建設成為適用的民族意識傳輸載體。但是,文化悠久,藏污納垢,積病亦深,對傳統文化與國民性的凈化成為必要的敘事主題,以期對民族精神重塑。
總體而言,戰時語境催生游記書寫成為一種新興的文學現象,而“抗戰的文藝”又作用于游記書寫的寫作策略,促使個人游記書寫戰時化,表現在文本中,是民族怨恨抒發、民族身份認同與民族精神重塑的多維民族意識表達。同時,多維民族意識的生成又服務于統一的抗戰母題,達到戰時動員之目的。
注釋:
① 四川謂客籍者為下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