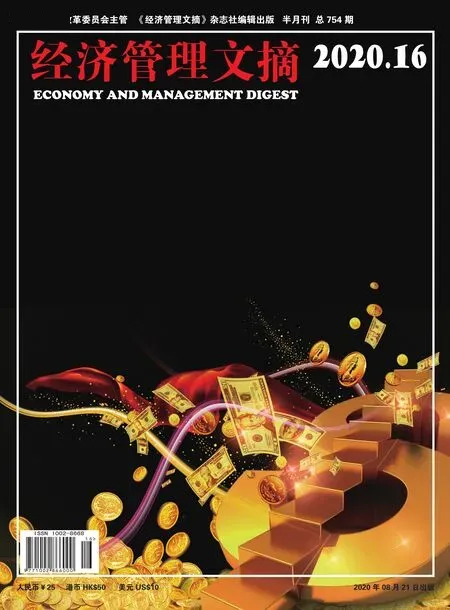德國“工業4.0”的戰略成效與問題探討
■任一蕾
(中德對接研究工作室)
引 言
德國工業4.0的概念和中國制造2025的概念是現在制造業帶動著服務發展的方向,德國在從科研投入,職業學校的培訓到模范工廠都在貫徹著工業4.0的發展戰略,那么成效如何呢?我們又能從中得到什么樣的啟示呢?本文就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1 德國工業4.0的背景和戰略目標
19世紀末,蒸汽機的發明是工業1.0的標志,20世紀初電成為了主要的動力來源,交流發電機也使得電力遠程輸送成為現實,機器和生產線也在這個時候產生于是產能效率都大大提高,這被稱為工業2.0的時代。20世紀末電子器械,比如晶體管和集成電路的發明產生了自動化的生產,同時為了配套軟件產品開始出現,軟件的賦能讓機器代替了一部分工作,這個就是工業3.0。工業3.0的制造業領導者是德國,但是隨著集成電路發明后,美國迅速在電子信息上領先,電子自動化提高效能的同時,產生了更多的技術人員,人的智慧資源更多的配置在開發應用上。于是到了21世紀,這一系列的革命都是借助于突破的技術發展,和技術的模塊化輸出推廣就是商業化,使得生產效能最大化。
1.1 德國工業4.0概念提出
德國首先在2010年提出了“高科技策略2020”,緊接著2011年德國科學院啟用了工業4.0的名稱,并且在漢諾威工業展上宣布。這個策略給聯邦政府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據是德國比較了亞洲、美國還有德國對研究開發的支出對比了歐盟亞洲美國,為了保持持久的競爭力,覺得必要從政策層面上將工業4.0放到戰略中。
1.2 德國工業4.0的戰略目標
緊接著2018年德國聯邦教育研究部向德國聯邦政府提交的“德國高科技戰略2025”中提到2025年科研投入占GDP百分比達到3.5%的目標:①首先科技2025的目標是無論科技還是社會上的創新只要能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獲益,都會受到鼓勵。②給創新創業文化提供環境。③增加國家未來的競爭力。
1.3 德國工業4.0的參與方
工業 4.0 的參與方包括制定政策的政府、金融機構、領先的大企業、通訊科技公司、中小企業以及技術人員。
2 德國工業4.0的衡量指標和挑戰
數字化轉型被歐盟定義成了歐盟增長的一個方面,此方面核心科技包括:社交媒體,移動設備,云計算,物聯網,網絡安全解決方案,機器人和自動化制造,大數據和數據分析,以及人工智能。
2.1 德國工業4.0的衡量指標
為了衡量歐盟各國家數字化轉型的現狀和發展環境,由普華永道還有Carsa等頭部咨詢公司和歐盟一起制作了數字化轉型監控板,衡量每個國家支持數字化程度的模型由5+2個維度。
5個支撐性維度:
(1)數字化基礎建設。
(2)投資和金融的支持。
(3)廣泛存在對技術的供給和需求。
(4)對獲得這些技術的教育培訓。
(5)人們青睞的企業家的行為。
2個產出維度:
(1)企業數字化科技的集成度。
(2)通信科技的創業公司。
在歐盟各國家的評分系統里,德國對數字化轉型的支持指數排在荷比盧和北歐國家之后,雖然在維度金融支持和存在的技術供給需求上不弱,但是在扶持科技創業企業上還有數字化的基礎建設上做的還不夠。
2.2 德國工業4.0的挑戰
德國的工業化轉型面臨著很多挑戰。德國的大企業都在自身內部孵化對自身生產有益相關的創新公司,但資金投入有限。在一些著名的孵化器中也是鮮有迅速成長為獨角獸的例子。跟中國還有美國甚至一些北歐的創業公司相比,原因一是語言的壁壘,二是保守的風格,三是金融資金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可以保證公司人員的生活但是不能戰略性的成長。雖然很多傳統的大公司每年1/3的利潤會投入研發來維持創新保持持久的競爭力,但研發的科技多是公司固有產品類相關。盡管歐盟定義了發展是要面對社會需要,而德國大企業對社會需要的滿足是在已有產品基礎上增加的用戶體驗,除了對已有產品質量技術的極致追求以外是保守的。要理解這種保守,可以參照當時中國移動推出的軟件“飛信”,本來占有極好的資源優勢,但是由于保守策略還是沒能抗衡“微信”。歷史上看突破性技術產生是隨著全面推廣才產生巨大社會價值的。
德國的這些挑戰由于和中國現有數字化科技生態形成了互補,也是中德合作的機遇。但這種機遇在目前國際環境的大局勢下更需要我們審慎的對待。我們對德國傳統企業的領先的創新科技一直想要學習利用,但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一直在提醒德國政府和企業,認為中國始終有爭取科技領先地位從未改變,所以正在用各種優惠條件說服企業將產業量最有技術含量的部分轉移中國,他們擔心中國企業不追求技術的極致而是力爭有競爭力的價格提供足夠好的產品這樣壓縮歐洲企業的利潤從而限制了歐洲企業研發的投入。他們建議不妨礙經貿條件的同時防范科技外流。但是實際上中國科研水平增加,越來越多公司的科研崗也轉移到了中國。既然德國在警惕技術外流,那么在這個新的局勢之下合作的方式就要被重新談判了。
3 德國工業4.0的成效和問題
德國對工業4.0的提出多是對目前領先制造業的賦能,希望已有的制造業完成工業4.0的轉換,從而保持技術優勢和持久競爭力尤其是規則定義的話語權。SAP也屬于軟件中的頭部企業,所以在各自制造工廠的落地上,德國處于領先地位。而在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建設上,甚至通訊網絡這樣基本的基礎設施上德國落后于中國。而中國在基礎建設上,科技創新企業的發展上,數字化平臺的搭建和應用上處于優勢,正好和德國形成了互補。即使在技術限制的基礎上,也能夠合作共贏。
3.1 研發投入
我們將德國美國中國從2000開始到2018年研發投入變化進行了對比。我國研發總投入從2004開始出現拐點奮起直追,總額2005年超過德國,在2018年已經接近美國達到近5000多億美元遠超德國1290億美元。而研發投入所占GDP的比例中國也在快速增長,從2005年1.3%到2018年的2.185%,雖然仍然落后美德。在2010年的時候,德國美國研發投入占GDP比例都是2.73%。
德國在2010年提出了工業4.0的戰略計劃,所以在執行這個戰略計劃的路途上逐步加大幅度提高研發投入占GDP比例2018年達到了3.13%,超過了美國的2.83%。德國新一輪的目標是研發收入在GDP達到3.5%。
所以德國提出工業4.0還是有了一定的成效,雖然發展速度不如中國,但是目前研發投入力度仍然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
3.2 創新創業的環境及金融支持
對于創新創業的環境支持也很重要,尤其在創新企業起步階段,挖掘出長遠有價值的技術進行支持,對必要的擴張和投入可以加速優質技術企業的孵化,也是新的科技企業孵化的必要條件。這里衡量的一個標準就是風險投資的力度。
德國風投在國民平均投入58美元上保持發達國家水平,但遠落后于美國風投人均282美元,瑞典264美元,甚至英國129美元。總體投入美國還是遙遙領先,中國次之,而德國遠落后于中美英。這樣也印證了之前在2.2所提出的德國沒有孵化出來迅速成長的獨角獸創新型企業的原因。
3.3 各國VC投出的獨角獸企業
已經成功孵化出來的成功獨角獸企業更能代表創新創業公司在政府和金融支持下的發展成效。在2019年,風投使中國產生了121家獨角獸企業,美國224家,英國24家,而德國只有12家,法國5家。當然風投資金是全球性的不是本國的風投就投給本國的企業。這里代表性的我們知道阿里巴巴當年的風投資金是日本的軟銀和美國的雅虎,而騰訊也是南非的風投。但是這個獨角獸產生的個數也反應了一個國家科技創新迅速成長的能力和潛力還有當下的競爭力,才會吸引到風險資金的投入。德國風險投資VC投入成就的獨角獸企業比中國少很多,孵化的效率研發產出的效率新科技上與中美有差距,而我國在這里做的很好。這也可以說明國際間投資德國本身或者被投資人看好的創新項目不多。
但獨角獸不能反應傳統領先行業的科技水平,而且我們還需要注意獨角獸企業的分布結構,我們在金融科技領域,安全領域,還有軟硬件上仍是短板,但是商業化應用上已經處于領先,而德國在這方面落后了中國,所以他們扶持新企業沒有中國的生態好,這一點可以成為我們的市場所在進行合作。
4 問題探討及對我們的啟示
我們目前已經走在工業4.0的卓有成效的大路上,但是還忽略了一些基石,比如在納米科技,金融科技,網絡安全解決方案,還有健康和旅游上還需努力,對標領先下仍有發展空間。工業4.0的路上最大的挑戰是大企業尤其頭部網絡科技巨頭供應商們之間的競爭還有車間的落地,這種落地不在于形式,而是如何切實提高車間的生產效率,增加工廠的持久競爭力,在國內還有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德國因為根基在于制造業車間,但是也擁有SAP這樣的軟件巨頭,我們也要為軟件積聚人才為此需要進一步戰略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