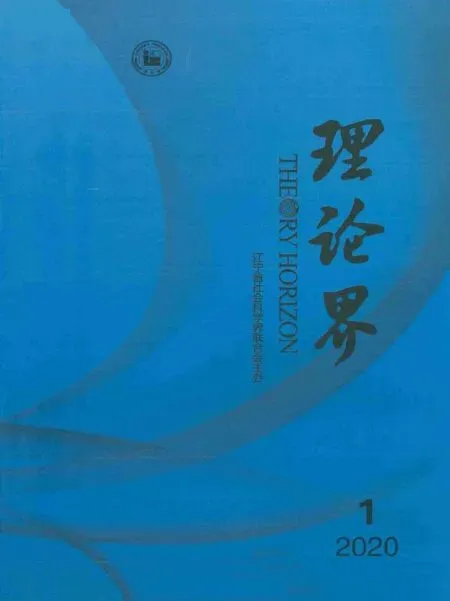論羅薩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
于桂鳳
哈穆特·羅薩(Hartmut Rose)是當代德國著名社會理論家,也是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現任所長霍耐特批判理論團隊的核心成員之一。他試圖復興西方的社會批判理論傳統,重新詮釋現代性。通過對晚期現代社會時間結構的批判性分析,羅薩揭示了隱含于現代社會結構中的“社會加速邏輯”,并在此基礎上將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引入當代社會批判理論,構建了他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理論可以看作是西方社會批判理論的當代版本之一,為我們深度發掘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當代價值,深入把握當代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邏輯,提供了新視野和新思考。
一、晚期現代社會的核心特質:社會加速
準確揭示現代社會的核心特質及其問題所在是晚期現代社會批判理論的根本宗旨。羅薩認為,對現代性和現代化進行反思的“古典”社會學文獻,雖然抓住了現代社會的某些特質,如韋伯和哈貝馬斯所主張的“合理化”,涂爾干和盧曼所論證的“分化”,齊美爾和貝克所聲稱的“個體化”,馬克思、阿多諾等所指出的“馴化或商品化”,但忽略了對普遍存在的社會加速問題的深入研究。此種研究之所以必要,關鍵在于社會加速是現代社會的核心特質,貫穿并作用于“合理化”“分化”“個體化”“馴化或商品化”,直接關涉現代社會的潛在病狀與現代人的美好生活。
羅薩關于現代社會核心特質的判定基于他對現代社會時間結構的分析。在羅薩看來,時間并非一個特殊的社會領域,而是整個社會領域的核心構成要素,一切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都具有時間上的過程性,并通過時間加以整合。所以“以時間作為分析社會的切入點,是一個分析的‘訣竅’,它可以為分析與批判不同的社會行動領域提供一個穩定且一貫的焦點”。〔1〕羅薩認為,時間規范已經成為晚期現代社會中最具支配性、控制性的規范。時間規范不同于道德規范和宗教規范:“它沒有披上倫理的外衣,也沒有佯裝為一種政治規范,而是表現成一種赤裸裸的事實、一種無可辯駁的自然法則。”〔2〕整個現代社會,無論是宏觀方面還是微觀方面,都通過時間結構聯結起來,并受嚴密的時間體制控制。正是這種特性,使時間規范逐漸演變為一種意識形態,并且帶有集權主義性質。最能夠表達現代時間結構變化趨勢與特征的概念則是“加速”,時間規范對現代社會的“規范力”或“控制力”集中展現為社會加速。社會加速“界定了現代社會的動力、發展與改變邏輯,以及推動力”,〔3〕由此構成現代社會的核心特質。羅薩得出此種判定的重要依據是盡管現代社會還存在一些減速甚至反抗加速的現象,但加速的力量始終占據優勢。
羅薩把減速或停滯現象概括為以下五種類型:一是自然的速度極限,如自然資源的再生產、感冒、流感和懷孕的過程。從原則上說,這些過程很難甚至根本無法提速;二是減速綠洲,指沒有被現代化進程所侵蝕的社會或文化“孤島”,這里的時間結構沒有發生變化。這也表明,加速與現代化相伴而生;三是因社會加速失調而造成的病態減速,如交通擁堵、長期失業等;四是刻意減速,包括功能上的減速和意識形態上(反抗性)減速,前者如過度疲勞之人暫停工作,后者如反現代性的“深層生態學”等社會運動;五是結構惰性和文化惰性,認為現代社會已經耗盡了夢想的能量,不可能再有重要的新觀點、新事物產生,如福山“歷史的終結”論。對于這些減速現象與社會加速的關系,羅薩指出,第一、第二種減速現象只是社會加速的限制力量而非反抗力量。第三種減速現象僅僅是社會加速的派生物,因而從屬于社會加速。第四種減速現象則是加速過程得以可能的條件,是加速本身的構成要素。第五種減速現象雖然不是加速的派生物,但卻內在于現代加速當中。正因如此,相對于社會加速力量而言,這些減速力量在狀態、重要性和功能方面都處于次要地位。即使現代社會存在對加速的反抗,但事實證明,“在所有的減速形式當中,沒有一個能跟現代加速趨勢有真正且結構性的不分軒輊抗衡之力”。〔4〕從經驗層面看,現代人也深切感受到現代社會的加速,并在現代文化中得到證明,如葛萊克(James Gleick)觀察到“加速牽涉所有事”,卡普蘭(Douglas Coupland)所寫的《一個加速文化的傳說》,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聲稱“現代性就是時間的加速”。〔5〕
基于以上分析,羅薩得出,整個現代社會都被一種強大的社會加速邏輯所控制,并改變了我們與伙伴、社會、時間、空間、自然、無生命對象的世界(客體世界)和人類主體形式(主體世界)及其之間的關系,改變了我們的身份認同模式、生命經歷和集體歷史,造就了新的時空體驗、新的社會互動模式及新的主體形式,并最終引發新的異化。這也是社會加速之所以重要的關鍵所在。
羅薩認為,指認并批判分析阻礙人們邁向美好生活的“社會病狀”是社會批判理論的宗旨,因而也是每一位社會批判理論家的責任。在他看來,“社會加速”就是晚期現代社會的“社會病狀”。由于他對現代“社會病狀”的這一診斷完全有別于其他社會批判理論家,他被看作是對當代社會進行原創性診斷的社會理論家。按照羅薩的觀點,以往社會理論家關于現代社會的診斷及解決方案,如哈貝馬斯的以“相互理解情境”為基礎的溝通行動理論,霍耐特的以“相互承認情境”為基礎的承認批判理論,其實踐也會受社會加速的影響——無論是相互溝通、相互理解還是相互承認,都需要時間。此外,關于現代社會是消費社會、風險社會、網絡社會等的判斷,雖然準確抓住了現代社會的某些特征,但這些特征也都與社會加速密切相關。他特別指出,現代化的歷史可以詮釋為一種社會加速的歷史,社會加速是現代性的獨立的基本原則,也是阻礙現代人過上美好生活的罪魁禍首。因此,現代社會批判理論必須關注社會加速問題。
二、社會加速:概念內涵與推動機制
界定社會加速概念的內涵是建構社會加速批判理論的基本前提。羅薩指出,以往社會學理論關于社會加速的討論,涉及生活的速度、歷史、文化、政治、社會,甚至時間本身,但還沒有形成定義清晰并被普遍認同的社會加速概念。因此,他試圖從一個不同的分析框架,為社會加速提供一個“在理論方面是清楚的、在經驗上是合理”的定義。
借助于牛頓物理學,羅薩認為“加速可以定義為時間單位內的數量增加(或者也可以在邏輯上同等含義地定義為相對每份確定的數量所需要的時間量的減少)”。〔6〕為進一步說明社會加速的本質內涵,羅薩在此基礎上又從紛繁復雜的諸多加速的社會現象中,歸納出三組加速范疇: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節奏加速。這三組范疇,既代表三種不同的加速形式,也是三個不同的加速領域,各有不同定義。
第一,科技加速。它可以定義為“每個時間單位當中的‘輸出’的增加”,〔7〕表現為運輸速度、信息傳輸速度、生產速度、服務速度、消費速度等變得更快,是目標明確、最明顯、最易測量和證明的加速形式。科技加速屬于社會“當中”的加速,因而對社會現實影響巨大:它導致現代社會的物質結構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被再造且發生變化,促使現代的科層體系和管理體系中的各種過程加速,甚至改變了社會的“時空體制”,即社會生活的空間和時間的體驗。例如由于受人類自身的知覺器官和地球重力的影響,在過去人類對時空的體驗中,空間具有“自然的”優先性,但現在時間獲得了這種優先性。在全球化與互聯網時代,時間“甚至消彌了空間”。
第二,社會變遷的加速。它可以定義為“指導行為的經驗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8〕屬于社會“本身”的加速,涉及社會制度、文化制度、家庭以及政治、職業等在內的所有類型的實踐。因其變遷的速率本身的改變,使得“態度和價值,時尚和生活風格,社會關系與義務,團體、階級、環境、社會語匯、實踐與習慣(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續增加的速率發生改變”。〔9〕正因為這種加速是社會“本身”的加速,且速率持續提升,所以測量有些困難。羅薩建議可以“當下時態的萎縮”這個概念作為測量的準繩。所謂“當下時態的萎縮”指社會各個事物、信息的時效性越來越短。羅薩以家庭與職業為例,對“當下時態的萎縮”進行了經驗的證明。在早期現代,家庭與職業以“數個世代”的步調發生改變,在“古典”(大約是1850年到1970年)現代是“每個世代”的改變,而到了晚期現代則是“世代之內”就已經改變。現代社會變遷速率的不斷提升意味著現代社會制度和實踐穩定程度的普遍下降。
第三,生活節奏的加速。它可以定義為在一定時間單位當中行動事件量或體驗事件量的增加,即在更少的時間內做更多的事。測量此種加速可以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個尺度。“主觀”的尺度指個體對此種加速的直觀感受。其中,最直觀的主觀感受是“時間匱乏”。很多人因為擔心自己由于無法跟上社會生活的快速節奏而被淘汰,甚至對這種“時間匱乏”產生恐慌感。“客觀”的尺度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測量可界定出來的行動所耗費的時間區間或單位的縮短,比如測量吃飯、睡覺、散步、娛樂、家庭談心的時間。另一種是測量行動時間與體驗時間的“壓縮”,比如在一定時間段當中,通過減少休息或間隔時間而做更多事。在此,羅薩也從社會學的角度簡要分析了科技加速與生活節奏加速之間的“矛盾”關系。從邏輯上看,科技加速會使自由時間“增加”,從而應該讓生活節奏“放緩”或“變慢”。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人們越來越感覺到“時間匱乏”。羅薩認為,造成這種“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需要完成的“事務量”在持續增加。科技加速提供了讓“事務量”得以增加的條件,但并不是“事務量”增加的“肇因”,因為“事務量”增加的速率超過了科技加速的速率。而且從歷史上看,工業時代的科技革命似乎就是為了回應“時間匱乏”問題。那么“事務量”不斷增速的原因到底何在?又是什么推動了科技加速、社會變遷的加速和生活節奏的加速?這就涉及社會加速的推動機制問題。
羅薩把社會加速的動力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社會動力是競爭。羅薩認為,競爭支配著現代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從社會結構上看,不僅經濟領域、體育領域,而且政治、科學、藝術領域,甚至宗教領域,都充斥著競爭邏輯。同時,從主體角度看,這種競爭邏輯既存在于民族國家之間,又存在于個人之間。因此,競爭是現代性的核心原則之一。然而,“由于在競爭當中的判決與區分原則是成就,因此,時間,甚至是加速邏輯,就直接處于現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當中。成就被定義為每個時間單位當中的勞動或工作(成就=工作除以時間,像物理學的公式所做的那樣),所以提升速度或節省時間就直接與競爭優勢的獲得有關”。〔10〕這樣競爭就成為社會加速的主要推動力。第二,文化動力是“永恒的應許”。羅薩指出,“在現代世俗社會中,加速的功能等同于永恒生命的(宗教)應許”。〔11〕這源于現代社會重視此世而非死后的彼岸世界。根據西方現代性的主要文化邏輯,好的生活就是有豐富的體驗與能夠充分自我實現的生活。但是在個人有限的生命歷程中可以實現的事物,總是比不上這個世界所提供的選項數量的增長速度。有鑒于此,生活節奏或步調的加速就成為消除這種差異和矛盾的重要策略。“現代加速的幸福應許,是一種(不言而喻的)觀念,它認為‘生活步調’的加速,是我們在面對有限與死亡的問題時,所作出的(亦即是現代性的)回答。”〔12〕第三,加速循環。按照羅薩的觀點,到了晚期現代,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步調的加速,已經形成一種環環相扣、不斷自我驅動的反饋系統。在此,羅薩深刻分析并揭示了三種加速形式或領域之間“令人驚訝的反饋循環”關系:科技加速推進社會變遷的加速,加速了的社會變遷造就生活步調的加速,生活步調的加速又必然要求科技加速。這種循環推動晚期現代社會不斷地加速。羅薩把社會動力和文化動力看作社會加速的外在驅動力,而把加速循環視為內在驅動力。總的來看,羅薩的分析主要是在直接或間接的經驗觀察基礎之上的“現象學”分析。
三、社會加速批判:功能批判與規范批判
羅薩指出,在晚期現代社會,社會加速已經成為一種新的集權主義形式。它對所有主體的意志與行動都具有一定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幾乎無法逃避,更無法抵御和反抗,并最終導致人的新異化。因此,必須對其進行批判。
羅薩對社會加速的批判相對區分為功能批判和規范批判。功能批判實質是揭示社會加速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及其消極后果。依據經驗觀察,羅薩認為雖然當代社會“所有的過程”都傾向于加速,但不同領域、不同事物的加速能力、加速程度存在差異,由此造成“諸多制度、過程和實踐之間的界限的摩擦與張力”,〔13〕他稱之為“去同步化”問題。這種“去同步化”既存在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也存在于人類社會各領域中。前者如人類消耗石油和耕地等自然資源的速度遠遠高于這些資源再生產的速度,后者如經濟轉變、科技發明的速度總是領先于政府決策的速度。從功能性質上看,“去同步化”已經引發社會各種系統性的功能失調,如政治失調、經濟失調、文化失調等,并有可能最終導致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斷裂,削弱、破壞現代社會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因而極其有害和危險。在此,羅薩不僅論證了全球氣候變暖、現代人的抑郁癥與“去同步化”的密切關系,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期現代社會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存在的“去同步化”及其危害。在政治領域,民主是一個非常耗費時間的過程,民主的民意形塑和決策的速度遠慢于社會變遷、文化變遷和經濟變遷的加速過程。因此,政治與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之間明顯存在著“去同步化”。這使“政治操控”在晚期現代成為社會變遷的障礙,而在早期現代和古典現代它曾是推動社會變遷的工具。這也是晚期現代政治功能失調的反映。在經濟領域,羅薩認為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就源于金融領域投資流動、資本流動與生產、消費之間步調的極其不一致:經濟或金融可以無止境地加速,而生產和消費卻不能。在文化領域,文化規范和知識的傳承也是一個耗費時間的過程,反映了社會世代之間的穩定性與持續性。但是社會生活的快速變遷,使世代之間生活于“不同的世界”,從而破壞了世代之間的穩定性。此外,不斷追求創新與變動的現代社會還會從根本上損害創新能力與創造性的適應能力,在“表面上過度動態化的晚期現代社會背后,出現了一個最僵固的硬化、凍結形式”。〔14〕
規范批判包括道德批判和倫理批判,羅薩比較側重于后者,并集中于兩個方面。第一,社會加速違背了現代性對自主性的承諾。羅薩認為,讓個體實現自主性既是“現代性的計劃”,也是“現代性的承諾”。原則上,社會加速與自主性應該相輔相成,因為個體要實現自主性,“必須得超越穩固不變的社會秩序,不讓社會階級或社會身份(以及政治威權和宗教威權)終身固定下來,也不要讓社會階級或社會身份就這樣一代接著一代地再生產下去”。〔15〕由此加速被人們視為一種解放的力量,一種可以實現自主性的手段。但是社會發展現實表明,在晚期現代社會,至少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當中,人們發現社會加速不再是一種解放的力量,而是變成了一種奴役人的力量。同時,社會加速不再保證個體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也不再保證社會能夠根據正義、進步、永續等觀念進行政治改革。這意味著承諾賦予個體自主性的“現代性的計劃”與社會加速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社會加速對現代性的核心觀念起了否定作用。第二,社會加速造成新的異化。羅薩在這里所說的新異化,是相對于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而言的。羅薩把馬克思所理解的異化概括為五個方面:人與自身行動(勞動)的異化、人與自己生產的產品(物)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人與他人(社會世界)的異化、人與自我的異化。羅薩認為,晚期現代社會加速已經使人類的異化不再局限于上述五個方面,又出現了新的異化形式。由此在馬克思異化概念的基礎上,羅薩提出了一種新異化觀。
按照羅薩自己的分析,這種新異化觀之“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異化概念本質的重新界定。與馬克思一樣,羅薩也把異化定義為一種負面的關系,但他認為這種負面關系表達的是自我與世界之間關系的深層、結構性的扭曲,特別強調“我們并不是與我們的真實內在本質產生異化,而是與我們吸收世界的能力產生異化”。〔16〕從這可以看出,羅薩所理解的異化是一種能力異化而非馬克思意義上的人類本質異化。他完全接受了當代德國社會批判理論家拉埃爾·耶基的建議,即重新引入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不需要再回過頭去處理人類本質或人類本質概念。二是對異化形式的重新歸納。羅薩把社會加速造成的異化概括為以下幾種形式:空間異化、物界異化、行動異化、時間異化、社會異化與自我異化。空間異化主要表現為社會相關性與空間鄰近性之間的脫節。物界異化是指我們自己生產和消費的物本應該是我們日常體驗、身份認同、生命史的一部分,標志著我們的個人特質,但社會加速使人類沒有時間去好好了解這些物,人類與它們處于相互疏離中。行動異化就是我們所做的事并不是我們真的想做的事,所有人都被“要事清單”的工作所支配。時間異化表現為社會加速使經典的“體驗短/記憶久”或“體驗久/記憶短”的時間體驗和記憶模式變成了“體驗短/記憶短”的模式。羅薩認為,上述四種異化必然導致我們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破壞,使所有我們所經歷的行動時刻和體驗時刻,所有我們的抉擇,我們所認識的人,我們需要的物等確立我們身份認同的素材,無法好好地被吸收進我們的生命當中,我們也就無法確切形成我們自己的人生故事,最終造成“自我耗盡”。
深入思想實際,我們會發現,羅薩對新異化的批判性分析并沒有超越馬克思的異化批判理論。首先,他對異化概念的理解,用他自己的話說,“還相當模糊不清,也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哲學方向的意涵”。〔17〕這使他不可能像馬克思那樣從人類本質高度把握異化的“真正的意義”。正因如此,羅薩對異化的理解顯得過于泛化,甚至認為有些異化形式是人們想要的、不可避免的,所以“任何想把異化斬草除根的理論或政策,都必然是危險的且潛在地是極權的”。〔18〕這意味著有些異化的存在是合理的,不用消解、沒有必要克服。這與馬克思的觀點完全對立。其次,他所發現并歸納的新異化形式,并沒有超出馬克思所理解的范圍,即使是他自認為很有新意的空間異化、時間異化,在馬克思那里也都有論述,只不過沒有直接表述為空間異化或時間異化而已。最后,他的異化批判也沒有達到馬克思異化批判的深刻性、徹底性。羅薩雖然把異化概念重新引入了社會批判理論,但他對異化的批判更多基于對具體的異化現象的經驗性描述,而非本質高度的理論性分析。另外,他把異化的直接原因歸結為社會加速,又把社會加速的動力概括為社會“競爭”、“永恒的應許”、“加速循環”等,但卻沒有進一步追溯它們的“最高因”。因此,他的異化批判并沒有上升到社會制度、生產關系批判的唯物史觀高度,他所提出的解決異化的可能方案,即建立主體與世界相互回應、充滿“共鳴”的社會關系,也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這些恰恰從反面說明馬克思的異化批判理論在當代依然具有其他批判理論所無法替代的價值,值得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