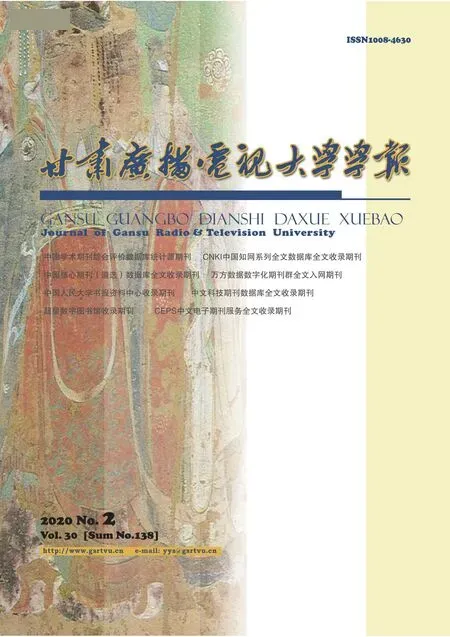文化匯融:絲綢之路的美好樂章
韓文奇
(甘肅廣播電視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曾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為世界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宗教、藝術、科技等許多方面。古絲綢之路保存至今的諸多文化遺產,留下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匯融的歷史印記,對于當代世界的人文交流與合作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本文不揣鄙陋,擇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加以論析,并就正于方家。
一、敦煌文化——絲綢之路東西文化多元共生的典范
絲綢之路為各種文明形態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展示與表現的平臺,東西方世界的文化在這個大平臺交流匯融,互鑒共生,博大深厚的敦煌文化是一個典型代表。
敦煌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交融之地。敦煌文化也是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的代表,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典范。如飛天形象是莫高窟壁畫中的典型藝術形象,與洞窟創建同時出現,在不同歷史時期又各具特色。飛天形象源自印度,有人認為就是乾闥婆、緊那羅,是佛國世界里的天歌神(又稱香間神)和天樂神。莫高窟現保存有十六國時期到元朝歷代所繪飛天6 000余身。早期洞窟(如北涼275窟)中的飛天,頭有圓光,戴印度五珠寶冠;或頭束圓髻,上體半裸,身體呈“U”形,雙腳上翹,姿勢略見笨拙,帶有印度石雕飛天的痕跡。北魏時期,飛天逐漸向中國化轉變,但仍有明顯西域樣式和風格,體態健壯,略呈男性特征,飛動感不強。西魏到隋代,完全中國化意義上的飛天藝術逐漸形成。隋代飛天一掃呆板拘謹的造型姿態,身姿與飄帶完全伸展,體態輕盈、簡練流暢[1]。唐代是莫高窟飛天藝術的高峰,也是其定型化的時代,完成了中國化、世俗化、歌舞化的歷程。敦煌飛天是多種文化的復合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
莫高窟藏經洞保存了四萬余件十分珍貴的文書。這些文書中有關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不同宗教的文獻或記載,以及為數不少的非漢語文獻(或稱“胡語文獻”),都可視為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匯融的典型例證。藏經洞里的非漢語文獻主要有吐蕃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等。回鶻文文書有50多件,內容包括書信、賬目和佛教文獻,對研究回鶻的歷史和文化有重要價值;于闐文文書有30多件,內容包括佛教典籍、醫藥文獻、文學作品、使臣報告、地理文書、公私賬目等;粟特文文書有20多件,內容主要是譯自漢文的佛教典籍[2]16。
絲綢之路上的宗教交流非常活躍,不同宗教思想在相互競爭中不斷傳播,分化融合,興衰起落。摩尼教、祆教、景教都來自西亞。摩尼教曾在北非、歐洲、西亞、中亞等地傳播,經由中亞傳入中國,在唐代曾流行了一段時間。該教被唐統治者取締后,漢文經典均散失[2]48。藏經洞文書中保存了三種漢譯摩尼教經典,即《摩尼教殘經》《下部贊》《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是研究摩尼教在中國流傳情況的重要資料,一向為研究者所重視。藏經洞文書中沒有保存祆教經典,但一些有關祆教的記載頗為重要。學者們通過釋讀敦煌長城烽燧下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已確知祆教在公元4 世紀初就由粟特人帶到了中國。從藏經洞文書中,可以得知唐朝時沙州城東有祆祠。敦煌歸義軍官府的支出帳中,記錄有“賽祆”的支出,如P.3569《光啟三年(887 年)四月歸義軍官酒戶龍粉堆牒》記有:“四月十四日,夏季賽祆,用酒四甕。”說明歸義軍時期祆教仍在敦煌流行。而且,敦煌的祆祠賽神已是民俗化的祭祀祆神活動,從中可見出祆教對中國文化的一些影響。
唐代稱基督教聶斯脫利派為景教,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記錄景教歷史的最重要文獻。藏經洞文書中保存的《尊經》《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等漢譯景教經典,是研究景教儀式和教法的重要資料。在莫高窟北區洞窟中,還發現了兩頁四面完整的敘利亞文《圣經·詩篇》,該文獻與元代漢文文書、西夏文佛經及回鶻文殘片同時出土,增加了蒙元時期景教傳播的佐證[3]。芮樂偉·韓森稱藏經洞是“記錄絲路多元文化的時間膠囊”,“代表了對不同宗教的包容,而這正是絲綢之路這段近千年歷史的突出特征”[4]303。他分析到:“藏經洞中的宗教文獻顯示,敦煌人對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驚嘆。保存這些文書的僧人不一定知道文書所用的語言,很可能也讀不懂這些文書,但他們還是愿意把這些文書保存好。這體現了絲綢之路國際化的特色。”[4]231此論頗有見地。
敦煌不僅留下了十分豐富的精神文化交流的遺跡,也有技術和物質文化交流的例證。如唐太宗曾派人到摩揭陀國學習印度的熬糖法,敦煌寫本P.3303 是有關五天竺制糖法抄本,涉及制糖法的許多方面,表明敦煌人對異域技術的認知。在吐蕃和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賬目中登記有許多西方來的物品,如高檔織物、刺繡、金銀器、寶石、香料、珍稀藥材等,大體反映了絲綢之路帶給敦煌的豐富物質文化[5]63。
又如,新疆吐魯番也是絲綢之路上多元文化交匯融合的典型地區。在吐魯番的出土文獻中有17種文字和24種語言,是絲綢之路上發現語言與文字最多的地方。文字包括梵文、怯盧、漢文、印度婆羅迷文、于闐文、焉耆—龜茲文、吐蕃文、突厥文、粟特文、敘利亞文、摩尼文、契丹文、西夏文等。每一種語言與文字都承載著一個民族的特有文化,眾多的文字、語言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吐魯番多元文化匯融的情況[6]。歷史上,來自中原和粟特地區的移民曾構成吐魯番的最大聚落。居住在吐魯番的漢人無論男女都會跳胡旋舞,粟特人則稱這個城市為漢城[4]107。麴氏高昌時期(502—640年),高昌(今吐魯番)完全接受了漢人文化,模仿中原的官僚體系,以漢語為行政語言,扶持佛教。學生學習漢文經典,也將這些經典翻譯為本地語言如龜茲語或粟特語[4]117。1959年以來,考古學家在吐魯番阿斯塔納和喀喇和卓共發掘墓葬465座,其中205座有文書出土,有2 000件之多,其中最早的文書是273 年的一份漢文契約,記載了一件20 匹練換一口棺材的交易[4]116。477 年的一件文書列出了招待幾個國家使節的花銷,有中亞的柔然,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子合國(今葉城),中原南朝的劉宋,北印度的烏萇國[4]120。584 年的一件文書是最早提到薩珊銀幣的一份租約,記載了用五枚銀幣租一畝地[4]121。凡此種種,大體可以見出某一歷史時期吐魯番文化的多元交匯特色。
二、粟特人——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匯融的重要見證者
粟特人是中世紀絲綢之路貿易的主要力量,隋唐時期成為中國與中亞等地區文化交流的重要溝通者。粟特人的聚落構成了中西關系的豐富內容,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主要轉運商,他們把西方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宗教、音樂等)輸送到中國,同時,把中國的商品轉送到西方”[7]73-79。粟特人的活動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匯融的生動情狀。
中國史籍稱粟特人為昭武九姓、九姓胡等。粟特人本土位于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主要范圍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粟特地區分布著一些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其中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康國最大,此外還有安國、曹國、何國、史國等。他們長期受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制,但保存了獨立的王統世系,成為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獨具特色的商業民族。
漢唐之間,粟特人沿絲綢之路大批東行,許多人移居中國。斯坦因1907 年曾在敦煌西北的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個郵袋,內裝八封用粟特民族的文字寫的信件,其中五封相對完整,學界稱之為“粟特文古信札”。研究者指出,這個粟特商團以姑臧(武威)為大本營,活動范圍東到洛陽、鄴城,西到撒馬爾罕,經營的商品有黃金、麝香、胡椒、樟腦、麻織物、絲綢、小麥等。這組書信寫于西晉末年(312年前后),反映了當時粟特商團在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5]66。芮樂偉·韓森認為:“這些信件表明,早在四世紀早期,洛陽、長安、武威、酒泉和敦煌就存在粟特部落。第二封信提到一個四十人的粟特定居點,在另一個地方有一百個來自撒馬爾罕的‘自由人'(兩處地名都缺失了),洛陽的定居點有粟特人也有印度人。當粟特聚落達到一定規模(也許40 人)的時候就會建一座火廟。薩寶負責宗教儀式,即看護火壇、主持祆教節慶、判案,等等。”[4]151
“薩寶”還音譯為“薩保”“薩甫”等,意譯為“商隊領袖”。薩保(薩寶)是粟特人建立的胡人聚落的統治者,由于大多數早期東來的粟特人信奉的是粟特傳統的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拜火教),故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薩保就成為政教大首領[5]68。為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北朝、隋、唐時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以薩保為一級職官,并設立薩保府,設“祆正”“祆祝”“長史”等官吏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務。“在漢文史料中,無論是在北朝、隋、唐實際擔任薩保或薩保府官職的個人,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記載的曾任薩保的其曾祖、祖、父,基本上都是來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5]69粟特人以移民聚落為支點,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為東西方物質文化的交流增添了許多色彩。粟特移民除了經商,也有不少人成為手藝人,還有人種地、做獸醫或當兵,他們將自己的宗教信仰、藝術以及生產技藝等也都帶到了各地。
西安北郊發現的安伽墓和史君墓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薩保及粟特人聚落的歷史記載,也是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匯融的一個重要例證。安伽墓和史君墓都是北周末年粟特墓葬。安伽墓是2000年發掘的,被評為2001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這是一座漢式斜坡墓道洞式墓,墓志為漢式形制,墓門楣的彩繪則融合了胡漢兩種元素。墓室當中有一張圍屏石榻,圍屏上刻繪有12 幅圖。其中有安伽和一名女性坐在一座漢式建筑中,有三幅胡旋舞的場景,有馱著貨物的駱駝,等等。據墓志,安伽祖上來自安國,后遷至涼州。生于537年,父親是粟特人,母親可能是漢人。安伽先在同州(今大荔)做薩保,后做到了薩保的最高官階[4]184-186。史君墓是2003 年發現的,也是一座漢式斜坡墓道洞式墓。史君墓志左半為漢語,右半為粟特語。兩份墓志都敘述了史君一生的事跡,但并非同一文本的翻譯。墓志記載史君與其妻同于579年去世,育有三子,曾任涼州薩保[4]186。
1970 年,曾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兩個陶罐和一個銀罐,三個罐子裝有千余件金銀器、寶石、藥材與錢幣,是珍貴而精美的絲路文物。其中的粟特式帶把杯和粟特式銀杯都相當精致,具有典型粟特風格。如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杯腹呈八瓣花狀,狩獵圖和仕女圖交替飾于杯腹八瓣。而多數金銀器則巧妙結合了胡漢藝術風格,很多器物能見出漢式特點。研究者指出:“粟特金屬匠移居中國并安定下來之后,便開始制作與他們在家鄉所做類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器物。他們學習漢式圖案并按照客戶的需求做出調整,制出許多胡漢融合的物品。”[4]198許多金銀器結合了中西特點。
粟特人在新疆地區的塔里木盆地也建有許多聚落。敦煌寫本S.367《沙州伊州地志》殘卷中記載粟特移民聚落的形成: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更名鄯善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磧(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隸沙州)。這條材料反映了粟特人在西域定居的一般情狀[7]73-79。吐魯番的移民中也以來自撒馬爾罕的粟特人最多。絕大多數粟特人都用康、安、曹、何、米、史、石等七種漢姓,很多生活在吐魯番的粟特人采用了漢式葬俗。可以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粟特人為絲綢之路的多元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
三、佛教東傳——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織共存的千載音詩
在絲綢之路上,佛教、基督(景)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三大宗教都有長時期的交流,印度教、薩滿教、道教、襖教、摩尼教等宗教形態也有過興盛的局面。這些宗教的相互傳播、沖突與融合,使得人類的各種信仰的觀念、形態等得以展開,從而持久影響了絲綢之路沿線民眾的精神信念,這是絲綢之路文化的重要特質[8]。
佛教文化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具有代表性。東傳的印度佛教首先傳入西域,再由西域傳入中原內地。坐落于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于闐(今新疆和田)是佛教東傳的重要樞紐,“公元200年,佛教徒首次從印度來到這里。之后的八百年中,佛教不斷向東傳播并成為中原地區最重要的宗教,其間于闐一直是研習、翻譯佛教文獻的重鎮”[4]254。坐落于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的龜茲(今新疆庫車)也是佛教興盛的地區。“漢文史料表明300年時,龜茲(庫車)有一千所佛教寺院和神廟,4世紀龜茲已成為重要的佛教教育中心。”[9]74-80克孜爾石窟是佛教藝術的一顆明珠,石窟壁畫中的龜茲人體藝術,吸取了希臘和犍陀羅藝術的特點,有很多呈半裸體形態,描繪佛教故事和世俗生活,展示了文化的交匯與創新。
東漢初年是佛教正式傳入中原之始,此觀點多為學術界認同。早期的西天取經不是印度而是西域。漢明帝派遣蔡愔等人去西域訪求佛道,在大月氏國遇到沙門迦葉攝摩騰和竺法蘭等,從西域求得佛經、佛像,用白馬馱回洛陽,并建起第一個寺院。“到了東漢末年,隨著大批有著雅利安人血統的大月氏人涌入京都洛陽,建立佛寺,同時帶來了印度的貴霜文化,影響到了皇室和貴族們的世俗生活。史稱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之貴戚,皆競相為之。”[9]74-80佛教作為異域文化給中原傳統文化帶來了許多新的氣息,在傳入的早期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盡量與中原傳統文化接近與融合,以適應新環境,并得以生根滋長。
佛教初傳中土時,以親近、模仿道家為主要手段。翻譯佛典則用老莊經典“格義”,造作佛像往往老子與釋迦牟尼共尊共處。佛教徒們刻意模糊與道教的界限,佛教中的道術、法術以及奇異故事,與道教的神仙思想、仙人故事附會連類。通過翻譯佛本生故事,以及創作大量靈驗故事,宣證佛教的法力,渲染得道僧人的神奇法術。中土更有《老子化胡經》問世,言老子出關西行至天竺,收釋迦牟尼為徒,宣稱道與佛為師徒關系。佛道交融,給中華傳統的仙人、俠客故事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增益了其道術和機變的內容,且頗富想象力、神妙性。
在佛教的傳播交流中,中外僧侶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如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天竺人鳩摩羅什東行譯經講法,唐玄奘法師西行尋求“真經”“真法”等。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僧侶往來于東西各國。眾多僧侶東來西行,弘法傳道,對佛教經籍的流傳,對古代東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鳩摩羅什是將佛教大規模傳入中原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佛教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其父是流亡到龜茲國的印度貴族,其母是龜茲國的公主。羅什七歲出家,九歲起隨母游學西域諸佛教國,十二歲就以精于佛學聞名。前秦建元十八年(382 年),呂光破龜茲,虜持羅什至涼州。前秦滅,呂光建立后涼,羅什滯留涼州十六七年。后秦弘始三年(401 年),后秦滅后涼,迎羅什到長安,待以國師之禮,主持翻譯佛經35 部294卷。所譯經論內容信實,文字流暢,在中國譯經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佛教的傳入及其本土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顯示了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匯融通的重要意義。
在絲綢之路的時空坐標中,眾多民族之彼此親和,多種宗教之交織共存,異質文明得以系連、對話與交流。今天,尊重文化的多樣性,意味著“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價值選擇,努力超越偏見與誤解,消解矛盾與爭端,克服沖突與隔閡,在平等相待中交流對話,在開放包容中互學互鑒,在深化互信中共謀發展”[10]。在新的歷史時期,傳承創新絲路文化,更應著力倡導開放包容,彼此融通,多元共生,這也是絲綢之路文化的當代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