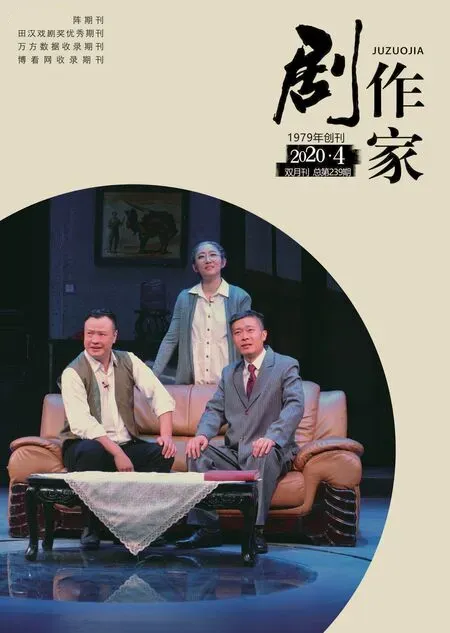中國民族舞蹈發展路徑探析
■ 張文龍
民族舞蹈是中國舞蹈體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它有著舞蹈藝術本身的共性特征,可以通過舞者肢體上具有節奏韻律的不同表現,用抑或柔韌、抑或陽剛的舞蹈語匯去達到敘述情境、抒發情感、烘托氣氛的目的。同時,民族舞蹈也有著自身獨有的審美特征,在表現的形式和風格上都有著非常明顯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彰顯了各民族文化的特色與風情。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藝術形式“多元化”的趨勢愈加迅猛,民族舞蹈在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的同時,也面臨著很多挑戰,如何充分發揮民族舞蹈的優勢,更好地去發展它的未來,已成為值得探討的話題。
一、深挖地域性
民族舞蹈的形成是與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習慣密不可分的。某一個具體地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民族舞蹈的風格化和成熟度,因此地域性是民族舞蹈最本質的特征之一。比如藏族舞蹈中那種連續不斷、步伐細碎、頻率較快的動作,以及身體動作上較為規律的顫動和弓背屈伸間的無縫切換,在松弛中將西藏地區的愜意和美感展現得活靈活現,有著明顯的西藏地域特點。再比如從最古老的祭祀儀式發展而來的東北秧歌,它的表演形式較為簡單直接,一直以來,載歌載舞、唱跳結合始終是它的標識。東北秧歌巧妙地運用頸、腕、腰、胯、臀的翻動和扭動,構成舞蹈姿態的曲線美。動作開闔幅度較大,能夠充分表現出東北女性潑辣豪爽卻不失嫵媚的特點,以及東北男性質樸粗獷又充滿陽剛之氣的性格。由此可見,不同地域的民族舞蹈呈現出來的審美特征與孕育它的土地有著直接的聯系。所以,民族舞蹈要想被更多的觀眾所喜愛,進而走向更為寬廣的道路,就一定要對地域性進行深入的探索與挖掘。因為地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每一地域的人民都有著不同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盡管地域文化有著各自根深蒂固的屬性,但從發展的態勢來看,地域文化也是動態行進的。比如,法舞《羌姆》歷史上始終堅持在寺院內由喇嘛僧侶表演的原則,但為了適應新時代宗教與世俗關系的改變,現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就將它和民間歌舞放在一起表演了,提高了藏舞表演的娛樂性和大眾性。
二、強化民族性
民族性可以說是民族舞蹈誕生的源泉。一個民族最為原始、最為典型的特性在其民族舞蹈中都能找到根源,還能窺視到以此為基礎的藝術化變型展示。這也是很多即使不了解民族舞蹈常識的觀眾,在聽到音樂響起的那一刻,在看到舞蹈動作開始的瞬間,便能立刻判斷出這是哪一個民族的舞蹈的根本原因。比如,歡快的俄羅斯舞蹈,含蓄的日本舞蹈,狂歡似的巴西桑巴舞……在這些辨識度極高的民族舞蹈身上都打著強烈的民族印記,同時也飽含著極具民族性的情感表達。從我國來說,隨著業界舞蹈觀念的更新和舞蹈本體意識的覺醒,我們的民族舞蹈更加側重于塑造真實而鮮活的舞蹈意象,在抽象的舞蹈意象中濃縮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民族性格。簡言之,我們的民族舞蹈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每一處精致的舞蹈編排無不透露出專屬于我們民族的文化與積淀。舉一個最易于被理解的例子,傣族的“孔雀舞”那優美的“三道彎”造型,將孔雀的各種姿態模仿得惟妙惟肖,更讓觀眾記住了舞蹈所反映出來的傣族人民的善良勤勞,還有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那份恬靜與美好。這也是應在民族舞蹈中不斷強化民族性的道理。
三、提升技巧性
無論是地域性還是民族性,無論是情感的表達還是個性的抒發,歸根到底都離不開舞蹈藝術的呈現,更離不開舞蹈技巧的運用。舞蹈技巧是蘊藏在舞蹈的律動中,隱藏在舞蹈的情節中的。合理運用高超的舞蹈技巧,可以使舞蹈作品擁有更豐富的內容與內涵,更具創造力與吸引力,同時也可以使觀眾擁有最佳的視聽體驗,給人以美的享受。我們之所以說民族舞蹈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也在于其技巧的不斷提高與更新。只有不斷提高舞蹈的技巧性,才能實現舞蹈動作的創新、舞蹈節奏的轉變和舞蹈隊形的別出心裁,才有誕生新的民族舞蹈樣式的可能。舞蹈和所有的藝術門類有著相通之處,即它雖然具有很強的地域性與民族性,但它仍然歸屬于世界舞蹈體系的范疇,對舞蹈技巧提高的追求是民族舞蹈終身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