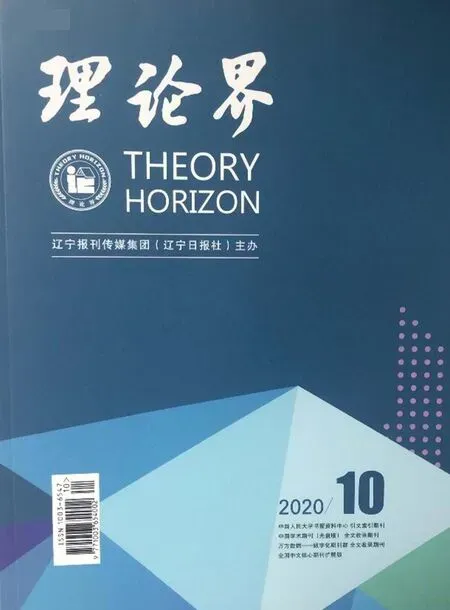列維·斯特勞斯神話理論的語言學淵源探析
斯竹林
列維·斯特勞斯開創了神話研究的新紀元。正如韋爾南所說:“在列維·斯特勞斯之后,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具體破譯工作上,情況都不一樣了,他的工作標志著一個轉折點和一個新的起點。對于他的對手、跟隨者和那些同行來說,神話研究現在不僅面臨著新的問題,而且即使用同樣的術語也不可能提出舊的問題。”〔1〕
韋爾南的稱贊并非夸大其詞。在列維·斯特勞斯之前,學者們的神話研究往往停留在外部,將對神話意義的分析引向共同的情感驅動力,或集體的夢,或宗教儀式,或社會文化背景,這會讓神話的本質和特性淹沒在文化遺留物、集體無意識、儀式或功能主義中。為了避免上述研究的弊端,列維·斯特勞斯將結構語言學的視角、原則、方法、理念擴展到神話研究中,將神話研究引向神話內部,并對結構語言學中的元語言、區分性特征、語言的不變性、能指與所指有具體運用。本文擬從神話學的研究視角,對其神話研究中所呈現出的對結構語言學的擴展加以描述和總結,以期為當代的神話研究提供些許有利的學術資源。
一、神話的“元語言”探尋
結構語言學對列維·斯特勞斯神話研究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神話敘事層面和結構層面的劃分上。列維·斯特勞斯將神話研究分為顯性的敘事層面(在敘述中直接表達的故事意義)和流動的文本背后恒久的結構層面(隱藏和不自覺的非敘述意義)。神話的敘事是流動的,但背后的結構卻是穩定的。
這種分層觀念來自結構語言學中言語和語言的劃分。索緒爾首先區分了語言與言語,提出語言是言語活動的確定對象,是社會的。而言語是個人的、流動的。結構語言學家要“站在語言的立場上,把它當作言語活動的其他一切表現的準則”。〔2〕語言是詞、慣例和語法的完整體系,它不是個人創造的,而是“已有的”。當個人發音時,會從語言系統中選擇詞匯、語法和語調音調,并按特定的秩序將它們排列起來以傳遞信息。言語是由音素組成的代碼,結構語言學家的任務是解碼,從流動性的言語中尋找穩定的語言結構,研究組織語言規則和構造方式,而不是個體說話方式。
在此基礎上,雅各布遜并提出語言研究應區分兩個層次——“談論語言之外事物的‘對象語言’(Object Language)和談論語言代碼本身的……‘元語言’。”〔3〕結構語言學的任務是要把語言社團中客觀的代碼轉化為元語言。
語言是神話由以開始的基礎,因此,列維·斯特勞斯從結構語言學視角劃分神話的結構。神話在講述時,沿著不可逆的時間軸展開句法序列,所以它是言語。可神話又是一種超時間的存在,它的敘述模式不受時間限制,能說明現在、過去和將來。它由不同元素有序組織成一個共時性的結構系統,以構成人們自覺遵守的讓故事產生的符號(語義)空間,因而它又是語言。
更進一步說,神話是更高層次的語言。神話的實質不在于文體、敘事方式或句法,而在于故事。神話由此脫離了它由以開始的語言基礎。神話“‘超結構地’使用語言形式,可以說,它們形成一種‘元語言’,其中結構在一切層次上起作用”。〔4〕正是這種元語言的特性使神話與其他文體相區別。神話的規則與詞所塑造的形象和描述的行動,不但是語言層面上的“常規能指”,還是另一個層次的意義系統的意義成分。于是,“國王”不僅僅是一個國王,“牧羊女”也不僅僅是一個牧羊女,而是詞和其所蘊含的所指構造對立系統的手段,這個由理智形成的對立系統包括陽/陰(從自然方面看)和尊貴/低賤(從文化方面看)以及在這六個術語中間的一切可能的置換。
神話的結構研究是解碼的過程,即要尋找這種“元語言”,即一種公開的意識背后隱藏和不自覺的深層思維結構。他相信,神話素組合關系的數量不是無限的,也不是人類憑空創造的。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從有限的思想庫存中選取特定的組合。通過神話的結構分析,能夠建立人類思想的“元素周期表”。
同時,“元語言”不在單個的神話之中,而在整個神話系統之中,個別的故事是系統中的單位語符列。神話對應著聽眾內部的“心理——生理”時間,對神話的理解,往往不是由發出者,而是由聽眾決定的。只有當聽眾的心智可以隨著故事的展開審察全部故事時,才能領會神話的含義。“神話和音樂作品都像是管弦樂隊的指揮,聽眾則成為沉默的演奏者。”〔5〕年長的社會成員,集體無意識地向年輕成員傳達神話的音訊。當接受者領會了每一個音訊的意思,并將它們放在一起進行解讀時,就會領會神話的含義。列維·斯特勞斯將單個神話比作一次演奏,將整個神話系統比作管弦樂隊的樂譜。人類的祖先集體向后代無意識地傳達了單個音訊,結構研究者通過了解神話中對立而又混合一處的人、動物、精靈、神的相對位置,解碼原初樂譜的形式。
二、從“區分性特征”到神話二元結構
在對神話的結構關系的解碼中,列維·斯特勞斯受到索緒爾結構語言學基本原則的影響:語言符號“不是通過它們固有的價值,而是通過它們相對的位置”來起作用的。〔6〕語言是封閉、自足的結構系統,語言的意義要在語言系統中找尋,單個語言符號的價值在組合關系中得到確證,如果只是孤立地考察元素,是得不到什么結果的。
雅各布森在音位的“區分性特征”分析中將相對關系發展為二元對立關系。“對立項在數目上是兩個……對立雙方聯系緊密,一方的出現不可避免地會引出另一方。”〔7〕在他看來,復雜的音位系統是對簡單音位系統的多維度發展,這種簡單音位系統——輔音和元音之間的對照——適用于所有的語言。幼兒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首先通過辨別音量的對立關系,認識基本元音和基本輔音的對立關系。再通過聚集與分散(Compact/Diffuse),銳音和鈍音(Grave/Acute)的二元對立產生“元音三角”和“輔音三角”。
列維·斯特勞斯將這種二元對立觀念直接運用到神話研究之中。在“結構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結構分析”中,他首次用結構語言學的三角結構分析人類的婚姻模式,提出了以交換與不交換,接受與給予兩個對立面產生的互惠(Reciprocity)、權利(Rights)和義務(Obligations)的三角。〔8〕
之后,他將此方法運用到神話的結構分析中。為了尋求神話文本背后永恒的結構,列維·斯特勞斯提煉出神話的基本情節,每個基本情節都是人物與個人特征之間的“關系”,或是人物與眾不同“狀況”。他將情節濃縮成的簡單關系(或狀況),稱作“神話素”(Mythemes,或大構成單元)。神話的意義并不在單個的神話素中,而在于神話素的組合關系中。
在神話學第一卷中,列維·斯特勞斯以自然與文化、常態(非人工商品)與變態(人工商品)的雙重對立繪制出“烹飪三角”,研究對立的感官屬性:生與熟、新鮮和腐爛、干與濕。在第二卷中,感官的對立被形式的對立取代:空與滿、容器與內容、內與外。在第三卷中,他又引入水和火兩個元素,將主要制作食物的方式(烤、熏、煮)組成與第一個形式相顛倒的結構形式。
在經典的“阿斯迪瓦爾的故事”分析中,列維·施特勞斯收集、分析和解釋了大量關于神話的文化和人類學的背景數據(人口遷移、經濟情況、社會結構、親屬關系),將植物、動物、事件和人群分類,確定了神話的結構框架。神話被分為地理的、宇宙學、社會的和技術經濟四個層次,每一個層次都有其符號意義,它們都被看作神話共有的邏輯結構的變化。地理圖示顯示出與玆姆申人捕魚路線一致的季節性遷徙,宇宙哲學圖示顯示出人們觀念中上下、天地、陸海的關系,社會學圖示顯示出隨夫居和隨妻居習俗的變換,技術經濟圖示顯示出捕魚的經濟活動。最后將四個層級加以整合,揭示出神話的整體結構:母系傾向和父系傾向之間的無法克服的矛盾。接著,在對變體的研究中,列維·斯特勞斯通過列舉東與西的對立、海與陸的對立、素食與葷食的對立、限制和不限制的對立,把地理學范疇的詞匯與食物范疇的詞匯結合了起來。他將不同的神話素看作同一個結構成分的置換,把對立神話素看作是由地理、習慣或功能不同而引起的倒置,從而把表面上的不同變體納入同一個結構體系之中。通過對神話進行結構層面的解讀,列維·斯特勞斯運用二元對立的手法,建立起隱藏在神話后的包括地理、宇宙觀、技術、社會經濟情況在內的復雜結構。
三、從語言的“不變性”到神話系統的自我界定性
列維·斯特勞斯認為,神話結構具有獨立性,它甚至可以操縱個人。他想說明的“不是去表明人如何用神話進行思維,而是去表明神話如何用人進行思維卻不為人所知”。〔9〕
神話的自我界定理念同樣受到結構語言學的影響。索緒爾認為,語言具有不變性,語言系統一旦形成和被使用,就不受個人主觀意志左右。“語言之所以具有穩固的性質,不僅是因為它被綁在集體的鎮石上,而且因為它是處于時間之中。”〔10〕語言既是歷史中形成的語言習慣,又對社會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又是特殊的社會契約,無法通過協商而更改。因此,語言系統獨立于人的主觀意志。
列維·斯特勞斯借鑒結構語言學的觀點,認為神話結構系統是封閉、自足的,具有自我界定的性質。首先,神話的元素取自于語言,受到語言系統的制約。列維·斯特勞斯將神話比作“理智的修補術”,神話思想借助結構性的語言,將個人和社會歷史中所凝結的事件碎屑拼合,建立起有結構的組合。它利用舊的社會性話語(原材料)闡發出新的意義(家具)。而神話的創造者為修補匠,神話(修補匠)的創作受到語言(零件)的限制。首先,符合神話意指形象的詞項本身是有限的。“神話思想的特征是,它借助一套參差不齊的元素表列來表達自己,這套元素表列即使包羅廣泛也是有限的;然而不管面對著什么任務,它都必須使用這套元素(或成分),因為它沒有任何其他可供支配的東西。”〔11〕其次,這些詞項在語言中已經具有了一種意義——它們必定不是單純的和單義的,卻也可以作為語義的或審美秩序中的不變項而存在,這些意義使其調配的自由受到限制。
同時,決定把什么語言成分置于神話結構的何種位置,也受到神話結構的制約。修補匠對組成神話的元素加以推敲,以便發現其中每一項能夠“意指”(Signifier)什么。元素可以放入不同的位置,但是所做的每種選擇都將牽扯到該結構的全面重新組織,這一結構的改組將不同于人們所構想的東西。神話意義的改變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與其說是人創造神話,不如說神話創造自身。
神話被創作或是被感知時,都要與神話系統發生聯系。個人和集體在創作神話時,總是受到神話系統在人們思維中的沉淀,即神話結構和規則的制約。換言之,神話系統的結構對具體的神話作品內容、語言、形式,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只有神話符合結構的規范,才能納入神話系統中,人們才把它當作是神話。破壞系統的規范的創新只能是低限度的,超過這個限度,人們或是無法理解它,或是把它歸入故事或傳說而不歸入神話的類別。因而是神話結構系統啟迪人們說出了神話,而誰來說出神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話體系的完整性通過說話者得到了證實。
從這個角度說,不是人創造了神話,而是神話通過結構和規則發展轉化并創造新的變體。但變體的產生與個人的創造相關。神話的創造者會在對有限的語言元素的選擇中,敘述他的個性和生活。因此,神話被無限地產生出來,每一個都與其他的略有不同。神話螺旋式地發展,直到產生神話的智力沖動耗盡為止。從獨立的神話結構出發,列維·斯特勞斯希望從結構意義上探尋人類的思維模式。
四、從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到神話對思維的濃縮
語言的轉變與人類的思維活動密切相關。索緒爾認為:“思想離開了詞的表達,只是一團沒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渾然之物……預先確定的概念是沒有的,在語言出現之前,一切都將是模糊不清的。”〔12〕語言不僅能讓人們進行交流,更是思考過程的基本要素。在思考之前,我們先要對事物分門別類,然后再用語言描述它們。這種分門別類的過程就是對意義劃分的過程。思想離開詞語的表達就是混沌一片的,語言是思想的媒介,是它讓聲音和思想結合,才導致各單位之間劃清界限。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這不僅指“能指”與“所指”之間任意結合,也是指人們以“能指”在混沌不清的意義連續體上任意地“劃分”出不同的“片斷”(所指)。
在此基礎上,列維·斯特勞斯提出,同語言一樣,神話是思想在生成邏輯架構時的濃縮。神話是通過故事(意象和事件)推進的,而故事大于詞和概念,所以它更明確地體現了人類思維活動的特征。當我們以神話去思考、整理和領悟周圍的意義世界時,也會將時間和空間的連續統一體切割成段,以探尋事物的分類和次序,而這種切分和排列的方式同樣會應用到對其他事物的思考中。
神話的創作者是思想的儲存者,他們將現實中的一切翻來倒去,將社會的、物理的、心理的概念嵌于神話的感性形象之中。人們既不將概念直接顯現,也不將之抽象化,而是將它們隱藏在具體物象背后。“我們在交易思想,他們則在儲積思想。野性的思維在實行著一種有限事物的哲學。”〔13〕這種思維方式被列維·斯特勞斯稱為“野性的思維”,它是一種直觀感性的思維,它借助知覺和想象,以持續不衰的好奇心改造自然、創作神話。
在索緒爾“能指”和“所指”互動關系的基礎上,雅各布遜以隱喻和轉喻描述了意義轉換的過程。“話語段(Discourse)的發展可以沿兩條不同的語義路線進行……一個主題(Topic)是通過相似性關系或者毗連性關 系 引 導 出 下 一 個 主 題 的。”〔14〕隱 喻(Metaphoric) 在于對類似的認識,轉喻(Metonymic)在于對鄰近的認識。隱喻和轉喻也體現在除語言之外的其他象征符號中,如弗洛伊德用轉喻(位移)和隱喻(冷凝)分析夢的結構,弗雷澤將巫術分為基于相似定律的模仿巫術和基于連續性關聯的傳染巫術。
列維·斯特勞斯將雅各布遜的“隱喻”和“轉喻”拓展到神話中。通過隱喻,神話中的超自然的世界——人、動物、精靈和神的關系組合得以被理解。列維·斯特勞斯認為,所有神話都隱喻了一個大主題:“從天性到教養的轉變,代價是永遠喪失與天空和大地交流的能力。”〔15〕通過轉喻,我們可以通過神話閱讀出某個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精神氣質,可以看到它縮影的世界的變化。神話是一面放大鏡,突出了慣有的思維模式。神話提供了一個思維框架,借此,人們對斗轉星移、晝夜交替、季節轉換的思考方式同樣可以運用到對社會組織、鄰近群體的政治關系的思考中去。
五、結構語言學的進展與神話研究的發展
早期結構語言學的缺失同樣出現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研究中。雅各布遜分析“區別性特征”時的刻板二元形式(反映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研究中),已經受到了許多結構語言學家的抵制。現代結構語言學家已經認識到,人類發出語言和接受語言的機制比雅各布遜的機制更為復雜。20世紀50年代喬姆斯基提出生成語法,認為人腦中存在先天的模塊或結構,人生來具有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語言研究的最終目的是通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揭示人腦的思維機制。從此,語言研究的重點從外在的語言行為轉到內在的語言能力。我國結構語言學者石毓智在解釋這種生物機制的本質和它與語言能力的關系時提出“語言能力合成說”,認為人類認知是層級系統,“語言能力不是一個獨立模塊,也不是處于認知系統最基層的,它是由更基本的認知能力協同合作的結果”。〔16〕語言能力依賴天生的認知能力(符號表征能力、對數的認識能力、分類概括能力等),在語言的結構和功能及非語言的技能和知識之間有密切的關系。生成結構語言學和認知結構語言學更加關心的是人類取得語言模式的生成規律,而不是“元音三角”和“輔音三角”中的語音本身。雅各布遜的區別性特征,無法揭示獲得語言模式的機制。同樣的,列維·斯特勞斯通過神話的結構研究,雖然揭示了一部分無意識思維過程的表現,但卻無法揭示人類思維的真正機制。
此外,雅各布認為“有一些簡單的關系是所有語言都具有的”,〔17〕列維·斯特勞斯也將從特殊族群中的神話中探尋的無意識的思維結構,作為全人類的共通的思維規律。將個別的神話看作是神話系統的單位語符列的。那么,索緒爾意義上的“口頭語言”——單個神話的特殊性和地方性在何處表現?它如何反映當地的文化?但列維·斯特勞斯不關心特定社會的集體意識,他追索的是人類思維的普遍結構,不僅適用于太平洋島岸的土著,也適合于所有語言的表達者。但語言不能離開社會事實而存在,它是符號現象,它的社會性質是它的內在的特性之一。神話同語言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性的,是所有講這種神話的人的集體意識的一部分。
列維·斯特勞斯以結構語言學對待音位的方式,將神話素從語境中抽離出來,無法對神話進行貼合語境和文化情境的結構分析。列維·斯特勞斯將神話看作語言的一部分,而神話素是根據音素作為參照物,從神話敘事的核心要素中提煉出來的。這似乎表明,即使沒有對產生神話的文明的深入了解,也可以解讀一個神話,除了神話自身提供的上下文外,它不需要在任何其他背景下進行。正因如此,在俄狄浦斯王的神話研究中,列維·斯特勞斯根據主題的相似性而分離神話素的過程,以及在神話矩陣中對神話素進行分類的過程也同樣武斷。
正如韋爾南所說,結構分析必須與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神話相關。他以希臘神話為依托,“分析萬神殿的結構,展示不同的力量是如何組合在一起、聯系在一起、相互對立和區別的。只有這樣,每個神或每一群神的相關特征才能出現”。〔18〕在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的基礎上,韋爾南以希臘神話為基礎,將神話的結構分成三個層次:首先是敘事形式分析,即表層結構的分析。其中包含形式的分析——對故事組成方式的分析,句法關系,片段在文本敘事中的聯系。也包含故事的語法——敘述背后的邏輯,建構在行動和反應之上的模型,情節變化背后的動力。第二個層次是語義內容分析。即通過建立對立或相似細節的情節網絡(時空、物品、行動、地點),破譯語義內容,定義按故事的語法建構的形式結構和在不同層面上的具體的語義內容。第三個層次是文化語境分析,即文化的特定形式產生和理解的符號空間。從神話中,可以獲得思維的特性及其分類的框架,并將它放置在思維和社會歷史的特定位置。〔19〕在神話的結構和情節中,每一個細節都具有精確的含義,在每一種情況下,都可以參照整個數據的其他部分來確認或反駁。希臘神話中體現的是希臘人的文化情境中會用到的元素:植物、動物、天象、飲食、社會、婚姻、性愛,神話的意義就存在于這當中,神話中所體現的思維模式與這些具體的元素相關。因此,在神話研究中,不應忽視具體的細節,這樣才能賦予文化和思維模式的獨特性。
六、結語
綜觀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研究,他對神話研究的視角、原則、理念和方法都有開拓和創新。具體表現為:(1)將神話研究引向神話內部,探尋神話的“元語言”。(2)將語言元素的系統分析發展為神話的結構分析。(3)受“能指”與“所指”的互動關系的啟發,探尋神話與人類的思維模式的深刻關聯。這種對神話研究的創新,與結構語言學的理論成果密不可分。
然而,通過以結構語言學作為探討途徑的神話結構研究,列維·斯特勞斯最終關心的是“人類思維”的真理,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會或社會組織。當他想深入探尋人類思維時,他以無意識思維的結構作為切入點,忽視了文化和思維模式的獨特性。
列維·斯特勞斯與韋爾南探尋的同樣是不同版本(或變體)的神話背后恒定的無意識思維模式,而不同的是,列維·斯特勞斯探究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話,最終是為了得出人類思維模式的普適性的結論,而韋爾南不是探尋人類的思維模式,而是古希臘人的特殊的思維模式。在韋爾南等一批結構主義學者的努力下,神話的結構研究逐漸摒棄對普適性的思維模式的尋求,而與特定的文化和思維模式相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