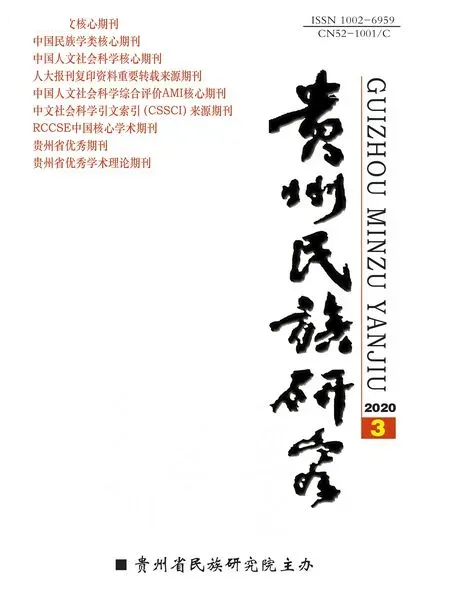蒙古族題材電影敘事方式與文化建構(gòu)研究
張瑞坤 南長(zhǎng)森
(陜西師范大學(xué),陜西·西安 710119)
愛(ài)德華·泰勒認(rèn)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義的民族學(xué)意義來(lái)說(shuō),是包括全部知識(shí)、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風(fēng)俗以及作為社會(huì)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xí)慣的復(fù)合體。”[1](P1)這個(gè)定義涵蓋之廣,包括社會(huì)規(guī)范、價(jià)值、信仰和表意象征符號(hào)等。從本質(zhì)上說(shuō),文化業(yè)是人類社會(huì)生活方式的符號(hào)系統(tǒng)。文化存在于物質(zhì)形態(tài)、意識(shí)形態(tài)以及與之相適應(yīng)的人們心理狀況之中,文化是描述為人們不斷賦予他們所見(jiàn)和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件的過(guò)程。斯圖爾特·霍爾曾提出大眾傳媒賦予意義之功能。電影作為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離不開(kāi)中國(guó)文化的照射。文化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映射,社會(huì)的真實(shí)生活也是一個(gè)文化建構(gòu)的過(guò)程。正如李普曼所言,個(gè)人僅通過(guò)大眾傳媒所建構(gòu)的情景來(lái)解釋和描繪世界。蒙古族題材電影是獨(dú)有的一種文化藝術(shù),其敘事方式也具有鮮明的時(shí)代特征。蒙古族題材電影在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建構(gòu)、美麗邊疆和日常生活呈現(xiàn)、民族認(rèn)同和草原文化表達(dá)以及聚焦個(gè)體和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等層面多維度發(fā)展,集中反映出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全人類的共同價(jià)值追求。
一、蒙古族題材電影概念的界定與發(fā)展簡(jiǎn)史
中國(guó)電影的百年發(fā)展歷程表明,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無(wú)疑是一道異彩紛呈、氣象萬(wàn)千的風(fēng)景線。學(xué)者王志敏曾提出,判斷一個(gè)電影是不是少數(shù)民族電影的標(biāo)準(zhǔn),即“一個(gè)根本原則(文化原則)和兩個(gè)保證原則(作者原則和題材原則)。
這說(shuō)明,文化原則、作者原則、題材原則是創(chuàng)作的生活基礎(chǔ)。饒曙光也曾總結(jié)過(guò)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電影概念界定的三種主流觀點(diǎn),即:“作者論”“題材論”和“演員論”。我們認(rèn)為能夠展現(xiàn)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地域特色的電影都屬于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范疇。依照這個(gè)邏輯,蒙古族題材電影可以界定為展現(xiàn)內(nèi)蒙古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地域特色的電影。從1942年第一部蒙古族題材電影《塞上風(fēng)云》到2019年內(nèi)蒙古重大主題文藝創(chuàng)作優(yōu)秀影片《海林都》的熱映,蒙古題材電影已經(jīng)走過(guò)77年的發(fā)展歷程。其中不乏有《內(nèi)蒙古人民的勝利》《天上草原》《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老獸》等多部電影先后獲獎(jiǎng),確立了蒙古族題材電影在中國(guó)電影史上的重要地位。蒙古族題材電影一方面以邊疆少數(shù)民族為表現(xiàn)對(duì)象豐富了影像表現(xiàn)區(qū)間,另一方面建構(gòu)了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想象,從而成為新中國(guó)政治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里將蒙古族題材電影的發(fā)展歷程主要?jiǎng)澐譃椤爸髁饕庾R(shí)形態(tài)時(shí)期”(1942-1976年)、“探索與發(fā)展時(shí)期”(1978-1990年)、“民族意識(shí)發(fā)展時(shí)期”(1991-2000年)、“關(guān)注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時(shí)期”(2001-至今)四個(gè)階段。即“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時(shí)期”的主要作品有:《塞上風(fēng)云》(1942)、《內(nèi)蒙古人民的勝利》(1950)、 《草原上的人們》(1953)、 《牧人之子》(1957)、 《草原晨曲》(1959)、 《鄂爾多斯風(fēng)暴》(1962)、 《金鷹》(1964)、 《沙漠的春天》(1975)等;“探索與發(fā)展時(shí)期”的主要作品有: 《祖國(guó)啊,母親》(1977)、 《蒙根花》(1978)、 《重歸錫尼河》(1982)、 《獵場(chǎng)扎撒》(1985)《成吉思汗》(1986)、 《騎士風(fēng)云》(1990)等;“民族意識(shí)發(fā)展時(shí)期”主要作品有: 《東歸英雄傳》(1993)、 《黑駿馬》(1995)、 《金色草原》(1997)、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1998)、 《活著,可要記住》(2000)等;“關(guān)注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時(shí)期”的主要作品有:《白魂靈》(2001)、《天上草原》(2002)年、 《嘎達(dá)梅林》(2002)、 《跆拳道》(2003)、《季風(fēng)中的馬》(2005)、 《圖雅的婚事》(2007)、 《心迷宮》(2014)、 《告別》(2015)、 《八月》(2017)、 《老獸》(2017)、《您一定不要錯(cuò)過(guò)》(2018)《海林都》(2019)等。這些作品說(shuō)明各個(gè)時(shí)期的發(fā)展呈梯次格局,是一個(gè)不斷演進(jìn)與發(fā)展的過(guò)程。
福柯曾指出:“在話語(yǔ)以外,事物沒(méi)有任何意義。”[2](P45)也就是說(shuō),“意義和意義實(shí)踐是在話語(yǔ)范圍內(nèi)被建構(gòu)的,任何文本、行為,只要在話語(yǔ)內(nèi)才能有意義。作為大眾文化工業(yè),電影與整個(gè)時(shí)代的文化環(huán)境及藝術(shù)生產(chǎn)體制有著密切聯(lián)系,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系統(tǒng)等多種社會(huì)力量都會(huì)積極地介入到生產(chǎn)當(dāng)中,因而每個(gè)時(shí)代的電影都帶有鮮明的時(shí)代特征。”[3](P15)蒙古族題材電影在不同時(shí)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征,是一個(gè)不斷演進(jìn)與發(fā)展的過(guò)程。其敘事方式呈現(xiàn)出國(guó)族化、景觀化民族化、個(gè)體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背后隱含著既定的時(shí)代風(fēng)潮和文化底蘊(yùn)。文化建構(gòu)是蒙古族題材電影必不可少的功能,反映了創(chuàng)作者對(duì)民族文化的一種情懷,而“多元一體化”的國(guó)家現(xiàn)實(shí),又決定了蒙古族題材電影進(jìn)行文化敘事的基礎(chǔ)。弘揚(yáng)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是文化建構(gòu)的核心內(nèi)容。
二、國(guó)族化敘事:以意識(shí)形態(tài)和政治需求為導(dǎo)向
國(guó)族化敘事可以理解為以表達(dá)意識(shí)形態(tài)和實(shí)現(xiàn)政治需求為導(dǎo)向,進(jìn)行話語(yǔ)表達(dá)的一種方式。其特征可以概括為意識(shí)形態(tài)屬性尤為明顯,同時(shí)還具有強(qiáng)烈的民族意識(shí)和高度的文化自覺(jué)。“歷史上的中國(guó)儒家講究‘詩(shī)言志’。最初的‘詩(shī)言志’原來(lái)的本意是指:載道和記事。也就是說(shuō),遠(yuǎn)古時(shí)代所謂詩(shī)本來(lái)是一種民族部落國(guó)家的歷史、政治性、宗教性的文獻(xiàn),并非個(gè)人的抒情作品。中國(guó)的政治屬于一種倫理政治,藝術(shù)作品當(dāng)中一貫強(qiáng)調(diào)‘成教化、助人倫’。電影屬于意識(shí)形態(tài)的文化產(chǎn)品和思想產(chǎn)物,電影本身也就可以擁有‘言志’方面的表達(dá)作用。”[4](P284)電影作為復(fù)雜的文化構(gòu)成,其屬性是多方面的,有時(shí)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電影是一種社會(huì)現(xiàn)象的反映,更是一定社會(huì)的上層建筑。1949年8月14日,中宣部在《關(guān)于加強(qiáng)電影事業(yè)的決定》中提出:“電影是藝術(shù)具有最廣大的群眾性與普遍性的宣傳效果,必須加強(qiáng)這一事業(yè),以利于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及在國(guó)際上更有力地進(jìn)行我黨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事業(yè)的宣傳工作。”
“統(tǒng)治階級(jí)的思想在每一個(gè)時(shí)代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shuō),一個(gè)階級(jí)是社會(huì)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zhì)力量,同時(shí)也是社會(huì)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P98)這進(jìn)一步說(shuō)明了精神力量是民族文化的推進(jìn)器。1942年的《塞上風(fēng)云》講述的是蒙古族與漢族共同抗擊日本帝國(guó)主義侵略的故事。新中國(guó)成立初期的第一部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題材的影片《內(nèi)蒙古春光》(后被毛澤東主席親自為其更名為《內(nèi)蒙古人民的勝利》),在周恩來(lái)總理的親切關(guān)懷下,該影片于1950年由東北電影制片廠完成拍攝并上映,1951年全國(guó)公演。該部影片的修改過(guò)程體現(xiàn)出黨和國(guó)家通過(guò)政策加強(qiáng)對(duì)電影事業(yè)的領(lǐng)導(dǎo),從而確定了電影首先是政治宣傳工具,具有教育觀眾的功能。蒙古族題材電影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現(xiàn)實(shí)政治需求的指向主要是建構(gòu)一種由各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體。安德森將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突出了“人為建構(gòu)性”的現(xiàn)代性特征,凸顯出民族建構(gòu)的文化意識(shí)層面。從這個(gè)層面來(lái)理解,蒙古族題材電影也是努力建構(gòu)這樣一種有關(guān)民族、國(guó)家的想象的共同體。
國(guó)族化敘事具有強(qiáng)烈的民族意識(shí)和高度的文化自覺(jué)。“從敘事學(xué)的角度來(lái)說(shuō),電影的故事空間和空間敘事分別是敘事中介和敘事方式,簡(jiǎn)單地說(shuō),敘事空間是電影中直接呈現(xiàn)的用于承載故事的視聽(tīng)空間形象,而空間敘事是指利用空間進(jìn)行敘事的行為過(guò)程。”[6](P21)影片《草原上的人們》體現(xiàn)了對(duì)農(nóng)業(yè)化運(yùn)動(dòng)的響應(yīng),導(dǎo)演將草原人民的話語(yǔ)納入民族國(guó)家話語(yǔ)建構(gòu)之中,將個(gè)人敘事升華到宏大敘事之中。影片《鄂爾多斯風(fēng)暴》的敘事風(fēng)格更是凸顯民族意識(shí),塑造了利用無(wú)產(chǎn)階級(jí)認(rèn)同來(lái)反抗敵人的故事原型。正如馬斯·沙茲所說(shuō):“電影的主要魅力和社會(huì)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屬于意識(shí)形態(tài)的,電影實(shí)際上在協(xié)助公眾去界定迅速演變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并找到它的意義。”[7](P353)再如影片《牧人之子》中蒙古族人民的正直、善良;影片《草原晨曲》中呈現(xiàn)蒙古族人民建設(shè)強(qiáng)大祖國(guó)的夢(mèng)想,在敘事方式上,影片通過(guò)蒙古族人民的文化自覺(jué)來(lái)建構(gòu)共同命運(yùn)、共同利益的整體觀。以“家”作為基本的敘事起點(diǎn),以“國(guó)”作為敘事的終點(diǎn),從而完成由“家”到“國(guó)”的轉(zhuǎn)化與重塑,突出了“人為建構(gòu)性”的現(xiàn)代性特征,進(jìn)而建構(gòu)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shí)。
三、景觀化敘事:以美麗邊疆和日常生活呈現(xiàn)為導(dǎo)向
景觀化敘事可以理解為通過(guò)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來(lái)進(jìn)行話語(yǔ)表達(dá)的一種方式。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呈現(xiàn)邊疆的日常生活和秀美的自然風(fēng)景,表現(xiàn)各民族團(tuán)結(jié)友愛(ài)、和諧相處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美國(guó)學(xué)者索爾作為文化景觀研究的倡導(dǎo)者和實(shí)踐者,他首次將“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引進(jìn)美國(guó),探討人類文化與景觀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研究景觀的形態(tài)及其變化。“景觀,從總體上理解的景觀,它既是現(xiàn)存生產(chǎn)方式的結(jié)果,也是該生產(chǎn)方式的規(guī)劃。它不是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替補(bǔ)物,即這個(gè)世界額外的裝飾。它是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非現(xiàn)實(shí)主義心臟。在其種種獨(dú)特的形式下,如新聞或宣傳、廣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費(fèi),景觀構(gòu)成了社會(huì)上占主導(dǎo)地位的生活的現(xiàn)有模式。”[8](P4)現(xiàn)實(shí)世界是有不同信仰和風(fēng)俗的各個(gè)民族組成,各地區(qū)不同民族正在創(chuàng)造著不同的文化景觀。蒙古族題材電影以景觀化的敘事方式,運(yùn)用時(shí)空藝術(shù)覆蓋社會(huì)生活的各個(gè)層面,建構(gòu)了“想象共同體”的景觀世界。任何敘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體的時(shí)間和某一個(gè)(或幾個(gè))具體的空間。蒙古族題材電影在呈現(xiàn)民族文化的過(guò)程中,不乏具有對(duì)國(guó)家的各種想象。
法國(guó)思想家列斐伏爾認(rèn)為:“空間不僅是物質(zhì)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容器”[9](P359)。應(yīng)該從物質(zhì)領(lǐng)域、精神領(lǐng)域和社會(huì)領(lǐng)域三個(gè)層面去理解空間,與之對(duì)應(yīng)的是,存在感知的空間、構(gòu)想的空間和實(shí)際的空間三種空間[10](P82-83)。電影的空間符號(hào)闡釋蘊(yùn)涵著巨大潛能,電影空間不僅具有敘事功能、亦具有意義生產(chǎn)的功能。蒙古族題材電影對(duì)蒙古族人民所生活棲息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邊疆想象,呈現(xiàn)出內(nèi)蒙古地區(qū)特殊自然環(huán)境與人文底蘊(yùn),同時(shí)也“生產(chǎn)社會(huì)關(guān)系和被社會(huì)關(guān)系所生產(chǎn)”,傳達(dá)出多元的社會(huì)語(yǔ)義與復(fù)雜的社會(huì)形態(tài)。依據(jù)索亞提出的“空間學(xué)說(shuō)”進(jìn)行界定,蒙古族題材電影的邊疆想象體現(xiàn)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真實(shí)存在“第一空間”,亦體現(xiàn)在人們頭腦中想象的“第二空間”,還體現(xiàn)在想象空間的復(fù)雜多變的“第三空間”。
蒙古族題材電影中的“第一空間”想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草原。“天蒼蒼、野茫茫、風(fēng)吹草地見(jiàn)牛羊”,遼闊的大草原孕育了燦爛的草原文明。如《塞上風(fēng)云》《草原上的人們》《草原晨曲》等影片中唯美的草原,意指著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tài)理念,呈現(xiàn)了蒙古族人民的生存家園。蒙古族題材電影中的“第二空間”想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駿馬。如《重歸錫尼河》《獵場(chǎng)扎撒》《騎士風(fēng)云》等影片中奔騰的駿馬,贊揚(yáng)了蒙古族人民的智慧和勇敢。蒙古族題材電影中的“第三空間”想象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雄。如《祖國(guó)啊,母親》《蒙根花》《成吉思汗》等影片中英雄形象,表達(dá)著草原人民對(duì)英雄的尊崇和歌頌。草原、駿馬、英雄構(gòu)成景觀化敘事的主體,描繪出蒙古族人民生活圖景。通過(guò)景觀化的敘事,建構(gòu)起一個(gè)全新的想象空間,映射出新中國(guó)各民族團(tuán)結(jié)友愛(ài)、和諧相處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
四、民族化敘事:以民族認(rèn)同和草原文化表達(dá)為向?qū)?/h2>
民族化敘事可以理解為,以實(shí)現(xiàn)民族認(rèn)同和文化建構(gòu)的一種話語(yǔ)表達(dá)方式。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對(duì)民族認(rèn)同話語(yǔ)的建構(gòu)和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現(xiàn)實(shí)思考。巴柔認(rèn)為:“異國(guó)想象是社會(huì)集體想象物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態(tài)。”[11](P188)民族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是蘊(yùn)含著文化認(rèn)同、民族認(rèn)同和國(guó)家認(rèn)同的共同體。實(shí)現(xiàn)民族認(rèn)同,傳播草原文化成為蒙古族題材電影進(jìn)行文化生產(chǎn)的主要組成部分。“從社會(huì)學(xué)的視角來(lái)看,很容易同意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所有的認(rèn)同都是建構(gòu)起來(lái)的。認(rèn)同建構(gòu)所運(yùn)用的材料來(lái)自歷史、地理、生物,來(lái)自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制度,來(lái)自集體記憶和個(gè)人幻覺(jué),也來(lái)自權(quán)力機(jī)器和宗教啟示。但正是個(gè)人、社會(huì)團(tuán)體和各個(gè)社會(huì),才根據(jù)扎根于他們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和時(shí)空框架中的社會(huì)要素和文化規(guī)劃,處理了所有這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他們的意義。”[12](P9)蒙古族題材電影通過(guò)對(duì)民俗生活與文化的鏡像表達(dá)來(lái)建構(gòu)對(duì)民族文化認(rèn)同。認(rèn)同與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密切相關(guān),不同的時(shí)期蒙古族題材電影映射出不同的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不同的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產(chǎn)生不同的意義生產(chǎn)。
“1990年以降,中國(guó)社會(huì)開(kāi)始進(jìn)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的軌道,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促進(jìn)人們的物欲急速膨脹,這一時(shí)期中國(guó)似乎進(jìn)入了一個(gè)量化的時(shí)代,一個(gè)指標(biāo)的時(shí)代,一個(gè)米籃子和菜籃子的時(shí)代,一個(gè)不但不關(guān)心人文價(jià)值、精神價(jià)值,而且也不關(guān)心政治的時(shí)代。”[13](P210-320)電影不僅具有娛樂(lè)功能,還具有教化功能。“否認(rèn)電影的教化功能是不可能的,作為潛藏著意識(shí)形態(tài)的神話,電影總是通過(guò)精心編織的符碼向觀眾灌輸意識(shí)形態(tài);否認(rèn)電影的娛樂(lè)功能是不明智的,這不僅影響著電影的生存與發(fā)展,再說(shuō),離開(kāi)了娛樂(lè),教化功能又何以實(shí)現(xiàn)?”[14](P39)蒙古族題材電影不僅承擔(dān)娛樂(lè)功能,還具有對(duì)民族文化的傳承功能。影片《東歸英雄傳》是一部具有強(qiáng)烈愛(ài)國(guó)主義的影片,影片中反映出民族或群族認(rèn)同意識(shí),也是土爾扈特人在漫長(zhǎng)的生活歲月當(dāng)中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質(zhì)的活態(tài)呈現(xiàn),贊揚(yáng)了土爾扈特部的愛(ài)國(guó)情懷和追求自由、勇于反抗、不畏犧牲的民族氣節(jié)。影片《黑駿馬》中對(duì)蒙古族傳統(tǒng)音樂(lè)(民歌)的運(yùn)用展現(xiàn)出意境悠遠(yuǎn)、底蘊(yùn)深厚的民族氣息,再現(xiàn)草原民族的風(fēng)俗人情,歌頌草原人民的善良、樸質(zhì)、勤勞的社會(huì)美德。這種美德超越了物質(zhì),回歸到人的內(nèi)心世界。
文化影響和制約著蒙古族題材電影的生存與創(chuàng)作。一個(gè)國(guó)家、一個(gè)民族的電影形態(tài)、功能觀念都與這個(gè)國(guó)家、民族的文化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聯(lián)系。羅伯特·考克爾指出:“電影是文化結(jié)體、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與影像發(fā)送與接受行為的綜合體,人為性的遺跡使它并不處于中性位置,其本身的用于再現(xiàn)與展示事物的創(chuàng)制方式使它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隱喻。”[15](P3)草原文化是中國(gu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作為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產(chǎn)物。蒙古族題材電影作為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對(duì)于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承起到重要的促進(jìn)作用。崇尚自然、踐行開(kāi)放、恪守信義是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影片《金色的草原》講述的是草原人民接納孤兒的動(dòng)人故事。影片《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將歷史化為神話加以敘述,這種敘事不僅是蒙古族內(nèi)部的凝聚和認(rèn)同,也是中華民族多元統(tǒng)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和認(rèn)同。影片《活著,可要記住》講述的是純樸善良的喜鳳在民族大義面前,大義滅親的故事。蒙古族題材電影的民族化敘事,有利于民族認(rèn)同的增強(qiáng)。
五、個(gè)體化敘事:以聚焦個(gè)體和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為導(dǎo)向
個(gè)體化敘事可以理解以聚焦個(gè)體和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為導(dǎo)向一種話語(yǔ)表達(dá)方式。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關(guān)注當(dāng)下時(shí)代變遷,體味時(shí)代變化對(duì)人的情感影響,再現(xiàn)微小個(gè)體與時(shí)代變遷的關(guān)系。“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lái),在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潮流下,放置在資本邏輯和市場(chǎng)邏輯里考量電影思潮在與其他思潮的融通中日漸淡化政治色彩,于對(duì)流與互動(dòng)中走向‘綜合創(chuàng)新’與‘中西調(diào)和’,激蕩出具有跨域性、跨界性的多元化電影文化景觀,孕育出氣象一新的電影創(chuàng)作實(shí)踐與大眾集體認(rèn)識(shí),觀眾群體相應(yīng)地循入廣域性、開(kāi)放性、多元化和個(gè)體化的審美場(chǎng)域中,在互聯(lián)網(wǎng)/新媒體時(shí)代,以理性/非理性相交織的‘批評(píng)’或‘輿論’姿態(tài)參與到電影思潮的流變中。”[16](P210-320)蒙古族題材電影也在積極尋找民族電影的創(chuàng)新之路,影片敘事風(fēng)格由原來(lái)的宏大敘事轉(zhuǎn)向微觀敘事,影片主題由原來(lái)的愛(ài)國(guó)主題轉(zhuǎn)向觀照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正如美國(guó)學(xué)者浦安迪所說(shuō):“敘事就是作者通過(guò)講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經(jīng)驗(yàn)的本質(zhì)和意義傳示給他人。他認(rèn)為,偉大的敘事一定要有敘述者即作者的個(gè)性的介入。”[17](P5-15)也就是說(shuō)敘事一定要觀照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人的內(nèi)心世界。
蒙古族題材電影個(gè)體化敘事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如:《白魂靈》觀照普通牧人的日常生活; 《天上草原》展現(xiàn)蒙古草原的仁愛(ài)情懷;《嘎達(dá)梅林》關(guān)注草原歷史英雄人物;《跆拳道》講述跆拳道國(guó)家隊(duì)員的成長(zhǎng)歷程;《季風(fēng)中的馬》反思草原荒漠化的現(xiàn)狀;《圖雅的婚事》呈現(xiàn)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心迷宮》演繹著老百姓的悲歡離合。這些影片聚焦當(dāng)下,關(guān)注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開(kāi)啟了影片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光照。正如王一川所說(shuō),“現(xiàn)實(shí)主義既是一種審美或美學(xué)規(guī)范,又是一種歷史規(guī)范;既是一種電影美學(xué)尺度,又是一種電影歷史尺度。也許這樣說(shuō)更具體而又準(zhǔn)確:它要求在電影的富于審美魅力的表現(xiàn)中揭示當(dāng)代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歷史蘊(yùn)含。”[18](P165-166)蒙古族題材電影秉承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藝術(shù)傳統(tǒng),以客觀紀(jì)實(shí)的表現(xiàn)手法,運(yùn)用生動(dòng)形象的影視語(yǔ)言,結(jié)合秀美的草原景觀,體現(xiàn)出蒙古族題材電影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美學(xué)特征。
美學(xué)家阿爾都認(rèn)為:“意識(shí)形態(tài)可以強(qiáng)化個(gè)體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聯(lián)系,通過(guò)意識(shí)形態(tài)的‘詢喚’,把個(gè)體變?yōu)橹黧w。”[19](P43)影片《告別》講述蒙古族導(dǎo)演塞夫的真實(shí)生活經(jīng)歷;德格娜作為內(nèi)蒙古青年導(dǎo)演的代表,她把自己的生活融入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中,一個(gè)面對(duì)未來(lái)迷茫的年輕女孩與一個(gè)面對(duì)死亡迷茫的中年父親構(gòu)成影片故事框架,亮點(diǎn)之處傳遞了無(wú)數(shù)個(gè)體生命中共生的情緒表達(dá);影片《八月》講述的是20世紀(jì)90年代國(guó)企改革的故事,展示集體環(huán)境下個(gè)體成長(zhǎng)的現(xiàn)狀,傳遞出一個(gè)孩子的內(nèi)心成熟的歷程,描繪了在那個(gè)特定的年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折射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結(jié)構(gòu)和人民的生活狀態(tài);影片《老獸》主題聚集中國(guó)式代際關(guān)系之間的矛盾,反思中國(guó)城市化進(jìn)程中信仰的失落與人的迷惘;影片《海林都》講述了孤兒走進(jìn)草原的動(dòng)人故事,通過(guò)幾代烏蘭牧騎人的經(jīng)歷,不僅展現(xiàn)了烏蘭牧騎薪火相傳、歷久彌新的精神,更為重要的是影片傳遞了三代沒(méi)有血緣關(guān)系的母女之間,令人動(dòng)容的親情與大愛(ài)。正如李恒基、楊遠(yuǎn)嬰所說(shuō):“電影必須去重現(xiàn)生活的全部形態(tài),換言之,必須把電影的藝術(shù)引向各種感情的淵源,通過(guò)運(yùn)動(dòng),在生活本身中去尋找生活。”[20](P53)于是,流動(dòng)的生命形式產(chǎn)生了詩(shī),電影產(chǎn)生一種韻味獨(dú)特的詩(shī)意美和韻律美。
六、結(jié)論
敘事不僅是講述故事的行為,而且是一種表意的活動(dòng),電影是運(yùn)用系列圖像進(jìn)行敘事、表意的代表性類型。蒙古族題材電影的敘事方式呈現(xiàn)出國(guó)族化敘事、景觀化敘事、民族化敘事、個(gè)體化敘事的發(fā)展軌跡。這種發(fā)展軌跡,在一定程度上還囿于固定化的模式,如何以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眼光來(lái)對(duì)蒙古族題材電影的藝術(shù)表征進(jìn)行觀照,進(jìn)一步探索蒙古族題材電影的文化建構(gòu)功能值得深思。蒙古族題材電影中邊疆想象、民族認(rèn)同與文化建構(gòu)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可以概括為:邊疆想象是實(shí)現(xiàn)民族認(rèn)同的一種現(xiàn)實(shí)路徑;內(nèi)蒙古地區(qū)各少數(shù)民族對(duì)本民族的認(rèn)同是民族及其文化存在與發(fā)展的必然前提;文化建構(gòu)是邊疆想象、民族認(rèn)同的最終目標(biāo),即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思想,集中反映出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全人類的共同價(jià)值追求。架構(gòu)三者之間的橋梁是電影,橋梁的基礎(chǔ)是敘事,敘事把蒙古族題材電影放置在特定的社會(huì)制度、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中進(jìn)行考察,從而顯現(xiàn)其功能和時(shí)代價(jià)值。
中國(guó)電影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文化傳統(tǒng)和當(dāng)下豐富的社會(huì)生活現(xiàn)實(shí)。迎著全球地方化、地方全球化的時(shí)代浪潮。電影所身處的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呈現(xiàn)出冗雜多元、眾聲喧嘩的狀態(tài)。當(dāng)下,蒙古族題材電影的生產(chǎn)與創(chuàng)作,無(wú)論是在劇情的構(gòu)思、主題的選取,還是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文化底蘊(yùn)的呈現(xiàn)等方面都承擔(dān)著重要的歷史使命。未來(lái),蒙古族題材電影的藝術(shù)表征還會(huì)呈現(xiàn)哪些變化,值得進(jìn)一步探討與深思。正如饒曙光所言:“要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電影的可持續(xù)繁榮發(fā)展,好作品永遠(yuǎn)是硬道理,中國(guó)電影不僅要滿足本土觀眾情感性需求、精神性需求、思想性需求以及價(jià)值觀需求,還要為世界貢獻(xiàn)更多的中國(guó)故事、中國(guó)智慧,雕琢出更多的與人心相遇的作品,成就新時(shí)代中國(guó)電影的‘光榮和夢(mèng)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