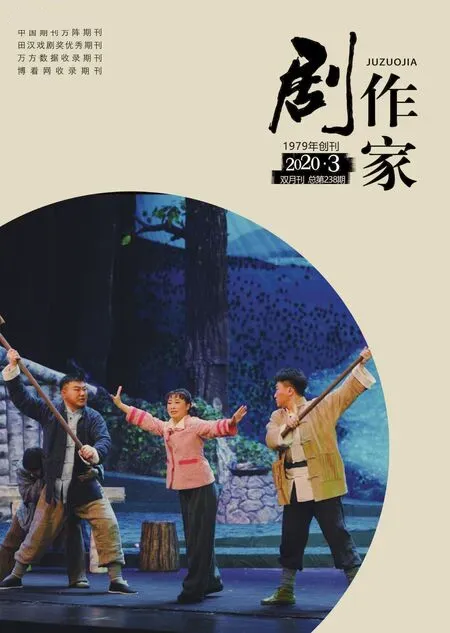林風眠中國戲曲人物畫在法國傳播情況探究(1953 年—1979 年)
■ 王沫
中國戲曲人物畫有著經典傳統藝術的文化積淀,并將一招一式的戲曲舞臺效果轉化為二維空間的視覺藝術。區別于以往傳統戲曲畫,以林風眠為代表所開創的近代戲曲人物畫樣式,伴隨著中國人物畫復興的特殊歷史時期,不僅繼承了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又受到來自西方不同藝術理念的深刻影響。據相關研究了解,林風眠也是第一位被法國公眾認知創作中國戲曲人物畫的代表畫家。同時,中國戲曲人物畫也作為戲曲藝術海外傳播的特殊表現形式,打破了傳統戲曲表演藝術所遇到的來自語言、文化場域、程式化表演等諸多方面的障礙,隨后更成為近代中國戲曲文化中珍貴的美術資源。本文圍繞林風眠中國戲曲人物畫作品在法國展出、收藏等傳播情況進行研究與思考。
林風眠中國戲曲人物畫在法國的傳播可追溯到20 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戲曲藝術開始以新的面貌走出國門。1953 年,任文化參贊的郭有守先生向法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捐贈了76 件中國近代名人繪畫作品。該博物館為此舉辦了一次小型捐贈展覽會。其中,林風眠《崔鶯鶯和她的紅娘》是向法國公眾展出的第一幅表現中國戲曲人物題材的作品。該作品創作于1940 年,取自著名京劇曲目《西廂記》中兩個主要戲曲人物形象崔鶯鶯和她的紅娘。這是林風眠探索中國戲曲人物畫的早期作品。富有韻律的中國畫線條與西方明快的色彩融合在一起,畫面構圖簡潔,但已經初見其中西調和的思想意識。同時,這也是第一幅被法國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戲曲人物畫作品,標榜著來自國家層面對此等藝術表現形式的最高審美標準和認識。事實上,中國戲曲藝術對于法國觀眾并不算陌生,19 世紀法國學者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就翻譯過《西廂記》《趙氏孤兒》等中國著名戲曲作品,但遺憾的是,由于對表演形式的理解和文化差異,中國戲曲藝術并沒有得到太多法國公眾的關注。進入20 世紀初期,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遠赴中國,接觸到了真正的中國戲曲表演藝術,1910 年路易士·拉羅已經開始嘗試融入西方藝術元素演繹《漢宮怨》。時隔八年后,林風眠等留法先驅又來到這片法蘭西大地繼續探尋藝術真理,吸取了來自西方各種藝術理念之大成。林風眠起初對中國戲曲藝術并不了解,在法國留學期間對西方古典音樂和法國戲劇表演十分迷戀,在其回國辭去校長一職后,才開始接觸到真正的中國戲曲藝術。他將“中西調和”藝術理念在其中國戲曲人物畫的創作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與西方對中國戲曲審美角度有著相似之處。
隨著1978 年改革開放,中法之間在戲曲藝術的交流上越來越積極。而中國藝術家也開啟了重返國際藝術舞臺的新浪潮。1979 年法國賽努齊博物館專門舉辦了一場“林風眠——中國當代畫家個人展覽”,由巴黎市長希拉克主持開幕。這次展覽也得到了法國社會各界的關注,共展出80 幅來自林風眠不同階段的代表作品。其中,中國戲曲人物畫有12 幅,除該館藏品《崔鶯鶯和她的紅娘》外,其他作品皆為林風眠創作于五十年代不同戲曲題材的人物畫,包括《打魚殺家》《轅門射戟》等。而此次展覽也是法國20 世紀以來第一次由官方系統地向公眾展出來自中國獨有的繪畫題材——中國戲曲人物畫。值得注意的是,在展出后《魯肅與張飛》被法國塞努齊博物館所收藏。該作品取自兩個重要平劇戲曲人物形象,魯肅與張飛為三國時期著名將領,畫面用黑線勾勒出幾個簡略的圖形,以濃郁的黃、綠、赭石色彩區別人物形象。五十年代初,林風眠開始關注民族傳統文化,這一時期創作了大量的戲曲人物畫作品。他曾回憶說:“我畫霸王別姬、張飛等歷史人物都是來自平劇的印象,我看平劇是把它作為一種中國舞蹈的味道,我用現代畫的形式表現了它。”國學大師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講道:“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國人最能理解中國和中國文明,因為法國人擁有一種和中國人一樣非凡的精神特質。”西方觀眾對中國戲曲的理解起初受到語言、題材、舞臺表演形式等方面的障礙,而林風眠的中國戲曲人物畫源自對中國傳統程式化戲曲意象的提取,又加入了西方藝術理念的形式語言,通過這樣的視覺呈現已然喚起西方對中國戲曲文化審美的感知能力,并深入感悟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的神韻。
博物館是匯聚著藝術與歷史復合之物的綜合載體,成為中國近代戲曲人物畫在法國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這些收藏在館內的中國近代戲曲人物畫如今已被納入法國外來珍貴近代藝術資源之中。法國是最重視藝術資源保護和發展的國家之一,并在近半個多世紀的交流研究中,逐漸豐富對此等藝術資源的不斷建設與保護。21 世紀的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教育和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不僅承擔著社會教育的責任,也是最直接取得國際社會接受、認可的方式。在未來的博物館國際合作中,我們需要建立對于國際藝術資源合作的制度方案,共同探索出一條融合中西藝術理念的收藏標準體系,從而逐漸喚起國際領域對中國現代美術資源的重視,將海外的中國近代藝術資源共同推向國際領域,共同向世界訴說獨具東方智慧的中國戲曲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