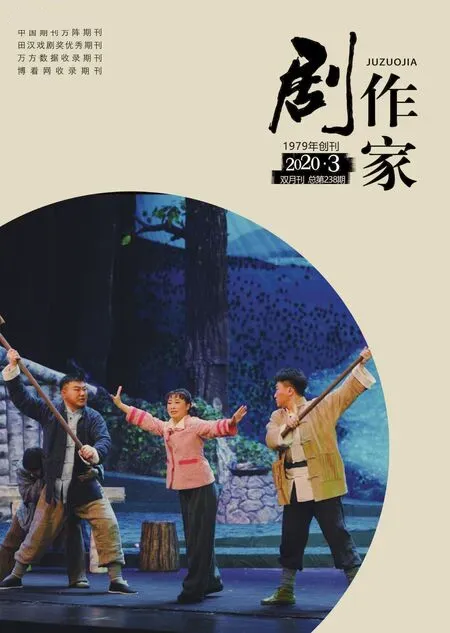淺談方筆、圓筆的征象及其得失
■ 魏立斌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道:“書法之妙,全在運筆,該舉其要,盡于方圓。操縱極熟,自有巧妙。”用筆的方圓,是書法研究的特點,也是書學研究的首要問題。目前學術界對此有諸種不同看法:一曰“方筆則漸成絕響了”,主張“易方為圓”。二曰“妙處在方圓并用,不方不圓,亦方亦圓,或體方而用圓,或用方而體圓,或筆方而章法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三曰“因時發揮,自然有別。古今只是風尚不同之區分,不當用作優劣之標準”。方筆真的面臨恐龍、三葉蟲一樣的厄運嗎?方圓并用能否行之有效?
要曲盡物象,正如古人所謂“戈戟铦銳可畏,物象生動可奇”。書法要有那樣可畏可奇的生動意態,單純使用圓筆是難以奏效的。圓筆得渾動而失雄強,得婉通而失精密,得蕭散而失凝整,得超逸而失沉著,得筋勁而失骨氣,各自有其偏頗的一面。
古人論用筆結字的方法浩如煙海,有蔡邕《九勢》、梁武帝《觀鐘繇書法十二意》、張懷瓘《論用筆十法》等。據不完全統計,約三百余法可作參考,但以不切實用者為多。
書法藝術必須兼備實用與美觀,要在規定的條件下,極盡賞心悅目、變幻方圓之能事,所以孫過庭感慨地說它“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
方筆的書法作品,表現出凝整沉著、精密莊重、硬朗雄強,深刻而有骨氣。多用頓筆、翻筆而折,運筆方頭側入,筆鋒居于筆畫的一側,或時入中心。由于棱角四出,頓筆時骨力向外開拓,一般認為宜隸、宜楷,硬毫易成。
圓筆的書法作品,表現出瀟灑、超逸、婉通、柔和、遒潤而自然。多用提筆、絞筆而轉,運筆圓頭逆入,筆鋒居于筆畫的正中。由于筆鋒中含,點畫圓勁,不露骨節,宜篆、宜草,軟毫易就。
《書譜》主張“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也就是方圓并用之意。“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說的是方筆之重要。“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不可一味圓潤、彎曲。“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骨氣”與“遒潤”兼而有之至要且難。“遒潤”與“骨氣”有著明晰的具體形態,而不是一般的、空泛的形容詞藻,它有助于澄清一系列的傳統問題。古人所謂“遒”并非勁挺之意,而指的是曲線;所謂“潤”是圓筆。
圓筆雖宜作草書,但初學宜用方筆始。《廣藝舟雙楫》認為:“以其畫平豎直,起收轉落,皆有筆跡可按,將來終身作書寫碑,皆可方整,自不走入奇褎也。”再者,作行草雖以圓筆為主,必間以方筆,否則無雄強之神。
圓筆盛于中唐,諸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印印泥,綿裹鐵筆等形態,以曲而圓不見起止之跡,不露圭角,中鋒暗過為能事。盛唐上溯到東晉,運筆的普遍法則為方頭側入,形成橫畫筆鋒在上,豎畫筆鋒在左的狀態。郭沫若有一段敘述:“具體地說來,是在使用方筆,逆入平出,下筆藏鋒而落筆不收鋒,形成所謂‘蠶頭’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寫經書,雖已收鋒,仍用方筆;凡一點一畫、一起一收,筆鋒在紙絹等上轉折如畫三角形。這樣的筆法,就是所謂隸書筆意。”這同繪畫的要求是一樣的,素描最終不是為了尋找到“圓”就完事,還要找到它的角和尖銳的地方,使之深刻化。
易方為圓、易圓為方、方圓并用,各有所宜,要因時、因地、因人各有采取和發揮,不可偏執。單純的方筆或圓筆有助于風格的形成,方圓并茂更有表現力,更具有時代意義。
總之,方圓變化以精致、意趣、胸懷、風氣為轉移。《藝概·書概》說得好:“書一于方者,以圓為模棱;一于圓者,以方為徑露。”當代書家林散之總結了數十年的藝術實踐,得出同樣的結論:“筆從曲處還求直,意入圓時覺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