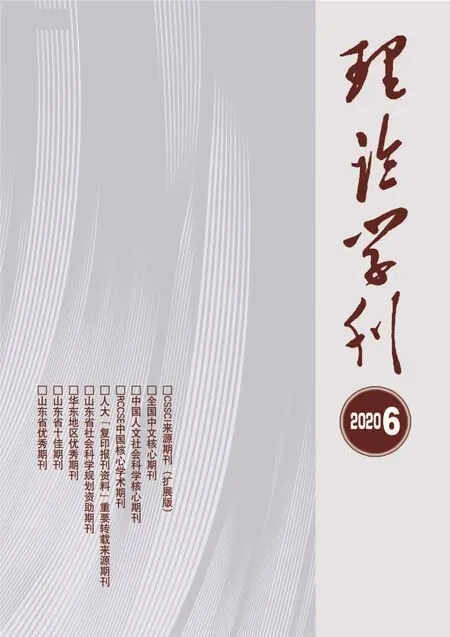越南阮福映政權的合法性塑造及對清越朝貢關系的認知與利用
葉少飛
(紅河學院越南研究中心,云南 蒙自 661100)
1802年五月,阮福映(1762—1820)在掃滅西山阮朝之后,改元“嘉隆”,建立起從紅河平原至湄公河平原的全國性政權,疆域之廣前所未有。阮福映隨即遣使朝貢,1803年清朝賜封“越南”國號。阮福映并未在建元之后立即稱帝,而是繼續以王號行事,至嘉隆五年(1806)五月即皇帝位。阮福映在攻打西山阮朝時謀借清朝之力,在政權建設過程中又請封國號,顯示其對中越朝貢關系有深刻的認知并加以利用,最終完成了新政權政治合法性的塑造。
一、嘉定中興
阮福映出身廣南阮主政權,是末代阮主定王阮福淳的侄子。阮氏遠祖阮淦在莫登庸篡權之后,于1533年擁立黎莊宗復國,1545年被毒殺,大權落入其婿鄭檢之手。1558年,阮淦之子阮潢鎮廣南、順化,逐步壯大。鄭檢死后,鄭松即位,其人系阮淦外孫,并在1593年推翻莫朝,成就黎朝中興大業。1600年,阮潢從昇龍回到順化,逐漸與鄭松對抗,但尚能顧念舅甥之情。1613年阮潢去世,雙方再無顧忌。1627年鄭主率軍攻打阮福源,之后雙方大戰七次,至1672年不再互相進攻,彼此劃江為界維持現狀,阮氏稱“南河”,鄭氏稱“北河”(1)陳荊和:《朱舜水〈安南供役紀事〉箋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卷(1968)。。鄭氏以王爵世專國政,黎皇徒有虛名,廢立操于其手,但并未稱帝。阮氏盡管具有事實上的獨立地位,仍奉黎朝正朔,用黎朝年號,名義上仍是黎朝之臣。
1773年,廣南阮主治下的歸仁西山邑阮岳、阮侶、阮惠兄弟起兵反抗阮主。1774年,鄭森趁機派黃五福率軍攻占順化,阮主殘余力量南逃嘉定。黃五福招安阮氏兄弟。1775年西山軍攻占嘉定,1777年擒殺阮福淳,17歲的阮福映逃脫,后被眾將立為大元帥攝國政。隨后,阮福映率軍收復嘉定,1780年稱王。史載,阮福映“即王位于柴棍,……用‘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仍用黎年號,群臣表章皆稱稟”(2)②⑤⑥⑦⑧⑨⑩ [越]張登桂等纂修:《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第2冊,東京:有鄰堂影印本,1980年版,第314、331、336、342、343、344—345、338、359、360頁。。《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關于阮福映的史事在明命年間修完,皆稱其為帝。“大越國阮主永鎮之寶”獅身金印為阮福淍1709年鑄造,阮福映即在嘉定繼承了阮主政權的政治傳統,為大越國阮主,用黎朝年號,即仍為黎朝之臣。
1782年,阮侶、阮惠再攻嘉定,阮福映敗逃富國島,向暹羅求救。1784年,暹羅國王遣軍進攻嘉定。1785年,阮惠在嘉定美荻大敗阮福映與暹羅軍隊,阮福映再次逃亡。1786年,阮惠擊敗鄭軍攻占富春后,與阮有整率西山軍“由海道直抵安南都城”,“整因教(阮)惠以扶黎為名,強請黎主視朝。惠入謁,獻國中版籍”。“秋七月,安南黎主崩,謚顯尊永皇帝,孫維祈嗣位,以明年丁未為昭統元年”②。黎朝對內為“大越皇帝”,對外則為“安南國王”,阮主為其臣子,自稱“大越國王”“大越國主”,又在對外交往中自稱“安南國王”(3)葉少飛:《十六至十七世紀越南古文書中的東亞世界秩序》,《元史及邊疆與民族研究》第3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盡管阮氏不斷接近本國的最高權威“大越皇帝”,但并未貿然稱帝,其自稱的“大越國王”名號也未得到清朝的冊封(4)葉少飛:《大汕〈海外紀事〉與“大越國”請封》,《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大南實錄》稱黎顯宗與昭統帝為“黎主”,其國為“安南”,在形式上降低了黎朝的政治權威。
昭統帝即位不久,阮有整隨阮岳和阮惠南歸。鄭氏卷土重來,丁錫壤逼請以鄭槰嗣位,“黎主不得已許之,而陰欲制鄭,乃召整,整于是復歸于黎”。阮有整率軍徹底擊敗鄭主勢力,“握兵專政”。“惠聞而惡之,召整,整不赴,惠即遣節制武文仕將兵誅整。整與仕戰,大敗,黎主奔京北。賊兵獲整殺之。賊遂竊據安南都城”⑤。昭統帝逃出昇龍流亡,遣使到清朝求救。
1788年十月,乾隆帝以“存亡繼絕”的名義遣孫士毅領兵送昭統帝回國,并攻占昇龍。《大南實錄》記載:“黎主維祈以清兵復安南都城。先是黎主出奔,遣文臣陳名案、黎維亶奉書如清,至南寧不得達而還。黎皇太后乃奔高平,使督同阮輝宿投書龍憑,乞師于清。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兩廣云貴兵分四路來援。西賊守將吳文楚退保清華,黎主遂復安南都城。”⑥此處仍然稱“黎主”和“安南都城”,即以“阮主”和“順化”相對應而言。1788年十一月,“西賊阮文惠自立為帝,偽號光中元年,偽西政令皆自惠出”⑦。阮惠北上擊敗清軍,孫士毅領殘軍回國,昭統帝君臣一起北歸。阮惠上表請罪,乾隆帝封其為安南國王,并將昭統帝君臣留置在中國。雙方關系恢復。《大南實錄》記載:“清兵與西賊阮文惠鏖戰于青池,敗績。孫士毅走還,田州太守岑宜棟死之。黎主亦奔清,黎亡,惠遂復據安南地,使其子光垂與賊司寇武文勇守北城,光盤守清華,鎮守阮文睿守乂安,復引兵還。”⑧“黎主”維祈奔清,黎遂亡。這樣的記述實際上撇清了阮主和黎皇的臣屬關系,而是以平等關系視之。
阮福映見舊都順化為西山攻占,告諭順化官軍等曰:“昔我太祖肇基南服二百余年,中外臣民莫非朝廷赤子,而順化一處乃我列圣宗廟所在,故此處黎庶我視之猶骨肉”。西山攻占順化必然征兵攻打嘉定,因而阮福映告諭舊都父老子弟,指出自太祖阮潢肇基,順化乃列圣陵廟所在,爾等皆是我之子民,不可從賊仰攻父兄,“天猶祚漢,人未忘唐”,以光武中興和唐肅宗靈武即位言事,定能恢復故土⑨。這份諭旨指明阮主政權是一個獨立的政權,肇基南服傳承二百余年。這與實際情況一致。
1790年,嘉定形勢逐漸穩定,阮福映開始營建城池以形成鞏固的基地,“號曰嘉定京”⑩。嘉定京中特意建了太廟,顯示這并不是一座簡單的守衛城池,而是基業的根本。自1558年阮潢以順化為基地,至1774年被鄭軍攻破,歷代阮主陵寢宗廟皆在其地,后來才被阮惠占據,故而阮福映在嘉定建太廟祭祀歷代祖先。阮福映又“建后殿奉國母,建方殿、金印殿、金花殿、朝陽閣”,新建宮室讓阮主政權以實地的形式重新呈現。營建嘉定京以及完善各種制度,使得阮福映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以京與廟的實地形式展現出來,從而增強了凝聚力。在阮福映打造嘉定基地時,死敵阮惠與清朝重建朝貢關系,對此,《大南實錄》記載:“西賊阮文惠使人朝于清。初惠既敗清兵,又稱為阮光平,求封于清,清帝許之,復要以入覲。惠以其甥范公治貌類己,使之代,令與吳文楚、潘輝益等俱。清帝丑其敗,陽納之,賜赍甚厚。惠自以為得志,驕肆益甚。”(5)③④⑤⑥ [越]張登桂等纂修:《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第2冊,東京:有鄰堂影印本,1980年版,第360、364、369、433—434、455—456頁。中越歷史學家爭訟紛紜的“假王入覲”事件即發端于此(6)關于此事,張明富在所撰《乾隆末安南國王阮光平入華朝覲假冒說考》(《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來者確為阮惠本人,越南學者阮維正《假王入覲》一書則確認來者為阮惠之外甥假冒,宗亮在所撰《紫光閣舊藏〈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像〉考》(《形象史學》2019年總第14輯)一文中亦認為來者并非阮惠。。史書沒有記載阮福映的反應,但在最初得知清朝出兵攻打西山之時,他即派人支援,史載:“帝聞清人發兩廣兵為黎氏討西賊,乃遣使臣潘文仲、林提等奉書如東,且以米五十萬斤助軍餉,遭風沒于海。音信久絕,至是聞清兵為賊所敗,既不復討,又從而封之,故命廷得往探黎主消息,因招諭北河豪杰。”③阮福映原要援助清軍攻打西山,豈料所助軍餉遭風沉海,清軍戰敗繼而承認阮惠并賜封,阮福映必然憤怒不滿,心中鄙夷乾隆帝的行為,但又無可奈何。阮福映繼續完善各項制度,史載:“帝自克復嘉定,庶事草創,每留意經畫,申軍制,定官名,明法禁,正朝儀,開國規模略定矣。”④在阮惠與清朝恢復關系之后,阮福映意識到阮惠政權將長期存在。阮福映確立各種制度,立太廟,定祀典,贈功臣,封陣亡將士,以忠孝塑造君臣關系,加強軍民對自己政權的向心力。他以嘉定京為基地作長期對抗的準備。如此措置,阮主政權規模已成,采用的仍是儒家忠孝家國的政治思想。
1792年七月,阮惠突然病死,西山阮朝內訌不斷,阮福映力量不斷壯大。1796年,阮福映率群臣上金冊,尊奉母親為國母王太妃,表達了“仁人孝子之心”,意在闡揚忠孝之道。阮福映又下諭旨,肯認綱紀名分是儒教國家的根本。冊文和諭旨提及的典故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女性,不止是母以子貴,更是“道在天地,禮通古今”。阮福映自稱“予一人”(這原本是周天子的自稱),表示將以天下奉養母親。這既合于古典,又可見阮福映的目標志向,即全取越地⑤。冊文和諭旨中展現的思想乃是儒教政治體系中的綱常名分和忠孝大義,這與阮福映發布的諭旨可謂是一脈相承。
二、克復舊京
在阮福映和西山政權相持之際,大臣阮文誠、鄧陳常上疏論阮主、西山、清朝、黎朝的關系:首先,表明阮福映政權和西山阮朝“正所謂以國敵國”,所以要攻其所交,結好其敵;其次,認為清朝戰敗一定懷恨在心,“清人自有事于北河,為西賊所挫,能不痛心疾首,積憾貽慚,姑釋此以俟可乘之機”,現在嘉慶新君即位,不似乾隆帝時政策,正該利用其與清朝的舊仇;復次,主張鑒于“清人患海匪,控制未得其術,曾檄西賊查緝,彼亦等之閑,忽則清人之怒,不止海匪,亦必移怒于西賊者矣”,我方當押送捕獲海盜以結交清朝,“清帝必嘉納,不忍以尋常眇我”,如果能覲見清帝,“提說西賊外帝內臣,投彼所忌,以構其隙”,即通過述其對清稱臣、在安南稱帝之事,造成彼此之間的裂隙;最后,“探問黎皇,潛通消息”,奏折明確稱“黎皇”,異于前文所引《大南實錄》稱“黎主”,這表明阮福映君臣很清楚自己和黎皇的關系,去清朝打探黎皇消息,激起其復國復仇之心,如果黎皇無動于衷,則顯我名節,揚“能夏之聲”,即效法夏少康驅逐逆賊⑥。
阮文誠所言的“西賊外帝內臣”,實際就是潘輝注所言安南歷代“內帝外臣”,只是兩人所言的“內外”顛倒了而已(7)葉少飛:《越南古代“內帝外臣”政策與雙重國號的演變》,《形象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165頁。。他認為清朝對戰敗一定懷恨在心,要伺機出兵報復。阮文誠奏折中關于清朝的提議雖不切實,但探問黎皇之事卻很重要,得到了阮福映的認同,即阮氏政權一定要處理好和清朝的關系以及擺平和黎皇的關系。阮福映遣吳仁靜“奉國書從清商船如廣東探訪黎主消息,仁靜既至,聞黎主已殂,遂還”(8)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越]張登桂等纂修:《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第2冊,東京:有鄰堂影印本,1980年版,第458、512、521、524、527、531、551、552、563—564、564—565頁。。
1798年六月,阮福映率軍攻占了阮文岳的歸仁城,除一二殘軍之外,前面即是阮光纘占據的順化舊都。1801年二月,阮福映即將進軍順化,再次強調自己是“天啟中興”②。五月,“克復舊京”③。自1774年12歲倉皇逃離,至今39歲滅敵還都,其間艱險不可勝計,終于造就了一代雄主。阮福映下諭:“我今克復舊京,賊阮光纘奔北,已委上道典章劉福祥會萬象攻乂安,爾宜率所部攻清華,竢我規措略定,進取北河,以收一統,爾其勉之。”④阮福映已然下定決心攻取北河,成就一統大業。“西賊阮光纘奔北城,改偽號寶興,使人如清乞師,清人不許”⑤。乾隆帝出兵扶黎,孫士毅戰敗,損失很大,嘉慶帝吸取教訓,對安南之變不加理會。
阮福映以舊恩諭順化軍民百姓,謀劃攻滅西山余孽,安排諸將“進取昇隆以定北河”⑥。這是自1613年阮福映即位以來歷代阮主夢寐以求而從未實現過的大業。同年十一月丙戌,“命有司設壇于安寧之野,合祀大地。帝親詣行禮,禮成,群臣稱賀”⑦。自李朝完善政治制度以來,祭祀天地皆是大越皇帝的職責,即便鄭主權勢熏天,也只能代黎皇祭祀。廣南阮主雖然自立已久,且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等級,但終究不是天子,因而無權祭祀天地。如今黎皇身死于清朝,西山阮氏逆賊大逆不道,阮氏基業中興,因而阮福映祀地以宣示其正統地位。
阮福映“以收復舊京,殲戮賊黨,布告嘉定”,再次強調已經實現了中興大業,“會逢再造,運際中興”,現在“盡括南河之壤”,自富安至橫山“都歸版籍”,這正是之前阮主政權的占有疆域。如今殲滅阮惠匪類,特告嘉定軍民以大快人心⑧。
阮福映強調的中興大業固然可以激勵人心,喚起思舊之情,如今恢復舊疆,足以告慰列祖列宗,但中興畢竟只是恢復阮主事業,而非奄有全越之地,中興大業在名義上竟成為阮福映攻占全越的阻礙。阮氏終究是黎氏之臣,阮福映并不像阮岳和阮惠那樣沒有任何政治包袱從而無所顧忌,阮福映背負的政治遺產,促使其必須做好各種政治輿論準備。
三、從改元到稱帝
舊京已復,逆賊已是強弩之末,阮福映政權的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
(一)改元嘉隆
對于并非自己舊疆的北河,阮福映作為成熟的政治家,心中自有思慮,史載:“帝嘗與群臣議用兵,謂之曰:‘北河,黎故國也。自我列圣肇基南服二百余年,用黎正朔。頃者西賊僭竊,我積意用兵,惟在復仇而已。今故疆既復,而偽渠北竄,若舉兵北伐,罪人既得之后,于黎如何?’”⑨阮福映的考慮很深刻:列圣肇基南服二百余年來盡管用黎朝正朔,但事實上已經成為獨立政權,西山逆賊逃竄北河,我舉兵北伐,逆賊定可殲滅,但對黎氏如何交代?阮福映在這里提出了儒家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存亡繼絕”和“恤鄰”的原則。無論自己是作為黎之舊臣還是黎之南鄰,對黎均有存恤的義務,即便黎主死于清,但黎氏宗室仍在,存恤黎氏可全大義,取人土地則屬不道。但歷代阮主與鄭主征戰多年,一統全越指日可待,如何甘心?
當此之時,鄧德超、陳文擢等人進言:“自黎主奔清一去不返,北河之地已為西賊所有”,“我滅西賊,奄有其地,是取于西賊,非取于黎也”,“今我北伐而猶用黎年號,誠恐北人謂我藉以扶黎為辭”,為避免給人口實,“莫若正位改元,聲大義于天下,則得國為正,無可議者”,敦請阮福映稱帝改元⑩。阮福映表示:“此大事也,卿等可熟圖之”。如此表態相當于認可。能夠成為從龍之人,群臣自然踴躍,于是繼續上表請阮福映即位改元,大略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故春秋之義大一統。我國家肇基王業,神傳圣繼二百余載。中間黎運寖衰,鄭氏專柄,構兵侵于我疆。繼而西賊倡亂,并吞土宇,天下靡定。我王上志圖恢復,間關二十余年,削平僭亂,王師所至,人皆向從。雖自古中興賢君,亦不是過。乃猶襲用黎景興年號,中外皇皇,莫知所向。茍不早正位號,恐無以系人心。伏愿王上以光祖宗之烈為重,盡子孫之孝為念。仰承天意,俯徇輿情,早正尊位,下詔改元,以孚臣民推戴之忱,衍廟社無疆之業。”(9)②③④⑤⑦⑨⑩ [越]張登桂等纂修:《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第2冊,東京:有鄰堂影印本,1980年版,第565、65、567—568、571、571、538、569、572、576、577—578頁。群臣上奏的內容與鄧德超和陳文擢所言大致相近,應該是出自二人手筆。阮福映推辭曰:“嘉定初復,已即王位,人心推戴久矣。今故京雖復,而國賊未除,登尊之事,未可議也。惟王者易姓受命,義貴更新,年必有號,改元為是,卿等其議行之。”②阮福映同意改元建新年號,卻拒絕了群臣稱帝的建議。1802年五月,阮福映正式改元,詔書指出:“西山倡亂,黎祚告終,數十余年國內無統”,而今從群臣之請,改元以明正法度,“紀元嘉隆,以一統紀,新視聽”。詔書明確了建元是“一統紀”,即終結因黎末和西山之亂國內“無統”的局面。但“統”并非無源之水,而是自有來歷,阮福映仍然在強調“粵我先太王肇基南服,神傳圣繼垂二百載”,但阮主政權并無國統,詔書對于繼承何方之“統”并未明示③。
阮福映拒絕稱帝,一方面是因為“余孽未除,海宇未一”,另一方面可能是擔心招來清朝的干涉。阮文誠曾希望使人至清,若能覲見清帝則“提說西賊外帝內臣,投彼所忌,以構其隙”,說明阮福映君臣很清楚安南歷代王朝在國內稱帝之事犯了中國之忌。清朝扶持黎氏在于乾隆帝行“存亡繼絕”大義,但阮岳稱帝在先,清軍出兵在后,二者聯系即給人以因稱帝而進攻的假象。阮福映僻在嘉定,很可能如此考慮,因此對稱帝之事慎之又慎。實際上中國官方和民間通過各種渠道知曉安南在國內稱帝之事,但歷代王朝皆未因此大動刀兵。此時大局已定,對清關系再次提上日程:“帝與群臣議通使于清,諭曰:‘我邦雖舊,其命維新。復仇大義,清人尚未曉得。曩者水兵風難,清人厚賜遣還,我未有答復。今所獲偽西冊印,乃清錫封,所俘海匪,乃清逋寇,可先遣人送還,而以北伐之事告之。俟北河事定,然后復尋邦交故事則善矣。卿等其擇可使者。’”④
隨后,阮福映以鄭懷德為如清正使,吳仁靜和黃玉蘊為副使,赍國書、西山冊印以及抓獲的海盜送至廣東。嘉慶帝“得報大悅”,命廣東方面“留懷德于省城,供給甚厚”⑤。
阮福映所言“曩者水兵風難,清人厚賜遣還”,即阮進定飄風至粵洋之事。《仁宗實錄》記載,當時兩廣總督吉慶奏報請給糧米放還本國,嘉慶帝認為自當撫恤,但鑒于阮福映一方正與阮光纘交戰,若阮光纘來問,不好答復,最終還是否定了吉慶讓阮進定等人搭乘商船的建議,略為賞恤,任其自行(10)⑧ 《〈清實錄〉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277頁。。
1801年七月,阮福映派清商趙大仕前往廣東。“(趙)大仕,清人來商,為齊桅海匪所掠,我兵攻破海匪,因活之。帝以舊京既復,議以國情移于兩廣總督,大仕請行,乃遣之”⑦。至后呈上文書,吉慶上奏,嘉慶皇帝指示:“上年撫恤爾國難番之事,既未具奏,此時爾國稟詞,亦不便代為奏達”,并要求兩不相幫⑧。之后“清人趙大仕自廣東還,帝問以清國事體,命兵部厚廩給之”⑨。阮福映果然以清朝撫恤落難水兵為由頭,正式以朝中大臣為正副使出使以重建朝貢關系。
鄭懷德等出發之后,阮福映下旨北伐,曉諭北河軍民曰:“春秋之義,莫大于復仇,王者之師,必先于誅亂。慨自西山煽變,順廣以北,久遭荼毒。朕今勵志殲仇,惟以伐罪吊民為念。”⑩諭旨中強調了自己復仇于西山、吊民伐罪的舉措合乎春秋大義。1802年六月,阮福映駕至昇龍,阮光纘逃走,為村民所執,送至昇龍,至此,“西山賊悉平,盡有安南之地”。阮福映“令涼山閫臣移書于清,探問消息,以北河大定布告中外”,詔曰:“自我克復京城,賊徒北走,二百年疆界,山限風移,十三道承宣,水深火熱。討罪安民,正不容緩。今大兵一舉,所向無前,……二十一日車駕至昇龍城,偽官相率拜降,群盜悉清,大勛用集。于戲!天地晦,王師蕩滌,迄成拯救之功;云雷屯,君子經綸,佇享昇平之福。”
阮福映繼續下詔:“賊黨悉平,戎功耆定,正興化致治之秋”,當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協念分猷,共成政道”;“從前有徇義捐軀者,聽子孫族屬以事陳奏,量加恤典”(11)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越]張登桂等纂修:《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第2冊,東京:有鄰堂影印本,1980年版,第581、581、582、582、587—588、588、587—588、593、597、600頁。。阮福映之所以不斷下詔曉諭北河地區民庶、士人、隱逸,有多方面的原因和考慮:第一,這里是黎朝故地,黎亡未久,人心思故,黎朝自1428年開國至1789年昭統逃亡,三百余年國統影響力無與倫比;第二,自1672年鄭阮停戰以來,南北分裂已久,雙方互相敵視,名屬一朝,實為異國;第三,北河鄭主挾黎皇,擁有政治正當性,多次以黎皇名義御駕親征,大義之下,阮福映的南河一方實為逆賊,如今逆賊入京,黎朝士人自難安分;第四,在鄭氏的不斷攻擊下,南河阮主不斷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并提升政治層級,以此來對抗鄭主,更加劇了南北的對抗和分裂。鑒于以上因素,阮福映必須善加安撫,以防止人心思舊,產生新的對抗。
阮福映“命擇鄭后主鄭祀”②。鄭主雖與阮主征戰多年,但祖上有姻戚之誼,鄭氏失政,阮福映行“恤鄰”之義,保存鄭氏祭祀,可以圓滿解決鄭氏問題。故而阮福映“親謁黎太祖廟”③,又“命禮部設壇祭山川之神”④。
八月,“命留京大臣權建太廟于皇城之左”⑤。阮福映建設嘉定京時,原建有太廟,但現在恢復舊都,又奄有全越,故而在順化皇城之左營建國家太廟。而嘉定作為中興之地,意義非常,因而仍郡國之制,由鎮臣代行典禮⑥。這意味著從京師到地方的太廟祀典重新確立。
大事甫定,“黎族鄭族與黎氏文武舊臣藩酋等上表勸進,請即帝位,帝謙讓不受”。阮福映在詔書中表示,“頃者西山僭逆,黎祚告終,二十余年國統舛紊”,自己“以社稷生民為念,先正王位以系人心,逮收復舊京,下詔建元,亦足以明正始”,如今“元惡既擒,戎功耆定”,“爾等交章請正帝位,推戴之情,誠為諄切”,但是稱帝“非朕意也”,且“自古歷代有興,曰帝曰王,稱號不同而君國子民”,意謂帝、王之號并無差別。根據阮福映屢稱先祖以及改元詔書的內容來看,拒絕黎鄭舊臣詔書中所言“我國自趙武以至于丁黎李陳,世稱帝號,具在簡冊”應該是勸進表文中的內容,阮福映照抄于此,這雖是歷代傳統,但并非阮福映認可的先祖肇基南服之統。黎鄭族人及黎朝舊臣勸進,雙方均做足了姿態,黎鄭族人認可吊民伐罪的大義之舉,阮福映則謙辭不受⑦。
九月,封黎氏后人為延嗣公。對于阮福映而言,保存黎氏祭祀非常重要。黎氏開國至今,相承三百余載,因西山逆賊,昭統帝黎維祈不能守宗廟,祭祀毀敗。現在阮福映“統一區宇,崇典禮以存黎祀”。阮福映不提雙方的君臣舊關系,而是闡明除亂存祀的新關系,即黎氏不能守其宗廟,奔逃于清,今我肅天威為黎氏重續廟祀⑧。
大事已定,阮福映班師,十月回到順化,“帝親謁太廟,既乃詣慈宮慶安,大宴群臣”⑨。十一月,“大告武成,癸酉,祭天地神祇。甲戌,獻俘于太廟”,又下詔書。詔書宗旨為“復仇”,此乃春秋之大義。詔書內容亦主要是復仇滅僭,自暹羅還復嘉定,繼而進取歸仁,再克復富春,最后“橫山一帶,盡復舊疆”,即之前阮主轄有的南河故地盡皆恢復,最后擒獲逆賊阮光纘等,梟首戮尸,“復廟社之仇”。詔書雖然以“復仇”成功告慰先祖,卻并未言及阮福映攻占北河、奄有全越之事⑩。此次太廟獻俘意味著阮福映的中興大業已經因克復舊疆和殲滅逆賊而完成,舊疆與新占的北河將組成一個新的國家。
(二)新建國號
北伐之前,阮福映與群臣商議使清之事,其言“我邦雖舊,其命維新。復仇大義,清人尚未曉得”,表明阮福映主導的對清關系是以《春秋》的“復仇”作為主導思想,這與太廟獻俘詔書內容是一致的。他在給清朝皇帝的奏文中稱:“臣遙仗天威,故獲掃清南徼,現當整飭兵戎,水路并進,報仇雪恥,志在必獲國仇而已。光纘既擒,則洋逃無所憑依,必能取次殲除,永清疆圉,是臣之大愿望也。”(12)《古代中越關系史資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頁。阮福映認為自己秉承的復仇大義定可得到清朝的承認,因而在攻占北城之后,即欲遣人在鎮南關迎候清朝使臣:“帝以西賊既滅,命移書于清兩廣總督,問以邦交事宜,遣……候命于南關,又以國家甫創,欲于關上接清使行宣封禮,以省煩費。問之吳壬、潘輝益,皆曰此事未之前聞。乃止。”(13)②③ [越]張登桂等纂修:《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第2冊,東京:有鄰堂影印本,1980年版,第589、596、601—602頁。曾在西山朝出使的吳壬、潘輝益,深知建交之事絕不會順利,最終此事以“省煩費”作罷。阮福映在昇龍等待鄭懷德的佳音,直到九月而未得,才決定回鑾,“若久稽于外,以竢邦交大典,于心有所不安”②。
太廟獻俘詔書中只言復仇恢復舊疆,不提新辟北河之地,顯然,阮福映心中已經有了計較。阮福映又遣黎光定等人出使清朝:“帝既克北城,移書兩廣總督臣,以事轉達清帝,令復書言:‘我國既撫有安南全境,自應修表遣使請封。其前部使鄭懷德等令轉往廣西竢請封使至,赍進燕京候命正路等以聞。’帝命光定等赍國書品物往請封,且請改國號為南越,命北城修造行宮使館。帝以邦交事體關重,令城臣仿黎故事,增構殿宇及河津、接使堂。又令諒山修仰德臺,自珥河至諒山,量地置驛凡七所,各設公館。”③
兩相比較,因“省煩費”而作罷的鎮南關遣使不過數月之前,而遣黎光定出使請改國號、與清朝再建邦交,隨即按黎朝規制從諒山至北城修建驛站使館,以迎接清朝使臣。鄭懷德等人告清“復仇”之事,黎光定則使清求封“南越”新國號。在阮福映看來,擁有新國號即意味著新建國家。阮福映之所以太廟獻俘只言復仇成功,還在于歷代阮主向清朝請封皆遭拒絕,此時貿然告先祖平定北河、新建國家之事,若再遭清朝拒絕,何以向列圣交待?故而他決定只言復仇,新建國家待請封之后再行報告先祖。
阮福映熟讀史書,知曉趙佗南越國在歷代國統中的力量,也知曉南越國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故而在請改國號詔書中提出另外的理由:“竊念臣之先祖,辟土炎郊,日以浸廣,奄有越裳、真臘等地方,因建國號南越,父傳子繼,二百余年。茲臣遙仗天威,掃清南服,有此疆宇,亦由先祖肇基南越之所自也。臣自惟締造伊始,實切兢惶,謹遣陪價恭遞菲儀,詣關候進,以白畏天服事之誠,伏望圣聰曲垂軫顧,錫以榮封,兼賜國號南越,俾臣賴得荷殊恩,繼先志,奠安南服,永保藩封。仰大皇帝幬覆柔懷之德,感佩于無窮矣。臣不勝惶恐戰栗待命之至。謹奉表以聞。”(14)《古代中越關系史資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92頁。阮福映提出先祖已經建號“南越”并傳繼二百余年,現在請求大皇帝賜號,確定名分。盡管阮福映信心十足,已經建立驛站使館迎接清使,但顯然低估了“南越”名號的潛在力量。嘉慶帝君臣因“南越”涉及趙佗南越國轄有廣東廣西地區,堅決不允改號,又恐阮福映有圖謀兩廣之心,令邊臣嚴加防備,并要求改回“安南”舊號。
阮福映請封“南越”國號意在宣示自己新建國家,改用“安南”舊號如何使得?鄭懷德和黎光定兩部使臣滯留南寧,清朝要求不改回舊號不得進京,使臣秉承阮福映之命拒不同意,雙方僵持不下。廣西巡撫孫玉庭認為不應當以字面挫折遠人之心,提出使用“越南”為國號,取“百越之南”之義,既不離阮福映所堅稱的“南越”國號宗旨,也與兩廣地域無涉。嘉慶帝同意用“越南”國號。阮福映亦無異議,遂受封“越南國王”,使臣進京覲見,圓滿完成出使任務(15)葉少飛:《中越典籍中的南越國與安南國關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
阮福映最大的目標在于用新國號體現自己新建國家,因而希望以赫赫有名的“南越”作為新國號。但“南越”牽涉太深,清朝拒不同意,使用“越南”以示和兩廣地域有別。對阮福映而言,只要不用“安南”舊號,“越南”亦是嘉號,新建國家之意亦明,故而欣然接受。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清使廣西按察使齊布森由鎮南關至北城宣封,阮福映隨即派黎伯品等使清謝恩。二月,阮福映“建國號曰越南”,“丁丑以事告太廟,禮成,帝御殿受賀,下詔布告中外”,詔曰:“帝王啟建有邦,必先崇國號以昭示一統。粵我列先圣王肇基伊始,辟土炎郊,奄有越裳以南之地。因以‘越’字名國二百余載,累洽重熙熙,衍圣神傳繼之基,保中外謐寧之運。頃因中葉國步多艱,予以藐躬思平僭亂,今仰憑靈貺,獲紹前庥,交南封疆,咸歸版籍。深惟顯謨承烈,居正作新,其以本年二月二十七日虔告太廟,改正國號為越南,以樹丕基垂久遠。凡本國事體有關于國號及諸有柬書報告外國者,并以‘越南’名國,毋得系稱安南舊號。又詔報暹羅、呂宋及真臘、萬象諸屬國,俾咸知之。”(16)②③④⑤ [越]張登桂等纂修:《大南實錄》正編第一紀第3冊,東京:有鄰堂影印本,1980年版,第646—647、676—677、677、699、701頁。如今擁有新的國號,且已經請封成功,歷代先祖“奄有越裳以南之地”,而今“交南封疆,咸歸版籍”,“顯謨承烈,居正作新”,顯示這是一個包括南河舊疆和北河封疆的新國家,國號“越南”,特告太廟,使中外知聞。
(三)即皇帝位
阮福映拒絕黎鄭族人所稱的“國自趙武以至于丁黎李陳,世稱帝號,具在簡冊”,而是不斷強調先祖肇基南服,顯示自己所受來自于先祖新建之國而非黎朝舊統,因而復仇之后即新建“越南”國家。
阮福映的心思如此細膩深邃,以至大臣亦難以體會。嘉隆四年(1805)二月,群臣再次上表勸進:“竊惟皇者初冒天下,帝者主宰天下,故立天下之正位者,必膺天下至鴻名,所以承正統垂后嗣也”,如今“圣上天錫智勇,作民元后,宅舊邦凝新命,功德隆厚,前代罕比,誠宜丕正帝號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愿圣上誕膺皇帝尊號,明示統紀”②。“宅舊邦凝新命”來自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雖然典籍可征,但并沒有體現出國家新建的氣象,自然不合阮福映心意,所以再次遭到拒絕,史載:“帝諭之曰:‘一初經理他務未遑,竢后再議未晚也。’”③
阮福映如此態度大出群臣意料,經過一年的揣摩探詢,嘉隆五年(1806)正月,“群臣復上表勸進,請正帝號。帝從其請,命禮部蠲吉鑄金冊”④。朝廷隨即開始稱帝的準備,“二月甲申,初建南郊壇”,“三月丁巳,初建社稷壇。命諸城營鎮各貢其方土以筑之”⑤。祭祀天地乃是真正的天子大祀禮儀。
嘉隆五年(1806)夏五月,“帝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土德王,色尚黃。前六日甲寅祇告天地,丙辰祇告列廟。是日設大朝儀于太和殿,群臣奉金冊上進”。群臣在勸進冊文中充分體現了阮福映大圣至德、文治武功鼎盛,繼承列圣基業,吊民伐罪,掃平逆賊,最終實現全越幅員一統。冊文的中心和重點在于表現阮福映“兼中興創業之難”。“中興”是阮福映營建嘉定京之時就一直倡發的政治理念,直到徹底擒拿阮光纘并獻俘太廟,中興大業始告完功。“創業”則是阮福映之前的詔書從未提及之事,阮福映以列圣肇基之南河舊疆,收北河壤土,歷經艱難險阻而完成國家再造,又請封“越南”國號,宣示中外,實為創業開基之主。如此大功至德,方登皇帝之位,萬世永尊。
第四次勸進的冊文深得阮福映之心,“帝即皇帝位,下詔布告中外,群臣上表稱賀”。詔書幾乎重復了冊文的內容,最后曰“弘先圣之業,正我越之統”。這里雖然沒有說明“我越之統”從何而來,但當是先祖肇基南服之統而非趙、丁、李、陳、黎之統,此處的“我越”乃是“我越南國”,而非前代之“大越國”。阮福映自嘉定稱王開始“中興”,至此即皇帝位建“我越之統”,成為新“越南國”的開基創業之君。
四、結語
18世紀末的越南波詭云譎,已經割據百年的阮主政權因權臣張福鑾亂政激起西山阮岳阮惠兄弟之亂,北方鄭森則因廢長立幼根基不穩,西山兄弟利用鄭阮之間的矛盾,先投靠鄭氏滅阮,又以“扶黎”為名反擊滅鄭。黎朝末帝黎維祈逃亡清朝,乾隆帝以“存亡繼絕”大義派孫士毅送其返回昇龍,但黎維祈并無掌控復雜局勢的政治能力。隨即阮惠在順化稱帝,建元光中,率軍北上擊敗孫士毅,黎維祈隨清軍回國,黎朝徹底滅亡。阮惠上表請罪,乾隆皇帝不再插手安南內部之爭,封阮惠為“安南國王”,清越朝貢關系恢復。
被阮惠數次擊敗的末代阮主侄子阮福映反攻嘉定稱王,秉承了傳統儒家政治文化塑造政權,營建嘉定京,修城池,建太廟,奉國母,祀文廟,褒獎功臣,從制度到形式重建阮主政權,以“中興”為號召恢復阮主舊疆,得到了臣下的一致認同,不斷積累力量。
1792年,阮惠去世,繼位者阮光纘才干不足,又與阮岳一系發生內訌,阮福映趁機逐步反攻,終于在1801年重新攻占順化。阮福映再次強調“天啟中興”,舊疆盡復。1802年五月,阮福映改元嘉隆,卻以殘賊未滅為由拒絕群臣稱帝的請求。面對歷代阮主夢寐以求的北河昇龍以及黎朝數百年的天命人心,盡管大臣言此是取國于西山逆賊而并非取國于黎,但是阮福映仍以復仇滅賊為號召攻占北河,存恤黎鄭族人,恢復祭祀,又拒絕了黎朝舊臣勸進稱帝的請求。阮福映凱旋獻俘太廟,報列圣舊疆盡復、大仇得報,中興功成。
阮福映政權的一切制度都在向稱帝的方向前進,但其兩次拒絕即皇帝位,并非是不想稱帝,而是在謀求塑造新的國家之政治合法性來源。李、陳、黎三代國統傳承有序,又均以“大越”為國號,若接續前朝國統亦是常理,但他意不在此。他屢次強調先祖肇基南服傳承二百余年,這才是阮福映認可的國統來源,即自己以南河舊疆攻占北河壤土,塑造新的國家。
但更改國統乃是大事,非但黎鄭舊人,即便從龍之臣,亦受黎朝國統影響甚巨。阮福映由外而內,以向清朝請封“南越”國號的形式來改變國統,稱先祖奄有越裳之南而建此國號。嘉慶帝以“南越”國號牽涉兩廣地區斷然拒絕,孫玉庭提出改稱“越南”,阮福映表示接受。嘉隆三年正月,清使齊布森宣封新國號;二月,阮福映告太廟,下詔布告中外。阮福映即以新的越南國號宣示自己新建國家,國統來自于列圣肇基南服,而非陳黎所在的北河安南舊地。
嘉隆四年群臣第三次勸進稱帝,但未能體會到阮福映新建國家的深意,故而再次被拒。群臣經深入研究,于嘉隆五月正月再次上表勸進。他們以“中興創業”立意,阮福映欣然同意,隨即建造南郊壇、社稷壇,五月即皇帝位。阮福映成為阮主政權的中興之主,亦是越南國家的創業之君。
然而傳統政治力量太過強大,嘉隆十一年(1812)十二月“復國號曰大越”,來自北河的李、陳、黎的“大越”國統與阮福映新建的肇基南服的“越南”國統合并,阮福映兼為“大越國”和“越南國”天子。
縱觀阮福映政權的發展歷程,其以傳統儒家政治文化塑造政權,對清先稱“復仇”大義,再受封“越南”國號,成功利用朝貢關系為新政權披上一層合法性外衣。這既充分展現了清越朝貢關系所具有的雙向力量,也生動反映了越南一方對它的認識與利用,以及由此所獲得的巨大政治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