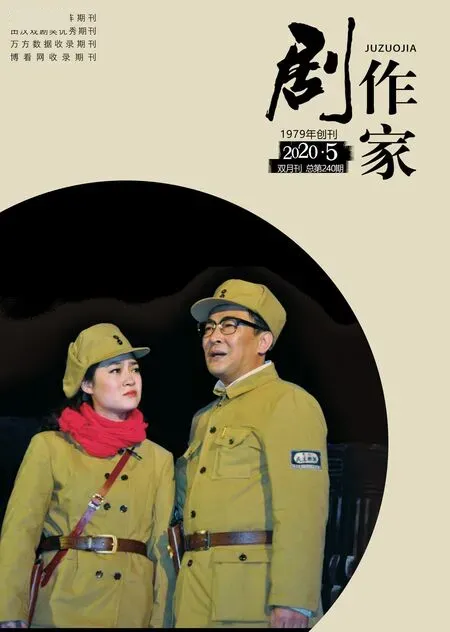單人劇的隱喻敘事
——論郭寶崑的《鄭和的后代》
■ 鐘海清
郭寶崑1939年生于湖北,1949年移居新加坡。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這一年,郭寶崑從悉尼國立戲劇學院畢業,與妻子吳麗娟創辦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由此開始了他近四十年的戲劇藝術生涯。郭寶崑跨越語言、族群及文化的界限,他的一系列充滿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品對新加坡戲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稱為“新加坡的戲劇之父”[1]。在郭寶崑的中后期作品里,出現了很多單人表演的獨白劇。郭寶崑為何選擇單人表演這種形式?是為了更自由地反思體制,還是為了突破早期作品的“罵觀眾”策略?這樣的做法在傳統作家中很難找到,即使高行健在后期創作中出現了單人表演,但也不像郭寶崑那樣如此“癡迷”。可惜學者對他及其作品的關注并不多,故本文從單人劇的角度展開對《鄭和的后代》的研究,期待在總結郭寶崑的單人劇作技巧的同時,為中國當下的單人劇創作提供反思的契機。
一、單人劇的若干探討
1.國內單人劇研究
從中國知網可查閱的論文數量來看,單人劇的研究似乎并不受學界的重視。較為系統研究的,有李欽君和王心怡的兩篇碩士學位論文[2]。其中,王心怡的學位論文《從單人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談女性角色的解讀與塑造》分析了孟京輝從小說中改編過來的單人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3]。而李欽君的《單人劇表演的主要特點研究及在教學中的應用》[4]則探討了單人劇的定義、基本藝術特征及其在教學中的運用。某種程度上,李欽君這篇碩士論文填補了中國大陸戲劇界對單人劇的研究空白。
中央戲劇學院院報《戲劇》刊登了一篇美國學者艾斯特·金·李的譯文《美國亞裔戲劇中的單人表演研究》[5],也豐富了我們對亞裔單人劇表演藝術的了解。此外,尚有零星的幾篇相關文章,如王文淵的《孤獨的表演之旅——澳大利亞單人劇〈查爾斯·狄更斯表演的圣誕頌歌〉》[6]是篇關于單人劇的演出劇評。
相對而言,中國臺灣的杜思慧在單人劇方面的研究應屬于開創性的。她有專著《單人表演》出版,同時也有著豐富的單人表演實踐經歷。她在書中對單人表演做了學理上的分析,也闡釋了她本人的創作作品,并在結尾給中國的單人表演做了一份翔實的資料匯編,列出了世界上研究單人表演的網站。
2.單人劇與單人表演、獨角戲、獨白劇
很多時候,人們對單人劇、單人表演、獨角戲與獨白劇的認識是模糊的。有些美學辭典或藝術辭典對單人劇下了一個定義,但這些定義的應用范圍是非常窄的,或者說,隨著戲劇藝術或表演實踐的拓展,其適用范圍已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日本的《美學百科辭典》這樣定義單人劇:“一個演員獨自演出的劇。但是也有不說話的輔助演員和合唱隊……有時,劇中的獨白脫離整體而獨立表演。”[7]又如《西方現代文學藝術辭典》則這樣定義單人劇:“該詞有三種含義,但基本含義都是一個人講話的劇情。該詞的第一個含義便是戲劇中的獨白。該詞的第二個含義通常是指講一個人與劇情發展密切相連的故事的一組韻律和詩節不斷變化的獨白。該詞的第三個含義是單人演出的獨腳戲。”[8]
在李欽君的碩士論文中闡釋道:“單人劇以演員扮演一個角色或多個角色為主要形式,以講述角色的經歷和抒發內心感受為主要內容,它帶給了觀眾一種全新的觀劇體驗和感受。”[9]這個表述,應該是基于臺灣杜思慧對單人表演的認識。
從上可知,單人劇有時與其他三個概念等同起來,有時被刻意地拉開距離。例如,李欽君為了區分單人劇與獨角戲,特地將獨角戲定義為一種以即興為主的喜劇表演;又將單人劇定義為以獨白為依托。
篇幅有限,本文不可能對這四個概念一一理清,更無法將它們的差異嚴格區分開來。筆者且簡單做一些區分,以供參考。
首先,單人表演包括了單人劇,像脫口秀、單口相聲等非故事性的節目也屬于單人表演的范疇,甚至單人演講表演也可歸類于此。一般來說,單人劇屬于戲劇類的單人表演,具有戲劇藝術的基本特征。如人物的角色性、故事的完整性、虛擬的表演性(不是即興意義上的互動表演)、主題的文學性等。
其次,單人劇的概念比獨角戲要廣一些。單人劇包括了獨角戲的范疇,但單人劇并不一定只有一個演員(可以有歌隊、影像、木偶等元素),而獨角戲通常指一個演員在不同角色之間跳進跳出的單人劇。
再次,單人劇與獨白劇具有一定的交集,但不等同于獨白劇[10]。單人劇可以是獨白為主體的單人表演;但獨白劇既有單人表演的形式,也有多人表演的形式。進一步說,獨白劇更偏向于獨白表演的處理與調度,同時其臺詞也一般更具文學性及詩意化。
最后,獨白劇一般不等同于獨角戲。獨角戲常常一人飾演多角,即演員需要自己跟自己對話。但獨白劇通常不需要跳進跳出,即使存在,其所占的比重也不多。說到底,獨白劇更考驗劇作者的臺詞功底和結構能力,而獨角戲更考驗演員的控場能力和個性化演技。
3.無對手交流≠無對象交流
李欽君在其碩士論文里,用了一節的篇幅來論述單人劇的無對象交流。“筆者所論述的無對象交流是指演員這個實體與存在于劇情中、但不在舞臺上出現的‘隱形人物’之間的獨特的一種交流方式。‘隱形人物’既非鬼魂又非演員臆想出來的對象,它存在于演員的回憶、想象和心理空間當中。”[11]可見,李欽君肯定單人劇有一個“隱形人物”是舞臺上演員與之進行交流的。但為何說單人劇是“無對象交流”呢?僅僅是因為他是“隱形人物”嗎?
這個觀點在王心怡的碩士論文中也有所論述:“筆者認為,無對象交流可以打破單人戲劇空間里的墻,將交流與傳遞通過多種表演方式,例如默劇、舞蹈肢體的表達來尋找交流與傳遞的窗口和對象。演員自身、影像、觀眾都可以成為單人戲劇空間里演員表演的心靈依托和交流對象。”[12]既然“演員自身、影像、觀眾”都可以是單人劇的交流對象,又何以說單人劇是“無對象交流”的?
在我們看來,單人劇的表演方式不是無對象交流,而是一種無對手交流的表演樣式[13]。何為無對手交流?簡單說,就是舞臺上的演員不存在“間際氛圍”[14]的交流。有時,即使舞臺上有兩個或多個演員,也存在著無對手交流的表演狀態。在一些歌隊表演中,每個演員可能只說自己的臺詞,而不需要產生交流。如漢德克的《罵觀眾》,演員之間就不存在對手交流,但跟舞臺下的觀眾產生了交流。
還有在一些特殊的語境中,人物角色各自說著自己的話。這些臺詞表面上像是對話,其實本質上還是人物的獨白。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大段臺詞的劇本里。如在漢德克的《非理性的人終將消亡》里,幾個主人公的大段臺詞情況竟出現了60次。
戲中有些人物在另一處看不見的空間,舞臺上只有一個演員,但他也處于一種交流的狀態。如美國劇作家埃爾默·賴斯《加算機》中的零太太正在做家務,跟零先生聊天,說了很多生活中瑣碎的事情,但零先生并沒有回應——整場戲就變成了零太太一個人的獨白。
單人劇不但不是無對象交流,反而更應分清劇中的人物到底是在跟哪個對象交流。在有些臺詞中,一會跟觀眾交流,一會跟自己內心交流,一會又跟看不見的人或物交流。不區分開,演員自己既不能準確地傳達出角色的狀態,也讓觀眾如墜五里霧中。
二、《鄭和的后代》的隱喻敘事策略
李岑帆、朱偉華在《新加坡“戲劇之父”郭寶崑創作研究》一文中,將郭寶崑的戲劇活動概括為三個階段:“一、批判現實體制的早期創作(60―70年代);二、關注社會傳統中個體生存的中期作品(80年代);三、結合社會現實探尋個體生命存在意義的后期創作(90年代)。這三個階段不可斷然分開,它們緊密聯系,早期作品對體制的批判,是第二時期個體關懷的現實基礎,而后期生命意義的探尋,則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鋪墊展開。”[15]郭寶崑的單人劇作品[16]主要出現在中后期。新加坡《聯合早報》編輯余云認為,郭寶崑“真正的藝術生命”是從1984年完成、1985年首演的短篇單人劇《棺材太大洞太小》開始的[17]。而《鄭和的后代》則延續了郭寶崑在《黃昏上山》中出現的無法辨別雌雄的大鳥、被閹割的神秘老人等意象,以太監鄭和的后代的荒誕的口吻,表達新加坡創傷的文化身體,同時對生命進行終極關懷,并反思社會更加深層的文化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鄭和的后代》內在的隱喻敘事。隱喻作為一種認知現象,其對人類思維方式、藝術創造、技巧策略等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它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中的修辭手法,更是被學者用于哲學、心理學和其他跨學科角度的研究。篇幅有限,不能展開論述。簡單說,隱喻,就是借一物或一事來說明另一事或擺出自己的觀點。它在作者構建作品的藝術特色時起到重要作用,比明喻(直白)更加靈活,富有形象性和意味性。《鄭和的后代》的隱喻敘事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貫穿意象,二是借夢說事。
1.貫穿意象
意象是一切藝術的魅力之所在,它將客觀之“象”與藝術家的創作情感相結合,塑造出具體的有意味的詩化形象;而在這詩化形象之中又往往包含了一種由之而升華的審美意趣。在戲劇中,意象是一個獨具魅力的創作技法。如《牡丹亭》《桃花扇》《雷雨》《茶館》及《青鳥》《海鷗》《櫻桃園》等名劇,之所以能產生巨大的震撼力,就在于它傳達出詩化的哲理,并將人物關系與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達到了意象與意境的統一。意象是劇作家對于現實人生的高度概括、精心提煉的產物。正如艾斯林所說:“戲劇不過是我們稱為現實的這種假象的結構加上另一方面的假象,戲劇是我們作為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種完美的意象。”[18]
戲劇中的貫穿意象,是指作者借這個意象統領全劇,并蘊含了該劇的主題表達。雖然一個劇可能有多個意象,但有的意象并非貫穿全劇,同時也不蘊含深刻的主旨。例如,郭寶崑的《棺材太大洞太小》運用了棺材意象的隱喻策略,反思了現實中每個社會都會面臨的問題,而“請了十六個苦力,由他們合力把棺材由靈車扛到墳口去”更是隱喻著傳統的厚重性和壓迫感。
《鄭和的后代》是郭寶崑最重要的單人劇作,全劇一共16場獨白,而閹割的意象則始終貫穿于其中。第3場獨白談到北京故宮里999個房間中,有一個房間裝滿了太監們被割下來的已經風干的吊在半空中的寶貝。太監的官越大,他的寶貝吊得越高。第4場獨白,談到自己的偉大學術發現:太監死后,他的寶貝要“寶歸原處”。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客死他鄉。就是說,叱咤風云的千古人物竟然死后不能全身而葬。第5場獨白轉換口吻,鄭和述說自己被閹割的過程。結尾又回歸作者的講述,談太監這東西倒是東西文化平起平坐。第6場獨白談道,自己夢里變成航行抵達非洲東岸的偉大航海家鄭和,突然醒來,害怕自己沒有了寶貝。“緊張萬分的伸手向下摸……這時候我多么高興我并不是鄭和啊,不管他是多么偉大的航海家、軍事家、政治家!”第12場獨白談到羅馬貴婦們喜歡給男奴“凈身”……第14場獨白說道,鄭和到了每個人都有王一樣權力的“人人之國”,發現美中不足的是,這里也有蓄養太監的習慣。第15場獨白說道,“人人之國”的保姆年復一年揉捏男童睪丸,直至生殖能力被摧殘。第16場獨白是一節詩,來回切換敘述者與鄭和的人稱,以抒發“我沒有家,我失去了性,我沒有了名”的悲劇人生。
單人劇雖然沒有對話的語境碰撞,但話題總得不停進行下去。通常情況下,一部單人劇不太可能只談一個話題,而是在一個主體話題中不斷地來回轉移。這樣就產生了話題的分形與回歸,即分形的話題總是在某個時刻出現,進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又要回歸到主體話題中來。話題分形的情況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因相近或相關的話題而分形,如“人人之國”的描述。這個話題結束后又要回歸到主題(貫穿意象)上去。另一種是出于主題的需要,如作者直面觀眾說出一些政治態度社會批判,如最后一場的“我沒有家,我失去了性”。
可見,閹割意象既貫穿了《鄭和的后代》全劇,同時在結構上充當了分形之后的回歸主題。它隱喻一種既定的社會制度,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只要有特權就會有閹割的太監。劇中雖然只是敘述鄭和一個人,但它其實已經超出了個體上的閹割,象征一種割裂的文化傳統。這傳統是摧殘與榮華、恥辱和成就的綜合體。眾所周知,旺盛的生命力總是與青春、健康、生殖力這些聯系在一起。雖然在“人人之國”里,每個人都有王一樣的權力,但太監的制度依舊存在。不言而喻,太監象征著人性中極為陰暗的權力與欲望的犧牲品,只要有權力與欲望的糾纏,那再合理的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完完整整地消除“被閹割的太監”。
2.借夢說事
借夢說事,也是一種很好的隱喻敘事策略。簡單說,就是一種以虛代實、虛實結合的美學范疇。關于這一點,可從中國傳統的繪畫之中尋到其類似的審美表現。中國畫家利用“虛實”把自然之境化為有意味的心象,從而創作出一種象與意相結合的作品。劇作家則借夢境自由地開拓人物的深度與廣度,讓自己的主旨表達更富有異樣的審美取向。
在黃維若先生看來,“戲劇中的夢中人物有以下一些功能:A.以插曲式的夢境場面,使人物動作出現突破性進展;B.以夢境中人物的精神自由,表現人物無意識(潛意識)及人物平時深藏不露的心理內容;C.以夢境中人物的行動自由,極大地擺脫人物的時間空間與具體事物邏輯的限定性,得以在更為廣闊的領域推進戲劇動作;D.以夢境中人物的獨特與自由,形成一種奇特的人物關系;E.以夢境中人物之口,說出作者自己的許多意念;F.通過對夢境戲劇場面的組織,獲得一種戲劇結構。”[19]
應該說,郭寶崑這幾個單人劇中的人物屬于“以夢境中人物之口,說出作者自己的許多意念”這一類型。例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的故事以夢開頭――“不懂為什么,這件事老是要回來,這個夢。”在結尾的時候――“這件事常常在夢里回來。”可見,在借夢說事的隱喻敘事中,一方面給讀者對傳統文化留下一個更深的思考,真假與否,并不重要。另一方面棺材作為全劇的貫穿意象,總是出現在夢里,它隱喻了傳統與當代的沖突自古至今總在不停重復著。所以,郭寶崑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心結——“我就不由自主地常想:‘我將來應該辦一口怎樣的棺材呢?’”[20]也就是說,郭寶崑開始接受一個沒有明確立場的戲劇結局,只是把自己的反思與困惑拋出來,讓觀眾自己去思考。
《鷹貓會》里的敘述者說:“這應該是個夢!因為世界上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但是它又顯然不是個夢,因為我使勁地咬自己的肉,不論用多大力氣咬得我疼也咬不醒,所以那絕不是做夢……”[21]這一種現代意識流的夢充滿著隱喻和超現實的東西,令人感受到一種達利經典名畫《永恒的記憶》中的神秘感。同時,虛實結合的超現實敘事,使這個作品被解讀的時候有了更多的審美維度。
在《鄭和的后代》第一段旁白里,郭寶崑就借敘述者的口吻談到了夢――“最近我經常做夢;做夢已經成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了。”在夢里,他覺得自己的命運與鄭和同樣充滿了漂泊和虛無。荒誕的是,他甚至漸漸地“認為:自己根本就是這位太監大帥的后代”。這是一種諷刺性的敘事策略——太監怎么可能會有后代呢?!可見,敘述者追認鄭和為祖先,是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身份認同感。此劇用夢呈現明朝鄭和七下西洋這一歷史事件,表現鄭和種種隱蔽的、被壓抑的、不為人知的層面,是郭寶崑作品中“最深沉與深刻的一個戲”,隱喻了被閹割者經歷了失去本性的生命創痛。
郭寶崑通過“夢的加持”讓傳統的記憶作為自我的認知過程,也是在挖掘多元文化的力量資源。畢竟他出生于湖北,帶有華夏民族的血脈與文脈。
總之,《鄭和的后代》虛實結合的隱喻技法貫穿始終,具有現實批判與哲理思考的超越性,巧妙地將宏大敘事與個人體驗結合起來,既表現了個體生命的飽滿,同樣也表現了人性缺失的閹割制度幾千年已經“深入人心”。夢中敘述者感到害怕,但“我每天都渴望著進入那一場又一場的夢幻”。作者沒有把自己的生命體驗拒絕于既定的社會制度,而是將自己置身于歷史長河中——郭寶崑的中后期作品常常令人覺得戲跟現實非常相似,它超越了具體的歷史人物,每個國度都會發生同樣既可怕又真實的歷史情境。
三、單人劇何去何去
本文通過對單人劇的若干梳理,并從單人劇的角度探討郭寶崑的《鄭和的后代》,期待更多的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單人劇。在美學上,我們已開始注意到單人劇的即興喜劇效果、間離效果、獨白抒情及其獨特的社會批判性。在表演特色上,也探索了單人劇的一人飾演多角、極強的信念感、夸張的表情、豐富的肢體和個性化的表達等。在運用上,也有人將之用于表演教學、單人演講表演及跨界藝術當中。此外,世界各地也有跟單人劇有關的藝術節或專業網站,如加拿大維多利亞市的單人藝術節、韓國單人劇藝術節、芝加哥單人藝術節等。應該說,這些成果值得注意和總結,但我們在這個領域里還需要進行更全面、更系統的拓展性的研究。例如,單人劇作的技法、單人劇表演藝術家的比較、單人劇理論的專題研究及單人劇的行業聯盟。雖然單人劇比一般舞臺劇在執行及呈現方面更為簡單和簡易,但并不是說它是粗糙和便宜的代名詞,它應該有著自己的藝術特色和呈現方式。
注釋:
[1] 柯思仁:《戲聚百年·新加坡華文戲劇1913—2013》,新加坡國家博物館,2013年,第65頁
[2] 中國美術學院賀冰的碩士論文《單人演講表演文化及形式分析》(2015年)也算單人表演研究的一部分,但由于其專業與戲劇關系不大,故不列為單人劇的研究范疇。
[3] 王心怡:《從單人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談女性角色的解讀與塑造》,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4] 李欽君:《單人劇表演的主要特點研究及在教學中的應用》,上海戲劇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另外,李欽君雖然還有幾篇已發表的期刊論文也是研究單人劇的,但它們基本上不出其碩士論文的成果,或者就是碩士論文中的某一章節。
[5] 艾斯特·金·李著,邢劍群譯:《美國亞裔戲劇中的單人表演研究》,《戲劇》,2014年,第4期
[6] 王文淵:《孤獨的表演之旅——澳大利亞單人劇〈查爾斯·狄更斯表演的圣誕頌歌〉》,《上海戲劇》,2013年,第1期
[7] 竹內敏雄主編,池學鎮譯:《美學百科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頁
[8] 范岳,沈國經主編:《西方現代文學藝術辭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387頁
[9] 李欽君:《單人劇表演的主要特點研究及在教學中的應用》,上海戲劇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第5頁
[10] 關于獨白劇定義及其外延的研究,可參見拙文《獨白劇場中的有聲語言創作》,發表于《晉城職業技術學院》,2020年第3期。
[11] 李欽君:《單人劇表演的主要特點研究及在教學中的應用》,上海戲劇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第31頁
[12] 王心怡:《從單人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談女性角色的解讀與塑造》,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第20頁
[13] 大體上,演員在舞臺上表演主要有兩種樣式:一種是有對手交流的,即至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演員同時在舞臺上。另一種只有一個演員,包括一人飾演多角的情況。不管怎樣,演員都跟某一對象進行交流。關于獨白的交流問題,筆者已有多篇文章論述,在此不作贅述。可參見拙文《獨白戲劇及其舞臺呈現》發表于《新世紀劇場》2018年第4期。
[14] 間際氛圍,是德國戲劇理論家斯叢狄創造的術語,指舞臺上的演員之間是基于一定的間際關系和特定語境而進行交流的。
[15] 李岑帆,朱偉華:《新加坡“戲劇之父”郭寶崑創作研究》,《南大戲劇論叢》,2016年,第2期
[16] 郭寶崑的單人劇主要有《棺材太大洞太小》《單日不可停車》《鷹貓會》及《鄭和的后代》等。
[17] 余云:《生命之土與藝術之路——從郭寶崑劇作看他的文化人格》,《戲劇藝術》,2002年,第2期
[18] 艾思林:《戲劇剖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年,第91頁
[19] 黃維若:《劇本剖析——劇作原理及技巧》,《新劇本》,2012年,第1期
[20] 在柯正仁看來:“葬禮事件的結束,不僅不代表著敘述者與官僚體系抗爭之后的勝利,相反,卻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為敘述者形塑一個更巨大的困境……早期劇本中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轉化成為一種互相牽制的循環:在一個充滿吊詭的新加坡現實之中,沒有是非,也沒有結論。”柯思仁,潘正鐳主編:《郭寶崑全集·第二卷》,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5年,導言
[21] 柯思仁,潘正鐳主編:《郭寶崑全集·第三卷》,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5年,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