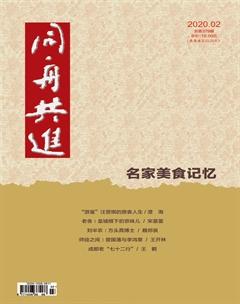劉半農(nóng):方頭真博士
魏邦良
劉半農(nóng)原名劉壽彭,與錢穆是常州府中學(xué)堂的同學(xué)。府中學(xué)堂首次招生,劉壽彭是江陰縣第一名;二年級考試,劉壽彭乃全校第一;年終考試,仍高居榜首。連中三元,劉壽彭成了學(xué)校名人,同學(xué)們都以結(jié)識劉壽彭為榮。
劉壽彭成績好,思想也進步。當(dāng)時,府中學(xué)堂舍監(jiān)陳士辛思想守舊,對學(xué)生管理甚嚴。一次,陳士辛在辦公室里將身為學(xué)生代表的劉壽彭訓(xùn)斥了一頓。出了辦公室,劉壽彭昂著頭,大呼:“不殺陳士辛,不為我劉壽彭。”小小年紀就顯露出桀驁不馴的脾性。四年級學(xué)年考試后,劉壽彭即退學(xué)去了上海,致力于小說創(chuàng)作,改名半儂。后應(yīng)蔡元培、陳獨秀之邀,赴北大任教,易名半農(nóng)。
做了北大教授,劉半農(nóng)仍然鋒芒畢露,沖勁十足。1919年6月5日,北大教授在一間簡陋的教室開會,商談挽留蔡元培校長事。當(dāng)時有位姓丁的理科教授上臺發(fā)言,此人方言重,說話啰嗦,在臺上嘮叨了半天,底下人只聽到幾個單調(diào)的詞:今天,北大,北大,今天……語不成句,不知所云。正值盛夏,悶熱難當(dāng),擠在教室里聽如此單調(diào)的長篇大論,誰受得了?這時,有人推門把劉半農(nóng)叫出去。不一會,屋外傳來劉半農(nóng)罵聲:“混賬!”里邊的人吃了一驚,那位丁教授聽到罵聲,不敢再啰嗦,趕緊下臺。等劉半農(nóng)回來說明情況,大家才知道,劉半農(nóng)罵的是北大法科學(xué)長,因為他不支持學(xué)生運動。沒想到歪打正著,屋外發(fā)炮,擊中了屋內(nèi)的丁教授。后來,劉文典對人說,他特別感謝劉半農(nóng)那句“混賬”。因為當(dāng)時他實在無法忍受丁教授的啰嗦,正準備上臺給他一個嘴巴,再低頭道歉。劉半農(nóng)一句“混賬”救了他。
劉半農(nóng)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也有“菩薩低眉”的時候。遇到壞人壞事,劉半農(nóng)是怒發(fā)沖冠的斗士,而在親友眼中,他又是一個溫情四溢的君子。
【慈】
劉半農(nóng)性格剛強,但心地非常善良。和朱惠訂婚后,劉半農(nóng)在岳家看到未婚妻穿的是纏足的繡花鞋。劉半農(nóng)就說:“她已經(jīng)和我訂婚了,也不必擔(dān)心嫁不出去了,何必吃這個苦。”岳母聽到未來女婿說這樣的話,當(dāng)然高興,因為她也不想讓女兒遭這份罪。能對女性纏足之苦感同身受,足以說明劉半農(nóng)之善。
結(jié)婚后,朱惠兩次流產(chǎn)。劉半農(nóng)父親以為兒媳沒有生育能力,為延續(xù)劉家香火,命令兒子納妾。劉半農(nóng)當(dāng)然拒絕了父親的“美意”,為讓妻子不受大家庭的氣,他把妻子接到上海,脫離封建家庭,獨立生活。
為進一步深造,劉半農(nóng)去英國留學(xué),因為不想和妻女分開,于是舉家赴英。不久妻子在倫敦生下一對雙胞胎,劉半農(nóng)的生活隨即變得異常忙亂。學(xué)習(xí)任務(wù)重,家庭雜事多,生活苦不堪言。全家五口人,全依靠劉半農(nóng)那一點微薄的留學(xué)金。為了貼補家用,劉半農(nóng)不得不在繁重的學(xué)習(xí)之余,不停筆耕。盡管身陷困境,但劉半農(nóng)毫不沮喪,他以一個男人的堅強,扛起家庭的重負,也以一個父親的慈愛,讓孩子們在寒冷的倫敦,享受到愛的陽光。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女性飽受壓迫,飽嘗凌辱。劉半農(nóng)在和妻子的一次談心中,道出了中國女性之苦:“世界最苦的人類,就是你們這班中國的女子。”他寫道:
然而你們是人類,以人類應(yīng)有的身份評判你們,你們卻苦極了。
第一,你們未嫁時,父母不教你們讀書;到了十歲以后,卻急急要替你們攀親了,人類是應(yīng)當(dāng)有知識的;你們父母卻不許你們有知識。人類對于本身,應(yīng)有自由處分之權(quán);你們父母卻要代為處分。這是養(yǎng)小豬的辦法:起初是隨便養(yǎng)它;養(yǎng)大了便糊糊涂涂的把它捉出圈去。
第二,到你們出嫁以后,因為自己沒有知識,所以不得不以‘無才為‘德;因為不能自立,所以不得不講‘三從;因為一失歡于男子,就要餓死,所以不得不講‘四德,不得不‘賢惠,不得不做‘良妻賢母。
其實,所謂‘無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謂‘三從,就是前后換了三個豢主……
劉半農(nóng)對中國女性之苦有如此深刻的認識,不僅在于他目光深邃,更是因為他有一顆善感的心,一副“憐香惜玉”的柔腸。
劉半農(nóng)雖身居象牙塔,但總能把憐憫的目光投向那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窮人。劉半農(nóng)寫過這樣一首詩《相隔一層紙》:“屋子里攏著爐火,老爺吩咐開窗買水果,說‘天氣不冷火太熱,別任它烤壞了我。屋子外躺著一個叫花子,咬緊了牙齒對著北風(fēng)喊‘要死!可憐屋外與屋里,相隔只有一層薄紙。”這首詩與杜甫那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異曲同工之妙。劉半農(nóng)的詩藝當(dāng)然不及杜甫,但他的慈悲心腸卻和杜甫一樣。
【諧】
劉半農(nóng)去世后,他的墓志銘是周作人撰寫的。周作人和劉半農(nóng)是至交密友,周氏筆下的劉半農(nóng)生動、逼真、傳神,如這段:“君狀貌英特,頭大,眼有芒角,生氣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勞苦。專治語音學(xué),多所發(fā)明;又愛好文學(xué)美術(shù),以馀力照相,寫字,作詩文,皆精妙。與人交游,和易可親,喜詼諧,老友或戲謔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
周作人說劉半農(nóng)“喜詼諧”,的確,一個“諧”字可貫穿劉半農(nóng)一生。在北大任教后,胡適、錢玄同、周作人都是劉半農(nóng)的好友。在和他們的交往中,劉半農(nóng)詼諧的一面展露無遺。
劉半農(nóng)和錢玄同的交情很深,且兩人都很詼諧,所以一見面就鬧。劉半農(nóng)記錄下錢玄同怕狗的趣事:“玄同昔常至余家,近乃不常至。所以然者,其初由于余家畜一狗,玄同怕狗,故望而卻走耳。今狗已不畜,而玄同仍不來,狗之余威,固足嚇玄同于五里之外也。”
劉半農(nóng)曾應(yīng)邀主編《世界日報》的副刊,錢玄同對《世界日報》早就看不順眼,得知老友竟被收買,而且看見報上聲稱“劉先生的許多朋友,老的如《新青年》同人,新的如《語絲》同人,也都已答應(yīng)源源寄稿”,氣不打一處來。隨即給劉半農(nóng)寫了封充滿火氣的信,表明嚴正立場:“我當(dāng)然是您‘劉先生的許多朋友之一,我當(dāng)然是‘《新青年》同人之一,我當(dāng)然是‘《語絲》同人之一;可是我沒有說過‘答應(yīng)源源寄稿給《世界日報》的副刊這句話。”
劉半農(nóng)以一首打油詩為這次爭執(zhí)畫了一個詼諧的句號:“聞?wù)f杠堪抬,無人不抬杠。有杠必須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猶他抬,杠還是我杠。請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錢玄同讀到這首打油詩,再火冒三丈,也只能一笑置之了。
周作人是劉半農(nóng)的另一位密友。劉半農(nóng)稱周作人為“方六爺”,這個典故出自《儒林外史》。書中有位成老爹,人很勢利,和別人聊天時,常吹噓自己見著方老五方老六了。方姓在當(dāng)時的安徽往往是做鹽商的富翁。五四之前,劉半農(nóng)和別人談話時常說自己見著魯迅、周作人了。于是,朋友們笑稱劉半農(nóng)是成老爹,魯迅是方五爺,周作人是方六爺。
劉半農(nóng)喜歡打趣別人,也習(xí)慣調(diào)侃自己。他曾請畫家王悅之給自己畫像,還作了一首《曲庵自題畫像》的詩,拿相貌狠狠自嘲:“眼角注成勞苦命(注:眼角下垂相者,言應(yīng)勞碌一世),頭顱未許竇窬鉆。(注:方頭,故不宜鉆狗洞)”周作人讀了這首詩,不禁手癢,當(dāng)即和了一首,不拘小節(jié),也把好友的相貌借題發(fā)揮:“眼斜好顯峨眉細,頭大難將狗洞鉆。”胡適也作了一首詩,和了劉半農(nóng)的自題詩,給了他一個傳世的外號:“方頭真博士,小胖似儒醫(yī)。”劉半農(nóng)的風(fēng)趣感染了朋友,真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趣者諧也。
【真】
劉半農(nóng)病逝后,周氏兄弟都寫了紀念文章。在周氏的共同朋友中,享有此殊榮的不多。
魯迅的《憶劉半農(nóng)君》雖褒貶分明,但流露的盡是真情;周作人的《半農(nóng)紀念》,貌似平淡,實則難掩沉痛。兩人不約而同在文章中提到劉半農(nóng)的“真”。
魯迅通過比較陳獨秀、胡適,來突出半農(nóng)之“真”:“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nèi)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guān)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nèi)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cè)著頭想一想。半農(nóng)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nóng)。”
正因為劉半農(nóng)坦誠實在,魯迅才不覺其“有武庫”,才親近他。在魯迅看來,劉半農(nóng)因為真誠而“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
作為劉半農(nóng)的至交,周作人認為,劉半農(nóng)有兩大優(yōu)點,其一就是“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卻是天真爛漫,對什么人都無惡意。”
劉半農(nóng)在北大時已經(jīng)是頗有名氣的教授,為何還要吃辛吃苦去外國留學(xué)?對此有各種說法。而劉半農(nóng)自己卻老實地告訴大家,是因為自己的知識不系統(tǒng)。在《留別北大學(xué)生的演說》里,劉半農(nóng)說:“我到本校擔(dān)任教科,已有三年了。因為我自己,限于境遇,沒有能受到正確的、完備的教育,稍微有一點知識,也是不成篇段,沒有系統(tǒng)的。”
劉半農(nóng)這樣的真人,從來不會往臉上貼金,相反,他總是有一說一,竹筒倒豆子。他還坦承,自己喜歡研究工作,不想做教書匠。甚至說教書“簡直是吃瀉藥”,雖然不妥,但和那些口是心非,兩面三刀,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的偽君子相比,劉半農(nóng)的實話實說要中聽得多。劉半農(nóng)是真誠的,真誠到他的缺點也一目了然。
1934年,周作人50歲,作了兩首詩,被林語堂以“自壽詩”名義刊登在自己主編的《人間世》。其一為:“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xué)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劉半農(nóng)讀后,直指作者在詩中撒了一些謊:“詩雖好,卻撒了一大堆謊,他不會作畫,也不寫草字,‘畫蛇之謂何?‘玩古董有些瞎吹,‘種胡麻更非事實,‘寒齋不寒,‘苦茶不苦……特發(fā)書復(fù),以明知堂是浪漫派,而區(qū)區(qū)則寫實派也。”可見,即便對自己的好友,劉半農(nóng)也不無原則吹捧,而是有好說好有壞說壞。
【勤】
在現(xiàn)代作家中,劉半農(nóng)的勤奮人所共知。
劉半農(nóng)中學(xué)畢業(yè)后,即去上海謀生。短短三年就發(fā)表了上百篇小說,在上海灘名噪一時。在海外留學(xué)那幾年,他的勤奮更是無人能比。為獲得博士學(xué)位,他要修多門艱深的課程,課余還得爬格子貼補家用,其間,家中的病妻弱女還須他照顧。除此之外,他還給自己一個額外的任務(wù),抄寫巴黎圖書館的敦煌資料。回國前,劉半農(nóng)去圖書館辭行,工作人員依依不舍:“博士回國后,這些書再也不會有人讀,只好喂蟲子了。”
胡適魯迅周作人在紀念文章中都提到劉半農(nóng)的勤奮,各人的側(cè)重點卻完全不同。
胡適說:“一個‘勤字足蓋百種短處。”胡適肯定了劉半農(nóng)的勤奮,“努力不斷”,但也沒有諱言其“缺少早期訓(xùn)練”,“有低級風(fēng)趣”。由此可知,胡適作為“血統(tǒng)純正”的博士,對劉半農(nóng)這種“半途出家”的教授,難免有成見。
魯迅在《憶劉半農(nóng)君》的最后,飽蘸感情地寫道:“現(xiàn)在他死去了,我對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并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nóng),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nóng),他的為戰(zhàn)士,即使‘淺罷,卻于中國更為有益。我愿以憤火照出他的戰(zhàn)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尸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魯迅對作為戰(zhàn)士的劉半農(nóng)贊賞有加,對他后來的保守和頹唐則極為不滿。在魯迅眼中,十年前的劉半農(nóng)和十年后的劉半農(nóng)判若兩人。十年前,劉半農(nóng)的“勤”于中國有益;十年后,劉半農(nóng)的“勤”,比如寫打油詩,為賽金花寫傳,給梅蘭芳做廣告等,在魯迅眼中,全是無聊而油滑的行為,于國無補,于人無益。
因為“勤”,劉半農(nóng)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獵、有所建樹。周作人很稱道他廣博的雜學(xué):“他的專門是語音學(xué)。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xué)美術(shù)他都喜歡,作詩,寫字,照相,蒐書,講文法,談音樂。有人或者嫌他雜,我覺得這正是好處,方面廣,理解多,于處世和治學(xué)都有用,不過在思想統(tǒng)一的時代自然有點不合適。”
周作人表面褒獎了劉半農(nóng)學(xué)問之雜,暗地里卻朝左翼文人放了一枝冷箭。因為,正是思想激進的左翼文人把劉半農(nóng)辛勤做事看成是無聊乃至“幫閑”的。
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三位高手借紀念友人半農(nóng),“燒”出了風(fēng)味不同的“菜”。
(作者系文史學(xu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