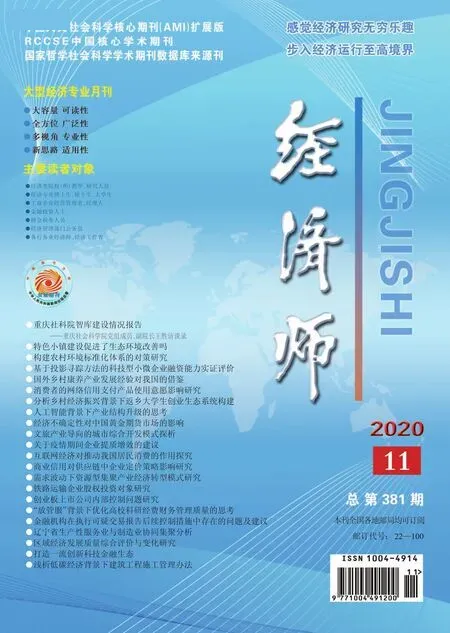集 體 化 時 期 工 分 制 演 變 的 分 析
●趙俊紅 高晉文
一、工分制的產生
中國最早有關工分(當時以工資為提法)的說法,是1933年在土地革命的根據地時期,中國共產黨發布的關于互助合作的第一個文件——《勞動互助組織綱要》。當時中國農村生產力水平低,農戶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工具非常匱乏,牲畜有限,逐步形成了農戶之間勞動力或是包括生產工具在內的生產資料的自發交換。這種現象被稱為“換工”。但這時換工計算的工分一般只作為農戶之間交換勞動力或生產資料的一種賬本,并沒有將工分換算成實際的貨幣。工分也按照農民自愿的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計算,并得到換工主體的認可。可見,這時的“工分制”主要是克服缺乏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不足的農戶的自身困難,在農戶之間自發形成的勞動價值的等價交換。其前提是私有制下的自由自愿和等價交換。
從最初工分制產生于農戶之間謀求合作的角度來看,它符合哈耶克的“自發秩序”,也符合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的動力來自于經濟主體對潛在經濟利益的追求。隨后,“換工”或“變工”的這種工分制,在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提倡,對提高邊區和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效率、增加糧食產量,并進而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和爭取全國解放奠定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二、集體化時期工分制嬗變及其制度分析
(一)集體化時期工分制的嬗變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改變經濟落后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開展土地改革,變封建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重建了私有制基礎上汪洋大海一般的個體小農經濟。從1953 年開始,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引下,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農業領域也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個體小農經濟走集體化道路,以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支持國家的工業化建設。
1956 年1 月,河北省邢臺地委書記總結初級社的經驗時指出,邢臺地區在近幾年大批建立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顯示出極大的優越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但是,初級社的發展逐步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生產需要,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顯著。許多貧苦社員比中上農社員多做了勞動日,但是由于土地極差報酬的存在,得到的總收入卻比中上社員低,因而積極性銳減①。從1955 年下半年開始,原來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普遍轉變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集體化運動進入高潮。如廣西區委決定,到1956 年,全區共辦高級社 2000 個。1957 年鄉鄉有高級社,約有 10000 個②。1956 年,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全國迅猛建立。年底,全國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87.8%③。為了使工分能夠準確地計量社員在集體勞動制度下勞動的數量和質量,1955 年11 月,中共中央發布《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一次對工分制的“定額計工”“死分活評”做出詮釋。這樣一種評工計分制度,既調動了社員勞動積極性,又省去了過去記錄繁瑣的弊端,方便于群眾。工分制轉變為國家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在從事生產活動中,衡量社員勞動的計酬、收入分配和規范社員行為的一項制度。這種工分制是之后其他所有工分制的雛形。
1956 年,中共中央正式頒布《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對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經營和管理,對社員、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資金、生產經營、勞動組織和報酬、財務管理和收入分配等方面,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規定入社的農民必把私有的土地和牲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④。一般來說,糧食、食用油等合作社生產的生活必需品是按照每個家庭的人口數量與工分數量以7∶3 的比例進行分配。每個家庭的人口數量在一個時間段里是固定的。這樣,決定社員實物和貨幣分配數量的多少就取決于工分的多少。
中國農村集體化運動與集體經濟的主體階段是人民公社時期。1958 年,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以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為標志的“大躍進”狂瀾⑤。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甚至社員的部分生活資料都歸人民公社所有。1958 年10 月底,全國共有26.5 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的農戶占全國總農戶數的99.1%⑥。公社是集體經濟的基本核算單位。人民公社普遍設立了以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為主要特征的公共食堂。這種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拉低了工分的價值。據親歷者回憶,社員渴望能夠真正衡量他們勞動數量和質量的工分,但是在集體勞動和集中分配中,社員無能為力,只能消極參與勞動,降低了社員的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農業勞動的低效率導致1959~1961 年糧食產量的連年減產。在這期間,中國農民發明了包產到戶這一變通的方法,以解決工分制的上述弊端。
1961 年,國家不得不實行國民經濟調整。首先是農業經濟的調整。《農業六十條》將人民公社所有調整為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明確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責、權、利。1962 年2 月13 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肯定了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農村集體經濟的基本核算單位的調整,并且規定這一政策至少30 年不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就此確定下來,也形成了人民公社最具代表性的,時間最長的基本經濟體制模式。
從初級社開始,社員實行集體勞動,集中分配,工分制開始逐漸偏離農民互助換工的愿望。經過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工分制完全變成了衡量社員生產勞動和實行收入分配的工具。“大躍進”運動時期,推行半供給制度,它取代了此前按勞動日計酬的工分。這是工分制一次較大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的效果并不理想。1962 年,人民公社調整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重新恢復了原來的“評分記工”的工分制。基本核算單位以生產隊為單位。但在“農業學大寨”的影響下,基本核算單位上升到以生產大隊為單位,成為此后一段時期內農業生產管理和收入分配的主要工具。
(二)工分制嬗變的制度分析
制度變遷是在制度變遷的主體、動力及適應效率的相互配合下完成的。制度變遷的主體主要是有效的組織,還包括個人和國家等,但有效組織是關鍵。有效組織可以是政治組織、教育組織,也可以是經濟組織等。其建立與運行的目的在于獲得潛在經濟利益。通過集體化建立起來的集體經濟,離不開中國農村傳統的自然村落這一基本組織。村落是以耕地作為空間布局,根據宗姓和血緣關系形成的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單位。費正清認為,中國“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單位(各個世系)組成,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種某些祖傳土地為生。每個農家既是社會單位,又是經濟單位。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據其家庭成員的資格取得社會地位”⑦。
制度變遷“來源在于相對價格和偏好的變化”⑧。而相對價格的變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偏好變化的誘因。相對價格的變化包括要素價格比率變化、信息成本變化、技術變化等。要素價格比率的變化對于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比較直接,例如,在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土地可以入股,勞動所得工分加上土地的分紅,成為農戶的最終收入。有些地區并未執行等價互利的原則,人畜換工時畜工的比價過高,對于無畜農戶而言,實際上是壓低了勞動力的價格;有的合作社內土地的分紅過高,收益甚至可以達到70%;還有一些完全將農具、耕畜、資金與勞動力等同,均按股分紅(上述這些不等價的情況實際上從互助組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一些地區的互助組或初級社也往往根據農村基層的政治人物的愿望或要求而不是根據全體社員的愿望或要求制定公平合理的等價互利的分配方法。)。因此,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受到打擊,對國家倡導的集體化運動情緒低落,不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當這樣一些問題出現之后,有些地區的互助組和初級社對于社員私有的耕畜和生產工具無償使用,農民的私有財產得不到保護,社員對于集體化的生產和生活信心遭到破壞。更有甚者,一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企圖過早地取消土地分紅。這種生產要素價格的不斷變化,導致工分制的嬗變。
三、工分制的嬗變緣于集體化的堅守
集體化時期工分制的嬗變緣于傳統社會主義對集體化這一意識形態的堅守。
工分制本來產生于自發秩序,與集體化并不相關。但是,在新中國集體化運動中,工分制卻成為國家推行集體化運動的重要制度之一。由于平均主義的存在,在集體勞動中,社員個人的偷懶成本被平均分攤給合作社的每個社員,因而鼓勵了社員的偷懶行為;同樣,社員個人努力勞動的收益也被平均分攤給合作社的每個社員,打擊了社員努力勞動提高勞動效率的積極性⑨。
在人民公社時期,各地基本都在社內推行工分糧與基本口糧的三七開或四六開的分配制度。1978 年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實行草案)》與1971 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確定的分配原則基本一致。這樣一種收入分配辦法,目的是保證廣大社員、軍人家屬、烈士家屬及五保戶等能夠得到基本的口糧,從而保障家庭的基本糧食消費需要。此外,工分在社員所在的集體經濟中,還起到核算集體經濟一個自然年度內的收入剩余的作用。
上述這些問題無法在合作社得到有效解決。然而,出于傳統社會主義對集體化這一意識形態的堅守,工分制在整個集體化運動中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時期發生了形式上的嬗變。從初級社開始,工分制作為衡量社員生產勞動和實行收入分配的工具的基本屬性并未發生變化。對經濟利益主體而言,既存在堅守集體化這一意識形態的單邊行動約束,同時,又在集體化這一制度安排下無法獲得潛在利益,從而發生了工分制的嬗變,以使經濟利益主體能夠獲得部分潛在利益。因此,工分制一方面在堅守集體化(公有制和集體經濟兩個方面,其中,公有制更具有意識形態上的意義)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基石性的作用,同時,在追求經濟主體的潛在利益方面,工分制又發生了許多的變化。工分制嬗變的這一特點,體現了經濟主體在堅守集體化過程中力圖實現對潛在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堅守和嬗變的結合,是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普遍實行以前工分制的最主要的特點。
四、結論
工分制是新中國計劃經濟歷史條件下推行集體化的一個邏輯環節。中國共產黨提倡農業合作化,并推動農業合作化轉向農業集體化,即力圖逐漸將個體農民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蘇聯式的集體農莊⑩。土地改革確認了農民對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權,而農業集體化的目標是建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共有產權的集體經濟。換言之,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是集體化的產物。這一產權變革的過渡時期和過渡形式便是從互助組經過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三部曲。這個三部曲是實現從私有制的個體經濟到公有制的集體經濟的橋梁。其中,工分制又是這個橋梁的核心,貫穿了集體經濟從生產到分配的全過程。
工分制的嬗變是堅守集體化意識形態的結果。但集體化與集體經濟并不是一個等價的概念,集體化具有運動式,是意識形態的范疇。集體經濟則是集體化運動的結果,它既不同于集體化,但它又是集體化的最重要的載體。工分制內生于集體化,而不是內生于集體經濟。工分制對集體經濟在進行勞動管理、評價和激勵勞動生產的過程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注釋:
①常青.重視小型社的合并工作.人民日報,1956.1.10
②王祝光.廣西農業合作經濟史料(上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③⑥趙德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下冊).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條
⑤謝春濤.大躍進狂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⑦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⑧李飛.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實績〉介紹.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2(2)
⑨瞿商.新中國農地制度的變遷與績效.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4)
⑩1951 年2 月,松江省(今黑龍江省)樺川縣的星火集體農莊就成立了。(羅平漢:《農業合作化運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78 頁)這是我國的第一個集體農莊,也是第一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集體農莊基本是參考蘇聯集體農莊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