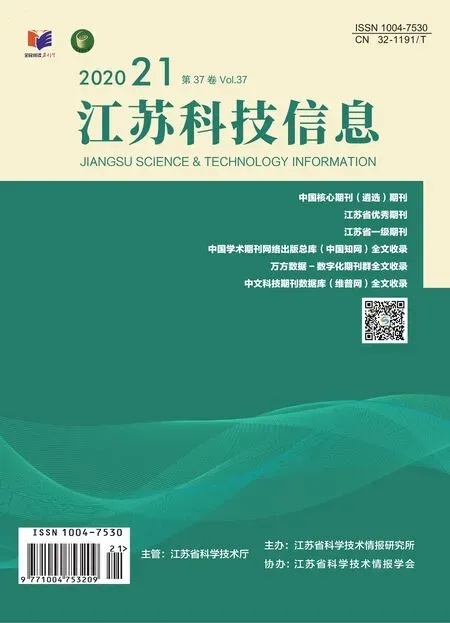圖書館導向系統的技術應用研究
曹泰峰
(貴州民族大學圖書館,貴州貴陽 550025)
0 引言
圖書館面積的增大和功能的豐富為讀者帶來了尋路困惑,幾乎所有相當規模的圖書館都會讓初入讀者感到恐懼和迷失[1],進而形成焦慮。為了解決讀者的空間迷失問題,學者們對圖書館的導向系統展開了相應的研究。其中,新技術應用最常被研究,幾乎每出現一次技術變革就會有與之相應的導向系統研究文獻出現。那么,學者們主要關注哪些技術,又是如何應用于圖書館導向系統之中?為了把握我國內圖書館導向技術應用的研究現狀,推動學術研究發展,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梳理有關圖書館導向系統技術應用研究的關注焦點,分析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思考和建議,為該領域的研究與實踐提供參考。
1 概念界定
1.1 導向系統的概念
導向系統是為了解決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工業化以來,城市結構越來越大,城市人口越來越多,為了避免迷路,找不到方位,于是出現了道路識別的系統設計,英文中稱為“wayfinding”,直譯為“找路”,本意為幫助人們在某個特定空間中判斷位置和方向,并采取計劃和行動以到達目的地的過程。作為一個學術術語,“wayfinding”首先出現于城市規劃領域,1960年被凱文·林奇定義為:“針對外部環境設計的一個具有持續使用性、準確的視覺系統組織。”[2]之后,這個術語被引入國內,“wayfinding”被翻譯為導視系統或導向系統,它是存在于一個基本的空間信息架構之上,利用各種元素和方法,有效地傳達方向、位置、安全等信息,幫助人們了解從此地到達目的地并且知曉返回路線的媒介系統[2]。導向系統不是簡單的標識標牌,而是圍繞某個特定空間而設置的一套體系,既包含一系列標識標牌,又可以涵蓋功能說明、導航定位、行為提示等內容。
1.2 圖書館導向系統
20世紀90年代,圖書館界就已經引入了導向系統的概念[3]。早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導向標識的探討之上,認為圖書館導向系統的基本功能在于“空間”的揭示與指引,從而幫助讀者在空間移動。這種認識延續了導向系統共性的探討,卻缺乏了對圖書館特定風格、屬性以及特定群體的尋路行為的思考。在圖書館,導向系統不僅有助于提高空間的使用效率,還有助于提高或實現空間的根本功能。美國楊百翰大學圖書館評估館員佐格·霍爾特[4]透過“空間”看到了導向系統背后的“價值”,他認為“導向系統是指幫助讀者快速、便捷地找到所需資源或服務的方法和工具”,能為讀者帶來滿意的、減輕壓力的圖書館體驗。它正滿足了阮岡納贊[5]圖書館學五定律中的第三項和第四項,即幫助讀者找到他們所需的書(或其他資源),并節省讀者的時間。
2 關注熱點
在導向系統的設計中新技術應用主要體現在其傳播媒介的應用上。傳統的導向系統往往以實物為承載信息的媒介,如紙張、竹木、塑料、石材、金屬、玻璃等,它們的應用往往隨著其材料合成技術、切割技術的發展而發展,但是其基本的展示方式沒有太大差異,并且難以改變其不夠靈活的問題。隨著技術的發展,燈光技術、聲控技術也加入到導向系統的應用之中,為視線較差的地區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導向系統的發展帶來了質的飛躍,既可以展現豐富的內容,又可以經常更換“主題”;既可以室內定位,又可以實現交互,成為理論和實踐中常常關注的焦點。
2.1 數字標牌
受承載信息材質的局限,傳統標識標牌具有展現形式單一、更新不夠靈活、缺乏與讀者的交互等問題,難以適應信息時代圖書館不斷發展的需要。網絡技術、多媒體技術的出現為解決上述難題提出了思路,即數字標牌系統。它是一種不受時間限制向讀者發布公共信息的多媒體視聽系統,有人稱它為平面媒體、廣播、電視和互聯網之外的“第五媒體”[6]。數字標牌系統由顯示終端、媒體播放器、管理系統、中央服務器等多個部分組成,具有很多優點,其一是功能豐富,不僅可以指示方向、揭示館藏,還可以發布信息、推薦服務;其二是形象直觀,不僅可以通過圖形文字展示信息,還可以通過圖表、視頻、音頻、flash動畫、網頁等多種形式展現內容;其三是交互性強,數字標牌系統可以實現信息的雙向流動,尤其是觸摸屏技術的發展使得讀者也可以便捷地向平臺發布信息。
2.2 物聯網標識
導向系統的最終目的是幫助讀者尋找資源,因此很多學者建議為資源加上電子標簽的方式幫助讀者定位資源。20世紀90年代,人們開始利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以非接觸讀寫的方式識別具體的物品。圖書館界將之運用于圖書的收藏和流通管理中,一方面為每一本圖書設置一個獨立的電子標簽,另一方面通過智能管理系統對圖書進行定位、上架、排架、盤點以及跟蹤圖書借還記錄,既節省了圖書館的人力,又提高了借還效率[7]。黃輝[8]建議有必要對圖書館的文獻資源、設備設施,甚至人員和服務進行標識實現資源的優化與改造,推動圖書館的智能化,實現人與人、人與物、人與圖書館、物與物之間的交互,實現即時管理、智慧管理。
2.3 二維碼定位
鑒于無源RFID只能單向定位,有源RFID標簽成本較高的原因,一些學者建議采用二維碼實現圖書館導向系統。彭吉練[9]認為,可以為重要區域和關鍵位置的標識上附以二維碼,讀者在通過傳統標識無法定位時可以使用手機掃描上面的二維碼,進而訪問圖書館的虛擬導向標識系統。在系統中,根據需要設置目的地,系統將自動繪制具體的導航路線,指引讀者快速到達目的地。實現二維碼定位導向系統的關鍵技術為二維碼生成技術和路徑導向算法。由于QR編碼內部容量僅有2 953字節,難以進行讀者交互,張莉娜等[10]依托微信公眾平臺,通過接入其Open API實現信息之間的傳遞與交互。利用微信公眾平臺開發的二維碼定位導向系統不僅具有傳輸延遲低、定位精度高等特點,還具有方便操作、便于推廣協同等優勢。更為重要的是,它將帶來由點狀閱讀向關聯性閱讀轉變,幫助讀者節約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2.4 VR與AR
虛擬現實技術(VR)是利用計算機模擬的一種虛擬仿真系統,它可以通過模擬環境的方式,增強用戶的環境沉浸感[11]。目前很多圖書館通過三維圖形模擬圖書館服務情境,通過游戲通關的方式解決讀者在利用圖書館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增強讀者的空間體驗。增強現實(AR)是另一種情境模擬技術,它可以使真實世界信息和虛擬世界信息綜合在一起,形成虛擬情境與真實場景的疊加,從視覺感受上來說,相當于把虛擬的世界呈現于人所處的真實環境之中[12]。AR與導向系統結合將能極大地提高了導向系統的直觀性和功能性,幫助讀者確定目標信息的位置,輔助讀者在圖書館展開尋路活動。美國邁阿密大學圖書館的ShelvAR、印度國家設計學院圖書館的LibrARi是AR技術在圖書館導向領域成功的應用;武漢工程大學的陳哲[13]開創了國內圖書館界AR技術應用于導向系統研究的先河;郝琳琳等[14]建議在圖書館建立“信息亭”呈現AR情境,激發讀者的內隱記憶,為了突破信息亭人數限制的瓶頸,開發相應的手機APP將是必然的選擇。
3 主要問題
3.1 深度問題
技術為導向系統帶來了方法和技術上的突破。然而,由于先前的研究過度關注于技術應用本身而忽略了導向系統的本質。實際上,導向問題歸根結底是用戶的問題。在新技術應用中只有了解用戶的內在要求,契合讀者的認知才能建設成高水平的圖書館導向系統。在智慧圖書館建設背景下,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技術、模式識別技術、傳感技術等技術的發展為收集、存儲讀者數據帶來了新的機遇。屆時,不僅可以形成對圖書館內讀者、資源及其所處的環境進行識別,還可以形成對讀者行為產生的信息進行計算、分析,以期實現對讀者的類型的自動判斷,對讀者需求的自動回應。
3.2 互聯問題
技術應用是管理的延續,是為了提高管理效率而進行的方法上的改進。之前的文獻大多關注于某項技術的應用,而缺少對技術關聯的研究。在技術快速更新的時代,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沒有辦法完全取代其他技術的應用,傳統介質與信息介質共存,新技術與舊技術共存將成為圖書館導向系統的常態。那么,它們如何共存以及系統之間如何互聯互通成為下一步研究的核心問題。
4 結語
信息技術將持續的更新,將會引領人們走進更加智能、更加智慧的時代,圖書館及其導向系統必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更新。在未來的導向系統新技術應用中,一方面需要緊緊圍繞用戶、發掘用戶需求、了解用戶認知、分析用戶行為;另一方面,需要注重新老技術的融合與更替,注重系統之間的妥善銜接,形成有價值的數據鏈。在此基礎上,未來的圖書館導向系統將能通過對讀者行為數據的挖掘與分析,自動識別讀者的尋路需求,并根據所在位置和行為為讀者提供尋路方案,高效智能地指引讀者到達目的地,獲取所需的資源與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