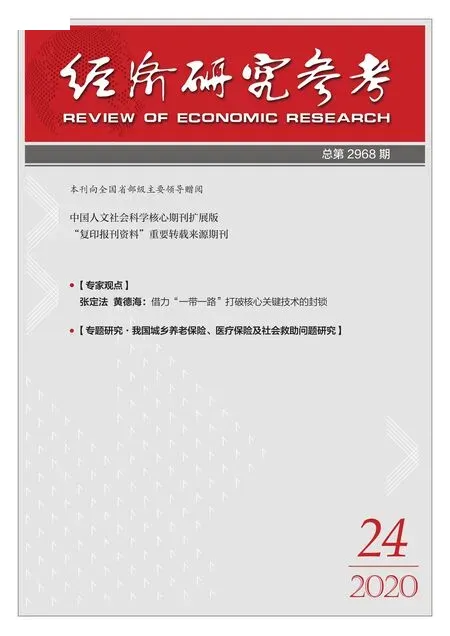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內涵與重要意義
黃群慧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大調整大變革之中。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都面臨著全球治理規則調整的制度之變與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創造式破壞,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更是使全球經濟發展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環境巨變要求戰略適應。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積極主動“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要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作為“十四五”時期發展的指導思想。這個新發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是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的必然要求。
雖然經濟學有眾多的概念和理論來分析描述經濟活動,但循環流動無疑是經濟活動的基本特征。無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經濟環節看,還是從西方經濟學中要素及產品市場的供給—需求經濟分析框架看,經濟活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個動態的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經濟活動的本質是一個基于勞動分工和價值增值的信息、資金、勞動力和商品(含服務)在家庭、企業和政府等不同主體之間流動循環的過程(黃群慧,2020)。如果考慮到經濟活動的國家(或者經濟體)邊界,經濟循環則存在基于國內分工的國內經濟循環和基于全球分工的國際經濟循環之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時代,很少有國家只有國內經濟循環,絕大多數基本上都參與程度不同的國際循環,參與國際循環程度的不同意味著經濟開放度的差異,無論參與國際循環的程度如何,其根本目的是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一個國家(經濟體)可以認為是一個開放的經濟系統,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程度可以根據系統環境和自身條件的變化進行選擇,可以通過國內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的協同互補來有效發揮一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同時避免國際環境的負面影響(曾劍秋、任淼,2005),這構成經濟發展的戰略導向。
基于上述認識,要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需要重點把握以下三方面內涵。
一是新發展格局立足國內大循環主體,以國內大循環促進國際循環,國際國內大循環相互促進。其實質意味著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以我為主開新局。正確處理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關系是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面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與“兩頭在外”國際循環帶來的問題,以及我國國內經濟規模、發展階段和各類條件的變化,必須審時度勢、積極求變,堅持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也必須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不重視國際循環,更不意味著主動“脫鉤”、閉關鎖國、經濟內卷化等,而是在更高開放水平的基礎上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新局”。
二是新發展格局以“經濟循環”為描述維度、根本視角和關鍵詞,而非供給、需求、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等經濟活動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環節,不能拋開經濟循環這個動態系統的視角而單獨從經濟活動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環節來談新發展格局。這決定了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更具有協同性和動態性的思維。也就是說,用“經濟循環”描述新發展格局,關鍵是把握如何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意味著構建新發展格局不僅僅根據供給側、需求側等單方面政策,也不單單是生產、流通、消費某個環節的戰略或者政策,而是圍繞經濟循環的系統動態的政策組合。
三是新發展格局形成需要新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新的發展戰略的目標要求。一方面,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對于以前的發展戰略形成的發展格局需要進行戰略創新和戰略轉型,需要拓展以前的比較優勢,尋求適應新發展階段和內外環境的新的經濟發展優勢基礎,例如,從低成本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轉向高質量創新導向工業化戰略,從“兩頭在外”的資源利用方式轉向協調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等等;另一方面,由經濟循環這個關鍵詞所決定,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與以前強調某類經濟主體、要素或者某方面經濟活動應該達到的目標之類戰略——例如科教興國、人才強國、鄉村振興、制造強國、區域協調、創新驅動等不同,新發展格局要求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內涵更具有系統協同性。也就是說,上述戰略是專業性戰略,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則屬于綜合性戰略。從這個意義上,形成新發展格局所要求的經濟發展戰略是類似于工業化、城鎮化之類的綜合性經濟發展戰略。
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形成新發展格局,既是中國積極順應全球百年未有大變局的需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要求。
一方面,在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新工業革命的挑戰等諸多因素作用下,全球經濟大調整大變革不斷深化,逆全球化也給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帶來巨大不確定性,全球債務的不斷積累和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原有全球經濟增長和經濟治理模式已經越來越不可持續。而20世紀末期,中國等東方國家的快速發展也使得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這一全球經濟調整趨勢愈發明顯,尤其是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已有生產分工體系和利益格局受到巨大沖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報告》總報告組,2020)。在這種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中國需要在變局中開新局,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立足本國優勢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重塑經濟全球化新動力,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全球經濟循環,引領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
另一方面,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一個百年目標,以此為基礎,“十四五”時期中國將全面開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到2035年中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中國將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一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發展格局無疑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國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經形成了超大規模的大國經濟基礎,產業鏈、供應鏈和消費市場具有滿足規模經濟、集聚經濟要求的條件,具備依靠國內經濟循環為主的經濟效率基礎。當然,有了大國經濟基礎,并不一定能形成新發展格局,還需要針對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不高、國民經濟循環還存在諸多堵點、國內需求還存在較大抑制、經濟安全風險比較大等長期存在的問題,依據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調整發展戰略,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著力點,堅持新發展理念,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從而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形成。
從理論意義上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提出,也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豐富開拓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從經濟思想史看,經濟循環流動是經濟學最早的范疇之一,也是經濟活動的最本質的特征。用循環流動描述經濟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國經濟學家魁奈1758年出版的《經濟表》,因此熊彼特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就誕生于重農學派對循環流動的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社會再生產理論,將社會再生產過程描述為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構成的經濟循環,還給出了產業資本循環從貨幣轉換為商品、從購買商品到生產出新商品、從新商品再轉換為貨幣的三個過程和公式。列昂惕夫在此基礎上提出要以循環流動理論——“可再生產性”論取代“稀缺”論,以此作為經濟學理論的基石(喬治·吉利貝爾,2016)。因此,從經濟循環角度來刻畫新發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經濟運行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也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的指導。而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更是很好地延伸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理論,形成了基于經濟循環流動的新的發展理論,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本文原載于《財貿經濟》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