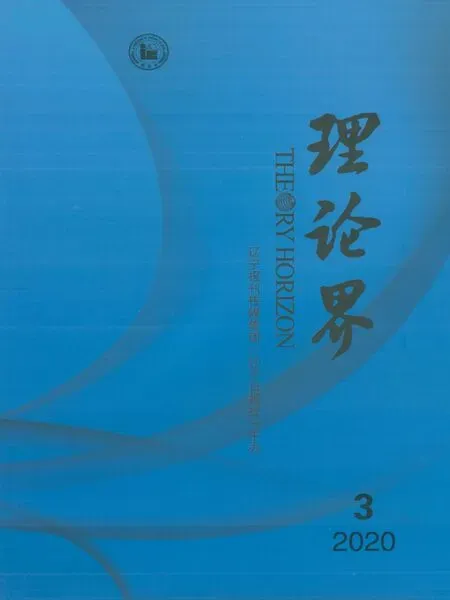波普爾社會科學哲學中的制度主義理論探析
金 輝
制度主義理論(institutionalism) 在波普爾(Karl R.Popper) 社會科學哲學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普波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作為一種獨特的方法論,具有明顯的反心理主義傾向,而制度主義理論就是波普爾方法論個體主義反對心理主義的一個重要環節和著力點,但是制度主義理論也絕不僅僅是用來反對心理主義的,實際上,制度主義理論已成了波普爾由方法論個體主義向方法論整體主義潛移默化轉變的重要一環,在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發展史上見證了該理論由強轉弱的這一漸進過程。波普爾的學生阿加西(Joseph Agassi) 在其主要代表作《方法論的個體主義》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一文中,明確提到該文的主要目標就是保衛制度主義的個體主義理論(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并且將之稱為波普爾對社會科學哲學的重大貢獻。
一、波普爾制度主義理論釋義
關于制度主義理論的主要涵義,波普爾對此并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制度是制度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主要基石和邏輯起點,所以本文中對制度主義理論的探討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制度概念闡述的,這是探討之前需要說明的。筆者認為,波普爾制度主義理論主要是在廣義的意義上使用的,波普爾在《歷史主義貧困論》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中指出,“‘社會制度’這個名詞是用之于非常廣泛的意義上的,既包括公共性質的制度,也包括私人性質的制度。這樣,我就用它來描述意向事業,不管是一家小商店、還是一家保險公司,以及同樣地,不管是一所學校、還是一種‘教育制度’,是一支警察部隊、還是一所教堂或一個法院”,〔1〕不難發現,波普爾主要是指人類所創造的相關社會建制。拉斯·尤德恩(Lars Udehn) 在其著作《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背景、歷史和意義》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Background, history and meaning) 一書中的說法,也印證了這樣一種分析,“波普爾看起來是在一個非常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制度’這個詞的,以此涵蓋了所有人造的社會建構,涵蓋了從諸如大學以及各種學校等社會組織到語言和著作等等”。〔2〕結合波普爾的整個社會科學哲學思想,其所涉及的制度具有如下的特點。
首先,制度具有廣泛性的特點,包含了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軍事制度等等,也可以說涵蓋了人類創設的一切社會建制,比如政府、軍隊、教會、學校,包括語言、著作等也屬于制度主義的范疇。
其次,制度是客觀存在的,波普爾認為制度是客觀存在的,是優先于“人性”和心理學而存在的,與其說制度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倒不如說是人類活動的前期。波普爾認為:“這就意味著,各種社會制度,隨之而來的還有典型的社會規則或社會學的規律,應該是優先于一些人喜歡稱之為‘人性’的東西、優先于人的心理學而存在。”〔3〕為進一步說明波普爾制度主義理論的客觀性,尤德恩對波普爾的制度主義理論和奧地利學派的制度主義理論進行了比較分析,按照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的觀點,社會制度的分析和解釋是作為個體行為的結果,而非人類行為的原因;但是按照波普爾的觀點,人類行為和思想,至少部分地是由社會制度造成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制度的客觀性甚至整體主義的思想;另外,按照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制度僅僅作為一種觀念存在于人們的思想中,而按照波普爾的觀點,作為自主世界中的客觀思想超越于個人而存在。〔4〕
再次,制度是無意識的產物。波普爾認為,制度的產生并不是人們根據自己的意愿、動機等有意產生的,而是無意產生的。波普爾認為,社會工程師和社會工藝師不大關心社會建構的起源或他們的締造者的原意,〔5〕社會制度是人類未經設計的產物,如果人們用需要、希望和動機來解釋社會制度是非常勉強的,也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制度往往是作為人類行為的一個副產品或無意識的反應而出現的,而這個副產品或無意識的反應又是人們間接的、非意愿性的產物,而這恰恰又是對心理主義的最有力和直接的反駁。
為進一步澄清制度的涵義,在《猜想與反駁》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中的一篇文章《關于一種理性的傳統理論》 (Towards a Ra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 中,波普爾還區分了制度與集體、傳統和個人等相關概念的聯系和區別。波普爾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在于解釋我們的企圖和活動怎么會引起不希望的結果,以及如果人們在某種社會情境中干各種各樣的事,那么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社會科學的任務尤其在于以這種方式分析制度(如警察、保險公司、學校或者政府) 和社會集體(如國家、民族、階級或其他社會集團)的存在和功能”。〔6〕波普爾在此將制度與集體做了大致的區分,依筆者之見,波普爾區分的標準應該是依據它們能否發揮出一定的社會功能而言的,但這樣的區分也不一定完全科學,正如尤德恩所認為的,這種區分不是特別清晰,就比如“國家”其實不必非要納入到社會集體這個范疇中,把其歸為制度可能更為合理。
波普爾將制度與傳統進行了比較詳盡的區分,雖然制度與傳統在很多方面存在著相似或一致之處,比如它們都必須由社會科學依靠個體的活動、態度、信仰、期望和相互關系來解釋和說明,但他們的區別也是明顯的,“但我們也許可以說,凡在一群(變化著的) 人遵守某套規范或執行某種初看有效的社會職能(如教書、當警察或銷售雜貨),而這些社會職能服務于某種初看有效的社會目的(如傳播知識、防止暴力或防止食物匱乏) 的地方,我們傾向于說到制度。而主要在當我們希望描述人們態度的一致性、行為方式、目的或價值觀或者情趣愛好時,我們則說到傳統。因此,和制度相比,傳統同人及其喜愛和憎惡、希望和恐懼等的關系也許更為密切”。〔7〕簡單說來,波普爾在此將能夠發揮出相關功能的社會建構稱之為制度,而將與人相關的主觀意念或行為方式等歸之于傳統。所以在此基礎上,波普爾進一步論述道,傳統處于人和制度之間,起著溝通人和制度的橋梁紐帶的作用。關于制度和人之間的區分,波普爾也做了專門的論述,他認為我們要考慮到“社會制度的矛盾狀況”,因為同一個社會制度會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起到不同的社會功用,比如警察可以起到保護人們免受暴力和敲詐之苦,但同樣警察也會以暴力或囚禁的方式來威脅人們,所以波普爾認為社會制度的矛盾狀況基于它們的特性,制度只能由人或其他制度來控制或監督,“制度的作用就像堡壘一樣,最終也取決于控制它們的人;而制度控制的上策是優先提供機會給那些打算為他們的‘正常的’社會目的而運用制度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8〕所以依照波普爾的觀點來看,制度的產生雖則不是人類的主觀有意設計,但是制度的執行、運作和人息息相關。
總之,波普爾對制度的理解和運用主要是從廣義的意義上來說的,制度具有廣泛性、客觀性的特點,制度是人類無意識的產物,總體上類似人類所創造的社會建制;波普爾同時也從狹義上區分了制度與集體、傳統和人的區別,通過比較分析,制度的重要特點是具有社會功能,其執行運作與人息息相關;但波普爾這樣的區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混亂之處,例如對制度和集體的區分就與其前期將制度理解成廣義的社會建構相矛盾,集體其實也可以理解成制度中的一種。在本文中,筆者主要是從波普爾廣義上的將制度理解成一種社會建構的意義上來使用的。
二、波普爾社會科學哲學思想中制度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
制度主義理論在波普爾的整個社會科學哲學思想中占有重要而獨特的地位,波普爾曾在其重要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主義貧困論》、《猜想與反駁》、《開放的宇宙》(Open Universes) 等著作中探討過,主要涉及他的反心理主義、社會進步理論以及零星社會工程學等理論,是研究其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重要內容。
制度主義理論首先與波普爾的方法論思想密切相關,并最終形成了一種制度主義的方法論思想。這一思想的提出,最主要是由于波普爾本人反心理主義的現實需要決定的。在波普爾學派內部,除了沃特金斯(John W.N.Watkins) 之外,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者都反對心理主義,波普爾更是反對心理主義的堅定擁護者和踐行者,他反對心理主義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為了防止主觀主義,為此,波普爾提出了兩種方法論上的策略,一是情境邏輯的策略,二是制度主義的策略。〔9〕簡要說來,情境邏輯意味著理想模型的建構,這一建構是基于人們要達到目標的假設以及人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在其中合理行動的假設,這是波普爾反對心理主義的第一個論證。關于制度主義的策略,波普爾通過運用制度主義的觀點反對和駁斥心理主義當然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自此之后,波普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觀點和制度主義理論的不相容之處就開始逐漸顯現,尤德恩也認為波普爾在此存在著含混不清的問題,既然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依托了個人,但同時又引入了制度的觀點,那么當涉及個人和制度時,為什么我們不能用統一的整體性的模型來替代呢?但是毫無疑問,波普爾本人隨后偏向了制度主義理論,當其后期不再提起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的時候,恰恰是情境邏輯和制度主義作為其社會科學方法論保存了下來。〔10〕
制度主義理論還主要體現在波普爾的自主性社會學思想中。自主性社會學理論倡導制度主義的觀點,其根本目的仍然在于反對心理主義。在波普爾前期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中,制度主義的理論主要是作為一種反對心理主義的理論而存在的,波普爾認為人類的行為是不能僅靠動機來獲得解釋,還必須依靠和動機相伴隨的社會境況、社會制度及其運行方式等來獲得補充,所以“制度主義者可能認為,將社會學還原為對行為的心理學或者行為主義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相反,每種此類分析都預先假定了社會學,因而社會學整體上并不依賴于心理學的分析。社會學,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個十分重要的部分,應該是自主的”。〔11〕所以波普爾的這一說法就直接否定了心理主義對人類行為和社會現象的決定作用,因為社會是自主的。波普爾用制度主義理論否決心理主義的原因在于制度理論的客觀性,他認為各種社會制度以及社會規則和社會學規律,都是客觀存在的,其在邏輯上是優先于“人性”、心理學而存在的,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就應該依據社會學而不是心理學。那么緊接著另外一個問題也隨即出現,既然社會制度也是由人類創造的,或者看似是人類有意識的人造物,社會制度為何又是客觀的呢?波普爾對此進行了解釋,他承認社會制度是人的行動和決策的結果,是能夠由人的意識和行為決策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制度是能夠還原為個體的行為、愿望和動機的。而是恰恰相反,波普爾認為,“只有少數社會制度是自覺地設計的,而大多數卻只是作為非人類行為所設計的結果而成長的”。〔12〕即使是少數幾種被人為地設計出來的制度,它們也不是按照計劃建成的,因為有意識的計劃總會引起無意識的社會反應,而且某一種制度還會和其他社會制度發生相互影響,當然也包括與“人性”之間的互動,總之,社會制度是不能由人類的單純愿望、動機和行為創造的,從而也就保障了社會制度的客觀性,制度理論的客觀性的確立就足以使其成為反對心理主義的有力武器。
除了作為反對心理主義的有力武器外,制度主義理論也被波普爾歸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波普爾并不完全排斥心理傾向在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但是這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還是遠遠不夠的,推動社會進步還有更重要的力量,那就是社會制度。波普爾認為,社會建制紛繁復雜,各種社會制度比比皆是,社會和工業的進步依賴于好的制度的實施,比如科學的進步依賴于大學、寫作、著述、印刷、語言等等方面的制度,尤其是還要有保護思想自由競爭的寬松的政治制度,此其一;其二,關于如何評價科學進步的“科學客觀性”這一問題,其實這也是由科學制度來確保得以實現的,而并非簡單地由科學家或科學家群體的心理作用實現的,所以從總體上說,科學的進步有賴于制度主義理論的應用和實施。但這也并非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并不是有了相應的制度科學就一定取得進步,波普爾認為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制度的作用無非就是盡最大可能減少人的因素的不可靠性,盡最大可能減少對人的依賴,但這也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波普爾也不是一味拒絕人的因素,他認為好的社會制度要達到好的社會效果,還必須要考慮人的因素,所以波普爾說制度的人員配備也必須適當,因為制度就像是要塞,〔13〕制度的實施一定程度上也是要依靠人的。
波普爾還將他的制度主義理論運用到“零星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思想中。眾所周知,在關于社會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問題上,波普爾提出的是“零星社會工程”的方案。他認為,零星社會工程師的主要任務即在于設計社會制度并重建和運轉現有的社會制度,〔14〕但是正如上文論證過的,這些被設計創造出來的社會制度是客觀的而非純粹人為的。波普爾認為,當社會的發展需要涉及長期的相對穩定的政策時,這就需要依靠制度而非個人,此外制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防止壞的統治者的重要保障力量。即使是按照波普爾的“零星社會工程”的方法對社會的局部進行改革時,波普爾也寄希望于按照制度化的方法在社會法律框架內進行些許變革。波普爾舉了國家推進經濟干預的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設計一種保護制度的“法律框架”,可以稱之為“制度化的”或是“間接的”干預,第二種方法是授權給國家機構,讓他們在一定限度內視實現統治者所承擔的目標之必需而隨時采取行動,這種方法被稱之為“個人的”或“直接的”干預。〔15〕根據零星社會工程的方案來看,波普爾是支持第一種制度主義方法的,因為這一方法著眼于依照討論和經驗進行調整,使試錯成為可能,而且具有長期性、永久性的法律框架可以在此得以逐步改造;同時,以制度化為依托形成的法律框架可以被個體理解和知曉,并且可以用來預測,把確定性和安全的因素引入社會生活,并且在其改變時能有較大的彈性,能為希望或不希望它改變的人留有較大的余地。與此同時,波普爾也批評了個人干預方法的不妥,因為這種方法把不可預測的因素引入社會生活,并進而發展成一種情感,這就讓社會生活處于一種不合理和不安全的狀態中。〔16〕所以波普爾認為,人們秉持“零星社會工程”的方法對社會進行改革時應堅持制度主義的方法。
三、波普爾制度主義理論評價
制度主義理論在波普爾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對波普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影響較大。筆者將其影響主要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波普爾的制度主義理論標志著強方法論個體主義向弱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轉向。制度主義理論關系到強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弱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發展。方法論個體主義出現的轉向,主要指的是解釋或是因果關系方向發生了變化。尤德恩將方法論個體主義分為強方法論個體主義和弱方法論個體主義,強方法論個體主義包含社會契約論、大眾均衡理論以及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理論,這些理論無一例外具有一個共同點,主張將社會現象的解釋還原到單個的個體,個體是人們解釋和理解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石和立足點。〔17〕弱方法論個體主義主要包括波普爾學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以及科爾曼(Coleman) 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這些理論已經在極力淡化個體的作用,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不再秉持徹底解釋(rock-bottom explanation) 的方法,而是引入了客觀的社會制度等外在性的事實,或者是用社會結構理論來建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相較于強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弱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主要特點就是引入了“制度主義”的觀點,并在社會現象的解釋上采用“半截子”的中層解釋(half-way explanation) 的方法。〔18〕所以波普爾學派在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發展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特殊作用,該學派也被稱為“制度的個體主義”,而且是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除了波普爾本人外,波普爾學派的重要成員阿加西以及賈維(Ian C.Jarvie) 等人都是制度主義個體主義的積極擁護者和推動者。
其次,波普爾的制度主義理論標志著波普爾本人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轉向。波普爾前期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后期不自覺地轉向了整體主義,而其制度主義理論在其中起了重要的過渡和承接作用。早在波普爾的《歷史主義貧困論》中,波普爾由方法論個體主義向方法論整體主義轉向的趨勢已初露端倪,波普爾認為,社會的進步僅僅只有心理的傾向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找到進步所依賴的其他條件,“于是,我們下一步就必須以某種更好的東西代替那種關于心理傾向的理論;我建議,以一種關于進步條件的制度的(和技術的) 分析來代替”。〔19〕在波普爾的另外一部作品《開放的宇宙》中,波普爾對三個世界理論進行了定義,他把物理物質、力場等等所在的世界稱為“世界1”,把意識也許還有潛意識的世界稱為“世界2”,把口頭語言的世界、藝術作品的世界和社會制度的世界稱為“世界3”,〔20〕作為客觀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各種制度的世界3,波普爾認為這是與其他兩個世界無關的,世界3不能還原為世界1,世界2依賴于世界3的客觀部分,世界2不僅創造了世界3,而且其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世界3所創造。波普爾論證的目的主要是證實還原主義是不可靠的和不可取的,“哲學還原主義是錯誤的。這個錯誤歸因于把一切事物都還原為一種從本質和實體方面的終極解釋的愿望,即既不能又無需做任何進一步解釋的解釋”。〔21〕所以這樣說來,波普爾在此是反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還原方法的,總體上秉持一種整體主義的原則,但是這是一種溫和的整體主義策略。波普爾認為,三個世界卻屬于同一個宇宙,它們之間相互作用。所以總體上我們要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還原主義尤其是寄希望完全還原的信念都是錯誤的,但波普爾也為還原主義留下了一點余地,波普爾指出,“嘗試進行還原的方法是非常富有成效的,這不僅因為我們通過它的部分成功,通過部分的還原學到許多東西,而且因為我們從我們部分的失敗中學習,從我們的失敗所揭示的新問題中學習”。〔22〕所以這樣看來,蘊涵著制度的世界3就和世界2以及世界1原則上不能相互還原,它們在共同組成的世界整體中相互作用,同屬一個宇宙,這實質上就是一種整體主義的觀點。
尤德恩也認為,在波普爾后期出版的著作中,他將社會制度作為社會狀況中除了物理環境外最重要的因素,作為這樣的一種客觀實在,這其實就是波普爾不再堅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個跡象。波普爾認為,制度主義理論所從屬的客觀的世界3理論可以作用于個體,并且超越于個體,這已經與方法論個體主義不相容了。尤德恩將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的理論稱之為一種“凸顯進化論”,這種理論已經屬于一種整體主義的傳統。〔23〕
再次,波普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制度主義之間始終存在一種張力。依筆者之見,這種張力表現為兩個方面,總體上說,個體主義和制度主義既有相容補充的一面,也有對立不相容的一面。
一方面,制度主義理論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補充和發展。在波普爾看來,其提出制度主義的觀點起初并不是為了反對和否決方法論個體主義,而是為了解決他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問題和困境,其碰到的最麻煩的一個問題就是心理主義,所以波普爾最初是帶著美好的愿望提出制度主義的,而且純粹是作為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補充而提出的。波普爾在其自主性社會學中提出,社會現象或社會行動的解釋不能僅靠動機,還必須依靠情境和環境來獲得補充,而且這種環境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質,所以如果不參照我們的社會環境、不參照社會制度及其運行的方式,人們的行動就不能獲得解釋。〔24〕足以見得,波普爾此時也純粹是從反心理主義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的,僅僅將社會制度和社會的情境狀況作為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種補充。所以此時的制度主義觀點應是對個體主義的補充,甚至退一步講,也可以說是與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處于平行狀態。波普爾在《歷史主義貧困論》中,也指出了方法論個體主義和制度主義相融相存的方面,“我們需要以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為基礎來對社會制度進行研究(觀念是通過社會制度而傳播并俘虜了個人的),對可能創造出新傳統的方式進行研究,并對傳統在其中起作用和崩潰的方式進行研究。換句話說,我們對民族、政府或市場之類的集合體的個人主義的或制度主義的模型,必須要由政治形勢的以及諸如科學進步和工業進步之類的社會運動模型來加以補充”。〔25〕這時的制度主義不僅需要個體主義的補充解釋,而且它們共同需要由其他的運動模型加以補充解釋。
另一方面,波普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制度主義理論的不相容的一面,體現在它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方法論路徑。波普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主張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用個體的態度、期望、行為、相互作用和關系來解釋和理解一切社會現象、社會集體和社會建構,這是波普爾前期的基本觀點。但是波普爾方法論個體主義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反對主觀主義和心理主義,拒絕使用人性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為此,波普爾不得不引入和運用制度主義的觀點,制度主義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建制,根本上與方法論個體主義不相容,尤其在波普爾后期的社會科學思想中,波普爾只留下了制度主義和情景分析的科學方法,非常順理成章地放棄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基本思想。
最后,波普爾的制度主義理論成為波普爾學派后期的兩種不同的方法論發展路徑的分水嶺。在波普爾學派往后的思想發展脈絡中,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制度主義的分道揚鑣已成必然,就波普爾個人而言,他的制度主義理論連同其情景分析理論已經成為其僅保留的方法論內容;對于其倡導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理論,這一思想主要由其學生沃特金斯進一步傳承發展,沃特金斯為捍衛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理論不遺余力,并成為闡發和繼承這一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制度主義理論則由波普爾學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阿加西繼承發展,阿加西將波普爾的個體主義、制度主義以及情境邏輯等思想綜合起來,提出了制度主義的個體主義理論,此理論走有是一條介于心理主義和整體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