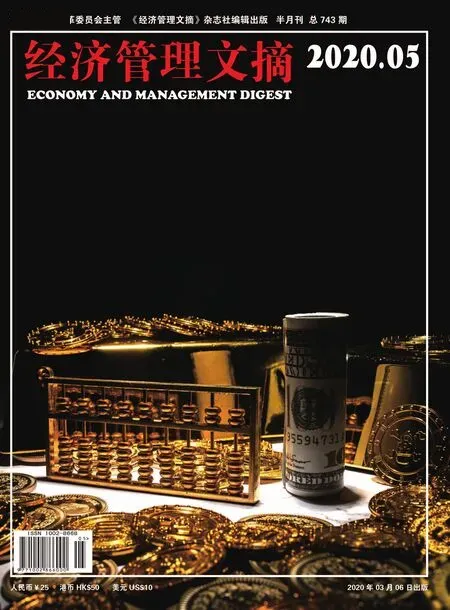精準扶貧背景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出路
■劉希華
(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魯村鎮人民政府)
1 精準扶貧政策的基本內涵
精準扶貧不同于以往的粗放式扶貧方式,其堅持將“扶真貧、真扶貧”作為核心要義。與“大水漫灌”式的扶貧方式不同,精準扶貧政策和措施會滲入到每一個村莊,甚至是每一戶人家,精準幫扶貧困的家庭和貧礦的人員,從根源深處掃清貧困因子,將“窮根”連根拔起,從而達到真正脫貧致富的目的。精準扶貧主要分為四個內容,分別從四個方面入手去落實精準扶貧政策:首先是精準識別,也就是說將真正有困難的人員找出來,經過公示、抽驗核查、信息錄入等一系列的步驟之后為他們建立起專門的貧困檔案卡,真正弄清楚這些人員貧困的原因和目前需要幫扶的工作。其次就是精準幫扶,在準確識別了貧困人員之后就要采取幫扶工作了,基于貧困戶和貧困人員的成因實施幫扶工作,做到有效脫貧。然后就是精準管理,精準管理并不僅僅局限在扶貧對象的精準上,其還要囊括項目安排、資金使用、脫貧成效精準等各個方面,保重精準扶貧工作的順利進行。最后就是精準考核,精準考核中考核的是脫貧政策實施的成效,其能夠利用量化考核審視貧困縣的扶貧工作情況,對于扶貧效果做進一步的強化。
2 精準扶貧背景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困境
2.1 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基數龐大
受我國國情的影響,我國的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眾多,有著龐大的基數,所以針對貧困地區的扶持工作還有進一步加強。同時我國的農村貧困人口不僅僅數量眾多,而且分布也比較集中,要想從根源上解決貧困問題難度較大。在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角度來看,農村的貧困人口占絕大多數,且在生活資源并不豐富、生活條件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還普遍存在著連片貧困的現象,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口過于集中,諸如西北、西南和東北的邊疆等地連片貧困的現象十分嚴重,其總的貧困人口數量占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是針對這些貧困人口“重災區”來說,我國目前對于其的財政性公共支出并不達標,同時農村的金融體系扶持力度也遠遠不夠,這就導致了農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諸如醫療、教育和就業領域等發展落后,同時在農村的基層治理中農村勞動者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其整體的知識素養還不夠高,直接影響著扶貧的效果[1]。
2.2 農村基層干部治理理念較落后
近幾年來,雖然國家一直在致力于提升農村基層干部的治理理念,并有了一定的收獲,但是距離精準扶貧的治理理念要求來說還不夠達標。首先就是形式主義嚴重,農村基層干部的“扶貧”行動僅僅流于表面,并沒有真正落實到實際中去;其次就是“不公開、不公正、不透明”,部分基層干部并沒有將救助資源應用都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扶貧資源分配夾藏私心,從而導致扶貧成本一直在上升但是效果卻微乎其微;最后就是基層領導干部的能力不足、經驗不足,在治理的過程中只會沿用老舊的方式和方法,不能夠清晰認識到相應的責任和權利意識,一味的推行強硬的治理控制手段,在整個治理過程中農民并不能夠感受到尊重和關愛,從而產生較強烈的抵觸情緒,最終影響到精準扶貧工作的順利開展。所以說,基層干部治理觀念極為重要,理念跟不上精準扶貧工作就很難展開。
2.3 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尚不完善
農村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比較單薄,其不能形成“共治”的局面。完善的農村社會治理體系擁有多個主體,不僅僅有基層政府,還應當存在基層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農村勞動者等諸多主體,但是目前即便新時代、新理念已經在不斷的傳播,還是受到傳統“官本位”等思想的影響。農村基層政府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導致其一直是獨自管控著農村貧困地區,在一個較為被動的層面上掌控著全局。
3 精準扶貧背景下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創新
3.1 加大對農村的扶持力度,加強農村基層自身的“造血”功能
政府要想在精準扶貧的背景下加大對農村的扶持力度,需要堅持為基層農村“輸血”和“造血”。首先是“輸血”,這就需要政府優化對基層農村的頂層設計以及加大資金扶持力度,將財政公共支出向基層農村傾斜,建立健全農村當地的社會保障制度,為當地的農民構建起一個以最低生活保障為核心的救助體系,舉例來說,政府可以頒布更多的扶持政策支持農村的基礎設施、衛生、教育等方面建設工作,同時以重大扶貧項目為出發點,進行資金的整合,加大資金投入力度,集中解決較為棘手的困難等。其次就是“造血”,要想發展基層農村,不能只顧及到眼前的經濟困境,只依靠政府的幫扶農村是沒有發展前景的,所以除了現有的幫扶,還要構想到以后的長遠利益,打造基層農村的“造血”功能。要想實現“輸血”到“造血”的轉變就要加強農村本身的建設,從根本上治理貧困。
3.2 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轉變社會治理理念
農村社會治理的領頭人就是基層干部隊伍,所以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對于社會治理來說至關重要。而要想提升整個基層干部隊伍的水平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優化現有的階層干部隊伍,針對現有的基層干部成員進行定期的培訓,致力于提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等,讓其能夠更快的融入到新時代、新發展過程中,充分了解新的治理理念,以便其在以后的農村基層治理中秉著“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則進行;第二,向現有的干部隊伍輸送高素質人才,政府需要不停地選拔、引進能力優秀的干部,同時選人的范圍不要只局限于大學生,還可以選調各個機關內部的優秀干部,將先進的社會治理的理念傳遞給工作伙伴。
3.3 制定精準扶貧責任清單和進度協調計劃
把握細節,制定出清晰的、準確的扶貧責任清單和進度協調計劃,可以幫助相關部門有條理的展開精準扶貧工作。同時使得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的多元協作機制有了進一步完善。精準扶貧責任清單和進度協調計劃的制定要立足于國家政策和實際情況,舉例來說,要率先了解2020年我國全部脫貧的總體目標,再依據國家的扶貧開發任務分工,將精準扶貧分每一份責任都精確到各相關負責的部門,最后再參考當地的實際情況,擬出一份詳細、全面的責任清單,以防止扶貧任務出現重疊或者疏漏的情況。在制訂出責任清單之后,還要明確進度計劃,這份進度計劃要根據任務和責任的完成次序來確定,精準確定完成的時間,以防止出現有關責任部門互相推諉的現象。同時還要更加深入的了解本地區參與扶貧的重點項目和重點對象,將有限的資金和人力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優化資源開發配置,提高資金使用成效。
3.4 健全農村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基層治理運行機制
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應當打破基層政府的“壟斷”地位,將公共服務投放到一個多元化的治理體系中,同時還要動員越來越多的利益主體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在基層的社會治理體系中,既要求自上而下的行政紐帶,又需要多元化的橫向合作關系,所以一個完善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要學會不斷開拓、創新其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讓越來越多的主體彌補基層政府無法顧及的治理區域。在此期間,基層政府需要給自己一個清晰的定位,拋棄以往用行政命令處理公共事務的習慣,轉而做好社會協調工作,構建一個服務型的基層政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服務型的基層政府并不等同于放縱型的基層政府,對于其它多元化的治理主體不能一味的信任和支持,基層政府在信任的基礎上必須要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監督體系,有效防止資源浪費、貪污腐敗等行為發生,確保政策、資金、項目的公開透明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精準扶貧。
結 語
自我國實施扶貧工作以來,農村扶貧、脫貧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相較以往我國的貧困人口數量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我國以往的扶貧方式大多是較為粗放式的扶貧,這種傳統的扶貧方式反映出了許多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而精準扶貧對傳統的扶貧方式進行了創新,其立足于實際不斷優化自身的扶貧方式,加大對農村的扶持力度、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制定精準扶貧責任清單和進度協調計劃、健全農村基層治理體系等,努力兌現“扶真貧”、“真扶貧”的承諾,為實現全面脫貧和共同富裕目標不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