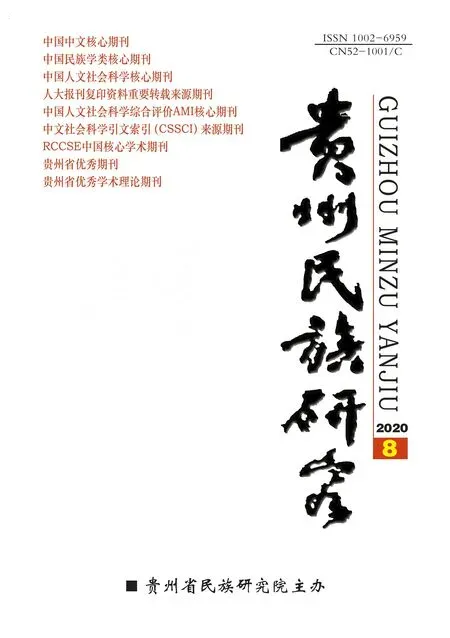清代改土歸流后地方社會控制權的交替
——以湘西永順地區為例
張 凱 成臻銘
(1.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長沙 410081;2. 吉首大學,湖南·吉首 416000)
標藍的地方改為:“改土歸流”標志著土司制度在土司區的消亡,但是土司制度的殘余力卻依然影響著改土歸流后的地方社會。另一方面,國家在改土歸流地區亦希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以將“國家”的概念灌輸到地方社會。這就使得清政府會通過一系列手段在地方扶植新的“國家”代言人,以消除土司制度殘余力的影響。如此一來,改土歸流后的地方社會就成為了各地方群體迎合國家政策,角逐地方控制權的“戰場”,地方控制權也由此在不同群體中發生著交替。本文將通過考證清代改土歸流后某一區域具有一定時間維度與延續性的碑刻、族譜等材料,說明改土歸流后國家政策在地方社會的推行狀況。并以此為基點,重新觀察地方社會新崛起的勢力是如何通過國家政策一步步取代原有的權力群體,從而成為地方權力新的控制者。
一、改土歸流后清政府與土目群體的權力沖突與和解
(一) 清政府與土目群體的權力爭奪
“土目”是各地土司為了更好地管理龐大的土司基層社會而設立的自署職官。由于土司基層社會的事務隨著土司區的發展日益繁雜,所以“土目”群體也逐漸壯大,成為了土司時期僅次于土司群體的第二大群體。清代西南地區大規模改土歸流之后,諸多土司地區掌握實權的在職土司以及其后代被安插至內地生活。如永順宣慰司使彭肇槐及其后代就被雍正帝發往江西安插[1]。這一方面使得改土歸流后的土司群體徹底失去了他們在當地掌握數百年的地方控制權;另一方面也使得留守在改土歸流地區的土目群體有機會繼承當地殘留的“土司權威”,以此與“國家”進行權力角逐。
在改土歸流后的地區,清政府會在當地建立地方政府,派遣流官管理。在內地的基層社會,地方政府依靠鄉里制度進行管理。這一制度在內地有著長期的發展過程,至清代已臻于完善[2]。保甲制度是清代鄉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這一時期極具代表而又十分有效的管理鄉村社會的制度。所以在改土歸流后的地方社會,清政府也引入了保甲制度進行管理[3]。
不過,改土歸流后的地方社會狀況往往十分復雜。以永順地區為例,新設的永順地方政府很難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一批忠心的鄉里勢力幫助自己管理地方社會。這就使得他們只能任用土司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土目群體為保長、里正[4]。地方政府這樣布政有著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其積極的一面是,土目群體在土司時期長期管理基層社會,十分熟悉當地的狀況,能夠很好地維護地方秩序;但隨之而來的負面影響是,土目群體管理地方社會的權力基礎是“土司權威”,基層土民將對土司的敬畏轉移到了他們身上。這就使得土司時期曾經存在的諸多“積弊”在改土歸流之后依然盛行于地方社會[5]。后者顯然與清政府設立保甲制度的初衷相矛盾。正因如此,改土歸流后的永順社會成為了以“國家權威”為代表的地方政府和以“土司權威”為基礎的土目群體產生強烈碰撞的“戰場”,“田爾根事件”由此爆發。“田爾根事件”的結果是,清政府通過“小案重判”的方式將一大批不服地方政府管理的強硬土目分別“以斬、絞、軍、流、徒、杖分別發落”[6],“國家權威”在與“地方勢力”的交鋒中取得了一次大勝。而后,永順地方官員以“田爾根事件”為由頭,開始趁熱打鐵對當地的保甲制度進行了改革,使之基本與內地無異。同一時間,永順地方政府還對當地社會所遺存的土司“陋習”進行全盤的清理,基本禁絕了永順社會的“土司積弊”[7]。
在剛完成改土歸流的地方社會,無不上演著這樣“國家”與土目群體角逐地方權力的“大戲”。多地的土目群體因為這種權力斗爭失去了地方社會的控制權,使得他們需要跳出“土司權威”的影響,與國家建立起新的聯系,以避免就此退出歷史的舞臺。
(二) 達成和解:土目群體的宗族重建運動——以內塔臥彭氏為例
在土司時期,有不少勢力龐大的土司在當地仿照漢人的宗族制度建立起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宗族組織系統。這一系統對內便于加強土司群體的凝聚力,提高土司進行社會管理的行政效率;對外又能將當地話語與“國家”話語進行對接,拉近與“國家”的關系。其中,尤以明代永順宣慰司使彭氏所建立宗族組織的特點最為鮮明。
從明正德年間到明萬歷年間,歷任永順宣慰使曾在他們的轄區內仿造內地的宗族組織形式建立起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宗族運作模式。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國家的戰亂導致永順地區社會動蕩,當地不少建筑遭到嚴重破壞。順治四年(1647年) 和順治八年(1651年),永順老司城周邊連續被逃兵洗劫,永順彭氏宗祠也在洗劫中付之一炬[5]。雖然之后彭氏土司一直有重修宗祠的意向,但隨之而來的苗疆開辟運動和改土歸流運動使得他們尚未行動便失去了在當地世代生活的權利。不過,改土歸流后被強制遷出永順地區的僅僅是彭氏的直系子孫,旁系的彭氏仍然在當地生活,他們也是土目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他們面對“土司權威”的影響逐漸在永順社會消退的狀況后,便將重建彭氏宗族組織的行動提上了日程,他們寄希望以這種方式重新獲得在當地的控制權。在土司時期,彭氏的直系子孫為了在當地樹立權威,采取了積極修譜、建造彭氏祠堂等多種手段[8]。這就給改土歸流之后的彭氏旁系提供了重建宗族組織的優秀范本。
改土歸流后,內塔臥彭氏是生活在永順地區最大的彭氏旁系之一,他們也是最早開始對彭氏宗族組織進行重建的群體之一(注:“內塔臥”為永順地區的傳統地名。“塔臥”土家語意為“田螺”,因當地版圖形似田螺而得名。“內塔臥”即為田螺地形的內部平地,與“外塔臥”相對。新中國成立后,內、外塔臥合并成塔臥鄉,屬永順縣地)。他們首先號召當地的彭氏族人“每家照丁多寡,每丁捐錢三百三十□□收齊,以購義田”,并選擇了有威望者做族長,主持宗族事務。到了乾隆初年,他們還在族長的主持下,開始定期在祠堂中進行了祭社活動[9]。根據陸群、蔣歡宜的研究,改土歸流后永順內塔臥彭氏祭社活動的過程和禮儀表現基本與漢人宗族無異[10],這就說明了內塔臥彭氏有意模仿了漢人的祭社活動,以強化自己的漢人身份。
另一方面,內塔臥彭氏開始將土司時期所流傳下來的《歷代稽勛錄》進行了續修。《歷代稽勛錄》在土司時期被彭氏子孫認為是有與漢地族譜一樣性質的譜書,但它只記載了彭氏直系一脈的傳承,所以更應該被認為是家譜而不是族譜[11]。而內塔臥彭氏在續修《歷代稽勛錄》時,增添了很多旁系的資料,并加入了更為詳細的瓜藤圖,完善了譜書結構,使之成為了真正的彭氏族譜,強化了重建后永順地區彭氏宗族的凝聚力。此外,執筆的彭氏子孫極其認同該書上所述的彭氏為江西漢人后裔的說法,并在之后各代《彭氏族譜》的新修過程中,均將“江西遷來說”寫入了譜中,以強調自身漢人身份的真實性[11]。
在彭氏族學的重建上,內塔臥彭氏也費盡了心思。由于在改土歸流之后,彭氏土司所修建的族學——若云書院被永順地方政府征用改為了永順府學,彭氏子孫便在內塔臥重新修建了一所新的學校以充當彭氏的族學[9]。在該族學外,豎立著一塊臥碑,該碑上寫道:
吾等既為圣世漢民,即當躬圣人至教用,是捐錢糧建立儒學。延師彭義才等,教以詩書,多刷圣諭廣訓,分布任領,令館師,日則教子弟在館熟讀,夜則令子弟在家溫習。庶幾子弟之父兄輩,亦得聞作孝之大端,立行事之根本。久久習慣,人心正,風俗厚,而禮義可興矣[9]。
在此碑文中,永順彭氏自認為是“漢民”,并通過日夜誦讀儒家經典這一手段,使得整個彭氏宗族的內部成員耳濡目染儒家文化。這一行為體現了當地彭氏極力維護自己漢人身份的決心。
值得注意的是,彭氏族人日夜誦讀的經典之一是《圣諭廣訓》,該典籍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是傳統的儒家經典,而是雍正二年(1724年) 國家所頒行的,以康熙皇帝教導臣民行為準則的《圣諭十六條》為藍本的官修典籍。當時的清政府不但在內地儒學廣推這一典籍,還將其列入了科舉必考書目之中。內塔臥彭氏顯然明白《圣諭十六條》在當時的影響力,所以他們十分重視這一典籍在彭氏宗族內部的普及,以體現他們對清朝統治者的認同。
乾隆年間,時任永順知府李拔在親自考察內塔臥彭氏族學之時,即興為彭氏族人題寫了千余言的《勸學箴》。文中的內容充滿了對彭氏興辦族學的贊美,但也嚴格要求學生忠君、尊孔,接受儒教倫理。最為重要的是,該文反復強調學生不得妄議國政和校務,更不準離經叛道,發表狂言怪論[5]。可見,當時的永順地方官員一方面對彭氏興辦族學主動重建與“國家”關系表示肯定;一方面又提醒永順彭氏應加強儒學教育,主動培養他們后代忠君愛國的觀念,從而在思想上杜絕他們作亂的可能,以長久維護當地的社會安定。
內塔臥彭氏的宗族重建行為在永順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彭氏宗族的勢力由此在當地迅速蔓延開來。直到現在,永順縣的塔臥鎮有些老人在描述當地大族的時候還說道“彭兩千,吼一吼,塔臥抖三抖;向五百,跳一跳,房瓦要震掉。”[12]其意思是當地以彭、向兩姓為大族,其中彭氏勢力最大,族人有兩千之多,可見內塔臥彭氏在當時發展規模之大。并且從光緒十八年(1892年)內塔臥彭氏族人重修的族譜來看,他們的宗族建構已十分完備,從底層逐步疊加,形成了“個人—獨立家庭—聯合家庭—小支—大支—各房—宗族”的嚴密等級結構[9],這些特點均與漢人宗族組織基本無異。
最為重要的是,永順彭氏至此在自身與國家之間再次構建起了新的聯系。這種聯系不再是以“土司權威”為基礎,而是以宗族組織為基礎。這展現了永順彭氏對漢人文化的“向化”之心。更進一步的是,這種“向化”行為使得土目群體的身份開始發生了轉變,他們由“土司權威”的繼承者逐漸變為“國家”主流文化的傳播者,就此緩解了他們與“國家”緊張的關系,得以繼續把持著永順社會的地方權力。
總而言之,在改土歸流后的地方社會,地方勢力在經歷了與“國家”的抗衡后,急需重新與國家建立起聯系,借此延續自身在地方社會的權力與利益。一般而言,這種新的聯系應是一種基于漢文化的行為模式,這就使得宗族重建運動在地方社會發展起來。不過,各地方社會和解行為也并不是都以宗族重建為手段。如廣西潯州府的地方勢力在改土歸流后就是運用將地方神國家化的方式與國家建立起新的文化聯系,并借此成為了國家在地方上的文化代言人[13]。雖然手段各不相同,但是地方勢力的目的均是以文化互動的方式與國家達成和解。這樣的行為,有利于地方社會秩序的重構。
二、改土歸流后土籍士紳群體對地方控制權的掌握
通過宗族重建,土目群體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以文化認同為基礎進行了重建。但是另一方面,地方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土地,仍然牢牢掌握在土目群體手中,這讓清政府又開始著手改革地方社會的土地政策,以期收回地方社會土地資源的控制權與分配權。
以永順地區為例,雍正八年(1730年) 三月,雍正皇帝正式下令在永順府進行土地重勘運動,規定“將永順一府秋糧豁免一年,令有產之家自行開報,準其永遠為業”[3]。這一條令展現了清政府強力打擊被土目群體私占土地行為的決心,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這次土地重勘不僅使得永順土民逐漸擺脫了與土目群體的人身依附關系,還使得他們開始通過賦役制度與“國家”建立起直接聯系,“國家”的概念就此進入永順土民的經濟生活之中[7]。清政府對永順土民“額以賦稅”之后,也相應地使他們獲得了科舉的權利。
其實,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 清政府就規定,永順地區凡是編戶納稅之人均可參加科舉考試[15]。但是,由于此時的土地重勘才剛剛起步,所以永順土民幾乎沒有自主的耕地,科舉權利牢牢掌握在土目群體手中。到了土地重勘完成之后,絕大多數的永順土民獲得了土地,開始向國家承擔賦稅義務,隨之而來的便是他們能夠與土目群體一同進行科舉考試。
不過,土目群體在土司時期就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本身就有一定的儒學積淀[16],所以在應付以儒學為宗的科舉考試時,他們較一般土民獲取功名的機會就更大。尤其在土目群體對宗族系統進行重建后,宗族內部的族學體制較之前更為完善,而底層土民只是初識儒教,土目群體的族人與土民們一起科舉應試,無疑是土目族人中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雖然永順地方政府看到了其中的問題,在當地確立科舉制度后開始興修府學、義學和書院,并就近設置考棚,加大科舉制度的普及程度[14]。但是永順地方政府的行政預算實在拮據,并不像內地州縣一樣能給在校的儒生發放足夠的廩食,這使得很多窮苦的土民根本不可能讓自己的子弟在政府所辦的學校內讀書,從而導致很長一段時間永順府的官學入學率十分之低[5]。反觀土目群體,不但擁有自己的族學,還為族學配置了一定的學田,這樣每年學田的收入能給族人子弟創造優良的學習條件,這就讓他們在當地的科舉考試中仍然極具競爭力。以內塔臥彭氏為例,從乾隆十一年(1746年) 到光緒十七年(1891年) 間,彭氏科甲出身的族人有秀才21人,舉人9人,進士3 人,成績十分不錯[9]。
如此一來,土目群體的族人因為科舉考試獲得了功名,為了報答宗族對自己學業的支持,往往會運用自己手中的資源繼續支持宗族的發展。這使得他們在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系統,宗族勢力日益壯大。而有功名的族人們由于所在宗族勢力的擴大,也隨之在永順地區樹立起了自己的權威,土籍士紳群體由此在當地形成。正如乾隆初年永順知縣李瑾對當地土籍士紳群體的贊美之言:“服勤力穡以供賦稅;誦詩讀書以為國華。”[15]這固然有夸張的成分,但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對他們的肯定。
從土地改革到“納糧當差”再到獲取科舉資格,當地大姓族人最終通過科舉制度獲取新的士紳身份,如此的發展模式普遍存在于改土歸流之后的地方社會之中。如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土目群體在改土歸流之后就因為當地土地所有權的變更,科舉文教的興起而開始發生了變動。當地黃氏宗族的崛起開始強烈沖擊當地原有的勢力格局,并與中央王朝建立了新的聯系[16]。由此可見,雖然地方勢力的主體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他們通過對國家新政策的解讀和迎合,開啟了與國家新的、友好的互動模式,并使得自身身份發生了較大轉變。
三、客籍士紳群體對地方社會控制權的爭奪
(一) 改土歸流后地方社會的移民概況
在乾隆時期,我國人口數量達到了歷史的巔峰。在這一社會大背景之下,改土歸流后的地方社會成為了內地人口最好的移民目標,也成為了他們進行土地開荒、商貿活動以及興辦文教的最好對象。以永順地區為例。根據史料記載,永順府從乾隆初到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 新增人口21 萬余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外來移民[17]。
永順社會短時間內會有如此龐大移民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土地重勘后,清政府對永順社會的土民進行了重新土地劃分和編戶,使得當地的民政制度與內地趨同。這也使得土司時期“蠻地”與“漢地”的劃分失去了依據。土司時期“蠻不出境,漢不入峒”的口號就此成為了空談[18]。再加上土司區原籍土民數量十分稀少,這就使得當地在重新劃撥土地所有權后出現了大量的荒山荒地無人認領。所以,當地官府在改土歸流后便提出了“任民自由占田”的政策[19],以借此發展當地較為落后的農業。這一政策的執行必然導致內地大量無田之人涌入永順地區進行開墾荒地的占地行為,也為永順社會帶來了第一批大規模的移民。
其二是商貿利益的驅使。如改土歸流后龍山縣的移民“多長、衡、常、辰各府及江西、貴州各省者。其先服賈而來,或獨身持幞被入境”[20]。而在永順縣,其遷入的客民“在他省則江西為多,而湖北次之,福建、浙江又次之。在本省則沅陵為多,而芷江次之,常德、寶慶又次之”[21]。可見當時永順地區因為商機而趨于此的移民之多。
除了開山占田與商貿利益的驅動,當地移民潮的第三大動因在于土民參加科舉考試的優惠政策。永順地區施行科舉制度后,當地政府考慮到土民文教水平較低,便規定當地科舉中第的名額按“土三客一”劃定,以示公平[14]。這本可使得土籍考生科舉中第的機會大大高于客籍考生,但是一大批漢人看到了政策的漏洞,開始蜂擁至永順地區占地或者買地入籍,“爭冒考嗣”。這就使得清政府“科舉公平”的愿望落空,還使得當地低廉的土地價格飛升。如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永順知府駱為香就因為漢人在當地亂抬田價,導致“田土價較前昂貴已不啻倍蓰”而下令“禁漢人買土地”[22]。針對這些負面效果,清政府緊急出臺了“在前朝入籍為土,在本朝入籍為客”[23]的規定,以期徹底杜絕這種“喧賓奪主”的科舉亂象,但是此時永順地區的科舉移民已有一定的規模。
正是以上三個動因,使得永順地區吸納了大量的移民,成為了當地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他們也開始積極參與永順地區的社會事務,逐漸在永順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成為主角。
(二) 反客為主:客籍移民身份的轉變——以龍山縣黃氏宗族為例
在改土歸流后,雖然土目群體與地方政府發生過不小的權力沖突,但憑借著自身的調試,使得他們仍然能夠以新的“土籍士紳”的身份繼續掌握著地方控制權。如在永順府的龍山縣地區,當地乾隆年間建造、修繕公共設施的表彰行文中,均有彭姓、向姓、田姓等人員慷慨的捐贈行為,批準立碑者也多為歷任龍山知縣[23],可見當地政府對他們積極參與地方事務行為的高度肯定。在土司時期,龍山縣境內的彭姓、向姓和田姓便是頗有勢力的土目大姓[24]。改土歸流之后,龍山縣地的彭、向、田這三大姓氏的后人開始通過配合地方政府做慈善事務重新確立了在當地的權威。更進一步的是,他們以這種方式為地方政府排憂解難,在地方官員心目中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與國家建立起了良好的關系。
但是,隨著當地移民的不斷增多,客民憑借著先進的農耕技術與大規模的商業活動積累了雄厚的經濟財富。在物質生活不斷充實的同時,客民們開始迫切地期望參與當地社會事務并有效地掌握地方權力。仍以龍山縣為例,道光至同治年間該地區公共設施的建造、修繕行為無一例外由黃姓一族的“善士”出資完成[25]。可見,在清末的龍山縣地,黃氏宗族已經替代土籍的大姓宗族,在當地士紳群體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
龍山黃氏的始遷祖為黃鴻祀,于乾隆年間由省城長沙舉家遷往龍山開荒和經商,是當地改土歸流后較早的移民之一。與當地其他客民一樣,黃鴻祀很快因為開拓荒地和商貿活動擁有了大量的財富。暴富之后,黃鴻祀開始有意識地參與龍山當地的社會活動,以凸顯自己之于當地社會的重要性。如嘉慶初年,龍山縣爆發白蓮教起義,黃鴻祀自掏腰包“募鄉勇,捍衛城池”,為打退“教匪”立下很大的功勛。除此之外,黃鴻祀還在思想品質上樹立了道德的標桿。他“年未及壯”便喪偶成單,卻“鰥居五十余”,終身未再娶。聲稱“吾雖能給饘粥,固未忘攙菜作飯人也”。黃鴻祀的努力終于得到了回報,在他去世后,因為生前的義舉和德行,被當地官府“請祀鄉賢”,黃氏家族在當地的地位逐漸發生了改變[26]。
而讓龍山黃氏開始獲得當地控制權的關鍵事件是黃鴻祀之孫黃大鎮的科舉中第。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黃大鎮通過科舉考試中得進士,任職柳州通判,此為龍山黃氏入仕之首[27]。黃大鎮任官后,龍山黃氏隨之由富及貴。黃大鎮的祖父黃鴻祀和父親黃之翰由此得封奉直大夫,其長兄黃大鐘得封承德郎[27]。黃氏家族能夠集體封官加爵除了黃大鎮的科舉功勛之外,還在于之前黃鴻祀的所作所為為黃氏家族在當地奠定的民間威望。由此,清政府才會以黃大鎮進士及第為契機,給予了黃氏家族豐厚的賞賜,以期樹立一個能夠忠于“國家”的地方勢力。果不其然,得到封賞后的龍山黃氏開始更加積極地參與地方事務的處理,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得力助手[28]。到了嘉慶年間,“歷三世,丁漸繁”的黃氏家族看到時機成熟,便將修建黃氏宗祠的計劃提上了日程。
黃鴻祀病逝后,其長子黃之翰成為了家中決策人。他從兩方面認定修建黃氏宗祠的重要性:其一是龍山黃氏每次長途跋涉回長沙祭祖十分麻煩,費時費力;另一方面又認為要在龍山縣更加突出黃氏家族的影響力,應在當地修建新的黃氏祠堂,即可遙敬“遠溯所自出之祖”,又可供奉“始遷之祖”,還可團聚永順府的黃氏族人,以發展成當地的大姓宗族[29]。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黃氏宗祠在黃之翰的主持下在龍山縣修建完畢[29]。黃氏宗祠的修建,一則標志著移民而至的黃氏家族就此發展為龍山黃氏宗族;二則預示著客民身份的黃氏家族開始朝著地方士紳的身份發生轉變。到了道光年間,龍山黃氏宗族已發展為當地最大的宗族之一,黃氏族人也由此能夠通過科舉制度不斷獲取功名,光耀門楣,充實著黃氏宗族在當地的權力基礎[30]。
與當地土籍宗族勢力不同的是,客籍宗族勢力與“國家”是直接通過科舉制度建立的關系,這也讓地方政府更能夠接受他們的崛起與壯大。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三月,黃之翰三子黃大鉞以舉人身份邀請前龍山縣令徐瑃撰寫《中南黃氏宗祠記》,徐瑃欣然揮筆成帖,并將此碑刻立于龍山黃氏宗祠正門側[30],以示地方政府對黃氏宗族的肯定。光緒三年(1877年),龍山地方政府開始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 《龍山縣志》的基礎上編纂新的縣志。新版縣志與舊版縣志相比,只有兩處不同。其一是續寫了近六十年來的大事記;其二就是編者在新版縣志的“人物傳”和“賢婦傳”兩條目下,花了很大篇幅補入了黃氏族人的社會功績以及他們夫人的忠貞事跡[31]。以上事實均表明,經過數年的經營,黃氏宗族在龍山地方官員的心目中已成為地方領袖和道德楷模,是當地“國家權威”的代言人之一。此時的龍山黃氏宗族的身份已完全發生了改變,他們不再是那個初來乍到、只富不貴的客籍移民群體,而是在當地有著絕對權威的士紳群體。龍山黃氏宗族就此成為了當地社會控制權的掌握者之一。
四、兩大士紳群體的“沖突”與“制衡”——以龍山縣為例
在改土歸流后的地方社會,雖然控制權在土籍士紳群體和客籍士紳群體中進行著交替,但是地方政府不會一味地任憑一方勢力無限坐大,以釀成尾大不掉之害。所以在兩大勢力的權力“沖突”中,地方政府往往扮演著“制衡者”的角色,以維持當地社會權力分配的合理性。
以龍山地區為例。在清道光年間以后,當地并非黃氏一枝獨秀,仍有其他頗具影響的土籍宗族勢力,如向氏宗族。改土歸流后的龍山向氏宗族繼承了祖上在土司時期所積累的豐厚田產,十分富有。改土歸流后,他們的族人又通過科舉制度獲取了功名,重新建立了與國家的聯系[32]。但是,向氏宗族所積累的財富數量以及獲取科舉功名的族人數并不及黃氏,所以在當地的影響力只能屈于黃氏宗族之后。
不過,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絕不允許某一宗族勢力在區域社會一枝獨秀,即使這一勢力較土籍宗族群體更加便于駕馭。地方政府深知,過于強大而又沒有制約的宗族勢力極有可能發展成與他們對抗的地方權力,極不利于“國家”的概念在當地的推行。所以說,當黃氏宗族勢力過于強大時,地方官員便開始動用手中的權力有意地進行制約。
道光五年(1825年),龍山黃氏宗族黃大鐘(黃之翰長子) 被人告官。訴狀指出,身為保約的黃大鐘伙同其他地方小吏在采買塘汛兵丁的軍糧時,“藉公滋擾,濫派里夫,大為民累”。面對這一“莫須有”的控告,時任永順知府吳傳綺在只有口供的情況下認定黃大鐘等人罪名成立。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吳傳綺并未對黃大鐘等人進行嚴厲的懲罰,而只是對這種行為“禁革在案”[33]。可見,當地官員也并不認為有真憑實據可以處理黃大鐘等人,只是尋求通過這一事件對黃氏家族進行打壓。
這一訴訟所引發的另一事件是,龍山向氏宗族提出將此次訴訟的前因后果刻碑立于縣邑之中,明示于龍山縣民。向氏宗族的提議明顯是對黃氏宗族窘境的落井下石,但是竟然很快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批準。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十一月,就在《中南黃氏宗祠記》碑于黃氏宗祠前豎立的八個月之后,《龍山插堤采買兵谷及重修神廟柱碑》也于龍山卸甲祖神廟門前落成。該碑由時任永順知府黃宅中頒示,向氏族人出資興修[34]。“卸甲祖神廟”為乾隆時期土司后人彭氏所出資修建,供奉歷代彭氏土司,每逢三月十五,便有土目后人聚集于此進行慶典[34]。隨后,由于清政府有意消除“土司權威”的影響,該神廟逐漸荒廢。而借由此次立碑事件,該神廟被向氏族人出資重修,這一行為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龍山插堤采買兵谷及重修神廟柱碑》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構成,其一是龍山縣所承擔兵糧的具體額數,其二是黃大鐘等人“濫派”案件的前因后果,其三是亦有對歷代永順彭氏土司的歌功頌德之言[33]。可見無論哪一部分的內容,都標示著永順政府對黃氏宗族的故意打壓和對向氏宗族的有意扶持。
根據永順地區相關地方志、碑刻以及族譜等材料的記載,除了龍山縣,其他地區也有類似土、客宗族相爭的事件。而在這些事件中,地方政府一般都會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他們會根據當時的地方局勢,有意地偏袒實力相對弱小的一方,以借此使得諸多地方勢力的權力分配達到平衡,從而有利于“國家”概念在地方社會滲透。
五、結語
研究改土歸流后的永順社會可以發現,不同時期擁有地方控制權的主體勢力是不斷變動的。不同的群體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中能夠借助國家不同的制度與政策,通過文化、經濟、政治等手段來塑造自身在地方社會中的社會地位,以達到掌控區域社會的目的。其實,從永順社會內部權力交替現象可以窺見出西南地區在改土歸流后,地方社會所呈現出的變遷樣態。改土歸流后的土目群體,以及中晚清時期的土、客士紳群體,其身份屬性大相徑庭。但是仔細研究,又能發現他們的聯系。土目群體在土司時期是土司群體的附庸。改土歸流后,土司群體被清政府強制遷往內地,土目群體由此接替土司群體把控了地方權力。但是土司群體繼任者的身份顯然不會被“國家”所接受,清政府便開始出臺一系列制度與政策致力于消除“土司權威”在當地的影響。如此一來,土目群體開始通過自身的努力轉變身份,希望與“國家”重新建立聯系,繼續把持地方權力。其結果是,土目群體轉變為了清政府可以接受的土籍“士紳群體”。另一方面,在改土歸流后,地方社會的移民逐漸增多,“占田”和“通商”使得客民積累了豐厚的財富,也使得他們開始積極主動地尋求參與地方事務的機會。而“士紳群體”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使得他們能夠以經濟資本、科舉制度等要素轉變身份。最終,晚清地方社會發展為了由多個土、客籍的“士紳群體”分享地方權力的區域社會。而代表“國家”的地方政府在諸多大姓宗族之間起到了調和關系、平衡權力的作用,地方社會由此達到了相對穩定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