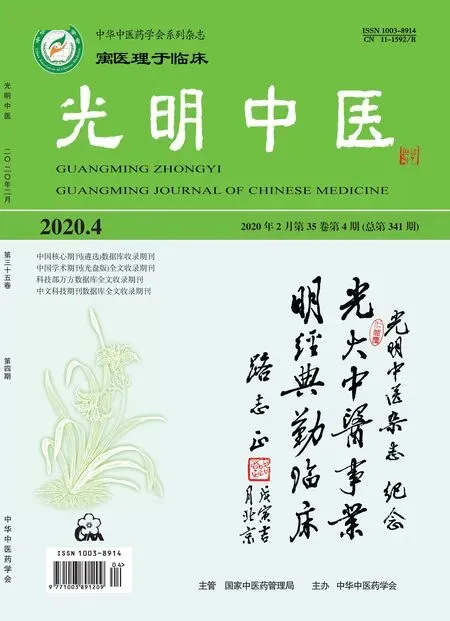蘇軾與中醫
——兼論宋代儒而知醫現象
王居義 汪居安 戴優雅
蘇軾是中國文人史上最濃厚的一筆,詞開豪放之風,詩數量龐大,文列唐宋八大家,書法為宋四家之首,畫尊文人畫派之宗。在“無儒不通醫”的宋代,蘇軾在中醫藥領域也有所建樹,筆者旨在還原一個真實而豐滿的蘇軾形象,一窺大歷史背景下宋代文人儒而知醫現象,了解宋代社會醫學文化,以期有所裨益。
1 歷史背景
兩宋為醫學全面大發展時期,上至皇帝重視,政府政策支持,宋歷代頒布與醫學相關的政令248條[1],下至文人士大夫學醫之風盛行,“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與疾病,謂之儒醫”。“儒醫”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朝廷詔令之中,反映宋代普遍的醫學繁榮現象和尚醫思想,而以蘇軾為典型代表的宋代文人[2],廣泛涉獵醫學領域,或通曉醫學基本理論,或熱衷養生之術,或參與編輯修訂校正方書,但這些人卻未真正從事醫療行業,較少或者無醫療臨床經驗,不可稱為“儒醫”,但他們卻對時代的醫學發展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我們將之稱作“儒而知醫”或“儒而通醫”現象。
蘇軾(1037—1101年),歷經仁宗(1022—1063年在位)、英宗(1063—1067年在位)、神宗(1067—1085年在位)、哲宗(1085—1100年在位)、徽宗(1100—1126年在位)五位皇帝,早在蘇軾生前992年已編成當時最大的方書《太平圣惠方》,仁宗時期,校正醫書局設立,醫藥衛生前所未有的發展,韓琦、范仲淹先后作為負責人,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員;神宗時期,采用王安石變法,改革醫學教育,由中央到地方,仿照太醫局制度,開辦地方學校,均設有醫學博士,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蘇軾與中醫的淵源由此揭開,縱觀蘇軾一生,其旁涉醫學的原因可作如下分析,首先在性格層面上,蘇軾樂觀豁達樂于接受各類事物,其思想中儒釋道三教合一,而后世的《東坡志林》之所涉內容范圍之廣,后世之人難以望其項背;其次,親人、好友、老師的離世是蘇軾接觸醫學的誘因,母程氏之死,蘇軾開始接觸醫學,以備時需,弟蘇轍、長子蘇邁體弱多病,其后父蘇洵和老師歐陽修離世亦然;最后,蘇軾一生久經貶謫,先后擔任八任地方知州,心系黎元百姓之生生性命,學習并參與醫學理論與實踐。
2 蘇軾與《蘇沈良方》
《蘇沈良方》為后人將沈括《良方》與蘇軾有關醫藥養生的論述合并而成,現有的一些文獻論述中常言《蘇學士方》,頗多舛誤,實際上并無《蘇學士方》一書,在蘇軾傳記和藝文志著錄中均未提及。據胡道靜、李淑慧考證[3,4],全書235篇篇目,蘇軾所作為57篇,而蘇軾偏好養生之術,且以丹藥頗多,為22篇,占1/3以上,追求延年益壽益氣服食之法,而體例形式上自由,多隨筆札記,甚者為書信、書貼,其內容上對養生方法和思想有精辟論述,涉及藥物醫理的闡發,具體內容在后文中會有論述。
[附]蘇軾57篇
暴下方、治泄痢方、茶方、治內障眼、記松丹砂、四味六麻煎、治癰瘡瘍久不愈、谷子煎法、脈說、蒼耳說、記菊、記海漆、記益智花、記食芋、記王屋山異草、記無修菜、記蒼術、論風癱、治風氣四神丹、服葳靈仙法、論圣散子、圣散子啟、圣散子方、服茯苓說、與翟東玉求地黃、治消渴方、龍膽丸、問養生、論修養寄子由、續養生論、養生偈、胎息法、養生說(2)、書養生論后、食芡法、藏丹砂法、上張安道養生訣、神仙補益、書辟谷說、陰丹訣、陽丹訣、金丹訣、龍虎鉛汞說、記丹砂、治眼齒、偏頭痛方、服松脂方、藥歌、柞葉湯、麥煎散、子瞻雜記(5)
3 蘇軾與養生
3.1 養生思想明人曾輯《東坡養生集》十二卷,且蘇軾性格上主體為樂觀豁達隨緣幽默。蘇軾曾有一句養生名言“善養生者,使之能逸能勞”為后世養生家所推崇。而究其養生思想我們用蘇軾自己所言的“安”與“和”來概括[5],蘇軾自己以舟行海上來喻“安”,以寒暑、晝夜、日月變化來喻“和”,并將二者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而“安”與“和”的養生思想其實也是蘇軾的行為寫照,久經貶謫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在條件異常艱苦的儋州,卻寫下“吾本儋耳氏,錯生巴蜀州”,還有像“一蓑煙雨任平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諸如此類,豁達自在可見一斑,將“安”與“和”發揮得淋漓盡致,安與和則是內心世界一份安寧自在,是處世為人為學的和而不同。
3.2 養生方法蘇軾曾創立胎息法,是一種呼吸吐納術,在《蘇沈良方》所錄的《養生訣上張安道》中,介紹了一種養神的方法,在中夜危坐,將意念、運氣、按摩相結合,因此也有學者介紹蘇軾時將之稱為中國瑜伽的創始人,由此看來,確實與瑜伽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養生說》中更是闡明“飲食五臟安和”,與中醫思維不謀而合。
3.3 生活習慣蘇軾有許多良好的生活習慣,這樣的生活習慣在當時是超前的,而且十分符合當下的養生保健行為。蘇軾注意睡眠姿勢,良好的睡姿能有效提高睡眠質量;吃飯時細嚼慢咽,飯后散步,十分利于食物消化;飯后用濃茶漱口,可以清除口腔中食物殘渣,同時濃茶具有殺菌作用,蘇軾自己也說過,“一是煩膩即出,而脾不知,二是肉在齒間,消縮脫去,不煩剔除”;五更起床,晨起梳頭,頭部為“諸陽之會”,含有眾多穴位,梳頭起到按摩保養的作用,現代頭療認為可以緩解疲勞,提高精神;泡腳,且冷熱水交替,水深至膝蓋;蘇軾還喜登山,“俯仰山林之下,可以養生治性”,登山為“動”,養生治性為“靜”,符合動靜結合的養生思想;注重生活居住的環境要優美清新,推崇住宿周圍廣植竹木,更有詩言“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而蘇軾的養生習慣我們可以概括為八字言,“樂觀、早睡、安步、晚食”。
3.4 食療藥養蘇軾主張多食菜少食肉,認為“甘膩肥濃”之物是“腐腸之藥”,且使人肥胖,同時主張少量肉與蔬菜同炒能保持形體,《東坡志林》里的麥門各飲、山芋羹是中醫營養學里的佳品,而其制作的東坡肉、東坡羹在民間廣為流轉,至今不衰,且蘇軾對飲茶飲酒頗具講究,后人稱之為美食家并不為過[6]。藥養方面,蘇軾種植茯苓、人參、地黃、菊花、枸杞用于藥療,且常年服姜乳延年,在種植的眾多藥物中,尤喜食茯苓,對其評價頗高,在《蘇沈良方》收錄的《服茯苓說》中稱“茯苓自是仙家上品”,與棗與芝麻同食。
以上這些構成了蘇軾的養生防病觀,從思想、習慣、食藥同源等多個方面構建,誠如蘇軾自己的三養理論,養福、養氣、養財。
4 醫學貢獻
蘇軾在醫學上有著一定貢獻,雖不是儒醫,卻儒而通醫,憑借其個人能力廣泛的興趣,在中醫藥諸多領域多有發揮,后世所編《蘇沈良方》《蘇軾全集》中在丹丸藥、攝生、飲食、情志方面有所裨益,至寶丸、蘇合香丸沿用至今;丹藥神仙一類則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化學發展;飲食養生方面已在上文詳述。在中醫理論上,《求醫診脈》一文批評時人以脈試醫的弊端,強調四診合參;《仇醫筆記 論醫》中指出過分取類比象的弊端,言近戲謔;蘇軾創麥門冬飲治療牙出血;蘇軾的醫學之路主要依靠自學,在其文字中出現《外臺秘要》《千金方》《傷寒總病論》等書,均是良書,學習經典,更重要的是蘇軾勇于求證,在其文字中常出現“有驗”“試之”字眼,為后學提供良好的范例,實踐去檢驗真理。更為后世稱道的是蘇軾被貶黃州時廣泛施藥,在惠州、儋州時治瘟,甚至向當地醫生交流經驗,在杭州任知府時,創立了安樂病坊,為百姓施粥用藥。
5 蘇軾涉病詩詞研究
涉病詩詞是指在詩詞創作中涉及疾病醫藥的作品的統稱,涉病詩詞的研究在整個詩詞研究中處于邊緣地帶,但于此文有較大意義,因涉病詞較少,先行論述,蘇軾存詞348首,筆者在其中找出涉病詞共11首,占比3.16%,具體如下:
涉病:
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瑞鷓鴣(城頭月落尚啼烏)》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
衰情少病,疏慵自放,惟愛日高眠。《一叢花(今年春淺臘侵年)》
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伏病入西州。《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
病緒厭厭,渾似年時個。《蝶戀花(雨霰疏疏經潑火)》
多病休文都瘦損,不堪金帶垂腰。《臨江仙(多病休文都瘦損)》
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行香子(昨夜霜風)》
涉藥:
芍藥櫻桃兩斗新。《浣溪沙(芍藥櫻桃兩斗新)》
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浣溪沙(羅襪空飛洛浦塵)》
其他:
今朝置酒強起/何事散花卻病,維摩無疾。《三部樂(美人如月)》
教有瓊梳脫麝油《南鄉子(未倦長卿游)》
蘇軾存詩2823首,據張子川考究存詩以及詩的序文,發現“病”字出現225次,而涉病詩206首,占比分別為7.97%和7.29%[7]。從蘇軾的涉病詩詞的研究中發現,出現過“病眸”“風痹”“苦于痔”“痢疾”“關節炎”“內障”“瘡癤”這些字眼,而關于蘇軾的死因暫無定論。蘇軾涉病詩詞所展現的人物形象,主體上是衰頹的,有苦悶煩躁不舒,但有豁達的情緒在其中,更多意義上是蘇軾對現行生命狀態審視的結果。疾病一直是中醫學關注的焦點,研究疾病發生發展和病人的病中心理不可忽視,而探討蘇軾與中醫的關系,自然不可忽視蘇軾的涉病詩詞。詩詞是蘇軾情感的宣泄點和爆發點,從中醫心理學上來說,可以反應病人的病中心理,繼而可以預測疾病的轉歸。蘇軾涉病詩詞的特點更多類似于一種精神療法,首先借助文學創作具有宣泄不良情緒的作用,繼而在創作中達到自我的和解。
6 蘇軾與龐安時
龐安時為杭城名醫、傷寒名家,著有《傷寒總病論》,正式提出寒、溫分治,對溫病學說的創立發展有重要啟示。蘇軾在元豐五年(1081)年患病求治于龐安時,也因此而結識。蘇軾嘆服于龐安時醫術,也時常舉薦龐安時為其他患者治療,二者結下深厚友誼。在《與龐安常》一文中,蘇軾與龐安時研討醫理,用哲學著作《太玄》解釋明目方的組方原理。蘇軾也為其《傷寒總病論》作序。而蘇軾與其最廣為流傳的則是圣散子方,其中淵源在此不再贅述。蘇軾曾與與龐安時同游清泉寺,亦寫下了千古名句,“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
7 儒而知醫現象
宋代時期,儒士普遍通曉醫理,而其中一部分文人,著書立說,參與醫療,甚至形成了一個儒醫階層,而以蘇軾、陸游為代表的文人,通醫而并不專事醫學,這種現象被稱作儒而知醫。宋代崇文,文人儒士地位極高,受儒家濟世思想的影響,加之諸多位統治者自身喜好醫學,故在宋代,大量普及醫學教育,編纂大型官修書目,舉辦國家藥材專賣,管理藥材行業,提高了醫藥行業人員的社會地位。宋代大興理學,儒醫相通,格物致知,儒士借此了解世界的“理”。在宋代,儒道釋三教迅速的本土化,許多儒士兼采佛、道的修煉之法,蘇軾便為典型。再分析來看,范仲淹曾為校正醫書局的提舉,發出過“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號召,后來甚至成為時代風氣。正是種種原因,才形成了“無儒不通醫,凡醫皆能述儒”的社會現象[1]。
8 總結
通過多個方面展開,力圖還原一個更加豐滿多元的蘇軾,條分縷析蘇軾與中醫的淵源,而以蘇軾為代表的文人,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儒而知醫的社會現象。他們探求醫理,豐富了中醫藥文化,他們借儒學研究,將仁愛、孝親、利澤生民融入到醫學之中,弘揚了“醫乃仁術”,并將醫學境界上升到一個全新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