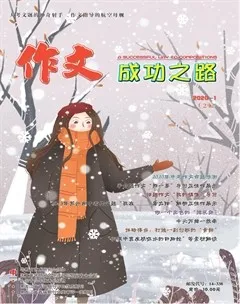微電影欣賞提升學生寫作素養
楊敏
剛下班回到家,我的手機微信的聲音就響了。“老師,前幾天我看到一部微電影,很震撼!明天星期五,您不是要給我們上作文課嗎?我覺得和明天作文題目很契合。”下面是一個網頁鏈接。
發微信的學生是俞某某,我的語文課代表。一向學習刻苦的她是老師的好助手。晚飯之后,我看了那部微電影《紅霧》:
明天的作文題目是課文《喂——出來》的續寫。一篇科幻短篇小說的續寫,最需要的就是學生在現實基礎上展開合理的想象。創作主題直指霧霾的微電影《紅霧》曾入圍2013年意大利卡斯特拉內塔電影節,與課文《喂——出來》在構思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結尾很有特點,出人意料且發人深省。但如何調動學生的寫作熱情,如語文新課程標準中所要求的“激發想象力和創造潛力,在實踐中學習和運用語文”“密切聯系學生的經驗世界和想象世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新精神”,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堂作文課中,學生的發言很積極。在結束語中,我這樣對學生說:“在看完《紅霧》后,我查詢了有關的資料。資料顯示,《紅霧》導演何帆曾就讀于武漢大學,上大學時加入了武大文華劇社。在老師看來,《紅霧》與課文《喂——出來》的結尾很相似,其實,我們也可以把《紅霧》看成是一篇微型小說,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嘗試寫一篇微型小說。”
過了幾天,我上完語文課回到辦公室,學生俞某某和王某某來找我。
“老師,這是我寫的小說《哥哥,我們看海去》。”俞某某拿出一本筆記本遞給我。
“老師,我也寫了一篇。”王某某羞澀地說。
“哦?”我顯然有點驚訝。想來上次作文課對學生還是有點作用的。我不禁竊喜。
“老師,其實,班上還有很多學生寫了小說。”俞某某打了小報告。
“是嗎?”我感到有點懷疑。平時寫作文的時候,很多學生喜歡在網上抄襲,為此,語文教師很是頭疼。
我回到教室,學生都圍了上來,興奮地告訴我這幾天寫了什么小說。看看這些小說的題目,什么“兩個女孩的世界”“來到土衛二號”“樹妖傳奇”“來自地球的生命”“相遇時間”“記憶機器”等等。
“寫得不錯!”我說,“老師想和你們一起寫小說。”
“真的嗎?”學生們都高興得叫了起來。
“不過,要想寫好小說,首先要學會認真讀小說,我想給你們推薦幾本書,不知道你們愿意看嗎?”我試探著問。
“好啊!”學生們回答得很整齊。
看到學生對寫作有這樣的熱情,我很高興。
這一周,我給學生推薦了畢淑敏的小說集《紫色人形》和葉辛的中短篇小說集《帶露的玫瑰》。
閑暇之余,整理書房里的報紙,在《中國教師報》上看到“同理心”一說。英語單詞“Empathy”,也被譯成“神入”“同感”“共情”“移情”等。“同理心”一詞最早是美國心理學家鐵欽納提出的,意思是指了解他人的感受、認知他人情緒的能力。“同理心”是心理學理論術語,一般來講,是認知和情感兩個方面,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換位思考”和“感同身受”。將微電影欣賞引入到寫作教學中,和學生一起看微電影、一起讀書、一起寫小說的快樂時光,不正是“同理心”理論所主張的,把讀寫教學看成是師生分享彼此體驗與思想的過程嗎?
中學生思想活躍,有豐富的想象力和獨特的創造力,對制作精良的微電影的喜愛是毋庸置疑的。將微電影欣賞和寫作教學結合起來,無疑是提升學生寫作素養的途徑之一。獨特體驗與見解是學生寫好作文的重要素養。“快餐式閱讀”充斥網絡的當下,學生靜下心來讀文學作品的不多,讀文學名著而有獨特體驗成為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葛威在《“同理心”——開啟學生心靈之門的鑰匙》一文中認為,“同理心,首先是理解和體驗他人的情感和認知”,教師只有“放下教育者的身架, 與學生平等對話,用同理心去接納他們, 理解、 寬容、體察他們成長的苦惱, 才能幫助其順利度過生活和心理上痛苦和迷茫,向上向善健康成長。” 和學生一起欣賞微電影、評電影、寫小說,教師把自己作為學生的一份子,注重的正是學生在閱讀、寫作過程中的真實的活動體驗。語文教師要培養“一個人在集體或與同伴的共同生活中的敏感度”, 就要和學生在一起閱讀、寫作。
微電影欣賞和寫作營造了和諧的師生關系。“同理心”理論強調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去理解彼此,師生共同觀影、寫作的過程就是要努力營造一種彼此了解的氛圍。微電影欣賞從師生情感體驗出發,通過寫作進一步挖掘微電影的價值和內涵。更值得一提的是,微電影的獨特魅力,吸引著學生,啟迪著學生,提升了學生思辨能力,在營造和諧師生關系的同時,也給學生寫作留下廣闊的創作空間。
微電影欣賞是在輕松、愉快甚至是親密的氣氛中進行的。電影欣賞和影評使得課堂閱讀教學中師生有了共同的話題,而且這種話題是學生們都感興趣的。活動中所體現的同伴關系使讀寫活動成為學生的一種“娛樂”活動。微電影欣賞下的同伴閱讀讓學生獲得更多的體驗、思考、表達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