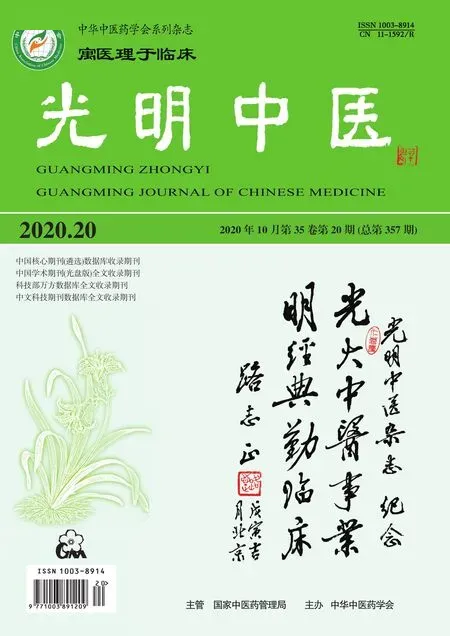六味地黃丸加減治療眩暈驗案心悟*
吉哲敏 徐 強
眩暈是以頭暈眼花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病證,眩即眼花或眼前發黑,視物模糊;暈是指頭暈或感覺自身或外界景物旋轉,兩者常同時并見,故統稱為“眩暈”,輕者閉目可止,重者如坐車船,旋轉不定,不能站立,或伴有惡心、嘔吐、汗出、面色蒼白等癥狀[1]。眩暈最早見于《黃帝內經》,稱之為“眩冒”“頭風眩”等等。仲景也延用《黃帝內經》之言,有“眩”“目眩”等名稱。《諸病源候論》中特設有“風頭眩候”一節。眩暈是臨床上常見癥狀之一,美國一項調查顯示:65歲以上的人19.6%有頭暈的癥狀[2]。現代醫學中的高血壓、低血壓、腦出血、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貧血、頸椎病、梅尼埃病等病,臨床以眩暈為癥狀者,均可依據中醫的“眩暈”范疇辨證治療。
1 眩暈的病因病機
引起眩暈的病因病機,各代醫家均有不同的見解,《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說明了肝在眩暈發生的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靈樞》中講:“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認為眩暈與腎精不足、氣血虧虛等虛損有關,張景岳一言概括為“無虛不作眩”;此外,《靈樞·大惑論》云:“邪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入于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又提出體虛加之外邪入腦可致眩暈;《金匱要略》中提及“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諸肢節疼痛,身體魁羸,腳腫如脫,頭眩,短氣……”等臨床表現,可概括為痰濕水飲能導致眩暈;宋代嚴用和在《重訂嚴氏濟生方·眩暈門》中講:“所謂眩暈者,眼花屋轉,起則眩倒也,由此觀之,六淫外感,七情內傷,皆能導致”,說明了外感六淫、七情內傷皆可引起眩暈;金元時期又有朱丹溪提出的“無痰不作眩”之論、劉完素的“內生風火致眩”之論;明代李時珍認為眩暈“皆是氣血虛弱,夾痰、夾火、夾風,或兼外感四氣”所引起;虞摶于《醫學正傳》中提出“血瘀致眩”之說;陳修園提出“無風不作眩“的觀點。總結各代醫家之觀點,眩暈起病有虛有實,病理因素多與風、火、痰、瘀有關。且眩暈一證,病變臟腑雖以肝為主,但與五臟六腑關系密切,頗為復雜。其治療原則主要為補虛而瀉實,調整陰陽[3]。虛者多滋補肝腎、補氣養血,實證則可平肝潛陽、化痰除瘀。臨床上以虛實夾雜更為多見,需要醫者根據舌脈癥狀辨證施治。
2 六味地黃丸方藥解析
六味地黃丸為宋代錢乙所創,原治腎虛導致的小兒“五遲”之證,后經易水學派的推廣和使用,逐漸被用于治療各種腎陰虧虛的病癥。趙獻可曰:“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薛己稱此方為“天一生水之劑”。縱觀全方,熟地黃滋陰補腎入腎經,山萸肉澀精逐風入肝經,取“肝腎同源”之意;山藥補脾固腎,補后天以充先天[4],三味補藥相配伍有滋腎、養肝、益脾的作用,稱為三陰并補,故為“三補”[5];澤瀉宣泄腎濁,又可防熟地黃滋膩;茯苓淡滲利濕;牡丹皮清瀉肝熱,稱為“三瀉”。全方以補腎陰為主,標本兼治,實為“滋陰補腎之祖方”。現代藥理研究證明,六味地黃丸具有降血壓的功效:熟地黃有強心作用,牡丹皮、山萸肉、澤瀉有降壓作用,茯苓、澤瀉、山藥有利尿作用,且茯苓、澤瀉又能促進鈉、鉀、氯等電解質的排出,抑制腎小管的重吸收[6];經研究表明,六味地黃丸對心、腦、腎等重要靶器官具備良好的保護功能[7]。在臨床上,徐強主任醫師用于治療眩暈,隨證加減變化,加上常用藥對,取得了良好的療效。
3 驗案舉隅
3.1 老年型眩暈張某,女,60歲。2019年11月因“間斷眩暈2年,加重3 d”來我院就診。患者2年前因眩暈就診于外院,測量血壓:150/100 mmHg,診斷為“高血壓病”,先后不規律服用“氯沙坦鉀片、馬來酸左旋氨氯地平片、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等藥物,血壓控制不理想。3日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眩暈癥狀加重,為求中醫治療,就診于徐強主任醫師門診。刻下癥見:患者自覺眩暈,無惡心嘔吐,無眼前黑矇,無肢體及言語不利,前額發緊,項部僵硬,近幾日間斷頭痛、心煩,腰背酸痛,下肢乏力,少寐多夢,健忘,口苦,納可,二便調。舌紅苔薄,脈弦細,尺部沉細。既往體健。平素飲食口味偏重,飲酒史30余年,約1兩/d,未戒斷。頭CT示:未見明顯異常;心電圖示:竇性心律,心率:89次/min;測血壓:158/104 mmHg。西醫診斷:高血壓病;中醫診斷:眩暈,腎精不足證。治法:滋補肝腎,平肝潛陽。予六味地黃丸配合對藥治療:熟地黃15 g,山藥10 g,山萸肉10 g,茯苓10 g,澤瀉10 g,葛根10 g,菊花10 g,天麻10 g,鉤藤15 g,牛膝10 g,黃芩10 g,川芎15 g,白芷10 g。7劑,日1劑,水煎服,早晚各1次。囑其戒酒,改善口味偏好,清淡飲食。二診時患者訴眩暈次數減少,前額發緊、頭痛、項部僵硬等癥消失,無口苦,寐差,心慌,余癥同前。望其舌紅好轉,診其脈弦象改善,血壓:145/98 mmHg。原方基礎上減白芷、川芎,加酸棗仁10 g,煅牡蠣20 g,煅龍骨20 g,甘松10 g。7劑,日1劑,水煎服,早晚各1次。三診時患者眩暈癥狀明顯改善,心慌、心煩癥狀消失,夜寐安,下肢乏力有所減輕,大便偏干,舌質稍紅苔薄白,脈滑,尺部沉細。血壓:140/90 mmHg。并訴已遵照醫囑戒酒,注意飲食口味。予二診方藥基礎上改熟地黃為生地黃,加火麻仁20 g。14劑,服法同前。后患者間斷來門診抄方拿藥,訴諸癥均見好轉,腰腿癥狀亦明顯改善。
按:本案患者年逾六旬,年老腎虧,證候群傾向明顯。腎精不足,髓海空虛,故而眩暈、頭痛、健忘、少寐;腰為腎之府,腎精不足則出現腰背酸痛、下肢乏力等癥狀;陰虛而生內熱,故患者可見心煩、多夢、口苦;觀其脈弦而細,舌紅苔薄,亦為腎陰不足、虛陽上擾之象,故診斷為腎精不足型眩暈。據王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的理論基礎,予以滋腎陰、瀉肝火治本,輔以平肝潛陽治標。吾師選以六味地黃丸為基礎方,舍牡丹皮防其寒涼傷胃;天麻與鉤藤,菊花與葛根是徐主任常用的2組對藥,前者平肝熄風,后者清熱生津。天麻中的天麻素與鉤藤中的鉤藤總堿對降血壓有協同作用[8]。 葛根能拮抗內皮素、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降低血壓[9],菊花同樣具有很好的降壓效果;牛膝一能引諸藥下行,二能活血利血,加川芎活血行氣,兩藥亦符“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論;且川芎又為治頭痛之要藥,白芷為治陽明經病要藥,均屬對癥治療。二診時患者眩暈次數減少,證明方藥對癥,守方繼服。然睡眠仍不理想,加酸棗仁養血安神,龍骨牡蠣平肝潛陽,鎮心安神;加能對抗心律失常的甘松一藥,治其心慌之癥;三診時患者癥狀明顯改善,唯大便干燥,改熟地黃為生地黃,清熱涼血,滋陰生津。加火麻仁潤腸通便。而腰腿酸軟等癥,屬多年舊疾,亦為肝腎虧虛之象,非幾劑藥物可解,需服藥一段時間方能見效。
3.2 青年型眩暈王某,男,37歲,2019年3月初診。主因“間斷眩暈2個月,加重1周”來我院就診。患者2個月前因頻繁應酬出現眩暈癥狀,就診于外院,測量血壓:155/100 mmHg,診斷為“高血壓病”,予“馬來酸氨氯地平片”5 mg晨起服用。1個月前查體,肝膽胰脾彩超示:輕度脂肪肝;血脂異常(具體未見);肝功能、腎功能未見明顯異常。1周前無明顯誘因眩暈次數增多,為求中醫治療,特來就診。刻下癥見:患者訴頭部眩暈昏沉,無惡心嘔吐,無眼前黑矇,無肢體及言語不利,頸項僵硬感,乏力,心煩,焦慮,納可,寐差,二便調,舌紅苔稍黃,脈浮細。既往體健,飲酒史10余年,約3兩/d,未戒斷。測量血壓:145/100 mmHg。西醫診斷:高血壓病;中醫診斷:眩暈,肝陽上亢兼氣虛證。中醫處方:天麻10 g,鉤藤15 g,菊花15 g,葛根10 g,黃芪20 g,生龍骨30 g,生牡蠣30 g,牛膝10 g,生地黃15 g,山藥10 g,山萸肉10 g,茯苓10 g,澤瀉15 g,牡丹皮10 g,白芍10 g,甘草20 g。7劑顆粒劑,水沖服,日1劑。西醫處方:馬來酸氨氯地平片 5mg 晨起服用。囑其戒酒,清淡飲食,檢測血壓動態。二診時患者訴仍偶有眩暈,但頻率降低,乏力明顯改善,頸項活動自如,無僵硬感,仍有心煩,雙上肢易有麻木之感,口干渴,納可,夜寐安,二便尚可。舌紅苔薄白,略干,脈浮細。檢測血壓最高為:140/98 mmHg,今日血壓:130/95 mmHg。原方基礎上改白芍20 g,加麥冬15 g,地龍10 g,遠志10 g,郁金10 g。7劑顆粒劑,水沖服,日1劑。建議停用西藥,血壓過高時臨時服用。三診時患者精神明顯改善,訴眩暈癥狀基本消失,心情愉悅,雙上肢麻木之感亦除,無口干口渴,服藥后稍覺胃部脹滿,納可,寐安,二便調,舌紅改善,脈較前滑而有力。檢測血壓較為穩定,最高130/95 mmHg,今日血壓:128/90 mmHg。于二診方藥基礎上改生龍骨20 g,生牡蠣20 g,減地龍、牡丹皮,加砂仁6 g。7劑顆粒劑,水沖服,日1劑。后隨訪血壓穩定,藥物均停,治療效果良好。
按:本案患者為年輕男性,主因不良生活習慣出現眩暈癥狀,中醫講酒屬風、屬火,發散力大,能行氣走血,易耗氣傷血[10]。患者長期飲酒,引動內風;加之工作勞累,出現乏力、脈細等氣虛之象,診斷為肝陽上亢兼氣虛之證。用天麻與鉤藤、菊花與葛根2組常用藥對;加龍骨、牡蠣平肝潛陽;白芍、甘草柔肝斂陰;二診時訴雙上肢麻木,吾師認為是血脈凝澀不暢所致,故予地龍通絡兼能息風;增加白芍劑量,并予麥冬用以滋陰生津,遠志、郁金用以安神解郁。三診因患者訴服藥后胃部脹滿,疑是方中寒涼藥物所致氣機不暢,故均稍加減量,并予砂仁溫中行氣。本案雖未見明顯的腎陰不足證之證,但吾師創造性地應用了六味地黃丸于其中,收效甚佳,說明了滋補肝腎之法在其他證型中也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4 結語
高血壓防治指南中指出,高血壓危險因素包括遺傳、年齡以及多種不良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如高鈉、低鉀膳食及肥胖、過量飲酒等等[11]。故吾師建議患者及時改正不良生活方式,對于血壓的控制也起到積極作用。這也提示我們在臨床中要重視詢問患者的日常生活,給予必要的醫囑,對于疾病的康復能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以上兩則醫案,雖然證型不同,但均運用了六味地黃丸于其中,治療效果顯著。其實,對于眩暈一病,自明清時起便有“肝腎陰虛,以腎為本”的觀點。本文所選兩案均符合以腎為本的思想,可見準確的辨證施治在治療復雜慢性病的過程中同樣能收獲很好的療效,且從腎論治的觀點也為吾輩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