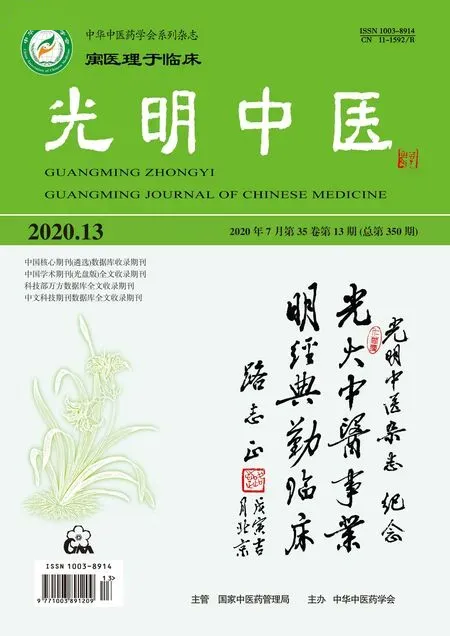從李東垣陰火理論論治糖尿病胰島素抵抗*
徐江紅 郝永蕾 吳雪紅 朱立春
2型糖尿病在我國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胰島素抵抗作為其發病的重要環節,貫穿于疾病始終,臨床控制不佳不但加重糖脂代謝紊亂,而且增加心腦血管并發癥發生風險。大部分患者通過飲食運動減重減輕胰島素抵抗依從性差,西醫治療胰島素抵抗藥物有限,且容易出現胃腸道反應及增加心衰風險。本課題組前期經過流行病學調查,結合臨床實踐分析胰島素抵抗形成的中醫病機,以李東垣陰火理論作為臨床指導,通過精準辨證隨癥加減,臨床收效明顯,對全面綜合防治糖尿病及由胰島素抵抗導致的心腦血管并發癥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1 西醫對胰島素抵抗的認識
胰島素抵抗是指機體對正常濃度的胰島素生物學反應低于正常。其涉及肝臟、脂肪及肌肉等多種組織的多種生物學作用。臨床一般以未接受胰島素治療的患者空腹胰島素水平超過15.7 μIU/ml考慮存在胰島素抵抗[1],其臨床表現形式多樣,包括肥胖(尤其是向心性肥胖)、黑棘皮征、多囊卵巢綜合征等。現已發現血清游離脂肪酸水平與胰島素抵抗密切相關,胰島素抵抗明顯時,脂肪組織釋放的炎癥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α、白介素-6等增加,內源性胰島素增敏因子脂聯素生成減少[2,3]。胰島素抵抗長期存在會發生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與肥胖和胰島素抵抗相關的惡性腫瘤。目前西醫治療胰島素抵抗的一線藥物主要是二甲雙胍及噻唑烷二酮類藥物,二甲雙胍主要是通過降低肝糖輸出、抑制肝腎組織糖異生及抑制胃腸道葡萄糖的吸收降低血糖水平,從而降低血清胰島素濃度達到改善胰島素抵抗的作用。而噻唑烷二酮類藥物主要是通過激活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相關受體γ,促進機體脂肪動員,提高胰島素敏感性,發揮改善胰島素抵抗的作用。但是臨床應用上述藥物仍存在一些局限,部分患者不能耐受二甲雙胍的胃腸道反應,而噻唑烷二酮類藥物會導致患者體質量增加,增加肝毒性及心衰的風險,并且與膀胱癌有相關性。
2 中醫對胰島素抵抗的認識
為了應用中醫解決胰島素抵抗問題,首先要了解胰島素抵抗產生的中醫病機。糖尿病屬中醫學“消渴”范疇,歷代醫家和古書沒有對胰島素抵抗做相應記載,但對消渴病的病因病機均做了詳細的論述。最早的文獻記載見于《黃帝內經》,漢唐以來,歷代醫家大多認為本病以陰虛為本、燥熱為標,病位在肺、胃、腎,分上、中、下三消論治。此后,隨著外界環境及患者生活環境的改變,國內中醫學者提出了許多新治法,如益氣滋陰法、清胃瀉火法、疏肝理氣法、活血化瘀法等[4]。近十余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轉變,肥胖和糖尿病患者發病率逐年上升,現代學者隨著對消渴病機研究的深入,突破了“三消論治”的觀點,提出了“脾虛致消”學說,主張從脾論治,結合西醫胰島素抵抗相關指標的臨床評價,推測中醫藥有改善胰島素抵抗及保護胰島β細胞功能的作用。本研究組前期曾針對秦皇島地區胰島素抵抗中醫證型分布做過流行病學調查[5],6個證型所占比例分別為:脾虛濕瘀證(55.4%),肝胃郁熱證(12.2%),濕熱內蘊證(12.0%),氣陰兩虛證(11.5%),脾腎陽虛證(4.7%),熱盛傷津證(4.2%)。提出脾虛濕瘀證是胰島素抵抗的主要證型。現代醫學認為胰島素抵抗主要與不合理的飲食結構和生活方式導致機體超重和肥胖有關,正如《素問·痹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過多的肥甘厚味不得正常運化,釀生濕濁,困遏脾氣;以車代步,多靜少動,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使中焦壅滯,脾失健運,水濕停聚,釀生痰濁;又多有陰虛熱盛說,失治誤治,予滋陰清熱藥,寒涼滋膩,傷脾礙胃,脾胃運化失司,而生痰濕,在脾虛基礎上發為消渴胰島素抵抗。現代學者第五永長等[6]認為,從臟腑看,脾虛、脾不散精是胰島素抵抗發生的病機關鍵;從病理產物看,痰濁、瘀血、痰瘀毒交結是胰島素抵抗發生的基本因素;從氣血陰陽看,氣陰兩虛是胰島素抵抗發生的病理基礎。黃開顏[7]認為2型糖尿病初期,胰島β細胞功能處于代償階段,機體出現高胰島素血癥,視其為中醫“氣郁”,陽不足則無以化津液,血中葡萄糖不能被外周組織合理氧化利用導致血糖升高,視為“津液輸布異常”,氣機不暢則津液不利,因此將“陽微結”視為胰島素抵抗的基本病機。
3 李東垣“陰火”理論的運用依據
李東垣,名杲,字明之,晚號東垣老人,“金元四大家”之一,補土派創始人。李東垣在《黃帝內經》理論的指導下,繼承了張元素重視脾胃及臟腑辨證用藥學術精華,結合個人臨證經驗,提出“陰火”理論,主張補益中焦脾胃,遣方用藥以“升發脾胃陽氣而瀉陰火”為基本原則,首創“甘溫除熱”治法,對后世影響深遠。
李東垣關于“陰火”產生機理的闡述見于《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中“若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則脾胃乃傷。喜怒憂恐,損耗元氣。既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于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即飲食勞倦及情志失調等導致脾胃損傷,脾胃氣虛不能充養人體生理之“少火”,而使之轉化為病理之“壯火”,耗傷機體元氣。中醫傳統理論認為,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而相火寓于肝腎兩臟。在正常生理狀態下,君火主神志,相火代君火行駛火令,心火的“陽熱”功能由相火完成。而在“脾胃氣衰”的病理狀態下,致心不主令,即君火不能主導相火,相火失制,故下焦相火代替心火行令之權,而妄行正令之火。心火亦失去了“陽化氣”之功,變成“心火獨盛”,即病理相火,也即“陰火”。因病理相火“壯火食氣”,又稱為“元氣之賊”。脾胃氣虛,升降失調,濕濁流于下焦,郁而發熱,陰火逆而上沖,加重對脾胃元氣的進一步損傷。可見脾胃元氣虧虛是“陰火”產生的基礎[8]。脾胃氣虛,元氣不足則陰火亢盛,元氣充沛則陰火自然消退,二者相互制約。“陰火”的臨床表現于《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中記載:“脾證始得,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陰火上沖,則氣高喘而煩熱,為頭痛,為渴,而脈洪,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9]《脾胃論·脾胃虛實傳變論》中記載:“脾胃一傷,五亂互作,其始病遍身壯熱,頭痛目眩,肢體沉重,四肢不收,怠惰嗜臥,為熱所傷,元氣不能運用,故四肢困怠如此”。
李東垣基于“陰火”理論,其臨床治療疾病十分重視升發脾陽,認為只有谷氣上升,脾氣升發,元氣才能充沛,生機才能活躍,陰火才能潛藏。若谷氣不升,脾氣下流,元氣將會匱乏,生機消沉,“陰火”即可因之上沖而產生各種病證。故提出了“胃虛元氣不足諸病所生論”“脾陽升則陰火降”等理論,創立了“以辛甘溫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等治法,所創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及升陽散火湯等方劑,皆是依“陰火”理論而設。并根據脾胃病隨四時氣候變化,隨證加減。時在春令,風濕相搏,于補中益氣湯加羌活、防風、升麻等補中升陽,風以勝濕;如暑傷胃氣,用清暑益氣湯補氣升陽,瀉火堅陰;時在秋令,秋涼外束,濕熱未退,肺脾兩虛,宜用升陽益胃湯健脾升陽,瀉火除濕,秋涼偏甚,寒邪克胃,宜用厚樸溫中湯溫胃理氣;時在冬令,脾腎陽虛,宜用沉香溫胃丸溫通陽氣,上熱下寒,寒熱錯雜,宜用神圣復氣湯清上溫下。選藥宜用黃芪、人參、白術、炙甘草健脾益氣;升麻、柴胡、葛根升陽舉陷;防風、蔓荊子升發陽氣;羌活、獨活、茯苓、澤瀉健脾利濕;黃連、黃芩、黃柏、牡丹皮、白芍清瀉陰火;陳皮、木香行氣消食;枳實、厚樸消滿除脹等[10]。
4 結語
綜上,胰島素抵抗產生的中醫病機與李東垣“陰火”理論不謀而合,針對脾胃氣虛、元氣虧虛,“陰火”鴟張的基本病機,以李東垣“陰火”理論為指導,經臨床辨證論治,隨癥加減,從而達到改善患者氣血津液代謝紊亂,臨床治療胰島素抵抗收效明顯。因此,希望從“陰火”辨治為糖尿病胰島素抵抗中醫治療提供一條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