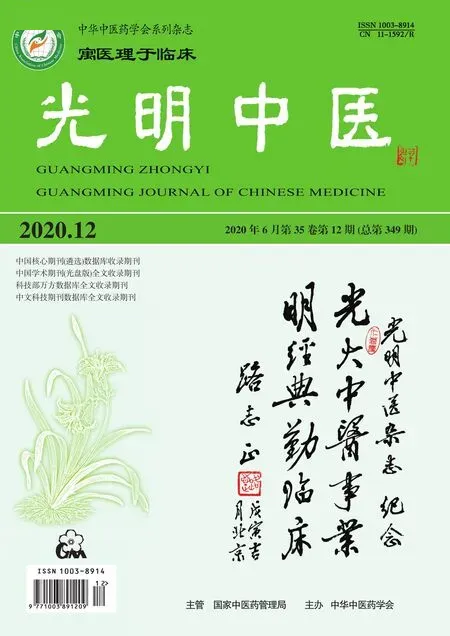張永康教授調氣化飲論治術后胃癱經驗*
霍華英 閆鵬飛 喬榮躍 張鵬鵬 王 姝 張永康△
張永康主任醫師,省優專家,碩士生導師,山西省學術技術帶頭人,全國第二批名老中醫專家學術經驗繼承人,師承原明忠導師;第三批全國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師承呂仁和、肖承悰、侯振民導師,現第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臨床經驗豐富,現將老師治療術后胃癱經驗介紹如下。
術后胃癱綜合征(PGS)簡稱術后胃癱,亦稱功能性胃排空障礙,該病主要發生于腹部腫瘤切除術后, 胃腸功能紊亂而致胃排空延緩,損害腸道屏障能力,尤以胃癌根治術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最為常見[1],是腹部手術后較頑固并發癥之一,嚴重影響術后患者生活質量及營養情況[2]。其發病率[3,4]在國內為0.6%~7%, 國外為5%~10%。術后胃癱綜合征是多因素所致,目前術后胃癱綜合征的發病機制尚不明了,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5]。文獻報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手術創傷導致胃腸動力障礙;②術中切斷迷走神經及胃腸道神經導致胃腸運動不協調;③Cajal細胞減少導致胃電波活動減少;④手術應激使胃壁順應性降低和幽門痙攣;⑤異常的胃腸激素和肽類的作用;⑥精神應激反應引起的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等,因此尚需進一步研究。目前尚以保守治療為主, 經非手術綜合治療后多能治愈[6-8]。胃癱一經確診即給予禁食禁水、持續胃腸減壓、靜脈補液、靜脈營養支持、維持水電解質平衡、補充白蛋白、維生素及微量元素、抑制胃酸分泌、高滲鹽水洗胃減輕吻合口水腫、糾正負氮平衡等。部分中醫依據“六腑以通為用”,主張以通降為其治則,方用承氣湯類加減,同時或可加用辛香入絡之藥促進藥物吸收, 作用直接, 不損傷脾胃[9-11];或用中藥保留灌腸,避免口服給藥并減少口服中藥給患者之不適感, 減輕吻合口負擔, 避免吻合口漏之風險, 使患者早日經口進食, 恢復正常生活[12-14];亦有湯藥聯合針灸采用穴位注射,更有利于胃腸整體功能恢復,比傳統療法效果好,且療程短,安全性高[15,16];另有中西醫結合治療胃癱療效明顯優于單純西醫治療, 可顯著縮短胃蠕動功能恢復的時間, 減少胃腸減壓引流量, 促進功能恢復[17]。
《中醫診斷與鑒別診斷學》提出胃飲,即狹義痰飲,也就是《金匱要略》的痰飲:提出胃飲分痰飲中阻和脾腎虛衰,分別用甘遂半夏湯和苓桂術甘湯加減治療[18]。張永康老師認為術后胃癱有濕熱蘊結型、胃陰不足型、脾胃虛弱型和氣滯飲停型即胃飲型。濕熱蘊結舌苔黃膩者,宜清化濕熱、調暢三焦,方用三仁湯加減治療;胃陰不足舌紅無苔者,宜滋陰養胃方用益胃湯加減治療;脾胃虛弱舌淡胖脈細弱者,宜補脾和胃,方用補中益氣湯加減治療;氣滯飲停舌淡苔滑脈弦者,宜調暢氣機、化飲啟癱,方用柴平湯加減治療。在此重點談談張老師術后胃癱從飲論治的經驗體會。
1 《金匱要略》中的痰飲
《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第十二》有云:“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為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原文最早提出飲證,并詳細論述水飲分類,因其停留部位其癥狀表現迥異。
痰飲一詞自此沿用至今,其病機乃臟腑功能失調,水液代謝失常,停聚體內為患,它既是一種病理產物,又是疾病發生之根源。臨床據其所停部位可見嘔、咳、喘、滿、痛、腫、眩、悸等癥。對此仲景有言,“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指出治飲當從陽虛立論,治宜溫通陽氣。
2 西醫“望診”辨胃癱
中醫歷來強調望聞問切,司外揣內,根據臨床表現推測機體內在,故而對內在構造的準確把握相對局限,病種的復雜化及精準度促使中醫要與時俱進,為實現中醫診斷疾病的可視化,進而更加精準地判斷疾病性質和部位,我們可借助現代醫學的先進手段。理化檢查中的X線、B超、CT、核磁共振、放射性同位素檢查及血、尿、便常規檢查等均可視為中醫望診的延伸。中醫辨證論治有效結合理化檢查,則病之機理更加明晰,痰飲病的診治即是有力例證。原明忠教授臨證中,通過B超、消化道造影以及胃鏡對水飲進行準確定位和定量,明確中西醫診斷,進而辨證用藥,療效更為顯著[19]。
3 調氣化飲論治胃飲
胃腸手術后患者胃腸道蠕動減弱或消失,導致胃內容物或積液滯留,患者常可聞及上腹部振水聲,胃區叩診呈鼓音,即水停胃中,可借助B超進行診斷,現代醫學以每日胃腸減壓量≥800 ml/d,連續治療≥10 d考慮為胃癱;同時伴有渴不欲飲,惡心、嘔吐,胸脅痞脹,納呆,喜太息,甚或出現胃痛、腹痛等癥,大便常硬,小便不利,舌苔白滑或泛黃、脈多弦,有力或無力。
《素問·刺法論》有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正氣充足,術后胃之蠕動功能方可盡快恢復;《素問·評熱病論》亦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可見正氣不足為本,水飲之邪停留乃其基本病機。《素問·經脈別論》:“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于脈”。《素問·經脈別論》:“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可見,水液正常轉化與脾、肺、腎三臟有關,脾主運化水濕;肺主通調水道;腎則主水,腎若關門不利,聚水而從其類,水谷停聚于胃,久則化成水飲和積滯。
中醫認為,外科手術尤其腹部手術多損傷中焦脾胃脈絡,耗傷人體臟腑精、氣、血、津液,術后脾胃受損,中焦氣機失調,水飲停滯中焦,濁氣上逆則欲飲而喜嘔,不思飲食;飲停則氣機不暢現胸脅脹滿、喜嘆息。該病屬本虛標實,治宜扶助脾胃,溫化水飲。
張師臨證常用西醫常規治療合加味柴平湯。藥物有:柴胡10 g,黃芩6 g,黨參10 g,半夏10~15 g,補骨脂3~5 g,吳茱萸3~6 g,蒼術10 g,厚樸20 g,陳皮10 g,生姜6片,杏仁10~12 g,炙甘草6 g。水煎服,100 ml/袋,口服或胃管注入,200 ml/d,每次30~50 ml,隔2~3 h一次。此法最快者胃引流液2 d消失可進食,平均7 d緩解。
4 典型案例
宋某,男性,52歲。2017年7月5日因胃癌入我院胃腸外科。 2017年7月 15日行“遠端胃大部切除術”,術后禁飲食留置胃管,持續胃腸減壓,2017年7月 23日初診,即術后8 d,病人仍有惡心,腹脹,腹痛無嘔吐,有排氣,無排便,每日胃液引流量仍大于800 ml,伴有口苦,煩躁,兩脅脹滿,舌質紅,舌苔黃膩、脈弦,有力。中醫診斷為胃飲,辨證為:濕熱蘊結,給予宜清化濕熱、調暢三焦,方用加味柴平湯合三仁湯加減,組成:柴胡10 g,黃芩6 g,黨參6 g,清半夏10 g,補骨脂5 g,吳茱萸6 g,蒼術10 g,厚樸20 g,陳皮10 g,生姜6片,杏仁10 g,炙甘草6 g,白豆蔻10 g。6劑,水煎服,100 ml/袋,口服或胃管注入,200 ml/d,每次30~50 ml,隔2~3 h一次。2017年7月 29日二診:患者胃腸減壓量每日約有400 ml,仍有口苦口干,大便干,舌淡紅,舌苔薄黃稍干、脈弦細。去蒼術,加白芍10 g,郁李仁10 g,6劑后患者停用胃腸減壓,給予胃管注入流質飲食。后調理半月后未出現反復,出院。
按:原柴平湯主要包含藥物為黨參、柴胡、半夏、厚樸、甘草、黃芩、茯苓、蒼術、陳皮、生姜,摘錄自《增補內經拾遺方論》卷三引《官邸便方》:“方用小柴胡湯以散風寒,平胃散以消飲食,故名柴平。”《醫方考》中“以小柴胡湯以和解表里,平胃散以健脾利濕,二方合一,故名柴平。”張師的加味柴平湯于原方中加入補骨脂、吳茱萸以及杏仁,其中補骨脂溫腎助陽,引上逆之氣下行;吳茱萸散中焦之寒,降逆止嘔,防陰濁之氣上逆;杏仁祛痰降逆,下氣潤腸。加用三藥兼顧上、中、下三焦,使氣機得以調達,水濕得以運化,共奏消滿降逆之效。該患者初診正氣微衰,濕熱較重,故給予加味柴平湯合三仁湯以清化濕熱,疏肝健脾和胃化飲,二診患者口干,四診后考慮飲已化,防過而傷陰,并鞏固其清熱利氣之功而加用白芍以養血平抑肝陽,郁李仁以潤燥滑腸,下氣,利水。
5 加味柴平湯方解
加味柴平湯源于小柴胡湯和平胃散合方加味。小柴胡湯出自《傷寒論》,主治傷寒少陽病寒熱往來、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目眩、脈弦細等癥。平胃散源于《醫方類聚》卷十《簡要濟眾方》,其主治濕困脾胃所致的脘腹脹滿,不思飲食,口淡無味,嘔吐惡心,噯氣吞酸,舌苔白膩而厚,脈緩等癥。
方中柴胡味苦性平,入肝膽經,能疏泄氣機之郁滯;黃芩味苦性寒,防柴胡升散太過;半夏、生姜和胃降逆止嘔;蒼術芳香苦溫,入中焦能燥濕健脾,使濕去則脾運有權,脾健則濕邪得去;厚樸芳香苦燥,長于行氣除滿,且可化濕。與蒼術相伍行氣以除濕,燥濕以健脾,使滯氣得行,濕濁得去;陳皮理氣健脾、除濕化痰,以助蒼術之力、厚樸之力;黨參補氣健脾;補骨脂溫腎而暖中焦助胃腐熟脾之運化,使停飲溫化而散;吳茱萸具有溫陽散寒、疏肝下氣之功,與黃芩為伍,寒熱并用,共收清肝止嘔之效;杏仁宣肺利水,肺與大腸相表里,肺氣宣則大腸通利,水液從大腸而下,肺可調水道,水液下輸膀胱,氣化而從小便排出;炙甘草補脾益氣,調和諸藥。以上諸藥,共奏疏肝健脾和胃調氣化飲之功[20]。可見調氣化飲與傳統飲證診療方法不同,不是單純的溫化水飲,而是通過調暢氣機使氣機升降得宜,痰飲水液自行,本法寒熱并用,升降并用,補散并用。
術后胃癱綜合征診療根據病人實際情況調氣化飲,針對標本同時治療。現代疾病較古代多樣,合病并病多見,其診治亦較前復雜。借助現代科學儀器可幫助我們觀察胃部蠕動、胃飲停留部位、性質及總量變化情況,但準確辨證是療效的關鍵,仍需結合中醫的辨證論治,辨證與辨病相結合、局部 (胃脘) 與全身分別辨證,在古人肩膀上聯合西醫先進技術,實現中西醫結合,為病患謀取最大利益[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