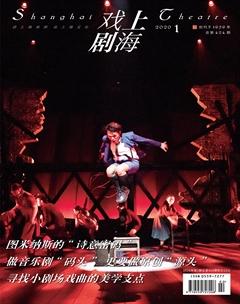當我們講故事時……
夢珂

《反極》(The Antipodes)是英國國家劇院2019年9月創排的新劇目。其作者和導演是2014年普利策戲劇獎的得獎人安妮·貝克(Annie Baker)。本劇的舞美設計則是克洛維·蘭佛德(Chloe Lamford),她之前與貝克合作的《約翰》(John)于2016年在英國國家劇院上演,也獲得了市場和口碑的雙重肯定。《反極》則是兩位女藝術家的第二次合作。
《反極》的劇情非常簡單,一群基本由白人男性組成的職員(整個團隊只有一位女性,一位黑人)在一個封閉的會議室里被要求創造出關于某個怪物的故事,這個怪物不能是司空見慣的精靈或是侏儒,它需要有空前絕后、絕無僅有的獨創性。盡管觀眾從未被告知這群人創作的究竟是什么(貝克在演后談“不小心”透露是電子游戲),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是,他們需要創作一個“故事”。他們直屬的老板Sandy是個看上去隨意且和善的人,他對他們提出的要求卻并非如此:為了激勵團隊的創作,他們被要求提供自己的“故事”。
《反極》便從幾位雇員分享自己的故事伊始,如晉人倒食甘蔗一般,逐層深入探討“故事”的含義,以及在當今由資本和市場雙雙把持的文娛產業中,“故事”到底意味著什么。Dave分享了自己利用背棒球口訣讓女朋友對他“贊不絕口”的秘訣,黑人小伙Adam則說出了自己初次歡愛的經歷,女性雇員Eleanor分享的也是她和男友之間的私人情趣。而當幾乎所有人的故事都和性/生殖器息息相關的時候, Danny看似毫不相關的故事卻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Danny講述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他和妻子在拜訪朋友家的時候,無意經過一片玉米地。他在玉米地上發現了一塊“一半深紅、一半淺紅”的粉紅色石頭,他覺得它漂亮極了,就和玉米須一起拿回了家。當他妻子問他這些是什么的時候,他發現這些閃閃發光的物件無外乎是一些“泥濘且粗糙的玩意兒”(muddy sort of crusty objects)。這些在玉米地的時候閃閃發光的粉色石頭和玉米須,一旦離開了玉米地放在家中,看上去慘不忍睹(horrible)。Danny下意識地感到羞赧,從不對妻子撒謊的他對妻子說“我不知道”,便把粉色石頭和玉米須一起丟了出去。這個故事是所有由他們講述的故事中筆者的最愛。在荒蕪廣袤的玉米田中熠熠發光的玉米穗子和石頭,一旦失去了襯托它的環境便黯然失色,這又何嘗不是“故事”,或者說,依賴于炮制“故事”的文娛產業的隱喻。我愿意相信創作者坦誠的表達欲和真誠的交流欲,然而當閃閃發光的石頭和美麗的玉米須被放在了劇院和電影院里被迫進行展覽的時候,它真的還能發光嗎?肉眼可見的物品尚且如此,更何況是與“生而為人”息息相關的故事呢?
第二個故事是Danny年輕的時候當養雞場看守的時候發生的。他的工作是在傍晚的時候將農場的雞全都抓到籠子里去,閂上雞籠并放下電閘門,以免它們在夜晚被狐貍咬死。然而,由于他對雞的一些怪奇幻想,他害怕自己抓雞的行為會傷害到雞,或者會被它們傷害。因此,他沒在傍晚就完成工作,而是拖到近午夜十一點才做完。盡管沒有雞死于他工作期間,他卻后悔于沒有真的完成“捉住”這一動作,并認為如果他能夠成功抓住一只雞,他的人生也許將大為不同。著名劇評家比靈頓(Michael Billington)認為它是最典型的“安妮·貝克式”風格,擅長在看上去平凡普通的事物當中描繪出非凡卓越的細節。和Danny同事們的“辛辣”故事相比,這個毫無波瀾的故事甚至幾乎只能算流水賬,然而Danny細細描述他幻想雞身上覆滿了羽毛、充滿活力的雞胸肉,抑或是他幻想自己將它們抱在懷中愛撫、卻被它們的爪子抓傷等細節,在沒有影像的情況下,給筆者留下了怪異悠長的回味,導致筆者在接下來好幾天中,一旦吃到雞肉,便同樣會控制不住地幻想它們起伏的胸脯,以及它們被像Danny一樣的中年壯男抱在懷中愛撫的樣子。
同樣在“樸素平凡中窺見卓越”的還有蘭佛德的舞美設計。作為貝克的老搭檔,蘭佛德的舞美設計乍看之下稍顯普通。筆者起初認為,她完全可以更為光怪陸離一些,一如她為《約翰》所設計的舞臺那樣,乍看上去是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的,卻在細節處透露出怪異(uncanny)和詭吊陰森(creeping)的氣氛。《反極》似乎也理應如此,一個講述“創造怪物”的故事卻只有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會議室大圓桌,除了堆積如箱的巴黎水外,什么都沒有。然而,當再度思考貝克想要表達的內容時,或許,枯燥無味的大圓桌,才是最合適的舞臺:那些激動人心的故事,誕生的場所確是那么枯燥無聊,甚至是那么殘忍。而當我們看到一箱箱堆積如山的巴黎水,多到Eleanor能夠當作一張床躺在上面的時候,其設計已超出了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的邊界而到達了荒謬的境地。它提醒著觀眾應該更早意識到其背后隱含的殘酷邏輯:有多少的礦泉水,就有多少無休止的加班,就有多少個不能回家的周末。盡管過勞和加班是現代社會職場人士共同的煩擾和困境,對這些“造夢者”來說,他們的處境更為諷刺:被榨干的不僅只是他們的身體,還有理應只屬于他們自己的故事。
終于,他們的集體創作陷入困境,而Sandy也越來越少出現在這個樸素到一無所有的辦公室中。某一日,在Danny離職、記錄員Brian生病、大家都疲憊不堪的情況下, Adam卻突然進入迷狂的狀態,講述了一個類似克魯斯神話風格的故事:
孤獨的深淵始祖生出了多頭多臂的怪物,又生出了原初的母牛(proto-cow)為怪物提供乳汁。當原初母牛吃草的時候,她舔過的灰色石塊,變成了三個最初的神祇,一個女神和兩個男神。他們謀殺了自己的兄弟,那個多頭多臂的怪物,用他的尸身創造了世界。女神和男神的交媾創造了毒蛇和惡狼,她孕育了年月、時間、四季、死亡、瘟疫。毒蛇和惡狼出于嫉妒,強奸并殺死了他們的女神母親,她的頭被他們割掉變成了月亮,她的嘴里爬出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和毒蛇一起環游世界,她看到了精靈和馬人,看到了頭上長著陰莖的女人和嘴里長著陰道的男人,看到了頭上長腳、抑或是用頭作腳走路的人們。她和毒蛇一起回到了住的地方,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告訴了男人。這是第一個被訴說出的“故事”。然而她的先祖男神因為她講故事而給予她懲罰,從此以后女人世世代代都有了月經。神為了懲罰人類而發明了戰爭,人類便不斷重復著戰爭,直到他們把地球另一端頭腳相倒的人類全部抹殺,而故事,也隨著戰爭的血腥程度變得愈發冗長。
盡管是出于貝克自己作為導演/劇作家的選擇,筆者還是對蘭佛德在這個故事上沒有什么發揮的余地而略感失望(當然,這確實是貝克一再提醒我們,炮制出的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故事的過程,本身有多么無聊甚至痛苦)。Adam敘述的這個故事,無論作為電影、電視劇還是電子游戲的題材都具備十足的吸引力,然而作為《反極》一劇的“點題”還是稍顯刻意且冗長,無非只是貝克作為創作者漫無邊際的表達沖動下的產物而已。
Antipodes是一個幾乎無法被準確翻譯的詞,它既可以指地球上可穿越地心、直接相對的兩極,亦可指地球彼端那些頭上長腳的異人。國家劇院《反極》的海報也明示了這點。它可能就是這些人苦心追尋的怪物形象,也或許,那個怪物就是“故事”本身吧。和Antipodes一樣,“故事”其實也是一個幾乎無法翻譯的詞。它可能意味著“生而為人”的定義,指向未來和希望;它也可能淪為資本的婊子,看客的玩物,奔赴被觀看被獵奇的深淵萬劫不復。華語電視劇經常被所謂 “抄襲風暴”席卷,筆者亦被科普所謂的抄襲不再是字對字的照抄,而是將不同橋段進行拼接,是為“融梗式抄襲”。在進行虛構文學創作的朋友亦告訴我說,故事即所謂大綱,那是故事的精華,冥思苦想出的“大綱”被“文筆”更好的人拿去“潤色加工”,是令“原創者”最痛不欲生的事。我想,或許我們對于“抄襲”的定義,其根本仍然來自于對“故事”的定義。明清戲曲小說互相剽竊的情況實際上非常嚴重,卻沒人稱之為“抄襲”或者“融梗”,然而到了當下,文娛工業的資本運作方式和市場的審查及期待,都在影響我們定義“故事”的方式。故事究竟取決于那個“大綱”,還是“我”與故事的關系,還是“你在觀看故事”這件事呢?有無數的年輕人在暑假去農場打工做養雞場的看守,但“Danny捉雞的故事”可以是獨一無二的嗎?如果它是獨一無二的,必定不是因為它的“大綱”,而是Danny對“抓雞”一事巨細靡遺的幻想,對沒能抓成雞的悔恨,以及對可能改變的命運的展望。同時,它如果可以獨一無二,也是因為演員Stuat McQuarrie對Danny這個角色的表現(presentation)/再現(representation),更是每個觀眾聽到這個故事后的反應。這些觀眾不僅是Danny的同事們和Sandy,也是坐在臺下的我們。對創作者來說,“故事”究竟意味著無處排遣的表達的沖動,還是為了觀眾/讀者/市場的拍案驚奇而冥思苦想?而對觀眾和讀者來說,觀看/思考/凝視/消費之間有沒有邊界呢?有的話,它們又分別是在哪呢?
“后來人們開始購買故事,花錢請人們講故事。再后來,故事就不再自由了。”這是Adam那個克魯蘇神話故事的結尾。如果人類的意義和歷史都由故事定義,那么我們或許從來都沒有自由過。但是,那又何妨?如果被誤解是人類永生永世不得解脫的刑罰和宿命,那么不斷地訴說與被訴說,傾聽與被傾聽,也是與之對抗的唯一希望和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