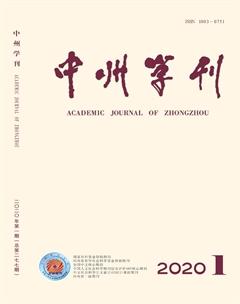市場自由的倫理限度
甘紹平
摘 要: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創造發明的一種精巧的調節生產與消費的有效機制。作為一種人造之物,其本身無所謂道德與否。但從市場經濟能夠帶來極大滿足民眾需求之結果的角度來看,它與倫理道德是有關聯的。市場經濟這種意義上的道德并不體現于企業家的素質之高尚與動機之善良,而在于市場經濟這一機制的功能與結果的合道德性。具體而言,一方面,市場經濟能夠導致有道德意義的結果;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運行邏輯中能夠反映出一些諸如自由、平等、誠信等重要的倫理原則。盡管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的經濟,有著自由的價值內蘊,但市場經濟的自由并不是萬能的,而是需要有其自身所無法創造的框架性條件的約束與保護,這一框架性條件充滿著倫理道德的意蘊。沒有國家建構的框架條件的保駕護航,市場經濟就難以避免從自由到自毀的命運。換言之,市場自由的充分展開,亟須倫理道德的約束與矯正。
關鍵詞:市場經濟;倫理限制;自由;框架條件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20)01-0095-10
在西方倫理學史中,亞里士多德、康德、邊沁、密爾、霍布斯、洛克、盧梭都是彪炳史冊的思想巨星、體大思精的學術泰斗,但在思之深刻、見之深遠方面毫不遜色的亞當·斯密,卻無法享受如此馳名宇內、光耀千古的隆重地位。在倫理學原理的研究中,德性論、功利主義、義務論、契約主義作為核心道德理論各霸一方,形成了四足鼎立、大體恒定的學術格局,盡管斯密的卓越貢獻與功利主義和契約主義的理論各自的精進密切相關,但是他未能被列入其中的任何一派。斯密的這種看似不公的歷史待遇或許與著名的“亞當·斯密問題”脫不開干系。斯密既是道德哲學教授,更是市場經濟學說之父。作為倫理學家,他寫了《道德情操論》,力陳同情原則;作為經濟學家,他撰了《國富論》,強調自利原則。按照傳統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十分盛行的觀點,道德與市場是完全對立的兩極,斯密的道德學說與其經濟理論正相沖突,在他身上體現了市場與道德之間的矛盾,這就是所謂“亞當·斯密問題”。即便是在當今,斯密問題仍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例如,根據調查,盡管德國有一多半的民眾已經長久地生活在市場經濟中,并享受到了該體制所帶來的極大的物質繁榮,但他們仍會拒斥市場與競爭。在他們看來,市場經濟與團結的道德要求是截然對立的,企業在競爭中只致力于盈利,市場經濟里的企業活動本身沒有道德質量。可見,或許正是由于斯密問題產生的困擾,他在倫理學史中的尷尬地位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
按照斯密本身的立場,所謂斯密問題根本就是一個偽問題。因為斯密的理論貢獻恰恰就在于,他揭示了市場經濟這一人類發明的偉大工具或重要機制,通過極大激發人們的自由活力和創造性潛能,而產生出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道德的結果;他的這一發現,在人類倫理學思想史上毫無疑問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
早在斯密之前,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在其《蜜蜂的寓言》中就提出過私之惡能夠成就普遍的公益這一思想。他指出,蜜蜂都是個體性的而且也是自私的,在沒有任何道德動機導引的情況下它們卻建構出了一個繁榮的整體。曼德維爾由此得出一條結論:個體的私欲恰恰才是社會繁榮的源泉。兩代人之后,斯密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把蜜蜂的工程視為所謂看不見的手的效果,在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下,無數單個的自利之聚合可以走向一種整體益處的產生與優化。
曼德維爾的蜜蜂工程到了斯密這里轉變成了市場經濟。在斯密看來,作為人類社會最古老的發明之一,市場經濟是一種以行為主體的自利為動力,以行為主體的勞動分工為前提,以建立在供求關系基礎上的價格確定為手段,以自由競爭為持續激勵,通過自主交換來滿足所有當事人之需求,從而實現整個社會普遍富裕的自發的、匿名的調節機制;它體現了一種通過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的分工、供求、價格與競爭機制)而使所有的人的自利活動相互激發與相互作用,最后導向全社會的普遍受益的精巧模式。
市場機制第一個因素就是行為主體逐利的動機。大家都知道斯密有句名言:我們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自利是所有參與市場經濟者的唯一動力,當然這同時也取決于市場經濟系統內在的邏輯要求:如果企業家無法獲得應有的利潤,則他自然就會被淘汰出局。
市場機制的第二個因素就是勞動分工。因為勞動分工才會引發市場交換,故勞動分工是市場經濟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必然現象,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是經濟繁榮的重要源泉,它極大增強了勞動者的技能、經驗與知識,明顯地激發了社會生產的能力以及勞動者創造性的活力。“在亞當·斯密看來,勞動分工是所有進步的源泉以及一個民族繁榮之最強大的杠桿。其好處只有在一種交換經濟中才能顯現。交換過程之決定性的因素是市場。”①
市場機制的第三個因素是基于供求關系上的價格生成與確定。勞動分工必然導致商品交換,面包師生產面包不只是為了家人食用,釀酒師做那么多的酒的目的也在于出售。當市場上的供求雙方對商品的價格達成一致時,則商品被出售,買賣獲得成功,雙方各自的需求得以滿足。對于商品的價格而言,出售者期待越昂貴越好,購買者則希望越便宜越佳。而商品價格的最終確定,并不取決于買賣的任何一方,而是取決于市場中商品的供求關系。如果某商品供者多而求者少,則價格下降;反之,如果商品的供者少而求者多,則價格上升。市場價格反映了商品的存量之多少。同時,價格也成為供求雙方下一步行為的指示器:對于供方而言,如果某商品出現了高價,則投資就會被吸引過來,供者就會數量大增,而東西多了,則價格自然就會下降;對于求方而言,如果出現高價,則就會降低購買的意愿,商品越來越多卻賣不出去,價格自然也會降低。在這種供求雙方的作用下,商品短缺的狀況很快就可以得到克服,商品的價格也就難以保持高位。在商品價格的調節下,生產會朝著正確的方向得以組織與運作,而最好的產品與最低的售價的出現也會大大有益于普通消費者。在供求關系的平衡中形成的物品的價格,直接反映了產品生產者勞動的價值,使得在時空中各自完全分離的勞動者們單個的決斷,有了一個共同的導向,讓形形色色的、其觀念與立場截然各異的人群,獲得了一種一致的追求。
市場機制的第四個因素是生產者之間的良性競爭。只要生產不是由獨大的一家來壟斷,則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就不可避免。任何一位生產者都希望自己的產品受到市場的接納,贏得消費者的歡迎,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只有讓產品的質量提高、品種多樣且價格下降。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其他生產者。一個成功出售其產品者的成就,或許很快就會被做出更大努力的競爭者所取代,市場上舊有的商品也有可能迅速被質量更高、價格更優惠的新產品所排斥。市場經濟就是這樣在競爭的作用下通過創造性摧毀的過程,而產生了有益于整個社會大眾的結果。
總而言之,市場經濟是一種以人的自利心為基礎、以自由為價值導向的極有效率的經濟模式,它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讓所有的市場參與者在交換活動自我獲利的同時,不自覺但卻又是有效地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公益。市場經濟的最大貢獻,在于它創造了以往任何一種其他組織形式都難以實現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都不曾想象的巨大的社會繁榮。它第一次使整個社會進入了一種生存的必需品在正常條件下不再匱乏的幸福時期,使所有的人理論上都有機會享受物質產品的豐富、基本需求的滿足、健康狀況的改善、人均壽命的提高、閑暇時間的增長和公共服務的實現。眾所周知,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歐洲曾經有一個幾千年以來在技術、科學和經濟上都不如大部分亞洲國家的歷史,五百多年以前,也就是在文藝復興時期,西歐與中國、印度、伊斯蘭地域也還是處于大致相同的發展水平上。重大的突破開始于市場經濟成為主導的經濟形式。恰恰是市場經濟的系統運用才使得西歐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站到了世界的前沿。市場經濟呈現出一種在自由與和平的前提下,通過合作與競爭來滿足所有當事方之需求的行為模式,它不僅貫穿與支配了經濟領域,而且也對社會其他領域,包括政治與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企業家要拉住顧客,政治家也應贏得選民,作家也需吸引讀者。竭盡全力滿足民眾的需求,成為一種時代的主張。誠然,嚴酷的競爭會導致差異與分化,市場經濟難以避免民眾的貧富不均,然而這一經濟形態所引發的財富的極大增長,會通過向社會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普遍的公共服務而使得窮人及其他弱勢群體也能享受到經濟繁榮所帶來的“外溢效應”。
如上所述,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文明創造的一種調節生產與消費的有效機制,它能使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由自利驅動的主體的行為,全然導向一個統一的著力點,從而讓社會整體最終因此而受益。從市場經濟能夠帶來極大滿足民眾需求之結果的意義上講,它與道德是有關聯的,而且還應當說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說市場經濟可以解讀為是有道德上積極成效的。當然,作為一種人造的機制,市場經濟并不是有生命的行為主體,因而其本身并沒有道德之舉動的能力。道德行為源自行為主體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礎上的能動選擇。而市場經濟是一種人造的作用模式,它并沒有自主選擇的能力,而是依照既定的邏輯必然性運行,故市場經濟本身不存在道德與否的問題。我們說,市場經濟與道德有關聯,有道德上積極的意義,這里包含有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市場經濟能夠導致有道德意義的結果;二是市場經濟的運行邏輯中能夠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倫理原則。
第一,市場經濟能夠導致有道德意義的結果。市場經濟占支配地位的時代有別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時代。而中世紀以前的人類社會基本上為自然經濟所統治。在自然經濟時代里,物質財富的相對匱乏是一種基本特征,整個社會的財富占有處于一種限量的狀態,財富的相對增加是以對他人的剝削與掠奪為代價的,而不是來自對資源的有效利用。因而零和博弈成為社會經濟的首要原則,即一方之得需以另一方之失為代價,于是得方之收益與失方之損失相加的總和一直保持為零而不變。由于財富的增加意味著從一只口袋掏出好處送進另一只,一方的益處必然導致另一方的損失,故整個社會對贏利之沖動均持鄙視的態度,經濟繁榮在前現代化的環境里沒有值得稱道的價值。傳統的倫理道德適用于小眾的透明群體,它強調中道、適度、公正、近愛、順應自然、禁止利息增殖。在傳統社會里,經濟服務于家政需求,在政治共同體中得到整合并從屬于一種等級性的世界秩序及其倫理與政治法則。在柏拉圖看來,對需求的滿足應達致適度,逐利是一種不自然的沖動,財富會通過享樂的欲望而窒息人的心靈。
可見,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不論是黃金規則、基督教的愛的律令,甚至也包括近代康德的絕對命令,都對逐利沖動持消極乃至敵視的態度。它們推崇與講究的是適度、公正、近愛和團結的美德以及更高的精神教養,而認定市場經濟是一種以自利為基礎,以盈利為導向,奉行競爭原則,追求無度的物質主義的行為模式。按照傳統的道德觀,人類的道德感是通過培育和訓練提升起來的,就像肌肉越練越強那樣。但是現代有許多人對這種道德資源可以通過運用而越用越多的觀點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這不妨分別從行為主體與行為對象兩個方面來看。從行為主體的角度看,道德只會是在運用中趨向短缺。例如,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Kenneth J. Arrow)看來,倫理行為是一種有價值的事務,但儲存有限,越用越少。像利他主義、慷慨大度、團結或國民義務,都是稀缺資源,持續使用早晚會有枯竭之日。因而道德能量應運用于最有需要的地方,如家庭、朋友以及市場手段所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②從行為對象的角度看,所謂感恩的邊際效應也會令行為主體心寒,以至其道德儲存逐漸透支。感恩的邊際效應是指:受助者在第一次獲助時會心存感激,但N多次獲助后就有可能覺得理所當然。連貫的援助能夠使受益人的感激遞減且要求提高。假若幫助停止,則感恩就有可能轉變成憤怒與仇視。本來的熱心幫助換回的很可能是冷酷的傷害。這樣,馳援者的道德激情就難以為繼。中國古代有關“升米養恩人,斗米養懶人,石米養仇人”的說法,也證明了這一點。
如上所述,在道德感是儲備有限,還是越用越多的問題上,兩種立場涇渭分明、相互對立。對于這種分歧,斯密有其獨特的看法。首先,與霍布斯倡導的消極悲觀的人的圖景不同,作為經濟學與道德哲學教授的他秉持一種積極現實的人的圖景。一方面人是自愛自利的。但另一方面人也是充滿同情心與責任感的。而同情則構成了人間道德的基礎。其次,斯密認為,在一種貧困的前提下,道德感的提升是非常困難的。道德者要想實現其理想,決不能依靠利他主義的激情,而是要靠貧困狀態的改變與消除。斯密的思路如下:倫理問題如果沒有經濟問題的解決作為前提,自己也就根本解決不了。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倫理學的基礎在于經濟學。而經濟學的原理則又根植于人的自利的本性與動機。換言之,只有基于人的自利的沖動,經濟學才能夠說明財富如何產生的疑問,只有財富充分涌現與豐富,社會的道德問題才有望從根本上得以解決。
于是,斯密道德學說的首要任務就在于為自利正名。他認為,應將自愛、自利與無度的自私嚴格區分開來,后者是以他人利益的犧牲與社會公益的損害為代價的。就自利而言,“實際上這里涉及到完全其他之事務,即關涉到人對其自身以及對其親屬的關注。人首先需顧及自身,這并不是自私自利。市場經濟在現實中所應用的推動力,是理所當然的、合乎理性的、合乎義務的每個人對其自身和對其親屬的顧及”③。人毫無疑問是道德主體,有擁有尊嚴和自由的欲求。但同時人也服從于生物學、社會學及其他自然與社會條件的制約,這些既定條件對當事人的行為起著形塑的作用,其中自利便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斯密看來,自利是人的一種與生俱來、值得肯定的本性。人生而以自利為行為動機,這構成了一種無可改變的事實。只是在外來強制下它才會短期受抑。但一個共同體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動力,恰在于個體之人對生存安全、物質富裕、精神認可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利才是所有的人獲得發展與強盛的主要原因。借此斯密便提升和鞏固了自利的價值地位,而與當時如日中天的以共同利益為行為導向并強調仁慈與近愛的基督教道德學說形成了對立。
在此基礎上,斯密對逐利體現了市場經濟體系內在的邏輯要求這一現象予以了闡釋。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逐利是行為主體最根本的驅動力,它反映出了行為者的內生需求與存在理由,甚至可以說折射了其道德義務。對市場經濟的許多道德批評強調說企業家的逐利應合理適度,而不能陷入對利潤的無窮競爭之中。這種批評完全偏離了市場經濟的固有鐵定法則。企業家永遠無法知道自己的對手在做什么,因此他只能追求利益的極值,否則就有可能在殘酷的爭奪中被淘汰出局。
因而,逐利成為企業家參與市場活動唯一的使命。企業家的道德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并不在于基于善良意志而捐款賑災、支持科研、獎掖教育、扶貧濟困等這些所謂社會責任的履行,在企業家的德性清單中,創造就業、提高雇員福利亦不算是首要任務。企業家的倫理道德或社會責任最重要的體現,就在于基于盈利的期待與激勵為全社會的消費者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與服務,通過滿足其需求的方式增進其福利,這也就構成了鑒別企業行為之道德質量的唯一標準。正如德國經濟倫理學家霍曼(Karl Homann)所言:“不道德與道德行為的界線在于,一面是犧牲他人的逐利,另一面是給他人帶來益處的逐利。在市場經濟中這些對于他人的利益并不表現為‘施舍性給予,而是以良好的、廉價的、創新的產品的形式以及通過規范的市場過程提供的服務。”④
值得指出的是,企業家的道德性并不在于其行為的善良動機,因為他的動機就是為了盈利;企業家的道德性在于其行為的結果,那就是理論上說整個社會所有的人恰恰是因企業家的盈利而普遍受益。斯密發現市場經濟是一種智慧的機制,獲利沖動、勞動分工、自由競爭等核心要素得以組合與調節,其結果是這種經濟模式既滿足了行為主體逐利的需求,也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財富的豐沛與富余足以使社會最底層的群體也能相應受惠,故市場經濟成就的物質繁榮可以支撐起整個社會的共同富裕。
斯密的發現特別向我們揭示了現代社會完全不同于小眾透明的自然經濟的社會,在后一種社會里,如要達到人際關系和睦協調的目的,需要強調的的確是家庭的孝道與朋友的友情。而在一種匿名的、陌生人的大社會里,個體普遍的流動性、深化的勞動分工、漫長的生產銷售鏈條,都使得對當事人行為的直接控制與迅速制裁難以實現。新的經濟形態所滲透的是新的運行法則,以前從一只口袋里掏出益品裝進另一只口袋的零和博弈,需為行為主體相互合作從而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收益的正和博弈所取代。而這里起決定性作用的就在于為傳統道德所不齒的自利原則。而斯密的功績恰恰就體現在:他揭示了在現代社會里,道德并不呈現為單向的利他主義與無私精神,而是表現在通過滿足所有的人之需求的供求關系而呈現出來的一種相互性的機制。并非仁慈愛心推動著我們為他人提供產品與服務,而是我們自己對利益的追逐導致了他人從中受益。故自利作為一種生產力可以服務于他人與社會,市場經濟的逐利機制可以借助于眾多個體利益的獨特組合而令所有的人的最大互助與團結得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謀求長遠的利益甚至被視為企業的一種道德義務,因為這種逐利活動可以最持久地普惠于全社會的消費者,從而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均從中得到好處。令人竊喜的是,企業家履行這種道德義務,無須當事人的道德自覺。一旦市場機制運行,只要企業家參與市場活動,他自然就會做出這種道德之事。企業家一進入市場,就會遭遇經濟競爭的挑戰,而殘酷的競爭不會保護和憐憫任何一個人。如果他人創造了更加物美價廉的產品與服務,則自己的產品就會滯銷,資本就會貶值,優勢就會喪失。但恰恰正是這種強大壓力導致了產品價格的穩步下降,質量的逐漸提高,革新的持續加速,整個社會富裕水平的普遍上升。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家自動便是一個有道德的人。賺了錢的企業家當然有義務幫助弱者,但馳援之道并不在于捐款輸血,而是通過投資讓弱者也參與創業活動,依靠市場機制解決貧困問題。對于企業而言,投資不是做出犧牲,而是著眼于對回報的期待。依照相互性原則,窮人命運的改善取決于富人是否從中也能得益。
總之,市場經濟之道德并不在于參與人的素質之高尚與動機之善良,而在于市場經濟這一機制本身的功能與結果的合道德性。道德在這里并不表現為自我上的特征,而是通過一種結構性的作用得以顯現。然而,與行為主體純粹的善良動機相比,市場之善、商業之善、貿易之善是更為強勁的向善與至善的力量。市場經濟的道德性昭示了市場的驅動可以改進社會這一現實,它證明了在一種匿名的、巨大的陌生人世界里,行為主體的自利可以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的運作而成為社會繁榮的動力源泉,可以轉變成為“一種機制化的近愛”⑤。如果說所有的人的自我發展機會的自由以及所有的人的團結構成了一項重要的道德標準的話,那么在現代化世界的條件下,具備著逐利與競爭之本能的市場經濟便是達到這一目標最合宜、最有效的機制。“市場經濟的道德優勢就在于,它體現了迄今為止所知的實現所有的人的團結的最好的方式。”⑥
市場經濟的這樣一種表現特征——道德不在于行為主體的個人動機,而是在于其行為的最終結果——使我們對道德哲學中的后果主義,產生了更為深刻的體驗。后果主義不追求道德動機的純粹性與道德原則的絕對遵守,而是顧及道德規則的可貫徹性、可執行性以及全部行為結果的最優和最佳,特別是強調所有相關者最大利益與需求均得以滿足。市場經濟恰恰能夠對道德后果主義做出完美的闡釋。“在市場經濟中,道德并不在于道德的或利他主義的動機,而是根植于市場經濟過程的結果里。所有的人的福祉并不取決于行為者的善意,而是取決于框架秩序,這一秩序借助于自利而使各方期待的結果產生出來。”⑦市場經濟之道德的這種不是以純粹的善良意志、暖人的利他主義為基點,而是以名聲在傳統思想中并不正面的自利為基礎的特征,并不意味著道德本身的衰敗,而是意味著在現代社會的條件下,自由與團結這樣的道德價值要想真正切實有效地得到落實,就必須通過一種全新的方式。因此,我們首先需要改變的不是企業家的道德素質,而是那種不適應現代世界要求的傳統的道德觀念。
第二,市場經濟的運行邏輯中能夠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倫理原則。如前所述,市場經濟是一種人造的機制,其本身無所謂道德與否。但其結果會帶來道德意義與價值。與此同時,在市場經濟運作的邏輯必然性的作用下,企業家的行為也能夠體現出某些道德原則。
一是自由原則。市場經濟在所有的當事人面前都呈現為一種自由的體系,甚至可以說是歷史上所出現過的最少強制的行為系統。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不再被束縛在一種毫無尊嚴的枷鎖里,也不再被控制在無所不在的監控之中,更無須被禁錮在某種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念之下,原則上講,所有的市場成員均享有一種至少是形式的自由,即自由地占有與支配其私有財產,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利益,自由地簽訂買賣合同并通過契約進行無統治、無支配的合作,自由地交換所需的物品與服務,自由地選擇消費品的種類及工作崗位。一句話,當事人可以依據自身的需求與偏好獨立自主地決斷所有的事務。由此可見,市場經濟不僅僅是人們相互聯系的一種紐帶和相互交往的一種機制,而且也體現了某種價值,即充分尊重人的自主性。“在尋找合宜的契約方以及依照自身想法交易契約形式的可能性中,一種在自由社會里得到確保的自由權利便獲得了表達。”⑧總之,市場經濟為人的空前的解放創造了前提,它激發了人的潛能與熱情,鼓舞了人獲得成功與績效的意志;同時,由于自由孕育著風險,市場經濟在使人享有決斷自主的時刻也訓導了當事人勇于迎應選擇所帶來的風險、肩負自由所蘊含的責任、承擔失敗所導致的代價。可以說,市場經濟為人的道德成熟得以培育和錘煉提供了重要場所與平臺。依賴于人的自由,市場經濟才能夠產生與運行,反過來,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使人的自由得以強化與提升。
二是平等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構成了一個核心的要素。而競爭則意味著平等。所有參與競爭者只要進場,就失去了任何特權,而享受著一種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反之,一旦特權與強權出現,則競爭也就立即停止。平等的競爭也意味著和平與無暴力。市場競爭體現著一種平和的、無統治、無支配、無暴力的文明交往狀態,競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阻止對方提供更加物美價廉的優質產品與服務。平等的競爭并不意味著傷害。所有競爭參與者都認可競爭這一程序,對獲勝的結果抱有高度的期待,對失敗的可能坦然予以接受,成功并不歸功于他人的仁慈與恩惠,慘敗則只能說明自己努力不夠或機遇不佳。市場就是通過獎掖與鼓勵優秀者,懲罰與淘汰劣質者而使全體民眾獲益,推動社會的持續進步。競爭失敗者并沒有經歷什么傷害,他應將痛苦的反思轉化成全面提升自己并力爭在下一次競爭中獲勝的巨大能量。
三是誠信原則。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契約行為依靠可貴的品性——信任與誠信作為價值支撐。誠實守信、言行可靠的企業家會為市場所獎賞,而欺騙、毀約的行為則必然導致當事人在市場上永無立足之地。
四是效率原則。市場經濟排斥強制也拒絕說教,它能夠通過自身的運行邏輯,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而促進公益的生成。例如環保困境的破解就是如此。所謂生態專制或喋喋不休的啟發教育,都無法證明自己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最佳途徑。最佳的途徑在于:全方位引入價格調節機制,將環境因素標上高昂的價格納入市場主體的考量之中,這樣才能使所有當事人的行為被引導到環保的方向,行為主體在為自身節省費用的同時,又為生態保護做出了貢獻。
二
如上所述,斯密所倡導的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創造發明的一種精巧的調節生產與消費的有效機制。作為一種人造之物,其本身無所謂道德與否。但從市場經濟能夠帶來極大滿足民眾需求之結果的角度來看,它與倫理道德是有關聯的。一方面,市場經濟能夠導致有道德意義的結果;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運行邏輯中能夠反映出一些諸如自由、平等、誠信等重要的倫理原則。單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以自利為驅動的市場與以團結為標識的道德之間就沒有什么矛盾和沖突,一只看不見的手就可以彌合自利與團結之間的裂隙;所謂斯密問題就的的確確是一個偽問題。盡管市場經濟能夠釋放人們自由的潛能并促進社會公益的劇增,但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人對市場經濟這一行為機制深感不滿乃至嗤之以鼻呢?問題就在于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要想滿足人類社會復雜的需求僅僅靠市場經濟是遠遠不夠的。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內容值得考量。首先,許多社會事務并不能被置于市場經濟的調節領域,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機制作為替代,以彌補市場作用的不足。其次,市場經濟的正常健康運行,需要有其本身所無法建構出來的框架條件的保障,否則它就會產生出一系列自身所難以解決的問題從而走向自毀,故市場經濟需要靠國家動用外在力量對其偏失予以矯正。總之,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的經濟,擁有著自由的價值內蘊,但市場經濟的自由不是萬能的且還包含有自毀的趨勢,故需要有人為的外在干預與糾偏,一句話,市場自由亟須倫理的限制。
我們先看第一點,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許多社會事務應靠其他機制的導引調節,從而彌補市場經濟的局限性。
大家知道,市場經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人類生產與交換活動的組織工具,同時它也體現為一種行為規則,能夠使人類社會所有的活動都整合進市場的價值體系的運作邏輯之中,甚至把所有的社會關系都轉變成為市場關系。當經濟學成為主導學科,市場規則侵入所有的社會領域,包括以前完全不屬于市場交換范疇的領域如政治、法律、醫療、教育、藝術、體育、家庭、朋友及公民義務,當所有的事務都可以轉變成為能夠標價買賣的商品,一句話,當市場價值牢牢掌控了我們的一切,則人類就進入了一種哈貝馬斯所言的由經濟學導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狀態,而當一個市場經濟轉變為市場社會的時候,我們便處于一種前所未有的價值危機之中。
我們的生活世界被經濟力量殖民化的惡果就在于,人類許多重要的事務會遭到價值上的貶損。眾所周知,市場的要旨在于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但是需求本身有著道德價值上的差異,例如觀賞歌劇的需求與看斗牛的需求之間在價值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而市場不會給由其所滿足的需求下判斷。當一種無法辨明道德是非的市場經濟將所有的事物都視為商品,當所有的事物都用同一的經濟標準被度量的時候,則那些本身具有完全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目的與意義的事物,其珍貴的道德價值便會在市場經濟的估價與交易中遭到嚴重的貶損。“如果在人類交往中所有的事物都只有作為給予和回報的交換來理解的話,則我們生活中某種重要的東西實際上就喪失了。”⑨世界上有許多存在,它們具有某種神圣性故特別值得我們珍視,它們無法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不可能用金錢來衡量,不是等價交換的對象。如果我們讓它們進入市場,就會扭曲其性質而貶低其應有的價值。
人的權利與尊嚴不是商品,而是每一個人的專屬事物,具有絕對的內在價值,不可能被標定價格進入市場并聽任盈利原則的左右。因而將人降低為物品、使人成為獲利之工具的人口買賣必須絕對禁止,這種市場交易行為沒有將人視為擁有尊嚴的主體,大大損害了其價值。人的義務不是商品。履行陪審員之職責,構成了每位滿足陪審員條件的公民的基本義務。它的選擇方式是抽簽,被抽到者就應該積極認真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而不可以雇用頂替者。“為何不允許呢?因為我們相信,公民義務不應被視為私產,而是針對公眾的責任。”⑩
總之,人間的事務千變萬化,人際關系復雜多樣,不同的情況需要有各異的規則來調節應對,市場經濟、金錢買賣不可解決所有的事情。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調控手段,其地位不能無限拔高。“經濟只有一種服務性的功能,它必須為個體與社會更重要的價值提供可支撐的基礎。”B11例如道德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更重要的內在價值的事物,其地位無法由經濟考量所取代。“在我們的道德權衡中,我們并非用不同的偏好來權衡其他,而是確立不可交易的事物。有我們可以貼標簽的東西,也有我們無法貼的東西。且道德首先是與后者相關,與我們不拋向市場的東西相關,比如人,或性、共同體,公正以及榮譽。”B12一句話,經濟本身只是人們達到某項目的的手段,而這個目的就是作為人類倫理最高價值的自由之需要,是個體之人對其身心的全面掌控與全面發展。“比經濟更重要的事物有無限的多:家庭、社會、國家、所有的社會整合形式,直到人性,再有即是宗教、倫理、審美,簡言之,人道與文化。所有這些巨大領域……比經濟更為重要。”B13
我們再看第二點,市場經濟的正常健康運行,需要有國家建構的框架條件的保駕護航,否則它就難以避免從自由到自毀的命運,換言之,市場自由亟須倫理道德之約束與矯正。
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的經濟,它充分調動每一位參與者自身的潛能與積極性投入創造巨大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的事業之中,從而導致了整個社會各個階層因此均受益這樣一種道德的結果。但是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需要有它自身所無法建構的外在條件作為前提,如果沒有這種前提,市場經濟內生的自由競爭力量就會自發地造成壟斷和貧富極度分化的現象,這一現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自由競爭不再繼續進行以及市場機制走向徹底的失靈。所謂外在條件,是指國家制定的由相應的法律法規構成的市場經濟運行的框架結構,這一框架條件對市場自由予以一定的合理限制,消除市場經濟從自由走向自毀的潛在隱患,通過對市場機制健康運行的保障而服務于整體和長遠的自由,促進全社會普遍和共同的福祉。總之,市場經濟的框架條件是這一自由經濟得以存活并保持永久活力的前提與基礎。
我們前面說過,市場經濟與道德有關系,具備道德上的積極意義,是從兩個層面上說的。一是市場經濟能夠導致有道德意義的結果;二是市場經濟的運行邏輯中能夠反映出一些諸如自由、平等、誠信等重要的倫理原則。現在我們談到市場經濟有賴于其自身無法產生的框架條件,而這一框架條件的出現恰恰又為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聯提供了第三個層面的內容,即市場經濟的框架條件本身擁有著豐富的道德意蘊。框架條件為每一位市場競爭參與者劃定了同一條起跑線,整個市場經濟的參與者行為的道德水平,并不取決于當事人自覺的德性與善良的動機,而是取決于這一框架條件的道德含量。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行動者的逐利沖動具有市場邏輯上的必然性,盈利可以說是企業的唯一動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個體的德性就完全不重要,畢竟良好的道德形象可以作為一種資本來增強行為主體受信任的程度。但在競爭的條件下,個體道德不能持續地遭受到經濟利益上的損失。在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道德需被嵌定在一種普遍有約束力的、對所有競爭參與者均起作用的規制之中,這一充滿道德要求的框架條件不僅不會壓抑個體的自利沖動,而且甚至還會強化企業家的逐利行為,借此而讓所有人從中受益,讓廣大民眾的團結精神得以實現,同時還能杜絕不道德者漁利。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倫理道德主要并不體現在個體的行為性質,而是內蘊于市場經濟的框架條件之中,行為主體在良好的框架規制的保護下,其道德行為能夠在競爭中獲得巨大的益處,而這最終又造成整個社會各個階層均受益的結果。故“現代社會與意圖脫節而與機制相連”B14。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所倡導的道德不是個體意圖性的道德,而是一種機制化的道德。這樣,我們就需要破除一種傳統觀念,即認為市場與競爭是不道德的,必然會導致社會的不端與民眾的困苦。恰恰相反,應當保護市場與競爭,鼓勵逐利之沖動,借由框架條件的設置使市場經濟得以改善并獲得更大的解放。“用發展與建構一種框架條件來改善和解放市場,這一框架條件如此地引導逐利沖動的活力,以至于所有的人都能夠融入這一生產性的過程之中。只有這樣,一個自由、和平、公正以及所有的人的團結的世界,才能產生于一種高度的繁榮水平之上。”B15
這一滲透著道德意涵的市場經濟的外在框架條件首先需要扼制的,是能夠導致最終壟斷的絕對的自由競爭。正如赫費(Otfried Hoeffe)所言:“‘市場自由不是一種絕對的,而是一種比較性的概念。絕對的自由市場既不是人們期望的,也從沒有存在過。”B16要看一個市場是否自由,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私有財產權的存在;二是充分和自由的競爭,不得有壟斷。而絕對的自由競爭的結果,則必然是幾個強者為了牟求高額利潤而結盟為卡塔爾、托拉斯,他們利用市場自由而獲得巨大的權力,最終形成對本行業的壟斷狀態。壟斷的后果是嚴重的:更高的產品價格、更差的市場服務、技術進步的停滯、新企業難以進入市場和競爭的徹底消失。為了避免市場的這種自毀力量的惡果,國家所制定的框架條件中就應有反壟斷的法律制度,如此市場參與者的自由競爭才能得到保障與持續。
市場經濟的外在框架條件其次需要扼制的,是能夠威脅社會安全的貧富兩極分化。市場經濟從表面上講是一種自由的經濟,理論上說所有的人都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參與競爭。但是實際上人與人之間在資金、能力、經驗上差別巨大,于是自由競爭的結果便是兩極分化,一部分勝者強者掌握了海量的社會財富,另一部分敗者弱者則陷入貧窮、病患、失業等困境。對于這些在貧困的極端情況下甚至連生存都無法保障者而言,自由只是一種形式的自由,他們雖有選擇的權利,但根本就沒有選擇的能力,他們缺乏實質的自由,即真正可以落實的選擇自由。而自由競爭導致一部分失敗者陷入極端貧困等社會問題,卻又是市場自由原則本身所無法解決的。
慘痛的歷史教訓表明,毫無限制的市場競爭有可能最終導致人間悲劇與驚天大難。因而國家就有責任運用框架條件的設置對市場的自由競爭予以調節。具體而言,就是建構各種稅收機制,為全體社會成員包括所有的弱勢群體,編織起一道法定的涵蓋醫療、事故、養老、失業等內容的社會保險及社會救濟體系,從而不僅使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民眾擁有其生存所必需的、符合人的尊嚴的物質生活保障,以便抗拒各種風險,而且還要為其就業與創業提供必要的支撐,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的活力資源。國家所建構的社會保險體系以及所制定的固定價格、最高價格、最低價格、最低工資等,目標就在于不僅讓弱勢群體擁有形式的自由,而且也應為其獲得實質自由做出貢獻。國家的這種通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而對自由市場的干預行為,從表面上看是對市場參與者短期行為的限制,但從實際結果來看他們的長期自由卻因此而得到了保障。而國家在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時,并不是依靠富人、強者、勝者的善良意志,而是有賴于一種社會調節機制:你賺錢越多,說明你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你只有給他人帶來好處,才可以使自己受益。所有的自由競爭參與者自利的欲求并沒有受到壓制,而是朝著有利于社會弱勢群體的方向牽引。
至于為什么國家有義務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讓窮人也能享有經濟繁榮帶來的成果,使其最起碼的物質生活條件得以保障,許多的論證都可以為此提供支撐。毫無疑問,最強大的是來自人權原則的理據:從社會弱勢群體的視角來看,他們不僅享有消極性的自由權利,而且也要求國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使自己積極性的經濟社會權利也獲得實現,否則,消極性的自由權就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屬于人權的有諸如財產權、個體自由發展權。這就包括對經濟生活的自由參與,消費者的職業自由、企業家的自由。不滿足于消極性的自由權利,人權理念也要求對市場進行附加的限制,從而使市場的自由前景不至于轉向非自由。”B17與此相關聯的是,國家對市場經濟所設置的框架條件中,基本上是由相應的法律法規所構成的,而法律系統在現代環境下,就一定要滲透著人權與公正的精神。
而經濟社會權利與“社會安全”的概念是密切相關的。眾所周知,在關于國家功能的理解的問題上,人類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存在的目的在于推進善的實現。何謂善?善即是指服務于人的福祉與幸福的事物。而所謂福祉主要不是指物質意義上的,而是精神、文化、品格上的。但是到了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們那里,國家的作用被理解為是為民眾的人身安全和公民的自由權利提供保障。這特別表現在,當民眾之間出現宗教分歧與政治利益的紛爭之時,只有國家才能作為立場中立的主管予以調停裁判,在不偏袒其中某一方的前提下,阻止公民陷入相互殘殺爭斗的血腥災難。國家就是這樣建構在統治者與民眾為維護個體人身安全所訂立的契約的基礎之上的。這是16—17世紀近代國家建立初期的基本圖景。到了19世紀,隨著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傳統職業衰敗、農業人口流失,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兩極分化和城市貧民的出現。整個社會逐漸劃分成為經濟強勢的資產階級與貧困潦倒的勞工大眾,由經濟的不平等和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所引發的階級對立與矛盾日趨尖銳。當貧富差距過于懸殊時,城市貧民盡管其人身安全不受太大的影響,但其物質安全問題卻極為嚴重,持續常態的貧困甚至可以導致生命危險。當勞苦大眾沒有絲毫希望,只有反抗才能拼出一條活路時,就會掀起大規模的社會政治運動,他們試圖通過革命來改變這種不公正的狀態,其結果便是整個社會急劇動蕩,原有的自由競爭的經濟秩序也就無法維持下去了。可見,經濟上的自由競爭的發展,會引發由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階級矛盾,這就又回到了一部分人加害于另一部分人的狀態了。如果此時國家仍然保持中立,以暴力方式對既有秩序予以維護,聽任兩極分化的繼續以及強者對弱者的壓迫,其結果實際上便是偏袒資產階級的一方,就像16—17世紀宗教戰爭時期國家偏袒一方那樣。過去是宗教戰爭,一種教派侵害另一教派從而損害后者的人身安全,因而國家必須出手干預,從而維護民眾的生命安全。今天則是經濟戰爭與階級斗爭,強勢的有產階級利用經濟優勢侵害無產者,最終導致后者的生命安全無法保障,因而國家必須干預,從而維護民眾的基本生存、經濟穩定和社會秩序。這就是國家意識到社會經濟發展到了這一階段,已出現一種與傳統的針對個體的“人身安全”概念完全不同的新的“社會安全”的概念的緣由。所謂社會安全,是指對民眾應創造生存、就業的條件,建構健康、事故、失業、養老方面的保險,從而弱化市場經濟自由發展帶來的最壞后果,為公民的實質自由的實現提供基本的前提。社會安全不同于傳統的人身安全,人身安全僅僅意味著公民享受針對國家對私人個體與社會生活的無端侵害的那樣一種防御權,這是一種消極性的權利,且人身安全很難獲得絕對的保障,除非每位公民都能盡享時時刻刻被一群保鏢嚴密看守的待遇。而社會安全則意味著國家的積極干預,國家須提供實實在在的物質條件,保證民眾擁有最低限度的私有財產,防止最弱勢者受到饑荒與貧困之苦,維護其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持續。如果說在近代國家出現的初期,國家是建構在統治者與民眾為維護個體人身安全所訂立的契約的基礎之上的話,那么到了19世紀,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契約,即此時國家亦是建構在統治者與民眾為維護個體的社會安全所訂立的契約的基礎之上的。新契約的核心內容就是社會安全。于是國家便有了維護個體人身安全和保障社會經濟安全的雙重任務。
三
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的經濟,它是自由主義精神在經濟領域中的一種具體化、現實化。古典自由主義是人類進化的文明成果,它掙脫了傳統的集體性約束,否定了將所有的人置于一種整體性、預制性的生存目標的觀念,把對公民“生命、自由、安全、幸福”的承諾作為一切社會建制的出發點。支配人的行為的不再是傳統束縛與宗教權威,而是出于自主性的自我約定的人際規則,借助于這些規則,人們追求個體最大利益的滿足。人不再是為了國家而存在,相反地,國家是為了普遍公民的自由與安全的保障才能贏得自身存在的理由。故國家對個體的限制必須是基于國家建構的目的,而國家本身的行為空間則受制于合法的約束。由此,古典自由主義生發出了一種嶄新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模式,它不僅實現了行業解放、農民解放、商業解放,為現代工業的興起創造了前提,而且也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質繁榮與技術進步,大眾生產與大眾消費的模式使處于各個階層的人群都獲得了生活改善的機遇。根植于自由精神的市場經濟也導致了社會價值觀念的巨大轉變,所有的人都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而不會被限定在某種好生活的恒定的標準之下,這就包括對私有制的肯定,對逐利的理解,對契約的贊頌,對風險的承擔,對失敗的容忍,對競爭的認同。
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本身能夠產生合道德性的結果。當然市場自由的施展以及市場經濟的持續生存,需要有市場自身所無法創造的框架性條件的約束與保護,這一框架性條件充滿著倫理道德的意蘊。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本身本來就是擁有道德關聯性的,只是僅靠市場經濟的道德性結果還是不夠的,且沒有約束與限制的市場經濟還會導致其自身的毀滅,所以才需要有外來的干預,而這又是一種道德性的干預。這種道德性干預的目的僅僅在于對市場經濟的支撐、支持、支援、提高與改善。
注釋
①Harald Randak. Unser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Muenchen, 2009, S.21.
②Vgl. Michael J. Sandel. Was man fuer Geld nicht kaufen kann. Berlin, 2014, S.157.
③Vgl. Bernd Noll. Grundriss der Wirtschaftsethik, Stuttgart, 2010, S.252-253.
④Karl Homann. Ethik in der Marktwirtschaft, Muenchen, 2007, S.14.
⑤Zitiertbei Karl Homann, vgl. Matthias Wuehle: Die Moral der Maerkte, Wiesbaden, 2017, S.113.
⑥Vgl. Karl Homann/ Franz Blome-Dress. Wirtschafts-und Unternehmensethik, Goettingen, 1992, S.49.
⑦Karl Homann. Ethik in der Marktwirtschaft, Muenchen, 2007, S.17.
⑧Bernd Noll. Grundriss der Wirtschaftsethik, Stuttgart, 2010, S.200.
⑨Dominic Roser/ Christian Seidel. Ethik des Klimawandels, 2.Auflage, Darmstadt, 2015, S.157.
⑩Michael J. Sandel. Was man fuer Geld nicht kaufen kann. Berlin, 2014, S.17.
B11Bernd Noll. Grundriss der Wirtschaftsethik, Stuttgart, 2010, S.254.
B12Roger Scruton. Gruene Philosophie, Muenchen, 2013, S.208.
B13Vgl. Bernd Noll. Grundriss der Wirtschaftsethik, Stuttgart, 2010, S.254.
B14Zitiertbei Andreas Suchanek, vgl. Karl Homann. Ethik in der Marktwirtschaft, Muenchen, 2007, S.18.
B15Karl Homann. Ethik in der Marktwirtschaft, Muenchen, 2007, S.27.
B16Otfried Hffe. Kritik der Freiheit, Muenchen, 2015, S.136.
B17Otfried Hffe. Kritik der Freiheit, Muenchen, 2015, S.144.
責任編輯:思 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