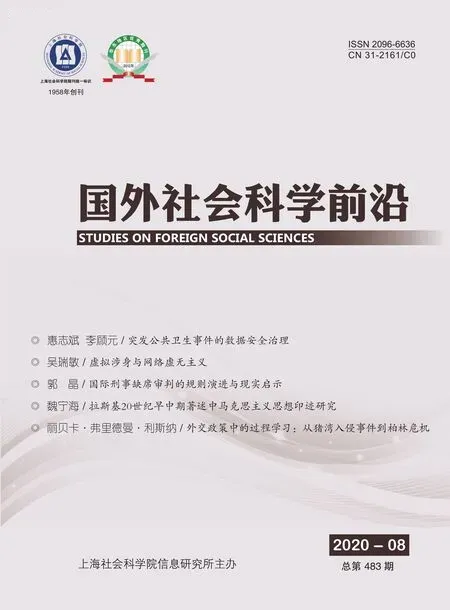國際刑事缺席審判的規則演進與現實啟示 *
郭 晶
內容提要 | 我國的刑事缺席審判程序自增設以來,還未有相關的司法判決。國際刑事司法中豐富的缺席審判實踐,可以為我國適用缺席審判程序提供參考。從紐倫堡軍事法庭到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法庭、盧旺達問題法庭、國際刑事法院,再到近期的黎巴嫩混合法庭,國際刑事審判機構對缺席審判的態度經歷了從寬容到限縮再到適度放寬的曲折過程。流變中的取舍之爭,對我們理解缺席審判正當性、平衡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國可以辯證地借鑒國際刑事缺席審判經驗,從案件選擇標準、送達規則和重審權限制等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缺席審判程序。
為加強境外追逃工作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增設了刑事缺席審判程序。由于缺乏相關的實踐經驗,2018年修法至今仍未有一例缺席審判的案例。如何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前提下,順利啟動缺席審判程序,回應反腐敗追逃的現實需求,成為司法實踐中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91 條,我國缺席審判程序允許對從未到案的重罪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該立法例與很多法治發達國家的做法存在不同,有侵犯被告人知情權和在場權的風險,因此有必要在司法實踐中輔以限制條件進行制約,以符合公平審判的要求。縱觀世界,國際刑事審判中的缺席審判與我國的立法動因相似、司法困境相同,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申言之,被指控人逮捕難、到案難也是國際刑事司法實踐中的“老大難”問題。在被告人蹤跡不明或者沒有主權國將被告人遞交到庭的情況下,是否允許缺席審判也是困擾國際刑事審判機構的兩難問題。一方面,啟動缺席審判程序有可能在被告人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訴訟,有違公平審判原則的底線要求;另一方面,不啟動缺席審判程序,則會導致“有罪不罰”,正義得不到彰顯。國際刑事審判機構在兩難之下如何基于司法利益的考量進行抉擇,如何平衡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值得我國借鑒。
一、首例探索:對戰爭罪犯進行缺席審判的重要突破
國際軍事法庭是國際社會首次對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等最嚴重的國際罪行進行審判的法庭,也是首次適用缺席審判的國際性刑事審判機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戰勝國設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追究戰爭罪犯的刑事責任,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創舉。
然而,由于一些重要的戰爭罪犯蹤跡不明、生死未知,使同盟國在是否對這些戰犯進行缺席審判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相較于審判,英國政府更傾向于直接處決納粹主要領導。蘇聯政府認為審判是毫無必要的,《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已經給這些戰爭罪犯定罪了。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對審判戰犯的想法不感興趣。①Jody M.Prescott, In Absentia War Crimes Trials: A Just Means to Enforc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ublisher: PN,1994, p.28.然而,羅斯福總統的離世,卻改變了這一走向。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強烈支持對戰爭罪犯進行審判。杜魯門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Jackson)擔任戰爭審判事務的首席顧問,開始起草關于建立戰爭法庭的備忘錄,以供美英法蘇談判。這份由美國戰爭部領銜起草的備忘錄,用模糊的表述肯定了缺席審判的可能性。有些奇怪的是,缺席審判并不是美國司法的慣常操作,為何會被美方寫入備忘錄并被舊金山會議采納?
有一種解釋是,談判的時間節點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約瑟夫 · 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自殺身亡,但該信息在短時間內無法得到證實。缺席審判能夠確保如果二人后續被捕,可以立行處決。舊金山會議后,美方又對草案進行了多次修改,并在1945年6月進行的倫敦會議上提出了修改版。在倫敦會議上,蘇聯方面建議將缺席審判的條文修改為“如果被告人藏匿或者法庭認為有必要在被告人缺席時進行審判,法庭應保有對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的權力”。英國方面則建議修改為“如果被告人蹤跡不明或者法庭基于任何理由,認為為了司法利益應當進行缺席審判,法庭應保有對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的權力”。最終,紐倫堡法庭基本采用了英國版本。《紐倫堡軍事法庭憲章》(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以下簡稱“《紐倫堡憲章》”)第12 條規定:“法庭有權對被指控犯有本憲章第六條規定的犯罪之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法庭如果無法找到被告人,或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情況下,法庭可基于任何理由決定對被告人缺席審判。”②Jody M.Prescott, In Absentia War Crimes Trials: A Just Means to Enforc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ublisher: PN,1994, p.29.
從《紐倫堡憲章》第12 條的規定來看,法庭可以在找不到被告人和基于司法利益需要的兩種情形下進行缺席審判。前者是指被告人自始至終缺席全部審判過程的情形,包括缺席審前階段。后者是指被告人擾亂法庭秩序,或者因身體原因等因素無法出庭時,法庭基于司法利益的考量,采取部分缺席審判。考察紐倫堡審判實踐,僅有一個案件適用了缺席審判,即對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的審判。③Elizabeth Herath, Trials in Absentia: Jurisprudence and Commentary on the Judgment in Chief Prosecutor v.Abul Kalam Azad in the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55, 2014, p.2.鮑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納粹黨總部主任、納粹德國的第二號戰犯。紐倫堡法庭對鮑曼涉嫌實施的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進行了缺席審判。審判中,法庭指定的辯護律師主張中止審判或推遲審判,其理由并不是缺席審判違反程序公正,而是鮑曼已在戰爭中死亡。然而,法庭根據審理中檢方出示的大量具有鮑曼親筆簽名的書證認定,即使被告出庭也無以辯駁,進而認定鮑曼有罪并判處絞刑。最終,由于鮑曼一直未歸案,判決沒有能夠實際執行。
作為國際刑事司法實踐中的首例缺席審判,鮑曼案非常值得研究。法庭在司法利益的考量上,更多地側重了實體利益,并巧妙地結合證據的因素進行說理。在實體利益方面,給鮑曼這樣的重要納粹戰犯定罪具有重大意義。這與《紐倫堡憲章》序言中明確的創設紐倫堡法庭的目的和意義相符,即“將戰爭罪犯繩之以法”。在程序利益方面,被告人鮑曼面臨可能判處死刑的刑罰,應當有出席自己庭審的權利。紐倫堡法庭之所以認定對鮑曼進行缺席審判利大于弊,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紐倫堡軍事法庭成立的法律基礎。紐倫堡軍事法庭是同盟國基于條約成立的,其代表的司法利益并非所有主權國,而是勝利國。作為基于條約成立的法庭,在進行司法利益考量時,一定意義上偏向于戰勝國是具有條約基礎的。《紐倫堡憲章》是《關于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Agreement for the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of the European Axis,以下簡稱“《倫敦協定》”)的附件。在對其規則進行理解時,應當考慮其所屬的主法律文件《倫敦協定》的相關內容。既然《倫敦協定》之標題已明確是為了控訴和懲處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那么《紐倫堡憲章》第12 條允許對找不到的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就不足為奇了。
第二,紐倫堡軍事法庭成立的時代背景。紐倫堡法庭是旨在審判二戰戰爭罪犯的專門刑事法庭。二戰剛剛結束時,各國人民對恢復國際秩序、審判戰爭罪犯,以及為戰爭中傷亡的被害人伸張正義充滿了急切渴望。在此背景之下,紐倫堡審判在面對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平衡問題時,更多地傾向前者,是回應各國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期待,也是改變戰爭罪犯有罪不罰情況的當然之選。
第三,紐倫堡刑事審判的時間節點。紐倫堡審判發生在1945年11月21日—1946年10月1日間,彼時國際人權法還未得到充分發展。《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到1948年才告問世,而明確規定被告人公平審判權利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更是在20年后才生效。因此,國際人權法的闕如也是缺席審判在紐倫堡法庭得以適用的原因之一。隨著國際人權規則漸成體系、日趨完善,紐倫堡審判受到的質疑也越來越多。允許缺席審判,尤其是允許對重罪進行缺席審判,允許對從未到案的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遭到很多批評。加之,沒有賦予被告人上訴的權利及獲得重新審判的權利,也嚴重影響了紐倫堡審判程序的公正性。①史立梅:《國際刑事司法中的程序與正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17 頁。
綜上,紐倫堡軍事法庭的審判開創了戰犯審判的先河,同時也創造了在國際刑事審判中適用缺席審判這種訴訟程序的先例,盡管其合法性和正當性后續受到了質疑,但其開創意義仍是毋庸置疑的。
二、選擇限縮:是否允許缺席審判的論爭及規則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總體上維持了和平的局勢,國際刑事審判也按下了暫停鍵。直到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出現武裝沖突和人道主義災難,國際刑事審判才重回歷史舞臺。然而,重啟之后的國際刑事審判在對待缺席審判的態度上,卻發生了180°的轉彎。
(一)前南和盧旺達問題刑事法庭的謹慎
受普通法系影響深重,前南斯拉夫問題特別刑事法庭(以下簡稱“前南刑庭”)和盧旺達問題特別刑事法庭(以下簡稱“盧旺達刑庭”)對缺席審判的適用非常嚴格。以前南刑庭為例,《前南國際法庭規約》(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第21條第4 款規定,在決定對被告人的任何指控之前,被告人均享有一系列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其中包括被告人于審判時在場的權利。該條款體現了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指導思想,奠定了前南刑庭不支持缺席審判的基本態度。
為切實保障被告人審判時的在場權,《前南刑庭程序和證據規則》(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第61 條僅允許在審前階段,也就是確認指控階段進行缺席審判。具體而言,預審分庭在被指控人缺席的情況下,根據檢察官提出的證據確認被指控人實施了起訴書所指控的犯罪行為,進而簽發國際逮捕令。除此之外,前南刑庭還允許擾亂法庭型的部分缺席審判。根據《前南刑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80 條B 項,法庭有權在被告人不聽警告持續擾亂審判的情況下,將被告人逐出法庭并且在其不在場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審判。
盡管規定較為嚴格,但在實踐中前南刑庭和盧旺達刑庭均存在被告人不在場情況下進行審判的案例。比如,前南斯拉夫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evi?)因身患疾病,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出席庭審,前南刑庭只得在米洛舍維奇缺席的情況下完成了后續的庭審。盧旺達刑庭也在檢察官訴讓·博斯科·巴拉亞格維扎(Jean Bosco Barayagwiza)一案中指出,被告人先前出席了庭審,之后拒絕出庭的,法庭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繼續審判。故此,前南刑庭和盧旺達刑庭通過審判實踐形成了允許被告人部分缺席的審判規則,即被告人在出席過庭審后,不能或不愿繼續出席庭審的,法庭可以進行缺席審判。
這種不成文的缺席規則被21世紀初成立的大部分混合法庭作為模板寫入法庭規約,成為一種明文的規則。具體而言,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塞拉利昂問題特別法庭和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都在法庭規約中明確允許部分缺席,前提是被告人曾經出席過庭審。①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ited Nations Interim Administration Mission in Kosovo)完全禁止缺席審判。至此,國際刑事審判機構基本形成了以英美法系“首次出庭規則”為藍本的缺席審判規則,然而該規則并沒有被國際刑事法院采納。
(二)國際刑事法院的“最嚴格規則”
作為常設性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對自身有很高的人權保障要求,故而在是否允許缺席審判的問題上幾乎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即缺席規則的“最嚴格模式”。國際刑事法院的締約磋商大會曾多次討論過是否允許缺席審判,在什么條件下允許缺席審判的問題。②1998年的羅馬外交大會共討論了缺席審判的4 種方案。參見Untied Nations Diplomatic Conference of Plenipotentiari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Conf.183/2/Add.1, 1998, pp.99-102.當時支持和反對缺席審判的各方均貢獻了很多重要的理由。比如支持方認為,缺席審判是一種政策性的制裁,可以防止罪犯從國際刑事法院的羈押下脫逃;缺席審判可以避免實施了種族屠殺、危害人類、侵略、戰爭罪行的個人有罪不罰;缺席審判盡管有一些消極的影響,但能夠切實給予國際刑事審判以力量,是追訴國際犯罪的重要抓手。而反對一方③包括澳大利亞、瑞士、新西蘭、美國和南斯拉夫。則提出,缺席審判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賦予個人的在場權,很多主權國的國內法均不允許缺席審判,如果允許國際刑事法院進行缺席審判,國際刑事法院可能會在后續的實踐中選擇“走捷徑”,不盡力抓捕犯罪嫌疑人。還有反對意見認為缺席判決后續的刑罰執行也會存在問題。
經過了多年的磋商,最終國際刑事法院采取了較前南刑庭、盧旺達刑庭更為嚴格的缺席審判規則。首先,《國際刑事法院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第63 條“被告人出席審判”第(1)款規定“審判時被告人應當在場”。此表述比前南刑庭規約所規定的被告人在審判時有權在場更具有強制性。④史立梅:《國際刑事司法中的程序與正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4 頁。《 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僅在兩種情況下允許法庭缺席審判,分別是第61 條第(2)款規定的確認指控階段的缺席審判,以及第63 條第(2)款規定的擾亂法庭型的缺席審判。⑤《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83 條第5 款規定:“上訴分庭可以在被判無罪的人或被定罪的人缺席的情況下宣告判決。”由于僅僅是宣告判決,法庭聽審階段已經結束,不視為一種缺席審判。
規約的出臺并沒有讓缺席審判的爭論歸于休止。相反,不允許缺席審判的國際刑事法院面臨著束手束腳、自廢武功的困境。很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無法到庭,訴訟不能開展或被迫延遲造成被告人訴權和被害人權利之間的不平衡。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的特派專員杜杜· 錫亞姆(Doudou Thiam)曾預見性地判斷,禁止缺席審判將使法院工作陷入癱瘓。盡管該論斷有些夸大,但也指出了國際刑事法院效率低下的癥結。
為解決部分被告人因擔任國家元首或政府中的重要職務無法出席庭審,導致庭審屢次延期,庭審效率低下的問題,在2013年11月27日,羅馬規約締約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對《國際刑事法院程序和證據規則》(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 進 行 修改,允許在國家層面承擔特殊公共職責的被告人,通過書面的形式向法庭申請缺席部分庭審。①參見《國際刑事法院程序和證據規則》,規則134 quarter。除此之外,規則134 ter 允許對無特殊公職身份的被告人,經書面申請進行缺席審判,但也必須是在極其有限的例外情況下,且允許缺席審判只得以個案審查的方式作出,不得成為一種新的常態。該修正規則在檢察官訴肯尼亞副總統威廉·魯托(William Ruto)案,以及檢察官訴肯尼亞總統烏胡魯·穆蓋伊·肯雅塔(Uhuru Muigai Kenyatta)案中被使用。②Alexander Schwarz, The legacy of the Kenyatta Case:Trials in absentia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ir compatibility with human Rights, African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vol.16, 2016, p.100.修改后的缺席審判規則仍然是最嚴格的,因為被告人僅僅能缺席部分庭審,且缺席必須有被告人書面聲明放棄在場權。之所以秉持最嚴格的出席要求,一方面是為了確保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得到最高保障,另一方面是出于被害人利益的考慮。被告人出席庭審聆聽被害人控訴,是治愈被害人所受創傷的重要手段。幫助被害人從創傷中恢復也是國際刑事審判的目的之一。綜上,國際刑事法院采取的最嚴格規則是基于多方、多利益考量的精心設計,但該規則遭遇了一些現實困境,有放寬適用的趨勢。
三、現實突破:黎巴嫩特設法庭的例外
紐倫堡審判之后,國際刑事審判已經幾乎沒有開展完全缺席的空間,但黎巴嫩特別混合法庭(以下簡稱“黎巴嫩法庭”)打破了這一局面,并因允許完全缺席審判成為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中的少數派。作為允許缺席審判的特殊典型,黎巴嫩法庭的缺席審判規則值得重點關注。
黎巴嫩法庭由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第7 章設立,旨在追訴2005年2月14日針對黎巴嫩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的恐怖襲擊。該爆炸襲擊造成包括哈里里在內的23人死亡,重創黎巴嫩社會、動搖區域穩定,被聯合國安理會界定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③2020年8月18日,黎巴嫩法庭裁決,黎巴嫩真主黨成員薩利姆·賈米爾·阿亞什(Salim Jamil Ayyash)在黎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案中有罪,同案其余三名被告無罪。
(一)黎庭缺席審判程序的具體類型
根據《黎巴嫩特別法庭規約》(Statute of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以下簡稱“《黎庭規約》”)第22 條第1 款規定,在以下幾種情況,法庭可以缺席審判被告人:(a)被告人明確表示或者書面放棄在場權;(b)沒有被有關主權國家遞交到法庭;(c)逃跑或者無法被發現,且已經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使其出現在法庭面前,以及通知其預審分庭所確認的指控犯罪。
對于上述第一類缺席審判,被指控人明確表示或者書面放棄在場權,隱含的前提是被指控人已經知悉對其的訴訟,從而才會有明確表示,或書面放棄在場權的可能。由于被告人放棄在場權的方式是明示的、書面的,這類缺席審判的爭議較小。第二類和第三類缺席審判爭議較大。假設行為人實施犯罪后潛逃敘利亞,但敘利亞拒絕與黎巴嫩法庭合作遞交被告人;又或者行為人實施犯罪后逃跑并藏匿,法庭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來通知其參加訴訟,仍然未果。這兩種情況下,黎巴嫩法庭可以分別基于規約第22 條第1 款(b)項和(c)項啟動缺席審判。如此一來,被告人就有可能在不知情、不自愿的情況下被缺席審判。不過,《黎庭規約》第22 條第2 款為啟動缺席審判設置了額外的限制條件,該款規定:“進行缺席審判,法庭必須確保:(a)被告人已獲知指控,或者指控已經通過其居住國或國籍國的媒體公之于眾;(b)被告人已經委托了自己選擇的律師;(c)被告人如果拒絕委托律師或者未能自行委托律師,法庭的辯護人辦公室應為其指定律師以充分代表其權利和利益。”然而,這些限制對被告人知情權和在場權的保護仍然是不夠充分的。
(二)黎庭缺席審判程序先決條件的正當性分析
黎巴嫩法庭缺席審判程序的危險性在于允許“雙重推定”,①當然,第22 條第1 款(c)項中的 “逃跑”并非簡單的找不到被告人,而是要求行為人秘密地或突然地離開某地以逃避抓捕、追訴或通知訴訟程序,不包括被告人公開居住在家的情形。參見Maggie Gardner, Reconsidering Trials in Absentia at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Tribunal’s Early Jurisprudence, The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43, 2011, p.92.也就是針對啟動缺席審判的兩項先決條件確保已知和放棄在場權,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歐洲人權法院在若干判例中形成了兩項關于啟動缺席審判的先決條件:第一,被告人必須明確知曉即將進行的訴訟,包括訴訟的時間、地點,以及不出席訴訟的后果;第二,被告人放棄在場權必須是以知曉訴訟為前提,基于自愿并以毫不模糊的方式作出。法庭都允許推定。只要法庭采取了所有合理的步驟來確保被告人到庭或者告知對他/她的起訴,比如在被告人的居住國或國籍國的媒體上公之于眾,就推定被告人能夠知曉即將進行的訴訟,是為“推定已知”。在推定被告人知悉訴訟程序之后,只要沒有主權國將其遞交到法庭,或者被告人逃跑并藏匿,就進一步推定其放棄了出庭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是為“推定放棄”。③Maggie Gardner, Reconsidering Trials in Absentia at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Tribunal’s Early Jurisprudence, The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43, 2011, p.115.
1.“推定已知”正當與否
有觀點認為,“推定已知”是國際人權規則所禁止的,通過推定被告人已經獲知訴訟并放棄出席庭審的權利,進而進行缺席審判不具有正當性。作為兼具國內和國際屬性的混合法庭,黎巴嫩法庭也必須遵守國際刑事審判中的最高人權準則。然而,無論是法庭規約抑或是具體實踐,黎巴嫩法庭的缺席審判程序都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歐洲人權法院所形成的規則相左,也與其他國際性刑事審判機構的做法南轅北轍。對缺席審判持寬容的態度,這在已完成以懲罰為基礎向以權利為基礎審判模式轉型的國際刑事審判史上,無疑走了回頭路。
盡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規定的“公平審判權”沒有明文禁止“推定已知”,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卻在判例中確認了“推定已知”違法。在1997年的馬萊基(Maleki)訴意大利案中,人權委員會指出通過為被告人指派辯護律師,就推定被告人可以通過該辯護律師獲知審判是不夠的,不足以證明被告人確實已知對其的審判。④Chris Jenks, Notice Otherwise Given: Will in Absentia Trials at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Violate Human Rights?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33, 2009, p.77.主權國負有證明被告人已知訴訟的義務,若僅僅是盡職通知被告人,不足以使缺席審判正當化。
另有觀點認為,“推定已知”具有正當性。根據《黎庭規約》第28 條第2 款,法官在制定程序和證據規則時,應受黎巴嫩國內刑事訴訟規則的指引。而《黎巴嫩刑事訴訟法典》(Lebanes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既允許對逃犯進行缺席審判,也允許公告送達。因此,《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第76bis 條規定,起訴書應當在報章上刊登或者通過廣播、電視、互聯網等渠道傳播出去,是對黎巴嫩國內法的尊重和采納。申言之,黎巴嫩國內法允許在無法完成直接送達時,通過其他方式完成送達,如公開出版、在被告人住所的入口處張貼十日、在被告人所在的城鎮或村莊的廣場展示、在法院的入口處張貼等。①《黎巴嫩新刑事訴訟法典》(2001年8月7日),第328 條。此外,黎巴嫩法律也允許通過將起訴書留置給家庭成員完成有效送達。②《黎巴嫩新刑事訴訟法典》(2001年8月7日),第147 條。
我們認為,《黎庭規約》本身雖然具有“推定已知”的風險,但法庭可以通過嚴格解釋《黎庭規約》第22 條來避免推定風險的現實化。比如,在T 訴意大利案中,歐洲人權法院認定被告已通過間接手段獲知刑事訴訟,所采納的證據是他寫給妻子的一封書信。但在該案中,由于當局沒有采取所有合理的、盡職的步驟來保障被告人通過正式的程序獲知訴訟,因此違反了最低人權保障,被判違法。此外,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沒有完全否定被告人可以通過家庭成員間接獲知訴訟的可能性。③Maggie Gardner, Reconsidering Trials in Absentia at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Tribunal’s Early Jurisprudence, The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43, 2011, pp.126-127.因此,間接送達輔以其他證據證明已知,也是國際人權準則所容許的范圍。
當然,允許其他旁證證明已知,還存在證明標準的問題。采用什么樣的證明標準也會影響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究竟是必須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被告人已經知道訴訟?抑或是只要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已知即可?還是如果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知道訴訟的可能性大于被告人完全沒有接到通知的可能?根據《黎庭規約》第28 條第2 款,法官在制定程序和證據規則時,除采納《黎巴嫩刑事訴訟法典》外,還應參考國際刑事審判程序中的最高人權準則,以保證公平快速的審判。因此,在符合刑事訴訟規則的前提下,盡量采取較高的證明標準,是符合《黎庭規約》和國際人權準則的優選。
從黎巴嫩法庭的實踐來看,黎巴嫩法庭采取了若干合理措施來通知被告人,包括:監視四名被告人,多次突擊檢查被告人的最后居所、工作地點,詢問被告人近親屬,詢問當地公職機關,在黎巴嫩的媒體上公告被告人生物信息、照片、所面臨的指控等。在窮盡了上述努力之后,法庭認為已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來通知被告人,可以進行缺席審判。④The Ayyash Case (STL 18-10) to Proceed in Absentia,https://www.stl-tsl.org/en/media/press-releases/the-ayyash-case-stl-18-10-to-proceed-in-absentia.可見,黎巴嫩法庭在實踐中允許了“推定已知”,并且沒有輔以其他證據來證明被告人對訴訟的知曉,其缺席審判正當性是存在瑕疵的。
2.“推定放棄”正當與否
“推定放棄”不為國際人權法所禁止,但必須是建立在被告人知曉訴訟,自愿放棄參加訴訟,并且以一種毫不模糊的方式加以表示的前提上。《黎庭規約》第22 條第1 款(b)項規定,若被告人沒有被有關的主權國家遞交到法庭,就可以開展缺席審判。然而,該規定可能違背放棄必須出自被告人自愿的要求。比如,被告人正在某國服刑,而該國不愿將被告人遞交到法庭。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的缺席并非出自本意,不得推定為放棄在場權。又如,被告人在某國身患嚴重疾病,該國不配合將被告人遞交到法庭。若通過推定認為被告人放棄了在場權進而缺席審判,同樣有違自愿放棄的原則。因此,法庭在根據規約第22 條第1 款(b)項開展缺席審判時,應同時確定被告人并非因為不得以、非自愿的原因不出席庭審,否則此種條件下的“推定放棄”應歸于無效。
有質疑認為,《黎庭規約》第22 條第1 款規定,出現(a)(b)(c)三項的任一種情況,法庭“應當”(shall)進行缺席審判。“應當”進行缺席審判意味著,若出現(b)項的情況,法庭必須進行缺席審判無須進行“自愿”調查,這有違國際人權規則。顯然,“應當”較“可以”(may/could)更具有強制性,表明出現這種情況時,法庭應當更多地考慮進行缺席審判而不是中止程序。不過,是否繼續進行審判,以及用什么樣的方式進行審判是一個法庭的固有權力(inherent power)。盡管《黎庭規約》規定“應當”進行缺席審判,法庭仍然有權力進行合目的解釋而停止程序或用其他方式保證被告人的訴訟權利。①Maggie Gardner, Reconsidering Trials in Absentia at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Tribunal’s Early Jurisprudence, The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43, 2011, p.121.根據《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106 條(B),相關國家拒絕移交被告人,或未能成功移交被告人時,法庭應當咨詢法院院長,確保已盡可能采取合適的方法幫助被告人參與訴訟。比如,通過遠程視頻連線的方式,盡量為被告人參與訴訟程序創造條件,提高被告人參與庭審的質量,避免出現非自愿的“推定放棄”。
需 要 強 調 的 是,2009年10月30日 以 及2013年2月20日黎巴嫩法庭修改了《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104 條,新條文規定:通過遠程視頻參與庭審,親自委托辯護律師或者接受法庭指派的律師參與庭審的,不再視為缺席審判。換言之,這種審判程序不再被視為缺席審判,而是對席審判;相對應地,也不再賦予被告人缺席審判時才享有的救濟權利。②Ralph Riachy, Trials in Absentia in the Lebanese judicial System and at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Challenge or Evol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8, 2010,p.1301.
(三)黎庭缺席審判程序救濟措施的正當性分析
開展缺席審判除必須滿足一定的先決條件外,還必須賦予被告人最低限度的權利救濟,才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權利救濟是缺席被告人的辯護權和申請重審的權利。作為法庭開展缺席審判的前提之一,為被告人指定辯護律師的要求規定在《黎庭規約》第22 條第2 款(c)項,在實踐中較易實現,爭議也不大。被告人申請重審的權利規定在《黎庭規約》第22 條第3 款:“在缺席被判有罪的情況下,如果被告人未能委托自己選擇的律師,則其有權在法庭面前獲得重新審判,除非其自愿接受此判決。”黎巴嫩法庭對被告人申請重審權利規定得非常全面,表現在:第一,被告人若在案件審結之前到案,審判分庭應直接停止正在進行的訴訟程序,開始一個全新的審判。③《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108 條(A)。第二,被告人若在有罪判決作出后到案,也享有多種選擇方案以保障自身權益,具體包括:(1)接受定罪和量刑;(2)申請重審;(3)書面接受定罪,申請重新量刑;(4)放棄申請重審,直接選擇上訴。④《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109 條(C)。第三,被告人在上訴分庭已就檢察官的上訴作出決定后到案的,被告人仍可以申請重審。⑤《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109 條(E)。
所以,從規定本身來看,被告人享有充分的申請重審權利,且不附加任何條件。然而,黎巴嫩法庭是否能夠切實保障被告人申請重審的權利卻面臨一個實際操作的問題。作為一個臨時法庭,黎巴嫩法庭在完成使命后將告關閉。若被告人在黎巴嫩法庭如期關閉后才歸案,其申請重審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國際刑法學者威廉·A.夏巴斯(William A.Schabas)認為,黎巴嫩法庭只有一直工作,才能保障被告人申請重審的權利。⑥William A.Schabas, In Absentia Proceedings Befor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in G?ran Sluiter & Sergey Vasiliev(e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Towards a Coherent Body of Law, London: Cameron May, 2009, p.379.另有意見認為,被告人申請重審的權利并不會隨著黎巴嫩法庭的關閉而落空,他/她可以通過向黎巴嫩國內法庭申請重審來保障自身的權益。①Paola Gaeta, To Be (Present) or Not to Be (Present): Trials in Absentia Before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5, 2007, p.1173.但國內法庭能否保障申請重審人的公平審判權利,又或者會否出現被告人借國內重審逃避責任的情況,均充滿未知。更何況,黎巴嫩法庭在被告人到案前就先告關閉的現實可能性是存在的。黎巴嫩法庭在設計之初就計劃自開始工作之日起三年內結束使命。②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Lebanese Republic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art.21, S.C.Res.1757, Annex, U.N.Doc.S/RES/1757 (May 30,2007).黎巴嫩法庭的經費負擔一直堪憂。截至黎巴嫩法庭正式開始工作前的一個月,即2009年2月,法庭共籌措了兩年的運營經費。因此,黎巴嫩法庭籌措經費的能力決定了法庭工作的期限,從而實質性地影響缺席被告人的申請重審權。③The Secretary-General, Fourth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ubmitt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757(2007), delivered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U.N.Doc.S/2009/106(Feb.24, 2009).
(四)否定黎庭缺席審判的其他理由
1.缺席審判不利于發現事實真相
有觀點認為黎巴嫩法庭的缺席審判實踐除了不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也不一定能夠實現實體正義。其中很重要的理由在于,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辯護律師無法制定一個恰當的辯護策略,從而減損法庭發現事實真相的訴訟功能。正如前南刑庭上訴分庭指出的,國際刑事審判機構所面對的都是極其復雜的疑難案件。庭審涉及的間接證據眾多,若辯護律師不與被告人進行良好的溝通,不清楚案件的來龍去脈,很難完成強有力的交叉質證。更為困難的是,為了保護證人人身安全、國家安全,保障偵查順利進行,法庭證據規則允許接受匿名的證人證言、事先的證人證言(即未經過交叉質證的證人證言),以及替代證據原件的相近證據或經編輯的證據。離開了被告人本人的充分參與,指定律師很難獨立完成對這些證據的有效質證。對于這些案件,若被告人不出席,法庭要證明其有罪或無罪都是極其困難的。
2.缺席審判也不一定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尚無證據表明缺席審判有利于改善國際刑事審判效率低下的情況。被缺席定罪的被告人一旦到案,很可能申請重新審理,這無疑會增加法庭的工作量。而根據其他國際刑事審判機構的經驗,重新審理一個案件會使本就極其有限的法庭資源更加捉襟見肘。時間成本也會是難以估量的,重新審判耗時通常以年計算。若案件所涉及的證據全部重新質證,所消耗的訴訟成本更會呈指數級增加。
四、國際刑事缺席審判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2018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法基本明確了缺席審判的適用范圍和啟動條件,但在具體適用上仍有諸多問題亟待厘清。通過上文梳理國際刑事缺席審判實踐的流變和趨向,我國可以在以下幾方面批判性地借鑒國際刑事司法中的缺席審判制度。
(一)借鑒國際刑事審判中“司法利益需求”的判斷進行案件挑選,嚴格限制缺席審判的適用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91 條,“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時進行審判,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移送起訴,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人民法院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符合缺席審判程序適用條件的,應當決定開庭審判。”那么,是否所有屬于貪污賄賂犯罪的案件,以及需要及時進行審判,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被告人潛逃境外,證據確實、充分的,檢察機關都必須提起公訴?從條文本身的文義來看,檢察機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意味著檢察機關有起訴或不起訴的裁量自由。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505 條幾乎全文照搬了《刑事訴訟法》第291條的條文,也沒有進一步明確檢察機關如何挑選缺席審判案件。
因此,這里可以借鑒國際刑事審判中“司法利益需求”的判斷進行案件挑選,嚴格限制缺席審判的適用。第一,司法利益需求的判斷既從正向考慮進行缺席審判的正向價值,也從反向考慮不進行缺席審判、有罪不罰的負面影響。比如罪行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惡劣,有罪不罰會對社會穩定和正義造成嚴重傷害,人民群眾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的,可以考慮納入啟動缺席審判的備選案件。第二,司法利益需求的判斷既考慮被告人的權利保障,也充分考慮被害人的訴訟權利。①Gilbert Bitti,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https://www.ejiltalk.org/the-interests-of-justicewhere-does-that-come-from-part-i/.See als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Policy Paper o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https://www.icc-cpi.int/NR/rdonlyres/772C95C9-F54D-4321-BF09-73422BB23528/143640/ICCOTPInterestsOfJustice.pdf.See also Human Rights Watch Policy Paper, The Meaning of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in Article 53 of the Rome Statute, https://www.hrw.org/news/2005/06/01/meaning-interests-justice-article-53-rome-statute.因貪污賄賂直接引發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事故、災難的,比貪污賄賂未引發進一步社會危害的,更具有缺席審判的必要。單憑數額認定缺席審判案件的優先順位不應提倡。第三,進行司法利益需求的判斷時,法庭應當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尤其是證據情況。比如在紐倫堡法庭審判的鮑曼案中,法庭正是基于案件證據已達到無以辯駁的程度給出有罪判決。在啟動缺席審判程序時,法庭也需要從嚴把握證據的證明程度,以更充分地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
此外,對于檢察院已提起公訴的被告人缺席案件,法院是否必須進行缺席審判?值得注意的是,《刑事訴訟法》第291 條后半段規定的是符合缺席審判程序適用條件的,法院“應當”決定開庭審判。此處的“應當”與第291 條前半段的“可以”相對應,與《黎庭規約》第22 條第1 款的“shall”異曲同工。“應當”是否意味著法院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五編第三章缺席審判程序條件的案件都必須進行缺席審判?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正如上文對《黎庭規約》的分析,決定是否進行審判、是否繼續審判、以什么方式進行審判均為一個法院固有的權力。《刑事訴訟法》第292 條規定的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規則并不能完全確保被告人已知即將對其展開的訴訟,因此如果法院結合案情審查認為送達盡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92 條,但并不能確保被告人的知情權和在場權時,可以決定不開庭審判。
(二)借鑒國際刑事審判中“公平審判”底線要求,完善我國缺席審判程序的送達規則
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前提下,合理適用缺席審判程序以實現正義,已經成為當前國際刑事司法的共識與趨勢。②“被控有違反國際法罪行的人有權在事實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審判”是紐倫堡憲章和紐倫堡審判中確認的一項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于1946年由聯合國大會第95(2)號決議通過成為公認的國際刑法原則。《前南刑庭規約》第21 條、《盧旺達刑庭規約》第20 條以及《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67 條也都規定了被告人享有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參見安東尼奧·卡塞塞:《紐倫堡法庭憲章》所確認的國際法原則,https://legal.un.org/avl/pdf/ha/ga_95-I/ga_95-I_c.pdf.而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確保被告人已知即將對其進行的訴訟。為此,我國可以采取介于國際刑事法院和黎巴嫩法庭之間的折衷方法。若采納國際刑事法院模式,完全禁止對從未到案的被告人進行缺席審判,則我國的缺席審判無法開展。因為潛逃境外的被告人,幾乎都是從未在法庭面前出現過的被告人。若采納黎巴嫩法庭模式,允許通過高覆蓋的公告推定被告已知,則可能有違國際人權準則。折衷的辦法是,允許間接送達,同時要求有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人已知訴訟,是既符合我國的缺席審判實際需要,又遵守刑事審判國際人權準則的解決辦法。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92 條,“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或者外交途徑提出的司法協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許的其他方式,將傳票和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后,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并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作出處理。”若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許郵寄送達、公告送達,人民法院就可以通過上述間接送達的方式完成對被告人的通知,進而進行缺席審判。但為切實保障被告人公平審判的權利,人民法院在實踐中應自我約束,禁止推定已知。在直接送達確有困難時,允許采取間接送達,但必須還要輔以其他證據證實被告人已知訴訟,以符合公平審判的底線要求。
(三)借鑒國際刑事審判對訴訟經濟的考量,避免被告人濫用“申請重審權”
為救濟缺席審判中被克減的被告人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95 條賦予了缺席被告人申請重新審理的權利。但若被告人濫用重審權,則會造成訴訟資源的重復浪費,對案發后主動面對司法的被告人不公。對此,我國可以借鑒黎巴嫩法庭的審判規則,有效避免被告人濫用重審權。
第一,規定“不允許重審的例外情形”。《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104 條規定,通過視頻方式參與庭審的,委托律師參與庭審的,或者接受法庭指派的律師的,不再視為缺席審判,不享有申請重審的權利。在這些情形下,被告人只是沒有親自到庭,但通過技術手段和辯護律師能夠實質參與庭審,為自己辯護,其公平審判權利已得到充分保障,到案后不應再享有申請重審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93 條和第295 條沒有規定類似的例外情況,不利于訴訟經濟。
第二,建立“重審權利一次用盡”規則。根據《黎巴嫩法庭程序和證據規則》第108 條(D),被告人若在缺席審判的過程中到案,法庭應當停止審理,開啟一個全新的審判。若在重新開啟的審判中,被告人又逃逸的,法庭應當繼續審判。也就是說,缺席被告人申請重審的權利只可以行使一次。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95 條規定:“在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自動投案或者被抓獲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理。”建議補充規定:“重新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又逃逸的,再次歸案后,不得再申請重審。”
第三,建立“缺席庭審部分承認”規則。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缺席被告人在到案后有申請重審的權利,但重新審理無疑會造成訴訟資源的重復浪費。因此,可以借鑒黎巴嫩法庭關于“部分承認缺席判決”的做法,來構建我國缺席判決重新審理的規則。具體而言,基于被告人的同意,缺席判決中的部分內容可以直接在新的訴訟中使用。這樣既可以保障被告人獲得公平快速的審判,又可以節約訴訟資源,是平衡程序正義和訴訟經濟的做法。兩高在后續制定有關“缺席審判程序”的司法解釋時,可以吸納借鑒“缺席庭審部分承認”的規則,以完善我國的缺席審判程序。